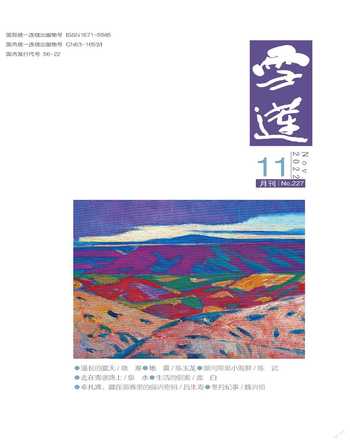乡土诗意与现代性的忧伤
2022-05-30李生滨魏海燕
李生滨 魏海燕
多年来,青海女作家雪归以“世俗生活”作为审美对象的小说叙事,颇有现实观照的内在张力。其作品先后发表于《北京文学》《芳草》《飞天》《清明》《朔方》《小说林》《青海湖》等文学刊物,已出版《在我之上》等五部作品集。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这世界》是雪归的第四部小说集,入选《河湟文丛》,其中收录了《时间给的药》《赵有田的一亩三分地》《意难平》等十篇小说。
情浓深处是吾乡,故乡是文学创作永远绕不开、说不尽的母题。一个人的故乡记忆是一种情感的内在沉淀,对于作家来说少年情怀和故乡记忆是至为深厚的审美资源。古代诗人用他們的行吟层层刷新了中华大地上的人文山水,当代作家的个性绘写了各自的故乡镜像和情感地图。河湟谷地是雪归情感依托的精神原乡,青藏高原是她故事展开的现实空间。对河湟乡土伦理的深切体验,牵动内里的每一次波动,她用文字记录父老乡亲的凡俗人生。雪归日常化的叙事笔调非常平实,将了然于胸的具有高原风情的真实生活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小说《我叫吴仁耀》中:“那只掉毛的老黄狗此时不再嚣张,乖乖地躲在狗窝里,把嘴巴搭在自己的前爪上,一阵阵惊雷后,偶尔对着上方叫一两声。只有老母鸡对一切充耳不闻,它的眼里,刨食才是最重要的任务,偶尔随着惊雷与狗叫拍打着翅膀小跑几步,然后又继续刨食的大事。”聒噪的老黄狗,信步的老母鸡,通过作者富有情调的笔呈现出来,读来倍感亲切。乡土的诗意与真实,生活的欢欣和感伤,构成雪归小说叙事的两翼。《时间给的药》中对拉姆下窖拾洋芋的描写,对窖里的黑暗,对拉姆在窖里的恐惧以及挑选洋芋等场景朴素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的真切体验。《赵有田的一亩三分地》在书写知识分子回乡的焦虑时,也不忘对乡土诗意生活的描写。中国人几千年来依存土地建立起来的家园意识和落叶归根的游子意识,使他们的故乡有如母亲般的大地情怀,与土地之间存在情感文化和多重交融的精神寄托。雪归以乡村日常生活为切入点,贴近每一个人物的心理,对处于社会变革中的乡村生活有着细致入微的描绘,其中不乏对故乡的情有独钟,更有在现代化浪潮中失去故乡的惶惑与无奈。单一的怀旧难以支撑起故乡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伤筋动骨的内在阵痛,而怀旧从一定的层面上来说是对现实的不满或是焦虑。雪归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郁的忧患意识去审视时代巨变中农村人生存的窘困,以及精神的贫瘠。在貌似田园诗意却深蕴忧虑惶恐的矛盾中,雪归肩负起作为作家的时代责任,去透视曾经封闭、落后的农村环境下形成的农民的偏狭心理,以此表达自己对家园的忧伤守望。
小说《我叫吴仁耀》是雪归矛盾心理的双重显现。小说真实描绘了乡村土地上农民的生活窘态,但也直击西部自然条件和小农意识滋生的保守懒惰。虽然我国的农民已经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改革或是革命,但是在既定的生活水平上自足自乐的心理几千年来并没有彻底改变。雪归深谙农民这种安逸心理,所以吴仁耀们安分守己的自负还带有强烈的排他意识。小说中当木子宁以一个“传道者”又或是“启蒙者”的身份闯进高原乡村时,自然遭受到来自村民们的敌视。因为这个偶然的来客不仅打破了吴仁耀们生活的宁静,更是给他们的内心可怜的自尊带来了难以言说的伤害。同一座山上,一个现代城市的来客,穿着光鲜亮丽,喝着刚冲好的咖啡,吃着烤肠、罐头、鸭脖、鸡爪,这和一个扎根土地、辛勤劳作后吃着咸菜萝卜、饼子馒头,吴仁耀们内心的沮丧难以言说,只觉得“今天的白饼竟如此难以下咽”。这一刻不仅吴仁耀的内心是沮丧难过的,作者的内心更是疼痛的。她以细致的描写剖析了作为农民的吴仁耀们自卑、自负、自怜的复杂心理。作者通过聚焦农民日常言行的透视描写,不仅体会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更是在乡土诗意与乡土悲悼的反思中理性揭示了当下部分农民精神与情感的双重困境。
小说《赵有田的一亩三分地》中,赵有田同作者一样是一位长于农村、落脚于城市的知识分子,临近退休之际,他想通过“种地”这一行动找寻自己的情感家园。雪归通过一个“返乡者”找寻家园,最终失去家园的悲剧,消解了日常生活的神圣性。在自身乡土经验与情感的交汇中,她塑造了赵有田这一“中间物”,展示了“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对西部乡村冲击所造成的裂变”(孙玉玲:《社会转型期西部乡土小说创作研究》)。赵有田的妻子菊香可看作这种时代流变的象征符号,在城市生活了几年之后,她变成了一个四不像:“既回不到农村,也不适合城里。”菊香是乡下人进城的典型代表,在脱离土地的那一刻,他们便失去了根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浮萍,而与土地脱离意味着曾有的宁静、和谐的心灵状态的消失,随之而来的日益躁动便是市俗化生活催生的欲望膨胀。这不仅是知识分子返乡之旅的书写,也是作者深挚乡愁的一曲挽歌。
雪归的小说叙事始终聚焦时代开放的当下语境,秉持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坚守文学初心,揭示困境当中的人们的窘迫处境。《这世界》中的《意难平》 《吊吊灰》 《就这么简单》,就是对这些城乡夹缝中生存的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意难平》采用双线交替进行的叙述方式,当胡小尼穿梭于城市为生活累死累活之时,染了一身紫毛的多多正在享受着无上的待遇。小说采用顺序、插叙、倒叙等多种叙事手法交叉进行的方式,把胡小尼们在城市求生存的辛酸与无奈呈现到读者眼前。历史和现实赋予作家的责任与使命,透过生活的万象检视社会存在的不合理问题。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雪归不仅从人的生存与人性的发展中揭示城市异乡者的尴尬境地,更是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病象展开解剖和反思。雪归承接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写出了普通人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打拼的艰难与悲苦。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就像西西弗斯与他朝夕相伴的巨石的悲剧性关系一样,生命力在无意义又无生机的工作中耗尽。雪归深知打工的艰辛,在作品《暗蚀》的后记中她曾悲伤地自省:“十几年打工生涯和严酷现实面前的碰壁之痛,在我的性格内注入了太多自卑怯懦的因子。在挣扎着生存的时候,面对现实的强大与个人的微弱,我只能凭借时间的流逝来消解被打压的疼痛。”生活的诸多经历给了雪归创作的素材,现实主义情怀以及人道主义的悲悯更让她理解了更多外卖员、临时工、农民工的悲辛和苦乐。雪归从生活的悲悯出发,关注每一位小人物背后的故事,在书写他们的苦难的同时探究造成悲剧的社会原因。
雪归的小说不仅仅是向下的探寻,更有高远的精神张扬。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避不开的永久话题,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更与人类的共同命运息息相关。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蕴藏了许多的珍贵资源,以前由于条件的限制人类无法踏上这块原始而又神秘的地方,但现在人类的侵入使生态变得脆弱不堪。小说《我们在一起》是作者从文学的生态纬度出发,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作品以一只藏羚羊为故事的叙述者,讲述了它在青藏高原生活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美好愿望。《我叫吴仁耀》中面朝黄土的吴仁耀们为改善生活上山挖虫草,草山植被保护与现代经济发展需求是冲突的。作家将乡村与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物质的追求与社会的转型联结起来,在不动声色中呈现了时代大变动中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
苦难不仅仅是生活表层的贫困,还有内在的性别承担。雪归的小说切入生活的苦难与忧伤的感伤中,却也时时不忘生命中的光亮。尤其在她笔下出现的一些女性人物身上,多了隐忍、坚强和乐观。对于具有城乡两种生存体验的雪归来说,这样辗转的经验使她对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压力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以至于当她将写作目光投向女性时,便发现了女性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小说《时间给的药》《小东西》《青蘋之末》《吹弹便破》中作者细腻地刻画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她们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虽未照亮深沉的暗夜,但也在艰难的生活中给人以温暖和美好。
《小东西》讲述了生活在城市的现代女性陈瑛梅的婚姻与生存的窘困境地。陈瑛梅与丈夫陆天侨结婚十年了,生活的热情早已被消磨殆尽,她既得不到丈夫的安慰,又无从发泄,自己的无助与忧伤急需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所以当那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出现时,她彻底沦陷了。小说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运用插叙、倒叙等叙述手法,将陈瑛梅面对一系列事件的心理活动细腻地表现出来。《青蘋之末》中张礼宁同样面临着婚姻问题,丈夫长期的酗酒、家暴使张礼宁毅然决然地选择结束自己七年的婚姻,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敢轻易走进婚姻的围城。这两篇小说以两个城市女性的婚姻问题为着眼点展开叙述,呈现出她们在前进的道路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同时又在人生的风浪中用坚强的壳包裹自己,以展示自己对生活的不屈。雪归以女性的视角展示了女性在婚姻中所受到的伤害,但同时又赋予她们面对生活困境时的韧性,使她们在生活中不知疲倦地奔跑。陈瑛梅奔跑的姿态代表了女性在生活中的一种姿态,义无反顾地向前奔跑的坚韧和乐观。
雪归的这部小说集中不仅有城市女性的忧伤叙事,还有生活在农村而顽强生活的善良女性。《时间给的药》塑造了一位温柔而质朴的女子——拉姆。通过第三者唐冉的视角塑造了这个生活在半农半牧村寨的藏族女子,展示了她纯真美好的品质。小说在结构上独具匠心,按照以往的故事发展,拉姆会在最后一刻等来唐冉,但作者打破了以往的故事模式,而后又安排了拉姆丈夫的出场,通过“照片”这一意象结构故事,给了小说一个急转弯,使结尾在不完美中有了完满。小说还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从唐冉对妻子于嘉怡的描述中,于嘉怡的飞扬跋扈与善良温柔的拉姆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的对比,呈现出了拉姆生命的亮色,即使生活得很艰辛,但她仍旧努力地生活,保持着善良纯真的生命本色。小说《吹弹便破》中,女性作为母亲的伟大在这个生活多舛的女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她最终没有自杀自己上岸,跌跌撞撞地回到家时,两个娃,一个满身屎尿,一个饿得在啃生洋芋:“我就着他的手啃了一口,生洋芋,真是涩啊!”贫穷生活的滋味就是涩,是苦涩。雪归就是通过这样的描写将一群女性生活艰辛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眼前,写出了她们性别的两难和生死的困境。但是不管她们的生活遭遇了怎样的打击,生的顽强和爱的直面,让平凡的女性在生活深陷灰暗的窘困中显现出力量。
文学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文学中的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描摹或是复制粘贴,它需要治愈每一个受伤的生命心灵的创伤。这或许就是雪归在作品中始终坚守悲悯力量和乐观精神的原因。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谈到自己作品中的女性时,雪归说:“在我小说中这些女性人设,大都来自底层,她们卑微,渺小,弱力。我尽我所能地展现她们身上的坚韧、顽强、克制、隐忍。因为经历过漫长的严冬,她们对光明与温暖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和更為敏感的反应,她们对高贵、对尊严的渴望,远远大于绝望。”张礼宁作为一个离婚的大龄妇女仍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那些残疾的孩子,而拉姆为了五十块钱不畏严寒,坚守在风雪天等待那个陌生人。这些女性自己的生活已然这般不尽如人意,但时光并没有淹没她们灵魂深处的良善,用自己的生命原色为高原增添了不一样的亮色,用自己的坚韧和乐观诠释着过往和当下。
简而言之,雪归的小说大多烛照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平凡人物和故乡生活,审视时代力量作用下个体生存者的现代性忧伤,特别是生活真实的各种困境,其中蕴藉作家个人的悲悯与同情。然而,我们更能感受到的是作家写作的笔尖所带着的浓烈的乡愁,它不是单纯的思乡或是怀旧,而是一种在时代巨变中无法回避现代性冲击的反省与自悼,甚或是无法直面的尴尬。“这世界”总括一种情绪,不言而喻的喟叹里是对当下西部之上的青藏高原遭遇现代化冲击的真实观照,亦显现了作者直面生活温热的悲情感伤和责任担当。
【作者简介】李生滨,字若水,青海平安人。陕师大硕士,复旦大学博士,河南大学博士后。已出版学术专著8部,发表评论90多篇,获我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六届、十七届我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在个性化的文艺研究中,认同王国维的“境界说”,崇尚审美批评的“性情说”。
魏海燕,女,甘肃定西人。西北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我国现当代文学和西部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