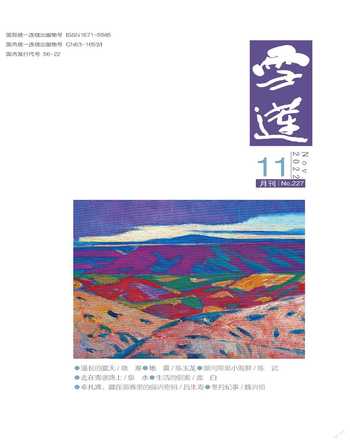地 震
2022-05-30陈玉龙
那年夏天,因了地震的传言使得黄泥村变得更加闷热。大家都不敢进屋,从田畈里干活回来后便挤在了村头的那棵大枫树底下。幸好这枫树枝繁叶茂,一把大伞样遮蔽了一块大的场地。可那么多男男女女挤在一起,汗味儿渗杂着别的味儿弥漫开来,年轻女人只好捂着鼻子,经自挤出去,站在边上,一个劲地用草帽扇着风,红扑扑的脸色才慢慢褪去。一会儿抬起头看了天上炙热的日头一眼,赶紧转回身子,挤到树荫底下,一屁股坐下来。想想又抬起屁股,把草帽垫上,才轻轻坐上去。男人们不大讲究,大多光着上半身,穿着宽大的裤衩,无拘无束。年纪大点的女人也学着男人样,敞开着胸怀,把两片褂子当扇子使,胸前的奶子跟着晃动,人们习以为常。
但有人就不能这样有空闲在这儿坐着,比如祥云婶,她要回屋做饭,一家人饿着肚子盼着她的吆喝。屋在村里的后边,祥云婶的儿子小明多次对她讲过逃跑的路线,祥云婶总是不屑地拍一下小明的大脑壳说,哪有地震呢,这天晴朗朗的热乎乎的,好着呢。小明说学校都演练了防震。祥云嫂说听老人们说地震是鳌鱼作怪,它一眨眼,地就抖,它一翻身,大地就翻转过来。小明就不知说什么好了,他把祥云嫂的话告诉我时,我正缠着三嘎嘎讲评话。三嘎嘎不去村头的大枫树底下,他说那儿是个浑水塘,他不掺和。正好小明过来了,三嘎嘎听到这话,摸着下巴那绺长须说,鳌鱼百年一眨眼,千年一翻身。两千多年前我们这儿就发生过一次,整个县城都沉到了鄱阳湖底。这个故事我听三嘎嘎讲过多次,我们县编的民间传说故事有多种版本,据说很早的县志上都有沉枭阳,浮都昌的记载。那时我还小,要等暑假过后才上初中,传说的故事基本来源于三嘎嘎的讲评话。
小明拉着我去找他妈。小明家的屋是老屋,中间有个小天井,两边的厢房有五六间,先前小明的父亲兄弟四家都挤在这几个房间里,那可是非常热闹的。但现在却空旷旷的,一进去,阴冷潮湿的风不知从哪儿钻出来,让我连打了几个喷嚏。突然,一只灰溜溜的老鼠横着冲出来,差点跑上了我的脚背,吱吱乱叫两声,给我打招呼的样子。我不由大吃一惊。小明两脚一蹬,大喊,不好,要发地震了,老师说屋里老鼠乱窜塘里鱼儿乱跳是发地震的先兆呢。小明急急往后面厨房里去,边跑边喊,姆妈,姆妈!快跑出来,要发地震啦!我见祥云婶手上还拿着炒菜的巴铲跑了出来,另一只手拉着小明。可一出屋门,祥云婶便停住了,抬起头望着天,然后一巴铲打在小明的大脑壳上,说乱喊叫什么,这么好的日头天上一丝云都没有,朗朗乾坤下哪来的地震,害得老娘锅里的菜都烧糊了。说着转身进屋。小明摸着发红的脑壳,一副想哭哭不出来的样子,看得我直想笑。
事后回想起祥云婶的话,我就很奇怪她嘴里也能吐出像朗朗乾坤这样的书面语言来,她并没读什么书,可能她也是听多了三嘎嘎讲评话的缘故吧。每到冬闲的季节,男男女女都喜欢挤在三嘎嘎屋里的火塘旁听他讲评话,有时吃饭都舍不得走。
要发地震的消息是谁先传进来的呢?我想应该是水仔的父亲大胡子。大胡子是生产队长,那个消息就是他去大队参加了一次会议后宣布的,这样说来应该是官方消息,不是什么谣言。当然,大胡子起先也只是叫大家都预防着,有个准备,不要慌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目前世界上谁也预测不准发生的地方,只是大概数。但村民却认为上面都作了宣传,地震是肯定会发生的,因此他们都紧张起来,很少进屋安歇,白天挤到大枫树底下,晚上则各自搬着竹床在塘坝上睡觉。刚才说了,三嘎嘎不愿出来,晚上也不到塘坝上睡,说一个人在屋里,清静。我很奇怪,三嘎嘎喜欢讲评话,应该喜欢热闹的地方,再说他就不怕发地震么,虽然他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可身板硬朗,没病没灾的,对生命还是有渴望吧。我把这些疑问提出来,三嘎嘎却收起了刚刚还是笑呵呵的脸色,指了指厅堂中方桌上摆放的一个瓷像,说她要我陪着哩。我莽撞地说了句,三嫲嫲不是早死了么。三嘎嘎一个烟管向我脑壳砍过来,我往边上一闪身,三嘎嘎身子踉跄了几步,站稳后喘着气儿说,歪崽俚不要乱说,你三嫲嫲可活着哩,你看,她在向着我笑哩。我感到身上毛骨悚然,急急地逃出三嘎嘎的屋。
晚上的热闹不是深入其境是无法想象出来的。一长溜的塘坝上,日头一落山便擺着大小不一的竹床或者长凳,这使我又想到那时的露天电影。大家选址在塘坝上,一是有着传统的乘凉方式,通南北二风,无遮拦,风儿从水面上吹来,多了一份凉气。二是这里开阔,更没有高大的建筑物,虽说塘里面有水,现在是用水季节,只小半塘,加上塘坝厚实,不会有什么危险,一旦地震来了,容易四散而逃或者蹲在原地不逃都不会碍事。父母早就叮嘱竹床不要搬太晏了占不到好位置,一个人自是难以搬动,便和小明还有水仔搭帮着,因而我们三家基本上在一起,晚上我们不像大人们那样规规矩矩地躺在竹床上扯着闲话,他们白天劳累了一天,躺下来扯着扯着话就响起了鼾声。我们四处奔跑着,有月的晚上亮如白昼,无月的天空有星星,还有四处飘忽的萤火虫。我们玩得最多还是一种叫“站住”的游戏,类似于捉迷藏,所不同的是我们手里都拿着一支自制的木枪,发现了对方,喊一声“站住!”如若不站住,对方就要开枪,啪地一声,应声倒地。玩腻了,便蹑手蹑脚来到那一长溜的竹床边,捏一下谁的鼻子,或是抓一下哪个的脚板,一溜烟溜回自家的凉床上。凉床真的很凉,一层露水洒在上面,倒正好洗净了我的汗身子,对面的水仔还想跟我说话,吵醒了大胡子,一扇子拍过去,水仔噤了声。这样的夜晚似乎平淡无奇,一点也不热闹,更没有故事。可是,可是……有许多热闹我没法描述出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只有身临其境才可感受到。比如大人们一开始谈论着田地的收成,家里又生下了几个猪仔,还有小明父亲每晚拿着计工本子记工,大胡子队长每晚安排明天的做工等等。这些,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也不愿细细地描述出来。我现在要写的是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说一些奇怪的事情,当然,我没有三嘎嘎讲评话的本事,有些事又不是我亲见,难免会有些混乱。
故事之一:祥云婶与黑影
据说祥云婶嫁过来时发生了一件怪事,闹新房的人们晚上听墙壁,竟然没有听到半点声响。祥云婶的男人在家里是老大,那个时候他的母亲还在世,一大家人住在那个有天井的老屋中。老大和祥云婶结婚是住在东厢正房,与厅堂相隔的都是木板门窗,说听墙壁其实也就是站在只隔着一层木板外听里面的动静。夜深人静,哪怕一声喘气都可听出来。结婚听墙壁也是我们这儿的习俗,偷听的人基本上都是未结婚的男人,第二天他们就会把夜里偷听的战果对全村人宣布,一时就成了村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可那天晚上他们硬是没听到半点内容,这确是一桩怪事。这事虽让村人们没了饭后的谈资,但背后叨叨絮絮的议论却不少,两三年过去了,祥云婶的肚子还是平平的,议论似乎更多了。直到第五个年头,小明的姐姐出生,过了三年小明才降生在小村,村里的议论才宣告结束。啰啰嗦嗦讲了这么多祥云婶的过去,当然是与后来发生的故事有关。老二老四都早成了家,生儿育女分开单过,只有老三没成家,仍然跟着老大一家生活。自从有地震的消息以来,大家都搬到塘坝上去住,祥云婶有时在家里住宿,理由还是那句老话,朗朗乾坤哪来的地震呢。老大说了几句,祥云婶只哼哼了两声,老大只好由着她。那天晚上,小明和我们玩得很晚,满天星星的夜空中忽响起一声闷雷,感觉地都震动了。不好,地震了!有人这样一喊,塘坝上睡觉的人们从梦中跳起来,一时间人们惊恐的叫声和竹床的吱呀声混在一起。小明这时拉过我的手说,快,跟我同去屋里喊我姆妈。我感觉到小明的身子在颤抖,他害怕。我们跌跌撞撞跑进村跑到小明的屋前,一推门,打不开,屋门上了栓。黑暗之中小明拍着大门高喊,姆妈,姆妈,快出来,发地震了!
门拍得响,在深夜里格外惊人,加上我们的喊叫,祥云婶显然听到了我们的呼喊。没等我们再次拍打大门,门却砰地一声打开了,祥云婶披散着长发跑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大黑影,他们似乎没有顾上我们,转眼没了影儿。我和小明在后边紧跑着,我说小明你爸今晚也在屋里睡么。小明说我爸怎会睡在屋里呢他在塘坝上。我说刚才不是有两个人儿出来了么,小明没有做声,黑暗之中我们的喘气像牛一样粗。塘坝上像捅了个大马蜂窝,星光的映照下可见不住晃动的影子以及大人小孩的嘈杂声。有的人离开了自己的床位,有的人跑到大枫树底下,也有跑到塘坝尽头的空地上。当然,大多数还是站在塘坝上,四处张望着。天空中的星星稀少起来,四周像洒下一层迷雾,天尽头处突然一道闪电掠过,一瞬间照亮了大家怪异的脸。说心里话,我心里的紧张和兴奋连在一起,我和小明还有水仔三人在人群中钻进钻出,水仔说地震怎个还不发起来呢。小明说那不是在闪电么,应该快了。我说这地好像在动。原来是旁边有人在跺脚,听见我们的话,一脚扫过来,死崽俚,给我死远点,你们倒巴不得发地震,看不把你们震到地底下去。
我看到人群中的祥云婶,脸色一明一暗,那是她丈夫老大在抽烟。
闪电后来消失了,我们有些失望。
折腾到了天亮,地震也没有发起来,我却躺在竹床上睡着了。
醒来已是满眼金光,日头早挂在半天云里。我翻身下竹床,身上的汗水一个个像花朵般盛开,之后啪啪往地上掉。塘坝上已无一人,我看见水仔过来了,我说小明呢。水仔神秘地对我说,你睡得真死呀,早上有场好戏也没有看到。我问又不是晚上,早上演什么电影呢。水仔一掌拍在我的小肚子上,真是笨呀,哪有什么电影,是有人打架。我一下子拉住水仔的手说,哪个打架?水仔故意不理我,我扬了扬自己的拳头,水仔才在我耳边说,小明的爸和他三叔呢,祥云婶上前劝,小明爸还把她踢了一脚。气得祥云婶反锁着屋门在屋里哭,小明一个人在屋门外哭。
我拉着水仔的手往小明屋走去,果然看见小明蹲在屋门口哭,见我们去了,哭得更凶了,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小明脸上似涂了个大花脸,看得我和水仔直想笑。我贴着门仔细听听,里面有细细的哭声传出来,推了推门,栓死了。我觉得无趣,拉了小明一把,小明不动。我和水仔便走出来,看见池塘里扑通一声,一个大水花飞溅开来,水仔说,鱼跳哩,莫非要发地震?
不多久,村里另一种议论开始了。一个嫂子与小叔子的故事在人们的意愿中慢慢生长起来,似乎比三嘎嘎的评话还要精彩。
故事之二:大胡子与老张
大胡子是我们孩子对生产队长的称呼,因他满脸胡子而得名,他的真名叫来发,是水仔的父亲。大胡子整天胡子拉碴,是个大块头,加上他的皮肤黑,平时又不苟言笑,浓黑的大胡子更显出威严,大家都有点怕他,他在生产队里是说一不二的人物。水仔的母亲瘦弱,与大胡子站在一起,不清楚的还以为是父女。我问水仔你姆妈不管你爸不刮胡子么,小明说姆妈也说过,可他爸就是很少刮,说是麻烦,又用忙来搪塞过去,姆妈也没办法。说忙,也不是假话,别看当一个生产队长,拿着生产队里最高的工分,操心的事太多。一个生产队,就是一个大家庭,各色人样,各种口味,分工安排上难免会做到真正的公平,更不要说东家吵架西家使坏,能管好一个全公社,不一定能管好一个生产队,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些事不能太认真,有些事又不能不认真,全在把握的火候。
闲话少说,还是言归正传吧。
那天晚上不知谁喊出地震来了后,大胡子第一个翻身跳下竹床,差点踩到了水仔的大腿。水仔蒙着眼坐起来又躺下了,他母亲一下子把他拉起来,说,要发地震了。一听地震二字,水仔的精神猛清醒过来,看看脚下,好好的没动。这时,他看到父亲紧急跑出去,好像是往村子里去了。水仔母亲跺着脚喊,人家都往空地上躲,你啷个还要往屋里跑?水仔就是在这个时候跟过去的,大概正是我和小明往他家喊他母亲的时候。
村南边尽头处有一个小屋子,先前是生产队放杂物的地方,现在却住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我们村子里的人,听说是省城的一个什么大单位的,我们都叫他老张。据说老张是犯了错误下放到我们队里改造的,犯了什么事我们小孩子当然不知道。老张来时穿着非常整齐的中山装,还戴着厚厚的眼镜,比我们见到的公社干部都不同,反正,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特别的人。开始的时候老张总是不理我们这帮孩子们,看到我们便把门轻轻关上。门关不严合,风一吹吱吱乱叫,胆大的便上前猛地推开那门,也不敢進去,快速地跑开,生怕老张出来打我们。后来大胡子安排老张在女人堆里做工,笨手笨脚的老把女人们逗得笑不拢嘴。老张却不笑,也不恼。有女人便教他怎样做,可他就是笨,老是学不会。歇息的时候,女人们都把外褂脱下,有的只穿着短袖衫,有的干脆袒胸露怀,只顾自己快活。旁边的老张低头坐着,身子裹得严严实实,汗水一层层地像浪头般涌出。一帮女人们实在看不下去,也不管老张愿不愿意,大家动手动脚把老张的上衣给脱了,当露出那雪白的皮肤时,女人们都怔住了,她们还从没有看到过男人有这样好的肌肤,每当在床上看到自家男人黑油油带有牛膻味的身子时,自然就想起了老张白瓷瓷的身子,不由就把身子背向了男人。这些事都是后来在塘坝上扯闲话时女人们自己讲起来的,老张无疑给她们的劳作和生活增添了一份乐趣。一次,祥云婶向大胡子提议别叫老张做工了,说他细皮嫩肉的在太阳底下晒,看得人心疼,又不会做工反倒添乱。大胡子摇摇头说,大队书记安排好的要我监督老张做工,老张是下来劳动改造的,一年做了多少工都是要向他们交代。
老张的屋里一片黑暗,大胡子喊门,没有玻璃的窗户里立马亮起了一丝光,打开门见老张一手拿着煤油灯,一手拄着一根拐棍。在这里先要交待一句,前几天老张烧火粪时一不小心摔下了田墈,扭伤了腿,这几天在屋里静养没出工。大胡子拉过老张往外走,老张却不肯出来。大胡子吼叫道,要发地震了,你想死在屋里啊。听大胡子这样一说,老张反而把油灯放在桌上,自己竟然坐上了床,昏暗的灯光下老张的脸色阴沉沉的,冷不丁发出一句话,发地震好,大家都干净。大胡子跳起来,身子带来一股风,噗地一下把灯给吹灭了。黑暗之中大胡子不再说话,只用力去拉老张,可老张死犟着不肯起来,大胡子由先前的吼叫变成了哀求,说死了人我可负责不起,老张你不能害我呀。老张也不说话,就是躺着不起来。
我知道,别看老张总是一副老实的样子,其实他犟着的时候谁的也不听。有一次大队书记来调查他的现实表现情况,大胡子自是美言一番,说他劳动改造得差不多了,做事非常积极。大队书记要大胡子带他去看看老张做工的地方,其时快近午饭时分,太阳正辣辣地光顾着老张的脊背,老张正弓背勾腰地扯着棉花地里的草,他没戴草帽,女人们给草帽他也不戴,来时那张苍白的脸早已晒成了黑不溜秋的牛屁股。大胡子喊,老张歇一会儿吧,大队书记来看你了。老张没有答应,不知是没有听到还是故意不答应。大胡子又喊了一句,才见他转了一下头,只看了大胡子一眼,连旁边的大队书记瞧都没瞧一下,仍低头扯草。大胡子有些尴尬,大队书记当然不高兴,气哼哼地说,还没有改造好。又转身对大胡子说,对付这种人不能有同情心,你怎么安排这么轻松的活儿给他干,要给他安排重活累活,这样才能让他彻底改造好。大胡子连连点头,但安排工时仍旧让老张干着女人们想做的轻快事。
水仔也跟进屋去,大胡子看到儿子,便叫水仔去喊些人来,要把老张抬出去。不一会儿来了两个壮劳力,大胡子一挥手,就把老张从那张吱吱作响的木床上抬了下来,一直抬到了塘坝上。
我和小明回到塘坝上时,看到老张像条狗一样蹲在那里。
故事之三:三嘎嘎与三嫲嫲
三嘎嘎曾经是景德镇的工人,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听说乡下一担萝卜都可以抵到他一个月的工资,头脑一热,便回到了村子里种萝卜。回来的时候身边还带着一个好看的女人,这个女人自然就是三嫲嫲。听村人们说,那时尽管吃不饱,可三嫲嫲却脸色红润身材丰满,在村里是数一的女人。只是许多年也不生孩子,后来二嘎嘎的儿子便过继给了他,二嘎嘎生了三个儿子,正愁供养不过来。孩子抱过来的时候只有一岁多,特难侍候,三病四痛不断,三嫲嫲那时把一身肉都瘦掉了,三嘎嘎心疼,三嫲嫲却笑着说,年轻时吃点苦算不得什么,留给下半辈子享福么。可三嫲嫲的下半辈子还是没有享到福。小时候我总看到她儿媳妇站在屋前咒骂她,儿子金狗端着饭碗站在一边,不敢上前说半句话。三嘎嘎站出来要打儿媳妇,女人却不怕,说现在不是旧社会了,公公打媳妇是要犯法的,有本事去把自己的老婆管教好。气得三嘎嘎嗷嗷叫,直骂世道变了,儿媳爬到婆婆头上去做窝。
那天晚上大家都慌乱地挤在塘坝上时,竟然没有人想起三嘎嘎,最不应该的当然是他的养子金狗,虽说媳妇不待见养父,可毕竟你还是他的儿子,族谱上明明记载着。三嘎嘎把金狗从小供养到大,和三嫲嫲不知操细了多少心,一直到结婚生子。本来以为他们做了父母会好一点儿吧,可一点也没转变,甚至他们还不允许孩子们走近三嘎嘎,他们建了一个新房搬出了老屋,与养父母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式。三嘎嘎和三嫲嫲后来也习惯了,特别喜欢我们这些崽俚们,给我们讲评话,拿给好吃的东西分给大家。三嘎嘎讲评话时三嫲嫲却不闲着,屋里的家务,洗衣做饭都是她动手,有时为了不打断三嘎嘎给我们讲评话,亲自把饭端到三嘎嘎手上。我也不知道三嘎嘎的评话是从哪里听来的,总也讲不完,这或许和他在景德镇当工人有关吧,或者和三嫲嫲有关。可关于三嫲嫲的故事他从来不透露半点,因为三嫲嫲不是我们本地人,村里人们也不知道她的身世,后来好像听大胡子队长说过三嫲嫲娘家成分不好,嫁给三嘎嘎,也算是高攀了。三嘎嘎那时是工人,谁也不敢欺侮的。
第二天发现三嘎嘎的还是大胡子队长,他刚刚拉开了老大和老三的打架,正回家拿铁耙到垅畈里去望水。做生产队长虽然操心,但在体力劳动上却轻松点,比如到各个垅畈的田里察看水情旱情就轮到他了,人们把这个工种叫做“望水”,每天一早肩扛着铁耙从东垅走西垅,南畈走北畈,整个农业生产的情况就了然于胸,晚上的安排工种就有了合理的理由。三嘎嘎家离大胡子家隔着两栋房子,前后排的房子落差大,无形中形成了一排高岸,有用石头砌成栏杆的,也有没遮拦的,平时大家熟门熟路,自然没出过事。三嘎嘎倦缩在岸堤下,低声呻吟着。显然,三嘎嘎昨天晚上听到有地震消息时也跑了出来,黑暗中他一下子跌进了这个沟底。
大胡子把三嘎嘎抱了出来。真是奇迹,三嘎嘎竟然没有大碍,只是把腿给扭伤了。事后三嘎嘎说是三嫲嫲保佑了他,在他跌下去的一瞬间托住了。三嘎嘎胸前抱着一个木框子,地上碎了一地的瓷片,三嘎嘎见状,大哭。我以前也见过三嘎嘎大哭过一次,那是三嫲嫲死的时候。三嫲嫲是如何死的我不知道,但听大人们说和金狗的老婆有关,那時我刚上小学,我只知道村里死了人要摆酒席。村里生和死都是要摆酒席的,还有结婚嫁女也少不了。那时我非常关注村里的酒席,因为可以吃到平常吃不到的肉。我知道,破碎的一定是三嫲嫲的瓷画像,我不能理解的是三嘎嘎跑出来时干嘛还要把三嫲嫲的瓷像抱在身边呢。厅堂桌上没有三嫲嫲的瓷像,三嘎嘎像落了魂一样,躺在摇椅上还在哭鼻子。大胡子队长懂得两下推拿,帮三嘎嘎推了几下,找来一根拐棍。金狗和他媳妇还是不肯来看三嘎嘎,三嘎嘎暂时不能走动,生活不能自理,大胡子便安排祥云婶过来帮忙,也不要整天在这里,几个紧要时段,比如三餐饭时,晚上过来问个情况什么的。工钱大胡子要在金狗的工分里扣,金狗不敢跟大胡子闹,他老婆却缠着大胡子,见大胡子不松口,便站在村头边骂街,听得过往之人连连摇头,说这个女人莫非不是爷娘生的。大胡子不理她,金狗和他老婆也没有办法。
三嘎嘎再也不跟我们讲评话,说除非我能把三嫲嫲的画像画出来。
我哪有那个本事能画像呀,多年后我还真画了一个,是用碳笔画的,小明和水仔都说画得很像,可惜三嘎嘎早已作古了。当然,这是后话。
闹地震的消息时不时地在村里沸腾一下,就像池塘里的鱼儿,乱窜的老鼠,打架坠地的鸟儿们一样,总要出来换个气儿或者换个方式体验一下生活。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出工回来的人们照例聚集在大枫树底下。荫凉似乎也罩不住人气相蒸的热气,有人烦躁,有人生事,时不时地发生吵架斗嘴之事,大胡子队长也管不了这么多,只是把相关的人赶出树荫底下,让他们在热辣辣的日头底下争斗。这样一来,反倒让他们销声匿迹,当昼的日头太毒了,没有哪个可以受得了,便只有圆睁着眼,气哼哼地坐在大枫树底下的地上,双方自是拉大了距离,中间隔着许多人,便只顾自说自听,一直到响起鼾声。
夜晚的降临并没有带来多少凉爽,塘坝上的人们都拥挤在一起,虽然啪嗒啪嗒的扇子声响个不停,可闷热依然不能退去。大家在一起,短时是可以忍受的,比如先前大家在一起乘凉时都是上半夜在外面,下半夜回屋去睡,现在全天候地暴露在一起,特别是到了下半夜,许多奇事怪事就不断发生。当然,我们这些小孩子下半夜是睡得死沉沉的,人家把我们搬走了都不知道,这些故事是事后慢慢听大人们说出来的,有的我们也听不懂,有的半懂不懂。这些故事我暂时还是不想讲出来,以后有机会时再说。不过,那些时候早上醒来时我总听到有人骂街,有人撕嘴,有一次还有个女人把另一个女人的裤子都扒了下来,白亮亮的屁股在日头底下炫得人眼放花。大胡子队长对着围观的人大声喝骂,看什么看,快给我出工,再要不去,给你们倒扣三分。
水仔和小明找到我,说怎么还不发地震呢,又跺了跺脚下沉实的土地喊,鳌鱼鳌鱼睡觉了吧,快眨一下眼吧。耳后传来一阵风响,接着便听到大胡子队长粗旷的声音,你们这帮歪崽,吃得没卵事在这里乱嚼舌,看我不撕烂你们的狗嘴。我们撒腿开跑,一直跑出到了村头,在老张的屋前我们停住喘气。老张的屋门锁了,他出工去了。我们来了兴趣,说到老张屋里玩玩,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有。水仔用力推了一下门,裂开了一条大缝,水仔试了试,说小明身子小可以先试试能不能钻进去。小明比我们俩小一岁,身子瘦小。小明便把身子用劲往里挤,脚先进去了,上半身还在门外,水仔说我帮你用力,说着把小明的身子往里揉,小明却哭起来,说门板硌得疼。见此情景,我赶紧叫小明出来,可小明身子却不能乱动,一动,门板就硌得疼,也就是说小明卡在了两块门板之中不能进也不能出。我吓坏了,叫水仔去喊他爸来,水仔说他爸来也没用,没有钥匙,得喊老张。我们两人慌慌张张地满垅满畈地呼喊着,老张,老张!大胡子队长去大队开会去了,我们也不知老张在哪个垅畈里做事,有人抬头朝我们这儿张望了一下,仍旧干着活,没理我们的喊叫。这不怪他们,谁叫我们平时在村里也是这么大呼小叫地喊着老张老张,他们以为我们喊着闹着玩儿呢。后来我们就看到了祥云婶,我们结结巴巴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祥云婶急喊老张老张,走上前一把拉起趴在地上扯草的老張就跑,脸上的汗水啪啪往下掉,把眼睛蒙住了。她腾出另一只手撩起褂子擦汗,顾不得露出了雪白的奶子。老张的脚还一拐一拐的,被她拉扯着乱叫,说我自己会走嘛。
老张一到,事情自是顺利解决,祥云婶把小明的褂子脱下察看,除了有一条红痕外没有受到什么伤,我们看了小明瘦骨嶙峋的样子直想笑。更没想到我们还因祸得福,有了一份意外的收获,老张不但没有责怪我们,还给我们每人拿了一块糖。
但是,另一份意外收获却在晚上获得,当着祥云婶的面,父亲和大胡子同时对我和水仔奖赏了两个巴掌,我们跑出了塘坝,脸上还有辣辣的疼。父亲的手真狠。水仔拉着我的手说,老张给的糖还真甜。我不愿这么快地回去,便来到三嘎嘎的屋门口,屋门没关,里面黑瞎瞎的,我轻喊了一声,听到了三嘎嘎一声咳嗽,我说三嘎嘎也不点个灯,万一发地震了怎么跑。我们进了屋,从三嘎嘎身边找出火柴,点着了灯,才看见三嘎嘎是躺在厅堂里的摇椅上,身边还有个拐棍。水仔说三嘎嘎给我们讲个评话吧。三嘎嘎说,忘记了,想不起来了。我说,要是能把三嫲嫲的画像画出来呢,三嘎嘎猛地一下坐起身,说,给我找个人画吧,画好了评话也回来了。我问三嘎嘎有照片没有,请人画像也要有个依据吧。三嘎嘎摇了摇头说,没有了,先前是有的,后来就毁掉了。三嘎嘎不讲评话,我们也不愿多待着。
转来转去,没有多大意思,我们准备回到塘坝上。这时,天地之间突然一闪光,接着传来一声响雷,我们惊吓了一跳。我们拼命往塘坝上跑,那里的人群沸腾起来,手电灯光闪烁交错。我跑到了父母身边,母亲紧紧抱住我,大家都在猜测到底是发地震呢还是要下大雨。大家也没有发现什么动物异常事,加上又经历了上次的虚惊事件,由此大家的判断是雷雨。一旦有人开始回家避雨,大家接着跟上,转瞬间塘坝上只遗留着许多竹床板凳,闪电之下像某些战争电影场景中留下的败兵残迹。
夏天的雨确实猛烈,雷电就在我们头顶炸响,雨点扑拉拉地打着窗子,缝隙处有水冒出,地下立马积下一汪水潭。父亲时不时走到门前去望望天空,母亲自言自语地说,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发地震哟。我感觉到母亲的身子不住颤抖,父亲转身拉着母亲的手说,怕什么哩,哪年没见过几场这样的雷雨。见我也呆愣愣地坐着,便说,困觉吧,困一觉就过去了。说着,不再看天,吹灭了煤油灯,翻身上床。
躺在床上我也睡不着,闪电像条蛇一样在眼前晃动,而雷又似一把大锤敲着脑袋,要不是在父母身边,一个人可得吓死。毕竟我那时还是个孩子,瞌睡沉重,不知什么时候就睡了过去。
醒来过后是第二天早上,风住雨停,鸟语啁啾,一看外面,村庄被洗涮得干干净净,只是远远看到池塘里漂浮着好多杂物。我正揉着眼睛要去厨房吃早饭,父母做工是一早就要出去的,母亲把早饭早早地做好,早上收工回来就可以吃上。这时小明和水仔赤着脚跑步过来了,拉起我的手说,快去村南头看热闹。我问村南头有什么热闹,水仔说听他爸说好像是老张出事了。
村里的男男女女差不多都在村南头那幢小屋前,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没有小屋,只有从山坡上冲下来的泥土和破砖残瓦以及被雨水浸染的木料。也就是说,昨夜一场大雨把老张住的小屋给冲毁了,那么老张呢?我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我大声问,老张呢,老张!没有人回答我,大人们紧张地清理着场地,我要挤上前去,被人给推开了。渐渐,有人说,出来了,露出来了。我和小明还有水仔紧拉着手,再想挤进去,被大胡子队长给喝开了,小孩子都给走开。祥云婶走出来,一下子把我们三人都拉到一旁,说,小孩子不能看,给我走远点。我问,老张怎么了?祥云婶没有回答我,我只看到她在不住地抹眼睛。
【作者简介】 陈玉龙,江西都昌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在《青年文学》 《雨花》 《天津文学》《四川文学》 《山东文学》《当代小说》《广西文学》《清明》 《安徽文学》 《星火》 《芒种》《鸭绿江》《西湖》《青年作家》《飞天》《滇池》等刊发表作品约2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