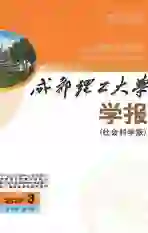我国隐瞒重疾撤销婚的立法模式、立法理念与主要制度阐释
2022-05-30高丰美
高丰美
摘 要:《民法典》第1053条对疾病婚的立法采用限定模式,将欺诈婚的欺诈事项限定于重大疾病。疾病婚的立法理念从“禁止疾病”转变为“禁止欺诈”,以婚姻欺诈理论构建了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制度。重大疾病须在客观上是重大的欺诈事项,即严重影响婚姻关系本质的疾病。重大疾病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应解释为主动告知,无需婚姻当事人另一方的询问。和一般受欺诈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相比,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撤销权在行使期限上具有共同性和特殊性,即受1年除斥期间的限制,但不受5年除斥期间的限制。
关键词:重疾撤销婚;婚姻欺诈;重大疾病;主动告知;行使期限
中图分类号: D923.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2)03-0077-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53条第1款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该款规定了因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婚姻被撤销的情形,学界将其称为隐瞒重疾撤销婚。然而,对于该款却存在不明晰之处:《民法典》第1053条属于开放型还是封闭型规定,如果存在隐瞒重大疾病以外的其他欺诈行为,婚姻是否可以撤销?该条款规定是否仍然属于“禁止疾病”的条款,只要患有重大疾病,即可撤销婚姻?比如,有观点认为不论婚姻当事人履行重大疾病告知义务与否,相对方均享有婚姻撤销权[1]。如实告知的重大疾病如何界定?如实告知义务在结婚登记中该如何履行,是主动告知还是经询问告知?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撤销权是否受到1年和5年的除斥期间的限制?上述问题的厘清,对于正确理解《民法典》第1053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民法典》对疾病与欺诈婚关系立法模式的选择
在婚姻家庭法领域,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已规定了欺诈的婚姻可撤销。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第2款第3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997条都规定欺诈婚,婚姻当事人一方实施欺诈行为,使婚姻当事人另一方陷于错误而与之缔结的婚姻,可以撤销。撤销婚制度的模式选择本身反映了国家通过婚姻想要推进的社会目标和社会愿望,以及婚姻状态的国家偏好(states preference)[2]。这也导致对于疾病与欺诈婚关系的立法模式各有不同。
(一)疾病与欺诈婚关系的传统立法模式
在疾病与欺诈婚关系处理上,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在婚姻效力瑕疵规定中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
(1)吸收模式。这种模式仅规定欺诈撤销婚,没有单独对疾病撤销婚进行规定,典型的如德国、瑞士、日本的立法例。在婚姻撤销立法上,德国、瑞士、日本法比较重视婚姻当事人的人格性。吸收模式下的立法认为隐瞒疾病和其他欺诈行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属于婚姻当事人出现因素认识错误,都是结婚当事人一方实施欺诈行为,使另一方陷于错误而结婚的情形,不存在特殊性,当然统一归入欺诈婚予以立法即可。
(2)并列模式。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为例,这种模式在立法中同时规定了包含疾病的欺诈撤销婚(第997条)和特定疾病撤销婚(第995条)。第997条规定因被欺诈而结婚的,可以请求撤销该婚姻,其中包括隐瞒疾病。同时,第995条规定不能人道且不能治愈结婚的,可以请求撤销婚姻。不能人道是指无法为性行为,在医学的诊断是性功能障碍,属于患有疾病情形。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特别规定不能人道缔结的婚姻为可撤销婚,但是对于其他疾病则区分是否存在婚前隐瞒,分别适用第997条婚姻撤销(隐瞒)和第1052条离婚(非隐瞒)。
(二)《民法典》的选择——限定模式的欺诈婚
在疾病婚的立法上,《民法典》没有采用上述两种立法模式,在处理疾病与欺诈婚的关系上具有自身考量。我国采用的是限定模式,将欺诈婚限定于隐瞒重大疾病这一种情形。
结婚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要求确保婚姻当事人合意自由和意思真实,存在欺诈这一意思表示瑕疵时,法律允许撤销婚姻。但是结婚行为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一般的财产行为,结婚行为的欺诈具有特殊性。结婚行为的欺诈与财产行为的欺诈在规范目的和意义上不同。与财产行为不同,结婚行为属于身份行为。身份行为以人伦秩序为基础,以维持家庭美满,达成延续生命为目的,主要规范内容是身份关系,除了缔结婚姻的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利益,还涉及婚姻所生子女的利益。就结婚行为欺诈而言,如果欺诈的性质与婚姻共同生活无关或影响很少时,不宜认定为婚姻欺诈。也正因如此,即便是采取吸收模式和并列模式的国家或地区,只有欺诈事项影响婚姻关系本质时才认定为欺诈婚,予以撤销。
基于上述理由,《民法典》没有采用吸收模式,没有规定毫无限制的欺诈婚,而是将欺诈婚的欺诈事项限定于对婚姻关系本质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疾病;只有隐瞒重大疾病缔结的婚姻才可以撤销;患有重大疾病(严重影响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类疾病除外),但是没有隐瞒的,婚姻有效;以隐瞒重大疾病以外的其他欺诈方式实施婚姻欺诈的,不影响婚姻效力。更何況欺诈婚的判定标准如果过于模糊,容易导致滥用,影响婚姻家庭的稳定。和其他欺诈事项相较,重大疾病可以通过医学鉴定进行科学判断,避免随意撤销婚姻进而影响婚姻家庭的安定性。由于《民法典》没有规定无限制的欺诈婚,更遑论选择并列模式,而且以不能人道作为单独的疾病规制也不符合生活实际。性生活是婚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不是每个当事人婚姻必备的内容,比如有些老年人的婚姻并不是为了性生活。立法应允许婚姻当事人自由选择,在不知情的情形下享有撤销选择权,在知情的情形下,婚姻有效,而不是不考虑当事人主观状态认定不能人道缔结的婚姻为撤销婚。
《民法典》对疾病婚的立法模式选择也正是反映了既期望保证结婚行为作为法律行为所要求当事人的合意自由和意思真实,又能维护结婚行为作为身份行为所需安定性的社会目标和愿望。欺诈婚的限定模式选择也正是《民法典》第1053条的制度阐释前提。
二、从“禁止疾病”到“禁止欺诈”的立法理念转变
对患有疾病缔结婚姻(疾病婚)的规制,我国民事立法经历了从“禁止疾病”到“禁止欺诈”的转变。自1950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以来,对疾病婚始终是“禁止疾病”的立法态度,将某些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情形。2001年《婚姻法》更是明确规定疾病婚为无效婚,第七条第二项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事由,同时第十条第三项将疾病婚规定为无效婚,无论婚姻当事人是否隐瞒,只要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该婚姻均无效,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这一规范设计旨在“禁止疾病”,“防止婚姻当事人所患疾病传染给对方特别是传染或遗传给下一代,保护下一代健康”[3]。
由于在实践中“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医学禁婚疾病无效条款在实践中难以适用,乃至裁判不一。特别是在强制婚检缺失的情形下,原《婚姻法》医学禁婚疾病无效条款偏离了最初的立法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以“禁止疾病”向“禁止欺诈”转变的理念和方式处理疾病婚纠纷[4]。为此,《民法典》第1053条对以往疾病婚的立法态度做了重大调整,删去医学禁婚疾病无效条款,引入隱瞒重大疾病撤销婚条款,发生了从“禁止疾病”到“禁止欺诈”的立法转变。具体表现为:一是在表述上不再使用“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改采“患有重大疾病”;二是对于疾病婚这一瑕疵婚姻效力,由“无效婚”转变为“可撤销婚”。
在“禁止疾病”的立法理念下,医学禁婚疾病无效条款具有明显的制裁性质,不允许反映违法的婚姻当事人的个人意思,只要有无效婚姻的原因存在,即发生无效的法律效果[5]。然而,婚姻家庭法属于私法范畴,结婚自由是民众的重要民事权利。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结婚自由意味着对于疾病婚的风险应由当事人自己思考、选择和承担法律后果”[6]。依据全国人大法工委说明,“在知情的情况下,是否患病并不必然影响当事人的结婚意愿,应尊重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7]。为此,《民法典》第1053条改采撤销婚的效力状态,考虑婚姻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区分婚姻当事人是否隐瞒重大疾病判定疾病婚效力。该条款旨在保障当事人缔结婚姻的真实意思表示,防范当事人在被欺诈的情形下做出违背内心真意的结婚意思,以及尊重当事人根据自身感情状况等因素自主决定婚姻效力。在“禁止欺诈”的立法理念下,考虑的不再是无效婚的违法性,而是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感情状况;考虑的不再仅是疾病本身,而是患病的当事人一方是否存在隐瞒这一欺诈行为。《民法典》第1053条将疾病婚效力的选择权交由当事人,提升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保障了民众的结婚自由权[8]。而且第1053条引入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条款、以“禁止欺诈”的方式提高了当事人的诚信义务和注意义务,督促当事人积极主动关注自身疾病状况,有助于达到婚检的目的,反而有利于做到及时发现疾病,做好疾病的婚后防治措施。
在“禁止欺诈”的立法理念下,我国用民事欺诈理论构造了限定模式的欺诈婚模式,这也决定了《民法典》第1053条中重大疾病的界定、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婚姻撤销权行使等制度的阐释基调。
三、我国隐瞒重疾撤销婚的主要制度阐释
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制度涉及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的内容。就构成要件而言,我国目前的通说认为欺诈的构成包括三个方面的要件:行为人存在欺诈行为,行为人具有欺诈的故意,以及欺诈行为与表意人的意思表示存在因果关系[9]。对于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的认定,在主观上,实施欺诈行为的患病婚姻当事人一方须在主观上有隐瞒重大疾病的故意,并有令被欺诈的婚姻当事人另一方在客观上因该隐瞒的意思产生错误认识而作出结婚意思表示的故意。婚姻当事人的主观故意和因果关系的认定均较为明晰,存在疑义的是隐瞒重大疾病这一欺诈行为的认定。其中,何为重大疾病、如实告知义务之履行是认定欺诈行为的关键。就法律后果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违反重大疾病如实告知义务在婚姻效力方面的法律后果非常明确,受欺诈的婚姻当事人一方享有婚姻撤销权。虽然《民法典》对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撤销权的行使主体等内容规定得较为明确,但是婚姻撤销权的行使期限这一问题却尚不甚明晰。有鉴于此,本文接下来对重大疾病的界定、告知义务的履行,以及婚姻撤销权行使期限这三项内容进行探讨。
(一)重大疾病的界定
《民法典》采限定模式的欺诈婚,将告知内容限于患有重大疾病。那么,何为重大疾病?目前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尚不明确。有观点认为重大疾病应按照是否足以影响婚姻当事人另一方决定结婚的自由意志或者是否对双方婚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标准判断[10]。有观点认为重大疾病包括“具有结婚行为能力的弱智(智力障碍)和精神病、与性、生殖有关的疾病、严重遗传性疾病、艾滋病和性病、其它乙类传染病和丙类传染病、重大身体疾病”[11]。还有观点认为第1053条中的“重大疾病”的外延“等于和宽于禁止结婚的疾病范围”[12]。
笔者认为,要界定《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的重大疾病,归根结底须回归到该条款的立理念和模式,即隐瞒重大疾病缔结的婚姻婚属于欺诈婚来探讨。在采欺诈婚的国家或地区,对于欺诈婚的认定条件是比较严格的,要求欺诈的事项在客观上应为相当重要的事项。如美国州法要求欺诈事项以影响婚姻关系之本质为必要[13]5;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314条第2款第3项,欺诈事项须是与婚姻本质相关的事实且在客观上是重大的[14]15;在我国台湾地区,如史尚宽先生指出关于婚姻本质之情事均有告知义务[15]264。《民法典》第1053条将欺诈事项限定为隐瞒重大疾病。依上述关于欺诈事项客观上为婚姻本质的论断,此处的重大疾病作为欺诈事项应解释为影响婚姻关系本质的疾病。《民法典》的起草者也肯定了这一点,指出隐瞒的疾病是对婚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16]。以婚姻关系本质作为重大疾病的界定标准,避免仅在外延上以列举方式界定重大疾病的不足,而对婚姻关系本质的恰当解释既保障婚姻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也避免婚姻的任意撤销,保障婚姻的安定性。
那么何为婚姻关系本质? 古罗马法认为,婚姻是以生育和抚养子女为目的建立的共同生活关系[17]。早期的婚姻本质理论比如康德也认为婚姻本就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相互占有对方的性官能而产生的结合体,并承认生养和教育孩子是培植性爱的自然结果[18]。在现代社会,如美国在实务上广泛运用的实质标准,认为婚姻具有永续性以及婚姻的主要功能表现为合法的性与生育,因此婚姻关系本质主要是关于夫妻一方对于性与生育之意愿及能力[13]8。德国通行的观点认为现代的婚姻应当从人本的婚姻观念出发,即婚姻是夫妻之间的精神情感关系,同时也要兼顾婚姻的客观功能,履行家庭责任、繁衍和教育后代等[19]。史尚宽先生也指出依据婚姻关系本质的事项包括关于性交、生殖能力、遗传病、传染病等情事,隐瞒的疾病须高度危害婚姻当事人或其子孙之健康[15]264。我国现代社会对婚姻的认识也是如此,婚姻是男女两性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结合。婚姻是基于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和固有的性本能建立的(夫妻共同性生活),并通过婚姻生育繁衍形成血缘关系继而形成家庭(生育繁衍后代),同时婚姻关系也是一定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的结合,因感情、道德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关系(夫妻共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0]。
综上,婚姻关系本质内容包括夫妻共同性生活、夫妻共同物质生活、夫妻共同精神生活、生育繁衍后代。概言之,婚姻關系本质表现为上述夫妻共同生活目的之实现或生育繁衍后代。重大疾病是指严重影响夫妻共同生活目的之实现或生育繁衍后代的疾病。严重影响夫妻共同生活目的之实现具体指患病婚姻当事人一方无法履行夫妻之间在性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层面的义务。足以影响生育繁衍后代具体指患病婚姻当事人一方无法生育子女或者所患疾病影响子女的健康出生。在认定重大疾病时,严重影响上述某一项婚姻关系本质内容的疾病即可构成重大疾病,至于婚姻当事人在意其中一项、两项或者三项共同生活内容还是生育繁衍后代,是否以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
(二)重大疾病的主动告知
重大疾病如实告知义务之履行,意指婚姻当事人在结婚登记前应如实告知对方自身是否患有重大疾病。重大疾病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包括告知内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等内容。从解释论角度,告知内容和履行期限在文义上较明晰,告知的内容须为重大疾病,告知义务的履行期限须为结婚登记之前;但是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是主动告知还是询问告知,却无法从法条文义中观知。而告知义务履行方式的正确解释是合理配置婚姻当事人的注意义务和认定婚姻欺诈行为的前提,需要进一步的阐释。
重大疾病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有主动告知和询问告知两种。在主动告知履行方式下,即使婚姻当事人不询问,另一方也负有主动告知的义务。在询问告知履行方式下,没有一般的告知义务,只有经婚姻当事人询问,另一方才就询问事项履行告知义务。比如德国法采此种方式。德国法对于欺诈婚没有规定一般的告知义务,告知义务可以根据婚姻当事人的明确询问,或者依据特别要求需要对某一特定事项进行解释说明时,仅对影响婚姻本质事项有告知义务[14]21。《民法典》第1053条采用了主动告知的方式。
如实告知义务是婚姻当事人为了结婚,在结婚登记时履行的义务,类似于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先合同义务”。婚姻缔结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婚姻当事人双方为了结婚,彼此接触、交换信息的过程。与一般的财产行为相比,结婚行为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以感情为基础而结合的身份上的法律行为。由于婚姻缔结具有身份属性,婚姻当事人对与缔结婚姻有关的信息依赖度也会更高。尤其是即将缔结婚姻的当事人在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建立感情后,彼此的信赖程度高于一般民事交易的当事人。在限定模式的欺诈婚项下,重大疾病对婚后生活具有重要影响,便属于对婚姻当事人双方建立诚实、信任和共处关系的重要性信息。而重大疾病信息往往具有较强的私密性,也没有统一的法定登记和查询机构,婚姻当事人无法也没有权利像一般的民事交易向有关机构查询婚姻当事人的疾病信息,较为便捷可行的信息获取途径即当事人彼此相互告知。基于此,在婚姻领域设计的如实告知义务必定要求由法律强制设定此种信息交换和告知义务,保障婚姻当事人的知情权。《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虽然没有使用“主动”的表述,仅规定患病婚姻当事人一方“应当”如实告知,但是此种告知义务的履行应解释为主动告知,无需婚姻当事人另一方的询问,这符合以上结婚行为中重大疾病告知义务的特殊性要求。而且依反面解释,如果解释为询问告知,则给非患病婚姻当事人另一方课加了不必要的注意义务,与第1053条“禁止欺诈”的立法理念和欺诈婚模式不符。在欺诈婚模式下,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的认定,对被欺诈的婚姻当事人一方的主观心态考察仅限于因果关系考察,即隐瞒疾病、错误认识和结婚意思的因果关系,而不考察其是否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16]。受欺诈的婚姻当事人一方在缔结婚姻时是否尽到必要的谨慎注意义务去看穿行为人实施的欺诈行为,如是否未积极探查婚姻当事人另一方病情,是否因过失未注意到对方病情或者隐瞒行为等均不影响患病婚姻当事人一方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不影响欺诈婚的构成。
综上,《民法典》第1053条的告知义务履行应为主动告知,即使在婚姻当事人另一方没有询问的情形下,患病婚姻当事人一方也有义务主动如实告知重大疾病信息。如果婚姻当事人隐瞒患有重大疾病的真实情况,即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可能构成婚姻欺诈。另外,此种如实告知义务属于法定义务,不需要婚姻当事人相互约定,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产生,也不因其他任何情形而免除。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如实告知义务属于一种不真正义务,婚姻当事人作为享有知情权的权利人通常不得请求患病婚姻当事人一方强制履行[21]。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强制婚检制度,为了督促重大疾病如实告知义务的主动履行,可推荐的方式是在结婚登记申请表中设计“告知条款”一栏。在结婚登记申请表中,增加一栏,载明:“本人未患有《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的重大疾病,或虽然患有但已经告知对方”,同时在声明附注中载明应告知的疾病类型以供参考。该声明内容由婚姻当事人双方签字,认可声明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对婚姻当事人缔结婚姻的最大诚信要求,以声明的方式督促婚姻当事人双方主动履行告知义务。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如实告知义务履行的声明,不是健康声明,因此不适宜载明“了解对方身体健康状况”或者“已经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原因是婚姻当事人没有主动询问的义务,表述为“了解对方身体健康状况”就会变相地将注意义务课加给不负有告知义务的婚姻当事人。此外,也不能表述为“已经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因为声明应体现的是告知后的结果,而不是给予告知义务人以是否如实告知的声明来逃避义务和责任。
(三)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虽然《民法典》对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撤销权的行使规定得较为明确,但是婚姻撤销权的行使期限这一问题尚有需要检视之处。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第2款,隐瞒重疾撤销婚撤销權的行使期间为1年,这与第1052条第2款和第3款受胁迫的婚姻撤销权的行使期间相同;而对于该1年期间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9条明确载明第1052条胁迫婚撤销权的1年期间属于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情形,并且明确规定受胁迫撤销婚姻的,不适用《民法典》第152条第2款中5年最长行使期限的规定。但是,对第1053条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撤销权的1年行使期间的性质,以及是否适用5年最长行使期间没有予以回应,这需要予以检视。
和一般受欺诈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一样,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撤销权在性质上也属于形成权,受欺诈婚姻当事人一方按照自己的意愿、以单方意思表示产生婚姻效力变动的效果,无需取得婚姻当事人另一方同意。在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下,如果受欺诈婚姻当事人长期不行使撤销权,使得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婚姻当事人双方所生子女的利益,而且还可能使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撤销婚姻当事人婚姻效力时,由于时间太长而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将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撤销权的1年行使期限解释为除斥期间符合撤销权的性质和婚姻家庭利益保护的需求[22]。综上,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撤销权的1年行使期间属于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情形。
与一般的受欺诈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不同的是,结婚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产生身份法效果的法律行为,涉及婚姻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利益。隐瞒的重大疾病具有较强隐秘性,比如一些遗传性疾病,可能在结婚后长期都无法为受欺诈婚姻当事人一方发现。如果规定自结婚登记之日起5年内不行使,撤销权消灭,将极大损害受欺诈婚姻当事人一方的人身利益,也与《民法典》第1053条将“禁止疾病”转变为“禁止欺诈”的立法理念不符。因此从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婚姻自主权和妇女权益的角度,排除适用《民法典》第152条第2款规定才符合婚姻家庭编保护当事人婚姻自主权的基本价值取向[23]。依据相同情形相同处理原则,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9条已经明确受胁迫撤销婚不适用5年最长除斥期间的情形下,应对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的行使期限做同样的解释。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排除规定情形下,隐瞒重大疾病的婚姻撤销权行使期限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19条规定,不适用《民法典》第152条第2款中5年最长行使期限的规定。
四、结语
《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的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是《民法典》在原《婚姻法》基础上新修增的条款,它以民事欺诈理论加以构造,但同时也基于结婚行为的身份行为属性加以限定。对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制度中重大疾病的界定、告知义务的履行、撤销权行使期限等内容的解释应立足于“禁止欺诈”的立法理念,这也是对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制度其他内容进行教义学阐释的基调,以及司法实践中应始终关注的价值取向,借此以实现立法者所期盼的保证婚姻当事人的合意自由和维护婚姻家庭安定性之社会目标的双层愿望。
参考文献:
[1]申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回归与革新[J].比较法研究,2020,(5):119.
[2]Sanford N. Katz:. Family Law in America[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42.
[3]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1-34.
[4]孙若军.疾病不应是缔结婚姻的法定障碍——废除《婚姻法》第7条第2款的建议[J].法律适用,2009,(2):66.
[5]李洪祥.论无效婚姻制度的性质[J].当代法学,1991,(3):51.
[6]马忆南.民法典视野下婚姻的无效和撤销——兼论结婚要件[J].妇女研究论丛,2018,(3):29.
[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议案》的说明[EB/OL].(2021-07-16)[2021-10-11].https://www.ccdi.gov.cn/yaowen/202005/t20200522_217915.html.
[8]王歌雅.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价值阐释与制度修为[J].东方法学,2020,(4):175.
[9]朱庆育.民法总论[M]. 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79.
[10]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编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102.
[11]张学军.民法典隐瞒“重大疾病”制度解释论[J].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0,(5):133.
[12]蒋月.准配偶重疾告知义务与无过错方撤销婚姻和赔偿请求权[J].法治研究,2020,(4):74-75.
[13]Kerry Abrams. Marriage Fraud[J].California Law Review,2012,(100).
[14]Marina Wellenhofer. Kommentar zum Bu?rgerlichen Gesetzbuch[M]. 8. Aufl. München: C.H.Beck, 2019,1314.
[15]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6]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48.
[17]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07.
[18]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95-96.
[19]Dieter Schwab.Familienrecht[M].22.Aufl.München: C.H.Beck,2014:17.
[20]杨大文,龙翼飞.婚姻家庭法学[M]. 7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4.
[21]王爱琳.民事义务的构成分析[J].政治与法律,2007,(5):103.
[2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49.
[23]郑学林,刘敏,王丹.《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若干重点问题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21,(13):44.
Marriage of Concealment of Serious Illness:Model, Idea and Doctrinal Analysis
GAO Fengmei
(College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Shaanxi 710063,China)
Abstract:Article 1053 of the “Civil Code” adopts a limited model to limit the fraudulent matters of fraudulent marriage to serious illness. The legislative idea of marriage concluded under disease has changed from “prohibition of disease” to “prohibition of frau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rriage fraud. A system of marriage annulment by concealing serious illnes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is determines the interpretation tone of important systems such as the definition of serious illness in Article 1053, the fulfillment of truthfully informing duty, and the time limit for exercising the right to annul the marriage. The serious illness must be an objectively significant fraudulent matter, that is, an illness that seriously affects the nature of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The fulfillment of truthfully informing dut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ctive informing without inquiry from the other party to the marriage.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right of revocation for fraudulent civil juristic acts, the right of marriage annulment for concealing serious illness has common and special points in aspect of exercising time limit, which is limited by the one-year revocation period, but not by the five-year revocation period limit.
Key words:marriage annulment of concealing serious illness; marriage fraud; serious illness; active informing; time limit for annulment of marriage
編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