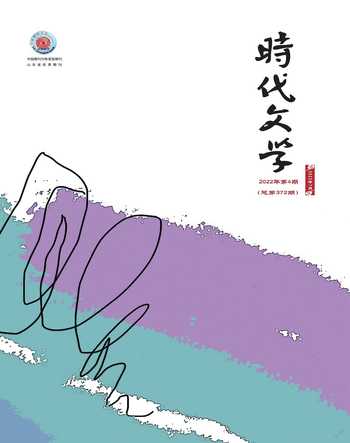老人与船
2022-05-30董伟伟
董伟伟
一
一艘老木船陈列在博物馆里。它不是博物馆的重要文物,却属于重量级的物件。从它庞大的身躯,可以看到它昔日的风采,看到它在波澜壮阔的海里劈波斩浪的样子,看到它远航归来鱼虾满仓,看到船上熙熙攘攘收获的场景。
博物馆里的射灯打在船体上,在灯光映射下,苍老、陈旧、坼裂的木纹里,依稀可见它曾经的霸气和豪情。船体上的旧痕,是在大海里航行时遭创结成的烙印。十多米高的桅杆和船体的长度接近,笨重地躺在船的一侧。若是挂上帆布,在海上猎猎雄风,十分壮观。而此刻,它静卧一隅,回忆着往事,回忆着与主人一起闯荡大海的日子。
很多年前,在离大海不远的海滩上,它像一只张牙舞爪的怪兽,被遗弃在一堆废旧的木船中。破烂不堪的船舱,朝天空张着大口,和流动的白云、过往的海鸥打着招呼。舱里堆积着鸟的粪便、覆盖着厚厚的尘土,连只鸟儿都不肯落在上面。敦实的船壳,一半埋在沙土里等着在时间中沦陷,一半在空气中磨着时光。由一根完整的肋骨支撑着的船体,隐约可以看出它优美的弧度。被风雨雷电侵蚀的前后搪浪板严重腐朽。船头翘着,似有召唤海浪之势。船尾下沉,又有万般不舍与无奈之意。
谁会在乎这艘破败的木船呢?就是这敦实的船壳,改变了船的命运!一位与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老人偶然间发现了它。老人在看到它的一刹那,凝固的记忆复苏。这是当年海上生产用的船,是他梦寐以求的大网船。老人异常兴奋,眼里滚着激动的泪花。
从小生活在海边的他,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情感,能驾驶一艘属于自己的船出海捕鱼,是他毕生所追求的梦想。但是,当年还是小伙计的他,是没有经济实力来“排”(建造)这样一艘大网船的。这艘废弃的大网船,让他生出许多情愫,搅和得他没法睡个囫囵觉,犹豫再三,他最终还是决定花“巨资”把它买下。
确切地说,老人买下的是满目疮痍的船壳。船壳里那些横七竖八、大大小小的物件,在老人脑海里翻飞,那么清晰,那么真实,他必须把它们组合起来,就像完成一场救赎。经过数月的收集,船壳里让船前行的零部件,桅、篷、舵、棹、櫓等全部收齐。
从那以后,老人再也闲不住了。很快,他请来几位七八十岁的老船工、艌匠、木匠,把那些物件一一安装在船的“腹内”。一艘毫无生机的船顿时丰满起来,有了生命和活力。
完成这项工程无疑是重造了一艘大船。老人深知,造船,就是在造一个古老的灵魂。对着这艘船,老人感叹万分,没想到风烛残年,他的梦想竟然成真了。当他把船收拾一新,憧憬着摇着大网船出海时的豪迈时,却被告知,这艘船早已报废,不可能申请相关手续披挂下海了。
老人因船不能驶向大海而痛心,为了不让它就此闲置,他主动联系博物馆,征得同意后,把船连同他收集到的海上捕鱼的老物件,一起捐献给日照市博物馆,也算为这艘船找到了归宿。
这艘船在博物馆与我邂逅,同时,我也有幸认识了给了船第二次生命的耄耋老人。
二
老人的幸福指数很高,不单单体现在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上,而是高于二者的英雄主义。
今年夏天,我偶然听到老人在海上有种种英勇行为,倍感震惊。强烈的好奇心作祟,让我萌生出进一步了解他的想法。
再次见面,时隔一年半,为了能够轻松自如地听老人讲述,我们选择在宽阔而宁静的海边。老人给了我地点,导航却把我导到离他很远的渔村。我把车停下,给他打了电话。不到十分钟,一辆小面包车疾驶而来,身着长袖条纹T恤、腰板挺直的老人下了车,左右顾盼,我试探着喊了一声“老伯”,他便向我走来。我吃惊不已,车竟然是他自己开来的。我忐忑地坐进车里,颠簸在窄窄的小路上,紧张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不经意间,扭头看到被岁月打磨得脸上闪着油光的老人正气定神闲地踩离合、挂挡、换挡、踩油门,灵活程度不逊于年轻人,才觉得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的老人,颠覆了我固有的思维。一下午三个多小时,我在听他讲述。
打开记忆闸门,老人把那些毕生难忘的经历和近期在海上遇到的种种险情对我和盘托出。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人生暮年竟然找到自我,活出了另一种精彩。我惊叹他的胆识,也不免担心他的年龄,是否还能与血脉贲张的激情成正比。
一位老人,有如此勇气一再萌生大胆的想法,他要划着笨重的木船,出没在危机四伏的大海里。他要在海里拍几个视频为此生留念,他甚至还有比拍视频更有挑战性的宏阔愿景。
我在与老人交流着,也在了解他的世界。他的世界里,藏着更加幽深的大海,藏着对古渔船那份热爱和执着。他要让那些编织好的梦想和对船深潜的原动力,冲破心中这片汪洋,驶向真正的大海里去。他是海的骄子,是海的弄潮儿,是海中劈波斩浪的骁将。
海边的夜色真美,一轮满月,几束跃动的光团,一队人在海滩上燃起了爱的烛光。那些故事很平凡,却又是那么与众不同。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与平凡打着交道,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是生活中不能分割的重要片断。
三
跟着老人的讲述,我走进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1938年秋,日照石臼一个极其贫寒的家庭,降生了一个男孩。男孩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快乐,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忧虑。三代十几口人,居住在不到20平方米的两间房子里,杂乱拥挤,甚至连呼吸的空气都显得珍贵。
家里虽然穷得揭不开锅,家长却是开明的,硬是靠两亩薄地,省吃俭用,供这个男孩读书,希望他能出人头地,兴旺门庭。
这个男孩没有让家人失望,他聪明好学,努力上进,在石臼上完小学后,17岁考取青岛一中,每月领到三块钱的奖学金。这几块钱的奖学金,解了他们家的燃眉之急,男孩靠它读完三年中学。19岁时,男孩考入山东建筑学校(后改为冶金学校,是现在青岛理工大学的前身)。这令全家引以为荣,令全村人羡慕。然而,在求学期间,他的性格发生变化。他少言寡语、特立独行,经常生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这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
学校里教条式的教学让他越来越反感,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学下去。幸好,这期间他接触到很多课外书。读课外书打开了他的眼界,也拨开他心头的阴云。他大量读书,除了中国的各类书籍,国外名著也是他啃噬的对象。书读多了,思想比较开通,也开放。同时,也有不利影响,他经常头晕、恶心、体力下降,影响学业,与老师、同学交流的机会也少了。老师再三警告让他好好学习无果,责令他退学。
一个被全村人以为最有出息的农村孩子,学业未成而被劝退,于家于学校于他都是不光彩的事情,校方体谅他没有大过,给了个肄业证书,留他在校办工厂协助工作。
1961年,国家号召支援农业建设,23岁的他鬼使神差辞去工作,踊跃响应号召,成为上山下乡青年。从此,带着各种“光环”的他回到家乡,回到出生的海边,到了农业生产队。
正值青春年华的他,在生产队热火朝天地干了两年苦力活,未找到一丝一毫成就感,便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严重怀疑。有一天,他到海边散心,面对大海,他豁然开朗,眼前一片光明,大海才是搭载他身体和灵魂的摇篮。
之后,他自告奋勇去海上当了渔民。他说,他爱大海,只有大海才能唤醒生命的内在活力。年轻的他把精力全部投入渔业生产中,一直干到渔业队解散。他动情地讲述着往事,讲着在海上进行渔业生产的那些点滴时光,时不时露出孩子般的笑容。他说他的梦想是排几艘五桅大网船,到深海里去……
四
大海用它蓝色的海盆,孕育出无限的生机和希望,它是人类丰富的食物源,也是人类构造幻想的世界。海里演绎着很多动人故事,有乘风破浪的凯旋者,也有葬身大海的不归人。
为了亲近大海,获取海里取之不竭的丰富资源,人类发明了各种捕捞工具,于是就诞生了筏和舟,有了捕捞的网具、钓具和刺具。最初,我们的祖先用几块圆木头捆绑扎实,编个筏子就能出海,木筏没有舵,靠两张橹调节方向。这种简单的出海渔业工具,时常会因大海的无常遭遇灾难。
早些年,海上的渔民还能照着过去古船的老样子、老规格,每年造几艘摇橹撑篙的小木船。小木船吃水线浅,不能到深海里,只能在近海处撒小网,收获不多。
随着时间推移和对海岸带的治理,海边的木船厂、修理厂的数量逐年递减。1990年以后,机器船代替了摇橹船。老旧的渔船闲置在岸上,经风吹日晒、雨雪风霜,很多都已经瘫痪、破碎,也有不少已经被拆散、移除。
古渔船就像过去老百姓常用的风箱、碓磨、牛具一样,即将被历史淘汰。那些以制造手工木船为生的老匠人,和陪伴老渔民半生的木质渔船,即将成为历史。但它们古旧的样子依然能勾起海边老人们的怀念。
为了能保存海上传统捕鱼生产方式,留住一刀一斧、一锯一锤的记忆,留住沿海渔民敢于乘风破浪、撑船摇橹的那段海上时光,也留住对大海难以割舍的情怀寄托,老人从15年前开始陆续收藏海上旧物。随着收藏的旧物增多,老人不满足于单纯的收藏了,他想自己建个渔业博物馆,让老渔船、老渔具这一文化符号,守住渔家人一片乡愁。终因势单力薄,能力有限,他自己的博物馆永远停留在构想中。
五
老人并未因大网船和那些老物件放在博物馆里而放弃梦想,那艘五桅大网船一直航行在他的心海里。
不甘于平庸的老人,不以颐养天年为幸福。他依旧游走在海边,依旧执着于寻找,终于有所发现。一艘破损的钓钩船静卧在肥家庄海滩上,落寞、萧条,与世无争。钓钩船虽小,但无论是空间、结构还是用途都与大网船相似。老人眼前一亮,如获至宝,摇橹出海的气焰,因这艘钓钩船再次高涨。
一位80多岁老人,总想打破常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不禁暗暗喟叹,这个老人对古渔船究竟痴迷到什么程度,对古渔船有多深的情结,这能给他带来多少价值和意义。
我观察着老人说话时的表情,从他嘴里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笃定。他没有浓浓乡音,却有浓浓乡情。
后来我才明白,发现和复原的过程远远大于收藏的价值和意义。他不再年轻,趁着还能动,他要冲破内心的块垒,实现一生中所追求的宏伟愿景,哪怕是人生最后一段路程,也要在海里完成。
像修复那艘大网船一样,老人开始对这艘钓钩船大规模修整。他找来木匠,做上舵盘梁、樯劲、桅、舵、棹,配上篷帆、大橹、边橹、牙篙……大船上有的,小船上一样不能少。同时找来老艌匠,把船上的裂缝艌好,安上舵梁后,一艘像模像样的小钓钩船诞生了。
钓钩船一般是4至5人操作,两人替换着摇后大櫓,推动船向前运动,并掌握方向。几个人替换着摇边橹,把棹的人只管用力把棹,船艄公专管掌舵。如果风向合适,是旁风或顺风,就可以张篷出海了。
老人在脑海里规划的那张航海蓝图就要付诸行动了,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兴奋着。出于安全考虑,海上管理人员阻止他出海,这艘小船被搁浅在肥家庄海滩上。
老人心里藏着大海和梦想,血液里流淌着斗士精神。是大海日日召唤,让他的激情喷涌而出。倔强的老人不管不顾,冒着生命危险,近一年里前后9次推船下海,他用行动表达着对船对海的迷恋和不服输的精神。他说:“只有在船上,在海里,我才真正感到这世界是活的,我是活的。”84岁的老人,他果真存在如此大的能量吗?
他娓娓叙述着他的境遇,其中隐含着对生命的某种暗示,我随着他的语速时而叹息,时而兴奋,时而动魄惊心。
六
在一个极好的天气里,无风无浪的海,平静得就像一面镜子。老人摇着小钓钩船,开始了首次出海行动。
他从附近村里找来三个经验丰富、赋闲在家的老渔民,雇了一个吊工,把船从岸上吊到海里,等待潮水。小木船被慢慢上涨的海水撑起来了,四个老渔民跳上小船,船就像一条小鱼欢快地游进大海。老人把紧舵,血液好像一下子涌向大脑,亢奋不已。他大喊一声:“发——船!”那气势酷似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有风扬帆,无风摇橹。没有风也就不必上篷,古稀之年的四位老人划着小船,晃晃悠悠向前行。蓝天下,三两只海鸥时而戏水,时而滑翔,轻盈地飞在小船左右。海水舔着船舷,殷勤地匍匐在船下。老人们摇橹的摇橹,掌舵的掌舵,每一张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老人们陶醉在无垠的大海里,兴奋中喊起了岚山号子,铿锵有力的音调把他们带回到年轻岁月。肥家庄海滩到小庄码头不足3海里的距离,他们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码头不远处的桃花岛,像一处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被海水包裹着。码头上有川流不息的游客等着坐游艇去桃花岛。在海里撒着欢的游艇跑得飞快,时不时掀起大涌,推动小钓钩船起起伏伏,像是在浪里荡秋千,惹得游人们发出一阵阵欢呼,老人们也乐在其中。
为了庆祝小钓钩船第一次出海成功,难得相聚的四位老人喝了一顿庆功酒,他们把酒言欢,诉说着快乐與激动的心情。
七
夏天的海看起来温柔,实则变化多端诡谲得很。一天,管理人员喊起大喇叭,告知渔民们近期会有暴风,让周边所有停泊的船,转移到避风港避风。机器船都陆续开走了,老人也只能让小钓钩船离开。
“这艘小钓钩船多么像我的孩子啊,我必须好生待它。”老人脸上流露出无限爱意。我感觉,在他的世界里除了船没有什么了。
北起任家台,南至奎山以南的臧家荒沿海,岛屿少而礁石多,藏在海里的暗礁更多。从小庄码头到张家台距离不算远,但近海处,时有海流子。
海流子是海底暗流,暗流湍急埋伏很深,无法想象平静海水下的真面目。人在近海游泳时,遇到海流子是非常危险的,海流会把人推到大海深处,很少有人生还。小船遇到海流会随波逐流,单靠摇橹是掌握不好方向的。涨潮时,礁石和暗流藏在海里,老人摸不准此处的海况,不敢轻易冒险,只得寻来附近的老伙计,一起摇船到张家台。
两位老人像两个顽皮的孩子,他们甚至没有考虑到年龄和海里那些不确定的危险。快摇到张家台时,船变得沉重起来,无论老人们怎么努力都无法靠近岸边,船反而反方向飘向码头外的乱水泥墩子。凭着经验,老人感觉可能是遇上了海流。若撞向水泥墩子,这艘可怜的小钓钩船将成为一堆废木头。眼看着小船随海流飘往深海里,进深海能不能保命就看造化了。正恐慌时,有出海打鱼的机器船回来,他们扯开嗓子吆喝来机器船,帮忙把小钓钩船拖到避风港。一阵折腾,总算让小钓钩船挤在大船的夹缝里安顿下来。
避风港三面竖起高高的防风、防浪墙,船停在避风港是最安全的。只是防风墙太高,人没法直接上岸,必须跨过多艘并行的船,借助大船的高度,爬上从岸上垂下来的软梯到达岸上。谁能想到,老人有恐高症,哪怕只有两个台阶的高度都会让他腿肚子发软,面对两层半楼高直上直下的软梯,老人犯了难。这是唯一通向地面的路径,84岁高龄的老人只得拼上老命咬着牙,顺着摆动的软梯爬了上去,让那颗悬着的心安全落地。
八
泊在码头上的船,用锚固定在海里,时间久了,锚会陷在淤泥里,很结实。起锚的过程也是一个技术活,不会使巧劲的渔民,越用力拔,锚会越沉越拔不动。这个时候需要借助于海浪的力量,借助于船头的起伏,拽紧缆绳一点一点把锚翘起。
在张家台停靠的时候,小钓钩船并不是那么安生,时常会有人打来电话,让他的船赶紧回到小庄码头。老人答应着,算好了流水(潮水)。这一次出海他准备充分,有了独自驾驭的勇气,他不想再麻烦别人了。
若说前几次的摇船出海是老人小试身手,与大海久别重逢的前奏。那么接下来几次惊险经历,确实让人心生敬佩,刮目相看。
为了能避开海上作业的机器船和暗礁,老人尽量不在近海处驶船。对于这艘小木船来说,行在深海中无异于汪洋中的一片树叶,离岸边越远,涌会越高,自然会更危险。
眼看快摇到桃花岛,海面上起了东北风,风大浪高,小船好似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控制,最好的办法是抛锚下海,等风势稍减再做打算。
风并没有减弱,反而有越刮越大的劲头。在海里等,总归不是办法,不如顺着风向,张篷起锚。借着风力,老人迅速把锚拔起,就势张起半篷。小船没有了锚的束缚,又借助五六级的北风,快速向西南方向驶去。
小船随着浪涌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上来。影影绰绰的高楼大厦矮了下去,岸越来越远,老人有点恍惚了。这艘应由四五个人配合驾驶的小船,由老人独立驾驶,困难可想而知。老人目测已绕开太公岛暗礁,便拉紧缭开始往岸上靠。他望见万平口高耸的目标塔,看见了世帆赛基地的入海口,老人松了一口气。待船进入世帆赛基地后,海浪平静下来,老人也累瘫了。
九
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领先”的日照世帆赛基地,是“国际水上运动基地,这里波平浪小,环境优美,是日照一张靓丽的名片。小钓钩船在这里享受了几天贵族级别的待遇。倘若允许长期停放,这便是小船最好的归宿。
游艇往来,帆船出没。寒酸的小钓钩船如同流浪的孩子,显得非常不协调。况且没有“户口”,更不便在此久留。老人沉思数日,扬帆起锚,驾小船离开这舒适的“安乐窝”。
老人轻舟熟路,轻松自如,张篷摇橹,顺着风向一路往北。老人兴奋啊,他觉得此生唯有摇着撸,驾着船,享受着海天一色、人船合一的乐趣,才是人生最高境界。
海是不讲情面的,它从来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温柔。上一秒还在微笑着绅士般地托举你的身体,下一秒就翻开肚皮给你点颜色看看。
老人惬意地摇着橹,沉浸在无垠的大海中,完全忘记大海的另一张面孔。眼看着快到桃花岛,船不知不觉进了礁石滩,锋利的礁石划得船底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舵揽子扯断了。
突如其来的意外就此降临。西北风乍起,刮起数米巨浪,100多斤重的舵盘梁被海浪掀起来砸碎了。眼看着篷像断了线的风筝,转着圈吹到了大桅顶。老人不顾危险,迅速把大篷撕扯下来。船失去方向,一个劲往深海里飘去。老人急忙抓住锚,用力把锚掀进海里。老人在讲述的过程中,急促地喘息着,我仿佛听到船被撕碎的脆响,看到篷被吹到桅杆上露出绛红色的神经。
“太阳还没完全沉下去,西北上空乌黑乌黑的云压在海面上,了不得了,上来阵头了(雷阵雨的前兆)。”老人心里嘀咕着,海里行船最可怕的事情被他遇上了。“我急忙把篷用绳索绑好压在船板上,又把另一只锚掀了下去,两只锚一前一后把船固定在海里。”
两个锚都抛了下海,仍然没有稳住上下颠簸的小钓钩船,风越来越大,随时都有被掀翻的危险,他屏住呼吸,将身子压在舢板上。“就这样等死吗?”老人对自己说。他深知自己战胜不了从天而降的灾难,内心有了少有的胆怯和绝望,他瑟缩着闭上了眼睛。
倾盆大雨与巨浪无缝衔接,而老人与船介于混沌间,渺小如豆。他想尽快找出救生衣穿在身上御寒,却眼看着橘黄色的救生衣被风从船的压板底下揪出来,吹到了船底,又被海浪从船底掏了出来,扯拉着飘远了。那一抹橘黄色,变成老人眼里的一条鱼游走了。
被锚固定的小船,发着脾气上下翻飞,企图挣脱锚的束缚。老人趴在颠簸的船上,有几次差点被掀到海里,他仿佛听到海浪狰狞的笑声,听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远远地呼喊他的乳名。
若被掀進海里,即刻会被巨浪卷进海底,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他在船上目睹了巨浪滔天,乌云翻滚,也明白人生如蜉蝣,朝不保夕。不知道过了多久,闹够了的风浪渐渐平息,雨也停止,老人幸免于难。
十
小钓钩船泊在桃花岛期间,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有人建议让船作为道具,为游人提供摄影素材,适当收点费用。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既能体现船的价值,又能让老人收收心安稳地过日子,何乐而不为呢。
小钓钩船本来就是来自大海的不速之客,在桃花岛没停多久,又被下了逐客令。老人只好在极短的时间里,把损坏的部位修好,看好风向拉起大篷头篷,摇着这艘命运多舛的小船,再次驶入大海。
进行了大修的船仿佛增加了无穷的动力,转眼到了灯塔。老人看见灯塔附近的礁石露在外面,这是“退半干子潮了”,老人自言自语:“靠进去会惹麻烦,弄不好还会撞毁了。”他没有停下,拽着舵继续向南,不多时驶进新建的海龙湾。
无法预见的遇见,代价往往是沉重而惨痛的。没有任何征兆,海上突起大风,起先是六七级,忽而飙升到了七八级,船就像瓢一样在海龙湾里滚动着,卷起的大浪像一头巨鲸,随时准备吞噬老人和船。老人使出浑身力量,眼里冒出火焰,与风浪较量着。他是无法与大海抗衡的,紧急之下,把着船沿趴在船上,把锚掀到了海里。
锚是船上不可或缺的主要部件,有了锚,船就有了主心骨,老人也就有了主心骨。眼看着日头西沉,周边无一船一人,海龙湾又是敞口子,少有船在这里停泊过夜。他没有时间坚持等待过路的大船来施救,在翻江倒海的水面上待一秒钟,就离死神近一秒。老人知道,与大海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他摸起手机打了110。
汹涌的大浪和呼啸的海风改变了海的颜色,老人虽然恐惧,但没有失去理智,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拨打求救电话,唯恐手机没电,索性关掉手机。半个小时殊死搏斗,半个小时奋力坚守,老人的体力与耐力明显下降,他抵不过风浪。老人心想,倘若这一日命丧大海,便是最好的归宿了。
半个小时后,三艘大船找到了老人。“手机打不通,他们以为我已经掉进大海的肚子里了,差一点放弃了寻找。”老人露出天真的模样,尴尬地笑了。
我不敢想象,假如在那一刻救援电话打不通,或者救援人员放弃了寻找,我还能有机会和老人面对面地聊天吗?
救生艇要求老人弃小船上大船,老人的固执劲儿上来了,他说人上了大船,小船撂在海里就没命了。大船只好用缆绳拖着小船驶入世帆赛基地。“唉,命不该绝啊!”老人心有余悸,对我讪讪地笑了,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晶莹的泪光。
老人孤身一人,摇着小钓钩船在汹涌的大海中与暴风对峙了八九个小时,危及生命之时也不肯放弃那艘小船,这位80多岁老人刷新了人体能承受的极限,完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壮举。
十一
经过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场面,老人终于下定决心为小船做点什么了。
他专门联系了摄像师,花钱雇了游艇,把他摇橹的过程拍成完整的视频,为这艘陪他冲风破浪的小船留下最后的记忆。
那天,大海出现少有的温柔,波浪有节奏地起起伏伏,海鸥像是接到邀约,成群结队往来其间。摄像师坐在豪华的游艇上,老人跳上寒酸的小钓钩船,一道美丽的风景在碧波荡漾的大海里出现了。
老人把橹柄挂在橹绳上,橹桨伸进水里“哗啦哗啦”欢唱。老人摇着橹,水中的橹板像鱼儿摆尾一样,左右摆动拨着水。船身略侧,如同一只轻灵的燕子。老人摇着橹一推、一板,海面绽开了一朵朵白莲花。镜头下,船慢慢摇进幽幽的大海里,老人升起来大篷、头篷。绛红色的篷布高高挂在桅杆上,被南风一吹就鼓起来,带着船驶向北方。
小钓钩船与老人数次探索大海,数次接受生死考验,都没能尽兴地展开大篷、头篷。这次老人要真正地扬帆起航,完成他与船之间最完美的拍档。
太阳隐去了所有光芒,星河还没布满天边,老人把船安放在平静的海滩,往船板上一躺,细碎的涛声在沉浮中渐渐远去。星光在上,波涛在下,他与船依偎在一起,一直躺到天明。
十二
老人对我说,早在秦始皇年间就有了这种小船,到民国时期非常普遍了,那个时候下海打鱼多靠这种小船。五十年前,沿海一带这样的小船一片一片的,一起张篷出海的场面很是壮观。后来,渔民在大海里摇橹非常不安全,摇橹船逐渐退出舞台。这些古老的旧船承载着渔业的历史,承载着一代人的期待与收获,它有一种沧桑的美。
老人虽然命硬,却十分孤独,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引起很多人反对。亲人们不但不理解他,还指责他,说他这么大年纪了,在家安度晚年多好。老人又怎么会安于现状呢,他有船,有大海,有蓝天,有心中的梦想,有眼中所有的热爱。在海里摇船冲浪,才是老人生活中最大的乐趣。老人命里是离不开船、离不开海的,他不会让自己就此消停。在那股执拗劲儿的驱使下,与船频频交流着感情,打破年龄的禁忌,与海一次次发生故事。
老人老了,小船也老了。老人和船完成拍摄的使命后,该为小钓钩船做个打算了。为了能让船亲近大海,还不会给他人造成麻烦, 小船的“养老院”就选择在了肥家庄海滩。肥家庄海滩虽不是避风港,但那里海岸线很长,海滩极为宽阔,最适合安置他的小船,落半潮的时候,他请吊工把船拉上海滩。
此后,这艘船无声地卧在沙滩上,成为道具,供游人游玩、娱乐、合影留念。没有人知道这艘船衍生出的很多故事都与一位老人有关。
这位极其普通的老人,走过平凡的少年、青年,有过一段辉煌的创业史,古稀之年开始学车,耄耋之年在海里冲浪,还梦想有朝一日划着小钓钩船驶入更深的大海,驶向更远的远方。
我没有劝阻他,也没有鼓励他。人在某一个地方留下足迹的时候,这个地方也会以某种方式记住他。老人叫安丰坤,是地地道道的渔民家的孩子。
这片蓝色的海域给了老人神秘的昭示、深厚的滋养。也许正是这种最单纯的蓝,才能孕育出最丰富多彩的故事。
若没有对海、对船的那份炽爱,他不会费尽心思,让那些没有血肉的生命体变得丰满而有灵性。安老伯不是富裕之人,但他有富裕的精神世界。他不够强大,但他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内心。他不想让那些古渔船被埋葬在岁月长河里。若干年后,这帧承载着船与老人的镜头会被人们铭记。
在一个微凉的雨后,我独自一人来到肥家庄海滩。
日光在海水中灿灿生光,浪花漫不经心地吻着沙滩,沙滩上印着波涛留下的水纹。
站在海边放眼远处,海尽头开裂着一条很长的缝隙,这条缝隙是海的彼岸,是天的尽头,它的两侧,是两个互不干涉的世界。
沙滩上有游人嬉戏,几艘破旧不堪的废弃的木船像一只只沉睡的怪兽四处散落。小钓钩船以非常标准的姿势卧在沙滩上,船的一头向着大海,另一头被缆绳拴着,牢牢地固定在沙土里,沉静安然。
我环顾四周,最想遇见那张熟悉的面孔,想从他那双忧郁温和的眼神里看到大海深处的吟唱。我依偎着船站了好久好久,直到海风吹湿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