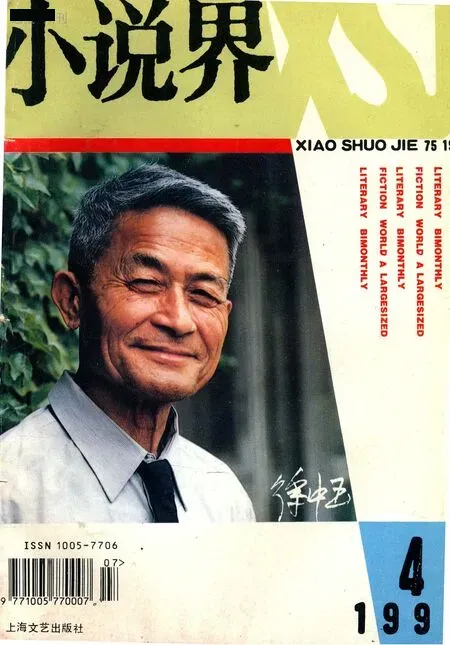高鸣:想潜到水底去看一看
2022-05-30蔡庆中
蔡庆中
电影《回南天》南京场放映结束后,轮到主创与观众互动,导演、编剧高鸣突然掏出手机,说就在刚才,又一次看了自己这部电影,忍不住在手机上写了一段话,想分享给大家——
“工作没有了,情感又厌倦了,我们的出口在哪里?我们不断地对外试探,互相伤害,它是真正的出口吗?因为自己情绪的下沉,对负面情绪敏感,很容易看到群体被困住的状态。我在想,人到底是被什么困住了?是被环境困住了,还是被彼此困住了,还是被自己的心魔困住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认真的人。专访中,他也拿出手机,点开备忘录,不时翻看朗读,看得出是认真做了准备。
《回南天》相当于我心里的一块砖头,必须把它搬掉
《回南天》是一个具有地域性的片名,用高鸣的话说,南方人听到这三个字“会有本能的体感”。回南天潮湿闷热,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笼罩着,渴望挣脱,但又挣脱不了,这也正是电影中四位主角的状态。
创作的初衷源于高鸣的个人经历:有段时间他患上轻微的抑郁症,“跟电影里梁龙饰演的龙老师状态挺像的,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不愿意去面对社会,不愿意去面对朋友,甚至不愿意去面对日常。”整日里无所事事,两眼放空,很想睡觉,但又无法睡着,一闭上眼睛就是电影般一幕一幕的幻象,“现在回忆起来仍旧感觉浑身都特别累。”
后来,他开始跑步。
有这样的情绪在,《回南天》注定了不是以叙事见长的电影,高鸣用碎片化的方式将四个人下沉的情感拼贴在一起,“甚至只有负面情感,没有正面”。电影中两男两女四位主角,被他设计成花朵的四个不同状态:“从含苞到开放,再到开过了,然后凋谢。”
除了跑步,有段时间高鸣为了缓解抑郁情绪就去钓鱼。在湖边,他忍不住幻想:“水底应该也是一座城市,对于鱼来说,它就是鱼的城市。”他说:“我特别想潜到水底去看一下,看水底世界是什么样。”
于是,高鸣想,在上帝的视角中,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大的湖泊,每个人都是游弋也是被困在其中的一尾鱼,“那些高楼大厦就相当于湖底我们看不见的岩洞。”有些钓鱼的人如果钓到不想要的小鱼,往往就把它们甩在湖边,“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觉得这些就是在城市打工被甩出来的人,而那些在湖里游得特别自在的鱼,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
关于鱼的这些思考和遐想,他也都用在了《回南天》里。电影中,鱼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和意象。主角家中的鲫鱼从水池跳到了地面上扑腾;女配放生金鱼,结果因为金鱼无法在湖水中生存,死去之后尸体浮出了水面……
《回南天》的剧本高鸣写了两年多,共十六稿。他需要将自己的心理情绪转为文本,再由文本转为影像,“其实非常困难,只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一步步接近自己冥冥之中想要的感觉。”好在,最终出来的影片状态他还是满意的。“其实《回南天》相当于我心里的一块砖头,我必须把它搬掉。否则,我觉得自己可能跨不过去。”
有人曾经问导演哈内克,他的电影暴力血腥,担不担心会把观众教坏?哈内克说:“只有看过电影里的残酷和暴力,你才知道生活的美好。”高鸣说:“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回南天》,你只有认知到了生活中的下沉,才知道你浮出水面以后的呼吸是多么宝贵。”
拍完电影后,高鸣说他至少现在不用跑步了。
小说,更有现实中的残酷性
《回南天》有一个特别奇幻却又令人感觉现实的结尾——
男主角曾经在舞台上饰演美猴王,但后来舞台被拆了,他一直希望它可以重建,让自己重上舞台,再现昔日风光,虽然现实残酷,但他心中美猴王的梦想从未泯灭。电影最后,他发现自己穿上了美猴王的戏装,浮游在城中村的半空,两边的人们吹着绚烂的肥皂泡……镜头一转,这一切都只是他的幻想,身后仍是那个破败的城中村,四下安寂,只有一个收破烂的人骑着单车自远及近穿行而过……
《西游记》是对高鸣影响很大的小说。他自小学习绘画,拍电影之前就已经是深圳当地小有名气的平面设计师,“我从小就建构起了特别图像化的思维,然后它给我造成了一个阅读指引,就是会对有想象力,或者说出其不意的作品特别感兴趣。”
他当年不但喜欢看《西游记》,画美猴王,收集所有关于孙悟空的连环画,“甚至尝试过自己重新画一套《西游记》的连环画。”
儿时的高鸣还会拿着《西游记》的书和电视剧进行对比。他发现,原来小说中唐僧的形象并没有电视里那样完美。比如有個情节,唐僧被抓,妖怪要吃他,唐僧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问孙悟空该怎么办?孙悟空说:“要我救你,那除非让我做师父你做徒弟。”唐僧回道:“我做你孙子都可以!”
“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一种影视剧的美化,而小说,更有现实中的残酷性。”
自《西游记》之后,高鸣就习惯于将原著小说和影视作品对照阅读。比如看了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想看一下王朔的《动物凶猛》;看了张艺谋的《活着》,也想看一下余华的原著;看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就会想看看李碧华原来那么短的小说,为什么能够通过芦苇老师的手改成这样一个鸿篇巨制。”
不过,最让高鸣触动的还是土耳其导演锡兰的《冬眠》,因为作家契诃夫的名字也在该片编剧之列。“我看了之后才知道电影是受契诃夫几部小说的影响,而不是单纯地改编他的作品,导演刻画出了契诃夫笔下那种中年知识分子的感觉。”高鸣因此大为惊叹,“锡兰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受作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又不是教条主义的,他有自己的东西,两者灵活运用,所以我很钦佩他。”
高鸣喜欢的另一个导演是胡波(笔名胡迁),他不但喜欢他的电影,还喜欢他写的小说。在高鸣看来,“胡波就是个天才!”
“他的处女作《小区》就很深刻。”高鸣还很喜欢胡波的《大裂》,甚至想过如果有机会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就改这一部。《大裂》写了一帮年轻人一起打架、互相伤害的故事,“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张藏宝图,说能挖出宝贝,于是一帮人就很认真地去挖。”高鸣很迷恋这种一群人特别认真地干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其实胡波小说的主题都是一致的,就是青春期荷尔蒙过剩,但你又觉得他不仅仅在描写青春,他是有一种高度在里面的。”
就像胡波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如果没有找大象这个意向,高鸣觉得电影就会减分很多——他很在意文艺作品中的意象和幻象,所以非常喜欢法国哲学家、《电影》的作者吉尔·德勒兹的名言:“电影,是将人们已然感知的幻象投影到银幕上。”
看100部书,不如拿出10部来看100遍
高鸣随身背一个很重的单肩包,采访中,他从包里掏出了三本书——他有随身带书的习惯,“不然没有安全感”,每晚睡前看一點,才能安心睡去,“否则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缺点什么。”
他看书很慢,“可能有点阅读障碍,很容易跑神”,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逼着自己读出来”,所以在家里,他经常和女儿一起给对方读书。
“阅读对于导演来说太重要了!”高鸣认为阅读文学是对人类的灌溉,导演的视野、眼界,甚至创作方法都可能被文学所开拓。“阅读可以改变,可以温暖,可以软化,可以让人变得有温度,可以让人变得平和……”
采访那天,他随身携带的那本书是雷蒙德·卡佛的《新手》。高鸣很喜欢卡佛,他无所谓大家给卡佛贴怎样的标签,极简主义也好,肮脏现实主义也好,在他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觉得卡佛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困境,以及两性关系,“还包括对于情感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这些对他都特别有触动。
《新手》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当年编辑戈登·利什将其中3篇小说的篇幅缩短了70%、10篇更改标题、14篇修改结尾,整体删改幅度超过50%,后以书名《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大获好评,奠定了卡佛的文学地位,但卡佛表示:“有朝一日,我必将这些短篇还以原貌,一字不减地重新出版。”这成了文学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高鸣说,他就将两本书放在一起对比阅读,“想看看以我的能力能不能看出它们两个孰高孰低。”
高鸣还有一个阅读认知就是:“看100部书,不如拿出10部来看100遍。”他觉得这样会比囫囵吞枣般追求阅读数量的收获大得多,“你能把加缪的《局外人》看50遍,契诃夫的《海鸥》《樱桃园》读50遍、100遍,我相信你的感受一定和看一遍是不一样的。”
最近,他就重读了川端康成的《雪国》。书中有一段是主人公去找艺伎,结果找到了一个乡下女孩,川端康成细致地描写了主人公对于找艺伎的期待,以及找到之后的反差,这令高鸣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次他拍完一部短片,制片人说附近有个温泉小镇,于是带全剧组去泡温泉放松,“结果发现温泉就是农家乐的后院挖了一个水泥池,连瓷砖都没有,你也不知道那个水到底是温泉水,还是农民家里烧的开水。”总之就是和大家想象中的美好完全不相干。接待的人说还有按摩服务,然后就来了一群中年阿姨,“穿的雨靴、裤子上都是泥巴,是刚下地干完活回来。”
“当我看到《雪国》中的情节,川端康成写得那样细腻,我为什么当时没想到要把这样的感受写下来?”他说,“其实有时候看到这些好作品,反过来就会特别自责。”
靠着语言在天空飞翔
很多人最初知道高鸣是因为他2005年拍摄的纪录片《排骨》——这也是他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排骨是个卖碟的青年,一边文艺,一边现实;一边向往都市,一边无法离开农村;一边渴望爱情,一边又不能把握爱情……很多观众都被排骨的故事吸引,纷纷打听他的下落。
高鸣后来也确实继续跟拍了他,片名都想好了,叫《五花》,“特别有意思的是,排骨年轻时期望的东西在中年的时候都有了,但年轻时有的东西中年时又都没了,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转,让他又开始找不到自己。”
这些年,高鸣积累了大概三百到四百小时的素材,“可以剪三部左右的纪录片。”其中有一部,他拍摄了一个流浪汉,“他给自己套了一个遥不可及的身份,还在这个身份中为自己编造了精彩的生活,而且描述得栩栩如生。”“中国独立纪录片第一人”吴文光导演看了素材后说:“当我们所有的人被生活击打得一塌糊涂,也许只能匍匐前进,只有他一个人靠着语言在天空飞翔。”
高鸣很喜欢这句话。他说自己是一个语言感知力很强的人。同时,“我自认对触觉、对空间、对人的感知也是很敏锐的。”于是他也开始了文学创作。
这两年,高鸣离开熟悉的深圳,去了陌生的北京。“在深圳总会有人因为各种事情来找我”,在北京,他可以安心写作,“目前大概写了7个短篇小说,5个剧本”,并且打算将《回南天》的剧本也改编为小说。
关于创作,高鸣说自己写东西就是写心里流淌出来的感觉。他的电脑里建了四个和写作有关的文件夹,分别是种子、小苗、长出枝桠、最后结果。“比方说我有了一个想法,就先写梗概,把它放到‘种子里发酵。然后,突然觉得它可以往前写的时候,我就放到‘小苗里,等到‘小苗开始长出东西了就到下一个文件夹……”
他的小说得到了作家毕亮的肯定,“其实我觉得自己的文字可能还是需要提升,但毕亮说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才是一个写作者的最高境界。”
在写新剧本时,制片人王磊推荐高鸣看美国作家、诺奖得主索尔·贝娄的《赫索格》。小说主角是个老教授,他的妻子出轨了他的朋友,他就郁闷地离开了。“然后他做了一个特别怪异的行为,每天给不同的人写信,但并不寄出去。”教授把信装在箱子里,提着到处走,最后回到了童年时的住所,拿到一把父亲留下来的枪,“他本来想去把老婆的情人杀掉,结果去到他俩生活的地方,在户外发现那个情人正特别认真地帮他的孩子洗澡,他就没有了杀他的勇气……”
让老教授写信的这一设计让高鸣非常喜欢,“给不同的人写信,然后写了不寄出去,我就觉得很有趣也很有想象力。”
说到想象力,高鸣不禁又聊起他拍的那部关于流浪汉的纪录片。
流浪汉对高鸣说自己住在满天星大酒店,但深圳并没有这个酒店。面对高鸣的质疑,流浪汉把他带到了大街上,说:“就是这里!”
高鸣一抬头,看到了满天星光。
他决定将这部纪录片命名为《满天星大酒店》。
( 感谢“后窗放映”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