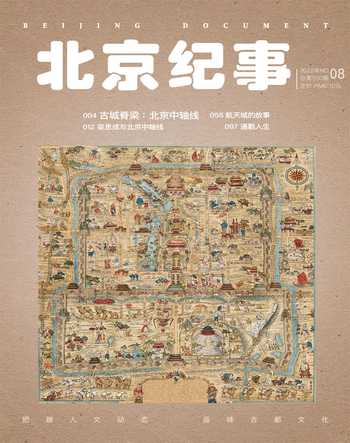在“思想之海”中从“痛苦”到幸福
2022-05-30张冲
张冲
1972年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1986)拍摄了波兰著名科幻作家、哲学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科幻小说《索拉里斯》(又译《飞向太空》),索拉里斯意为“思想之海”。电影故事讲述了心理学家克里斯在“索拉里斯学”陷入僵局时被苏联政府派往空间站,以便做出决定“要么停止研究,移除空间站,从而承认索拉里斯学的危机;要么采取极端措施,也许用大量射线轰炸索拉里斯海”。
老年宇航员伯顿反对苏联当局“毁灭人类无法理解的事物”这一“人类中心主义”行为,并前来游说克里斯,他不赞同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知识,认为知识只有在道德基础上才有效,这一观点契合了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的逻辑。
克里斯到达索拉里斯行星空间站后准备与控制论学家、天体生物学家及生物学家一起工作,却发现生物学家在抑郁、痛苦中自杀,另外两位科学家也满脸焦虑、痛苦与挣扎。随后,克里斯也陷入了“TO BE OR NOTE TO BE”(生存还是毁灭)的焦灼与痛苦之中,十年前自殺身亡的妻子哈丽出现在空间站里,甚至更深层次的恐惧与黑暗也出现——克里斯的妈妈也出现在空间站。这些死去的幽灵变成了由中微子构成的可见的具象化形象,哈丽是赛博朋克还是可知事物的可视化?而最令克里斯痛苦的是,哈丽通过他的大脑逐渐拥有了他们以及哈丽自己的回忆与记忆,并拥有了睡觉、饮水以及痛苦的情绪,这愈加使得克里斯的选择困难起来,是摧毁这个让他痛苦的“中微子哈丽”存在,还是保护她?这不但是爱情与罪愆问题,也涉及人类的诸多终极问题,人类与未知事物的关系、与“恶”的关系、与整个人类的关系。何去何从?塔可夫斯基从“痛苦”这一角度对其进行了俄罗斯式读解与阐释。
对“恶”的痛苦之思
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认为,“正是知识(关于善恶之别的知识)导致了人的堕落(原罪)。”这也是夏娃、亚当吃了“智慧之果”后有了辨别的能力,并肯定/否定某些事物的存在,会导致对真相的无视与误认。比如他们用树叶盖住身体遮羞这个动作,标志着建立起了“善恶道德”的价值判断谱系,破坏了“道法自然”的朴素与真实。
索拉里斯星的“思想之海”,它可以“从人类潜意识里‘读解出来的一些模型,分别代表着猥亵的诱惑、淫秽的欲望、被压抑的罪恶感等等,总之是所有折磨着人类心灵的东西”。
索拉里斯星可以理解与探索空间站里每个人的大脑,并将他们在地球上潜意识中的邪恶以及世俗生活中的罪愆以可见的方式再现,无法控制的欲望以及对至善的平衡,导致每个人陷入痛苦与恐惧之中,并从罪愆中反观人类灵魂的“崇高与诗意”,而这种“崇高与诗意”并非是理想化的,而是世俗的,如何面对它们则成了探讨“痛苦”的“存在意义”。
《索拉里斯》小说作者莱姆作为哲学家、控制论学家,他在给导演塔可夫斯基的信中认为,他的最初剧本应该“把宇宙演化的悲剧性冲突偷换成一种生物性的循环论的观念,把认知和伦理的矛盾降低成家庭争吵的小闹剧”。塔可夫斯基尊重了莱姆的意见,再次改回原著线索。
电影中空间站里每个人的原罪与恶都通过屏幕呈现出来,并且着意突出了克里斯对自己的无法掌控的恶或者阴影而感到的恐惧与绝望,他向斯纳特喊道“假如我突然想让她死呢?想让她消失呢?”因为这突然之“恶”的想法以潜意识的方式在默默践行,克里斯将标本从实验室带回来放在家里的冰箱内,并向妻子哈丽解释它们怎么起效。当他们陷入日常争吵时,妻子以死相要挟,克里斯也说了可怕的话,并暗示实验室标本可以致死,妻子如果想死就注射吧,然后一走了之。在恐惧与担忧三天之久后,克里斯才回到家,直觉预料到的事发生了,妻子果真注射实验室标本而死。
克里斯向中微子哈丽讲述了同妻子的这段世俗生活的日常经历:“我们吵了一架,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吵架很多,我收拾东西走了,她并没有直说,但是我明白,当你和一个人生活了很长时间,这些事情就不必要了,我确定只是些气话。”但为自己的罪责开脱说它们只是些“气话”,并不能解决自己的“痛苦”。

塔可夫斯基
在影片结尾他向“思想之海”岛屿上的父亲跪下行忏悔之举,恰如那些属于俄罗斯文学的因素:“忏悔、自我牺牲与寻神”。哈丽在空间站里人类文化博物般的阅读室内,同克里斯一起观看勃鲁盖尔的《打猎归来》《谷物的丰收》,克里斯的篝火录像带、贝多芬的面具、苏格拉底的半身像、米洛的维纳斯雕像、《堂吉诃德》等书籍及当代装置艺术等,经历与习得地球上的时间记忆与空间概念,逐渐成为“哈丽”,但是遭遇到了“我不是哈丽我是谁?”“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痛苦问题,哈丽该怎么面对这些终极问题?塔可夫斯基用“往哪里去”作为情节设置来回答此问题,并完成了中微子哈丽的精神性存在与幸福,甚至也影响了克里斯的幸福,犹如那道强烈的光的力量和隐喻。
良药苦口:“痛苦”作为医治“痛苦”的药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推崇的俄罗斯天才的最大优点是“对全世界的敏感关注”,这也是塔可夫斯基电影具有的特点,电影《索拉里斯》中哈丽说“你们人类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争吵”,说话时的哈丽的背景是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画作《巴别塔》等,揭示出了人类为了追求所谓的观点自由,各抒己见,但真正的自由、至善只有一个真相,人类被太多的画面、声音与讯息窒息,无法认清本质,陷入“无辜者受苦,有罪者受罚”的痛苦与庸常之恶之中而不自知。

《心灵奇旅》剧照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始终关注崇高的“人类生命意义”,在电影《乡愁》的开始,他借教堂司事之口进行了表述:“人人都追求快乐,可是有些东西比快乐更重要。”
“比快乐更重要”的内容塔可夫斯基没有直接进行陈述,而是通过给小女孩安吉拉讲“泥塘”故事间接地暗示了“比快乐更重要的东西”的内涵,在故事中他用“泥塘”来比喻人的“苦难”或“痛苦”,这一象征意义可与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起来,他曾坦言唯恐自己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或“痛苦”,因为后者是他培育“救赎”的土壤,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白痴”般、圣愚式的“牺牲”是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认知与选择。
塔可夫斯基认为:“人类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和我们心灵中的邪恶争斗,而我们日常生活样态以及一般顺应俗世的压力,都是使我们极易选中的堕落之道。”具有赛博朋克科幻电影之称的《骇客帝国》(1999,沃卓斯基兄弟)中的AI电脑人评价人类时说:人类的“第一个母体被设计成没有痛苦的世界,当时每个人都很快乐,结果一塌糊涂。没人习惯这种生活,整批人都死亡了,所以母體才要经过重新设计,因为人类是透过痛苦和苦难来面对真实的”。关于这一点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索拉里斯》及其他电影中也可以看到此种论述,如斯纳特说:“当一个人高兴的时候,生命的意义和其他永恒的主题很少引起他的兴趣。”克里斯说,在妻子哈丽自杀后的十年里,只有当自己不高兴的时候,就会想起妻子,妻子以及对妻子的罪愆是他触摸到了“真实界”的存在以及思忖自己存在的意义。
塔可夫斯基的另外一部电影《乡愁》,里面的农奴音乐家索诺夫斯基明明知道自己回俄国还要继续做农奴,但他还是放弃了在意大利作为著名音乐家名利的东西,回到了俄国,在痛苦中生活。农奴音乐家的情况如1969年索尔仁尼琴的遭遇相似,当时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协开除,瑞典文学家建议他移居瑞典并给他提供别墅。塔可夫斯基如是评价说:“他不会那么做。如果他走了,他将无颜面对自己的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在禁区里受难,而他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仗义执言的人,却躲进别墅,这他做不到。”
农奴音乐家也好、索尔仁尼琴也好,他们犹如卡夫卡在小说《饥饿艺术家》中所说:“伟大的艺术是一种牺牲,也不可能得到世人的真正理解。艺术家要想衣食无优,甚至享尽荣华富贵,就应当改行做别的事情。卡夫卡生活的年代,艺术家是独立而匮乏的,常常要忍受孤独和穷困的处境。”因为他们知道“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农奴音乐家、索尔仁尼琴、饥饿艺术家、地下室人以及《索拉里斯》电影中的克里斯及中微子哈丽,他们是终极英雄:他们以“痛苦”医治“痛苦”,并给世人带来信念与希望,给自己带来自由与永恒幸福。
“认识你自己”后的幸福
塔可夫斯基认为:“艺术的存在不仅因为它反映现实。它还应当使人有能力面对生活,使他在令人窒息的生活重压面前有力量去抗争。”电影《索拉里斯》中在父亲家及空间站都放置了苏格拉底的半胸像,并把他的理念引入到电影中,如“知识即美德”及“认识你自己”。前者如电影中年轻的伯顿“并不赞同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知识”,他认为“知识只有在道德基础上才有效”,否则广岛原子弹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及各种生化工厂爆炸事件将导致世界毁灭,亦即末日来临。而后者则表现在了哈丽“我是谁”“从哪里来”等的提问上。因为人类世俗化的“有用的精明的知识”,使得“我们失去了对宇宙的感觉,古代人完美地理解它,因为他们从没有问过为什么或什么目的”。这一句话既有“FAITH”毫不犹疑的含义,也折射了古代人“主人道德”的特质:质朴、真实而勇敢等。
塔可夫斯基说他最爱的诗人是普希金,他自己也自认为犹如诗人一样在使用电影表达一种预见性,恰如普希金在1826年的诗中写道的:“起来吧,先知!你要看,你要听,去执行我的意志吧,走遍陆地海洋,用言语点燃人心。”电影《索拉里斯》从忧心忡忡的克里斯入手,谈及西西弗斯,有关涉痛苦,但并没有止于痛苦,而是在为人类寻找答案——“永恒的快乐”或幸福的西西弗斯。电影以克里斯说“我很幸福”这样的表述来结尾,既呈现了“局外人”式的清醒认知与胜利,也呈现了他跪下忏悔真正情感的复苏与认识“反者道之动”的狂喜与喜悦。
《索拉里斯》中妻子哈丽与丈夫克里斯陷入日常琐事的争执,妻子在负面非理性情绪的驱使下进行了“自杀”这种极端行为的选择。《索拉里斯》中天体生物学家萨托雷斯从物理学的角度认识世界的本质与人的真相,并向克里斯解释了“原子”与“中微子”的区别,他说:“我们由原子构成,而他们(指空间站中的哈丽等‘幽灵‘灵魂或不可见的潜意识幻象)是由中微子构成的。”控制论学家斯纳特在回应这一问题时说,是索拉里斯海用其他方式回应了人类的强射线,探测人类的思想,并提取出他们的记忆岛,将他们脑海中的记忆、幻想等印象具体化。对“幽灵”或不可见的“灵魂”的具体化呈现,使得人的存在及“我是谁”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微妙与复杂,这也是塔可夫斯基电影不朽的地方——呈现了人类不可穷尽的样式与属性。犹如《索拉里斯》电影剧本开始的描述是“水下漂动着的长长的水草,平缓的水面上漂浮着零落的树叶,一个橙黄色的蚌迅速地沉入河底”,电影开始的画面如实地刻画了绵延般的万物生长,屏幕上的图像带出了经验与超验的气息,卓越超群,令人沉醉迷离。
写这篇文章时想到了朋友的一个提问:“西方所谓的‘国宝电影《拯救大兵瑞恩》(1998年)用六个人的命换一条命,值吗?”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它涉及了不同智慧类型对终极问题或者人的存在的不同看法。“值不值”这是一种带有世俗“功利”色彩的衡量标准,也是西方这类电影用尽全力试图超越的世俗人性标准。
从古希腊到当代,西方思想领域对“人的存在”一直有多重思考,如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提出的人之“感性”“理性”与“宗教性”三种存在,《拯救大兵瑞恩》就是完成了人从人性或理性向人的神性存在升华的过程,即完成了在西方文化体系中的人的存在认知,即人的二性中,向最高存在“神性”僭越与升华。同样在《索拉里斯》里中微子哈丽的“牺牲”也完成了这种“僭越”及“升华”,也使用了这种评价体系与认知体系,但它的诗意与“幸福”给观众带来的是更多无限绵延的体验,不仅仅是人类哲学与神学层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