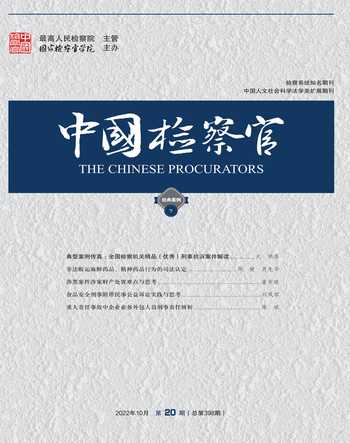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司法认定
2022-05-30周健肖先华
周健 肖先华
摘 要:我國毒品立法的双轨制导致毒品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概念上的混乱,两者在自然属性上并无差异,用途是否为“医疗目的”是区分两者的关键。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案件认定“医疗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注重客观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妨害药品管理罪后,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仍有适用非法经营罪的空间,需结合情理和法理,审慎定罪量刑。
关键词: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 毒品 医疗目的 非法经营
一、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争议
[基本案情]被告人王某长期在国外生活,她发现在当地药店可以买到一些国内购买不到的安眠类药品,于是便萌生了“代购”药品的念头。王某知道其“代购”的药品在国内属于管制类精神药品,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仍多次从国外批发精神类药品后邮寄到中国境内,并利用网络病友群贩卖给他人。2021年9月,王某陆续向国内邮寄了多包药品。公安机关根据线索查获王某邮寄的5个包裹,并在包裹内发现可疑片剂138.23克。经鉴定,可疑片剂检出了氟硝西泮、三唑仑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后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对于王某行为的性质,有观点认为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也有观点认为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还有观点构成非法经营罪,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争议较多。刑法第357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从字面看,所有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均是刑法意义上的毒品,如此,案例中认定王某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似无不当。然而,2015年《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武汉会议纪要》)规定,“行为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非法贩卖上述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据此,涉及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不能一概按照毒品犯罪处理。
二、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与毒品的关系
(一)毒品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概念辨析
毒品概念在国际公约中或者域外法律中较为少见,往往采用更为中性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管制物质”“管制毒品”“危险物质”等。[1]我国对毒品定义最早见于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后被1997年刑法吸纳。从刑法对毒品的定义看,采用列举加概括模式,毒品的属性可归纳为“国家管制性”和“成瘾性”(也称致瘾性),其外延理应小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而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概念起源于联合国《麻醉品单一公约》和《精神药物公约》。我国于1985年加入公约,此后颁布《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予以界定,“依赖性”“成瘾性”是共同特征。[2]2005年上述规定废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颁布,但未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进行定义,而是采用列举模式,同时将“滥用性”“社会危害性”作为药品列管的重要因素。[3]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概念演变看,“依赖性”或“成瘾性”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核心特征,“滥用性”“社会危害性”是纳入国家管制的关键因素。
简言之,“依赖性”“成瘾性”是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自然属性[4],也是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需要严格列管的根源;而“滥用性”“社会危害性”是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社会属性,滥用往往伴生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管制性”则是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法律属性,是追究法律责任的前提。[5]
(二)毒品的核心属性
既要充分重视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医疗价值,也要关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滥用带来的社会危害,限定其合理使用范畴,这是世界各国禁毒工作的共通要义。1997年刑法对毒品的定义并未将其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范围科学界分,也导致了实践中的适用困境。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以下简称《禁毒法》)对毒品的认定做了调整,提出“根据医疗、教学、科研的需要,依法可以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既契合禁毒的价值目标,也回应了科研教学医疗的需求。
因此,从《禁毒法》对毒品定义的调整看,毒品相较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其核心属性在于“违法目的性”。如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被用于合法目的,则不属于毒品的范畴,如用于非法目的,则应当适用刑法和《禁毒法》,以毒品违法犯罪追究责任。《武汉会议纪要》以“医疗目的”来区分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法律适用契合了《禁毒法》对毒品定义的调整。
案例中王某代购境外精神药品行为如何适用法律,关键要看其主观动机,是帮助购买者治疗疾病,还是其他非法用途。当然,主观动机和目的的认定不能单纯依靠口供,还需要结合其认知能力、行为手段等客观方面综合判断。而如何结合主客观证据准确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是认定此类犯罪的难点。
三、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目的”的认定
(一)“医疗目的”的内涵界定
“医疗”,顾名思义,是指医治疾病。行为人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目的繁杂,有缓解疼痛、治疗失眠、提神醒脑,还有减肥、助性等等。行为人经过医疗机构诊断患有癌症疼痛或者睡眠障碍等疾病而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或者将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贩卖给上述患者用于缓解疼痛或者失眠等,认定为“医疗目的”应无争议。但对于行为人使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用于减肥、助性等目的,能否认定为“医疗目的”则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上述目的并非将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替代传统毒品使用,而是利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兴奋或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药学功效,也应当认定为“医疗目的”。笔者认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能够替代传统毒品被滥用,其根源正是其兴奋或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功效,是否认定“医疗目的”仍要从合法的医疗需要出发,这也是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严格管制的题中之义,减肥、助性等功效只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自然属性的延伸,是药品“副作用”,而非被医学界所认可的合法用途(被医学界认可用于治疗肥胖症等疾病的除外),不宜认定为“医疗目的”。
此外,“醫疗目的”也仅限于经科学论证合理的诊治目的,一般应当经医疗机构诊断并建议使用,否则就会导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滥用。实践中,行为人往往辩解购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目的是用于治疗失眠、缓解疼痛等,但又无法提供有效的医疗就诊记录,司法机关应当如何甄别和准确认定?据统计,中国有45.4%的被调查者在过去一个月中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失眠。[6]失眠较为普遍,诊断的标准也较为主观,行为人未经医疗机构诊断而自行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安眠药服用的现象并不鲜见。因此,行为人如果基于缓解失眠、疼痛等医疗目的,虽未经医疗机构诊断,但经查实未超出医疗合理用量的,仍可认定为“医疗目的”,不宜作为违法犯罪处理,对于“医疗目的”的认定,要避免违背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
(二)“医疗目的”的证明标准
如前所述,对于实际使用者而言,认定其主观目的相对较为简单,但对于案件中的王某等销售者来说,“医疗目的”认定与否往往存在较大争议,这是司法实践的难点。有观点认为,针对用于“医疗目的”的“幽灵抗辩”,应当由行为人承担举证责任。尽管毒品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强,举证责任倒置可以减轻司法机关证明犯罪的难度,为打击犯罪提供便利。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无罪推定的应有之义,主观的事实推定是打击传统毒品犯罪的重要利器,相关司法解释也予以明确。
但在认定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中存在不少困境,譬如,行为人往往通过寄递渠道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但由于寄递实名制未能完全落实,行为人通常辩称为保护隐私未如实填写真实姓名和住址,如果简单地适用推定规则可能会与社会大众的认知相违背。另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不当使用除了行为人的因素以外,也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制度不完善的原因,简单定罪论处也有违情理。[7]
主观必见之于客观,网络现已成为毒品犯罪的主要渠道,非接触式交易也使得口供的指控效果大大降低,客观证据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要高度重视客观证据的收集和审查。譬如,行为人之间的通讯联络、短信、微信等聊天记录、邮件往来、支付宝、微信资金明细、快递记录等电子数据,已经成为指控毒品犯罪的利剑。再譬如,行为人的毛发、血液中麻静药物残留鉴定,医疗就诊记录、网络购物记录、购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数量和频次、网络搜索记录等。当然,电子数据的易删改也给司法人员的取证和审查带来困难,一方面要更加关注取证的程序规范,另一方面要借助科技的力量,有效恢复、固定电子数据。
案例中王某通过网络通讯群组向不特定主体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行为,是否认定出于“医疗目的”,要注重客观证据的收集和审查。要求行为人逐一核实购买者的身份和用途有点强人所难,简单地推定为放任的间接故意似乎也难以让人信服。客观证据的全面收集极其重要,譬如,行为人与购买者的聊天内容、行为人发布广告的渠道以及宣传内容、进货的渠道、成本价和销售价的对比等,必要时还需要抽样复核购买者的使用情况等。如果系在特定疾病“病友群”做宣传,向特定疾病患者及其家属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一般不宜认定为毒品犯罪;如果未核实购买者的实际用途,基于放任的故意,向不特定的人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则涉嫌毒品犯罪。案例中的王某向多人贩卖氟硝西泮、三唑仑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在认定其构成走私、贩卖毒品时需要查明其宣传的渠道,购买人群的身份和用途等情况。如果确系在特定病患者群体中贩卖的,则宜认定为出于“医疗目的”,不构成毒品犯罪。
四、以医疗为目的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行为性质
(一)非法经营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法律适用争议
案例中的王某如果出于医疗目的,在特定病友群体中贩卖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则不构成毒品犯罪,但能否追究非法经营的刑事责任,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设立妨害药品管理罪后也产生了较大争议。根据《武汉会议纪要》,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2014年11月,“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4年解释》)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未取得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非法经营药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明确规定“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品而销售的”,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由于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刑罚较轻,法定最高刑只有7年有期徒刑,而非法经营罪刑罚较重,法定最高刑15年有期徒刑。有观点认为,对同一行为不符合较轻之罪的构成要件却以较重之罪论处,这明显违反罪刑均衡原则。[8]2022年3月,“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22年解释》),删除了《2014年解释》中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让非法经营药品行为能否认定非法经营罪产生了更多争议。
(二)非法经营药品与妨害药品管理的辨析
不可否认,《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契合了2019年《药品管理法》的修订,假药和劣药回归本源(删除了拟制假药和劣药规定),重新建立起严厉打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法网。但能否认为非法经营罪无用武之地呢?妨害药品管理罪将“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进口药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药品而销售”纳入规制范围,与非法经营罪有密切的联系。
根据《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需要“双许可”,药品经营企业首先需要申请药品的生产、经营许可,其次生产特定的药品还需要得到药品监管部门的批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双许可”,并不能等同视之,前者是基于保障国家药品生产、经营的专营制度需要,后者是基于药品质量的监督管理需要。妨害药品管理罪并未完全涵盖违反药品管理秩序的所有行为,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未将违反药品专营许可制度的行为纳入管制。这并非《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疏漏,而是因为违反专营制度已有非法经营罪予以规制,无需在妨害药品管理罪中加以规定。保障国家药品管理秩序需要非法经营罪和妨害药品管理罪互为补充,才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譬如,行为人获得药品生产和经营许可,但未获得特定药品生产批准,可能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如行为人既无药品生产和经营许可,也无特定药品生产批准,则可能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和妨害药品管理罪,根据想象竞合一般原理,应当择一重处。因此,不能简单地以《2022年解释》删除了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否定非法经营罪在危害药品安全犯罪中的适用空间。[9]
对于有观点提出的可能导致罪责刑不适应难题,还是要从妨害药品管理罪与非法经营罪的关系入手解决。妨害药品管理罪侧重于规制违反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但其本质上仍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保护的法益相同,保护的是公众的健康与生命权益。[10] 由于妨害药品管理罪旨在保护公众的健康与生命权益,所以除了要求满足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的要件外,还需要满足“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入罪条件,《2022年解释》规定,“涉案药品在境外也未合法上市的”,才能认定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非法经营罪旨在保护国家专营、专卖制度,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方才动用刑法规范,以区分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譬如《2014年解释》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系“情节严重”[11]。由于妨害药品管理罪与非法经营罪的保护法益不同,尽管都需要具备行政违法的前置条件,但在追诉标准的设定上思路不同,前者强调必须具有危害公众健康和生命健康的危险,后者强调必须达到严重侵害市场经济秩序的状态。因此,单纯从法定刑的配置认为妨害药品管理罪轻于非法经营罪也有失偏颇。
(三)适用非法经营罪的限制
当然,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要兼顾情理和法律的平衡。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医学发展尚不发达,部分特定病、罕见病国内缺乏有效的药品,尚需要境外进口,但由于药品进口程序复杂,部分患者通过代购等方式购买进口药品入境的情形仍一定程度上存在,《药品管理法》第124条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案例中如果王某基于医疗目的,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仍进口药品并予以销售的行为,因进口的药品在境外已合法上市,没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风险,依法不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但如若非法经营数额巨大,仍有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的空间,只是量刑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医学医疗发展现状和社会大众客观需求,不能简单依据非法经营数额认定“情节特别严重”,如若非法经营不大,危害较小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200082]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助理[100726]
[1] 如美国《管制物质法案》、俄罗斯《联邦麻醉品和精神药物法》和我国香港地区《危险药物条例》等。
[2] 1987年《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麻醉药品是指连续使用后易产生身体依赖性、能成瘾癖的药品”; 第3条规定:“麻醉药品包括: 阿片类、可卡因类、大麻类、合成麻醉药类及卫生部指定的其他易成瘾癖的药品、药用原植物及其制剂”。《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精神药品是指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之兴奋或抑制,连续使用能产生依赖性的药品”。
[3]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本条例所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指列入麻醉药品目录、精神药品目录(以下称目录)的药品和其他物质。精神药品分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上市销售但尚未列入目录的药品和其他物质或者第二类精神药品发生滥用,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该药品和该物质列入目錄或者将该第二类精神药品调整为第一类精神药品”。
[4] “成瘾性”或 “依赖性”实际并无指代含义上的差别,“依赖”(dependence)相对中立,1964年世界卫生组织以“依赖”取代“成瘾”,动机即在于尽可能消除用语上的污名。当然医学上还有更为中立的用词,例如“物质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
[5] 譬如,“笑气”虽然被不少不法分子作为毒品的替代品使用,但由于我国尚未纳入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制目录,则不能以毒品犯罪追究责任。
[6] 援引自《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2017年)》。失眠的诊断标准:①失眠表现入睡困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②睡眠质量睡眠质量下降,睡眠维持障碍,整夜觉醒次数≥2次、早醒、睡眠质量下降;③总睡眠时间减少,通常少于6小时。
[7] 譬如,根据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调查分析,抽取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7200张,其中使用氯硝西泮的处方为1080张,超说明书用药处方为972张,超说明书使用率高达90.00%,超适应证用药占95.06%,超剂量用药占4.94%。
[8] 陈兴良:《妨害药品管理罪:从依附到独立》,《当代法学》2022年第1期。
[9] 刑法第124条之一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之罪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0] 参见敦宁:《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法教义学分析》,《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2期。
[11] 《2014年解释》失效,导致非法经营药品类非法经营犯罪的追诉标准不明确,但以非法经营数额以及违法所得数额作为“情节严重”评价因素的思路仍较为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