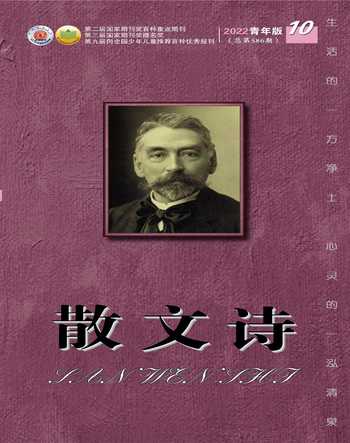阿什贝利晚期散文诗选
2022-05-30李海
李海 译
主持人:姚 风
主持人语:去年本栏目推介过诗人、译者少况翻译的阿什贝利的一组诗,本期推介的是由青年译者李海翻译的这位诗人的一组散文诗。散文诗是阿什贝利偏爱的写作形式,它更自由,更适合他所倡导的“自动联想”的写作实验。他的散文诗已不是我们阅读的传统散文诗,喜欢围绕一个中心意义而延展词语,而他喜欢打碎中心意义的镜子,让词语的碎片没有指向性地星落各处,在无意识的引导与瓦解中闪烁着迷狂的光亮。他在《水务督察员》说:“命运就是各种事情,不,它关涉各种事情。你明白我说的话吧?没有人需要全部真相。”而对诗人来说,词语就是他的命运,而“关涉”应该是他写作的一个关键词。
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1927-2017)生于纽约州罗切斯特。美国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65年前,在法国任《先驱论坛报》艺术评论员,后回纽约。1974年起在大学任教。后现代诗歌代表人物。其诗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
无家可归的心
当我想到作品就要完工,当我想到已完工的作品,巨大的悲哀裹袭了我,矛盾的是,这悲哀却似与喜悦无异。有所为的详情被收起来放好,随之入驻的是作品的存在,就像一个住在出租房的房客。无家可归的心,你在哪儿?被铰链卡住,还是藏匿在清水墙背后,像你那些无名的前任,既然他们已有了名字啦,最好别沉湎于我们的境遇,不过,栖居其中倒是极其令人精神焕发。像摆满了斟酒瓶和水果的餐柜。一如箱形风筝与风筝的关系。磕磕巴巴的内部。呼吸的路径。黑板上的漫画。
(选自《简单问题》2012年)
如果你说过你会跟我一起来
在城里,一切都非常城市化,但在乡下,奶牛布满山丘。云朵近在眼前而又非常湿润。当时,我正和安娜一起沿着人行道步行,欣赏着零散的风景。突然,一声低沉的钟声似的响声从背后传来。我们俩都转过身去看。“这是你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如今又回来纠缠你,”安娜解释说。“你知道的,情形一贯如此。”
我的确说过那些话。很多次,这种低沉的钟声一样的声调不请自来,闯入我的思绪,首先扰乱它们,接着,把它们重新排列得整整齐齐。“两只乌鸦,”那个声音似乎在说,“停在日晷的表面,在神赐的日光下。然后,其中一只飞走了。”
“是啊……然后呢?”我想这样问,但我沉默不语。我们拐进一个院子,走上几段楼梯来到屋顶,那里正在举行一场派对。“这是我的朋友汉斯。”安娜这样介绍道。在场的人都不甚在意,有几位客人走到栏杆那边,开始欣赏起果园和葡萄园临近秋天时的壮丽风光。不过,倒是有一位女士走过来对我们友好地打着招呼。我心想,这是不是一個“收获到家”①,一个我经常听人说起但从来都不能理解的说法。
“欢迎来到我家……嗯,我们的家,”那个女人喜气洋洋地说道,“正如你们所看见的,我们正在收获葡萄。”她似乎能读懂我的心思。“他们说今年的葡萄收成会很普通,但不管怎样,看上去挺迷人的。难道不是吗,这位……先生?”
“汉斯!”我唐突地插了一句。丰收在望,的确令人高兴,但我却想离开。我找了个借口,牵着安娜的胳膊肘往楼梯走去,接着就离开了。
“你可真没礼貌。”她不动声色地说。
“亲爱的,我受够了那些能看透你心思的人。若是我想的话,我会去找一个读心师。”
“我恰好就是读心师,我敢说,你此刻的想法是错误的。听一听那只大钟是怎么说的吧:‘我们都是自家地盘上、我们自己时代里的陌生人。你早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现在必须作出调整啦。”
赤胸朱顶雀
它穿过马路,以避免和我打招呼。“可怜的家伙,但我自个儿也是,”我说道,“要是没有一首歌,日子永不会结束。”②小家伙警惕地靠近。我如此同情它的愚笨,以至于硕大的泪珠开始从眼眶里涌出,噼啪一声,落到坚硬的地上。“我不需要这样的欢迎,”它说道,“我早就等着你呢。所有瓢虫、嗡嗡叫的苍蝇及短吻鳄都知道你跟你那套把戏。可怜又卑鄙的家伙。走开,带着你的歌走开。”
夜晚早已降临,而我一点都没察觉。我肯定在那里站了好几个钟头,瞎琢磨着,前思后想,该怎样对这个不幸的家伙作出回应。一个泥瓦匠仍站在一架梯子顶上,借着月光在屋顶那儿修瓦。但天上没有月亮。然而,我能看到他的腋窝,那里腋毛横生,也能看到他的手艺,他一心想靠手艺把那面墙修补好。
博宾斯基兄弟
“她的名字叫莉兹,我的生意靠她润滋。”我肆无忌惮地哼唱着。一群朝同一方向倾斜的白云飘过发际线处的地平线,就像一大群成人和小孩,一起赶往某个未知目的地。一声清脆的猛击声。对你妈妈做了什么?现在是不是……?这么说你知道这回事,她……我。一旦你通过了道德说教这一关,一道新的冬日暮光就悄悄潜入进来。有许多家伙刚好从中幸存下来?硬化的汤盘,用榫眼接合的单桅帆船。伍迪有一根无所用的拐棍。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是那样想的。我们像两个音符一样滑开,远离对方的防护性嫉妒。那只正在晒太阳的老猫对此无异议。同样无异议的,是那些满载精灵的半透明火车,它们从某个天空垂落下来,表明他们哪里都没去过,尤其是那里。当时,我们觉得这一切挺好笑。但它的确令人伤心。至今还是。我就是那样想的,他给了我一记耳光。
葡萄收获季节③
十五区的一栋高楼逐渐淡出,然后,彻底消失不见。将近十一月了,天气变得异常寒冷。没人知道其原因,甚至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我忘了告诉你,你的帽子看起来很神气。
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睡眠方式。老年公民多管闲事,非要强制推行这种睡眠。你醒来,感觉精神焕发,但某样变化已经发生。或许是孩子们唱歌唱得太多了。索菲真不该带他们去听音乐会的。我当时就恳求她别那样,但徒劳无功。而且,整个院子都被他们占了。其他人没准想用一下院子呢,或者想把它清空。某个晚上,所有的椅子坐满了人。
而我面色苍白,坐立不安。演员们和我一道向那些小木屋走去。我知道某个人想夺去或摧毁我毕生的成就,或发明。但某种东西敦促我保持冷静。
偶尔会有一个朋友离开,是的。已婚男士,糊口度日嘛。我前去看展览。我们回来之后,听了一些唱片。奇怪,我之前竟没有注意到岩浆在喷发。但它就在那儿,她说道,每晚都在喷涌,像一条河。我猜,我的观察能力大不如前了。
那时我还很年轻。
而它是那么的随心所欲,就像羊毛梳子梳出来的羊毛。你没法做到时刻保持警惕,她说道。你必须一直这样,开放而脆弱。像一个体腔。然后,假如有人注意到你,也来不及拿锉刀把设计师裤子锉光滑了。正如你说的,我们必须保持联系。不要被人注意到。好像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干这事似的,我低声咕哝了一句。整整一个月,我在这儿都干了些什么呢?等待那个修理工,要我说。
当最后的小水滴一滴滴落下时,你在哪儿?正把吊袜带往连袜裤上系呢。整个事情结束了,快得你来不及喊一声“杰克·罗宾逊”④,而我们又回到了大本营,小事一桩接一桩出错,但总的说来,生活充满了灵性。然而,该是拔掉篱笆桩的时候了。我们很可能会在路上遇到一个戴兜帽的陌生人,他会为我们指点方向,而这也算不错了,哪怕无聊,也是一种有趣的无聊。
我記得满世界的樱花仰望着太阳并纳闷,我究竟做了什么,要落得这般或那般下场?
水务督察员
扰乱那些“信徒”按钮。让那些鸡噤声。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比如情报。我们一辈子说了那么多残忍的话,可还是——在娱乐场所,年轻的我犯迷糊。命运就是各种事情,不,它关涉各种事情。你明白我说的话吧?没有人需要全部真相。
尽管如此,我们强求重复。节拍持续不断。对这份报告,对你父亲的过世,我感到非常震惊,但这类事情在所难免。死者往往第二天才被发现,活着但惊魂未定,想知道自己究竟碰上了什么事,在地下室的门下面直哆嗦。而我们同样纳闷,不知怎么搞的,我们熟悉的天空这会儿裂成了两半。鸣叫的甲壳虫为我们演奏小夜曲。大地和大地上的喷泉对我们关怀备至,但我们记得,也很震惊,像从前那样。
我们正在看书,突然传来一声敲门声。水务督察员,我们心想,但当然喽,外面一个人都没有。被刺痛,又一次被刺痛。于是我们继续,总是在行程中,总是恳求群星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我们是否真的清白,是否走在正轨上。而寂静永远在说是的,你现在可以回家了,聚拢你的伙伴们,朝最近的林木茂盛之地进发,如果你觉得这有帮助的话。
我一度很诧异,但又躺下来沉思,我的生命如今已在我的背后,我的话语就像远处湖上的水草。它必定已经来到我身边,它总是如此,我意义深远的事业的一部分。
我在智库中思考,我的思考总是那么优雅,在遥远的地方。远离我考虑的事物。在上升途中,曾充满恩典。不好对付,是的,还很令人困惑。
实录电影
要好心对待你那些长有蹼足的朋友,我带着点焦虑喃喃自语,一边急匆匆赶往电影院。毕竟,一只鸭子或许就是某人的叔叔。或侄女。我迷路了。我向一位长着马脸的警察问路,得到一个不令人满意的答复。真是这样吗?“就在那边某个地方……你一定能找到的。”他提议说。我想把他那一副沾沾自喜的表情从他脸上抹掉。又或者那是一种善意的天使般的笑容?我沿着自以为是正确的路线继续赶路,来到一处芳草萋萋的海滨度假胜地,草丛深处,整洁时髦的新宾馆当中坐落着几家锈迹斑斑的旧宾馆。一个红黄相间的巨大塑料牌上写着“电影院”。
那些石头具有一种玄武岩的颜色。这里我以前来过一次。从清风急匆匆刮过的样子,我就知道了,此刻,它正轻拍着我的脸颊。哦,神圣的清风!你是我唯一想遇到的事物,这个岁月的混凝土峡谷中唯一重要之物,那么,我为什么不能靠近你呢?你已逃之夭夭了,顺带卷走了我带到电影院,本打算迟一点当晚餐吃的鸡肉。现在,我将饿着肚子,为了你,也为了他们,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讲述我的冒险故事,在外面那滑溜的大理石梯级之上。又或者在一个满屋子都是人的房间?
(以上6首选自《留名在此》2000年)
注:①harvest home,(最后一批庄稼)收割入仓;收获节;收获节祝宴。②这句话是弗兰克·辛纳特拉经典老歌《要是没有一首歌》当中的歌词。③Vendanges法语,葡萄收获季节,或收获的葡萄。④这是一个过时的英语成语,可翻译成:转瞬间;一刹那;说时迟,那时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