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伙伴计划
2022-05-30格林EVRICKA
格林(周芳) EVRICKA(叶梓颐)



周芳纪录片《水下中国》 导演。历时数年,带领团队走访中国 24 座城市,首次完整地拍摄和记录下被封存水下的中华文明,呈现独一无二的水下中国 。
周芳:奔流入海
周芳可以被轻易贴上很多标签:追鲨鱼的水下导演、放弃百万年薪的“ 叛逆”女博士、单亲妈妈……如实,也不尽然。撕掉标签,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中脱离,生命是自由而无畏的。
上个月,周芳刚回北京,脖子上有一圈浅红色印记,水母的蜇伤。
但她没提,说起水母时反倒是另一个场景:“有一天晚上,我记得快两点了,我跟潜伴在海底拍带鱼,突然发现有一个这么大这么大的水母。”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在眼前画出一个巨大的圆,“一米五的‘冠(水母的伞状体),从我旁边呼呼游过来。好漂亮,那时候感觉像遇到外星人,突然闯到你眼前。”
起初她以为是狮鬃水母,一种巨型且性情凶猛的水母。后来回看影像,才发现不是,那是一种体型更加巨大的越前水母,部分个体可达两至三米,重量可达220公斤。对这些周芳如数家珍。
拆开盲盒
6年前她从投行辞职,成为纪录片导演。先是满世界拍摄鲨鱼,又在与前辈交谈中意识到一直被自己和周围人忽略的领域—中国的水下故事。于是自组团队,花3年时间走访24个城镇,录制超过7万GB的素材,最终制作成6集纪录片《水下中国》:从广西水下洞穴到千岛湖水下古城,从台湾兰屿“堡垒号”沉船再到蜈支洲岛龙宫般的珊瑚,幽深绚丽,也填补了国内同类纪录片的短缺。
结束之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二季的拍摄,将视角从人文转向自然和生物,以6种濒危生物为线索,串联它们栖息、迁徙、繁殖的水域故事。重回自然,这是周芳从第一季开始就想做的事情。
但在国内,成熟的潜水点不多,许多水域不一定有详细资料。周芳和团队的起步如同盲人摸象,“你知道整个要探索的区域很大,但又不知道它每一个部分长什么样,真的是要自己一步步摸,摸到耳朵,你才知道耳朵长这样,摸到鼻子,知道鼻子长这样。”第一年他们收获寥寥。在广西走访20多个人迹罕至的地下河洞穴,“有些地方花了很长时间拍,最后发现它们只是一个景观,没有故事,也没有关联的人或者生物,没法做一个故事完整展现出来,就觉得特别特别可惜。但那时候有一点点不服输的心态在,所以从没有想过认输不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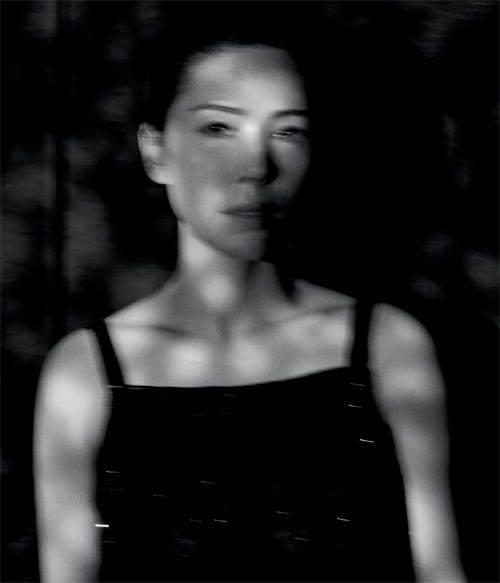
吊带亮片装饰连衣裙 Giorgio Armani
彼时,周芳和团队手中唯一的线索是一段文字资料,讲述一个法国人在广西洞穴河中看到过盲鱼。当她和潜伴Rachel终于在洞穴中发现一只浑身透明的盲虾时,她兴奋得跟着它一路游进侧洞,回过神来已经偏离牵引绳。如果在氧气耗尽前找不到回水面的路,她将很难生还,更糟糕的是,洞穴里淤积了大量沙尘,稍踢动两只脚蹼,周围就混浊得几乎无法看清,“这回是潜进了棺材里。”周芳心想。还好她很快摸到了侧洞的尽头,原路返回,从主洞穴游回水面,出水的那一刻周芳和Rachel大呼:“我们拍到盲虾了!”好像上一秒鬼门关那一遭根本不是她俩经历的。
然后,她们继续潜入水底,等待,寻找。
拍摄自然纪录片,或者说进入大自然,对周芳来说就像拆盲盒。“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也期待能够像打开哆啦A梦的口袋一样,结果呢,有时候会比哆啦A梦的口袋更惊喜,有时候可能什么也没有。”
对于探索,她乐此不疲。今年8月,周芳和团队一同前往浙江舟山,拍摄渔汛期的带鱼风暴。夜晚在海底,微弱的灯光只能维持两米左右的能见度,还总是只有三四条带鱼在镜头周围撞来撞去。周芳就是在那里遇到了那只巨大的越前水母。
“风暴没有来,来了外星人。”

丝质连衣裙 Loro Piana 金属耳环 Bottega Veneta
离经叛道,或是顺其自然
“我现在想当时的自己,应该用四个字概括,”周芳說着说着自己先笑起来,“离经叛道。”
她所说的,是1999年的事。那时她从法律系毕业,被分配至湖南省公安厅。父母觉得那是十分适合她的工作,性格颇像男孩的女儿既和想象中的公安气质相符,又能体面地穿上制服。但周芳把派遣证扔了,没回去报到,也三个月没和父亲说话。
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周芳想起来:“那个时候有一点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我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方向。”然后她得到机会进入外企,又考托福,两年后到俄克拉何马大学就读MBA。
MBA班的同学都是事业有所成的企业家,一众人里,周芳资历最浅。但那段经历带来了一个重要经验—每个人都需要通过一件件事情,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来验证自己的能力。毕业时周芳是班里唯一一个拿到荣誉学位(honor degree)的学生,那意味着她的每门课都拿到A以上。“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不怕起点低,也不怕不如别人,但认定的事情,一定要努力去做成。提升自己的信心,这个是最重要的。”
毕业后,周芳便进入投行。至今仍保留在她身上的干练、严谨,这和十多年的投行工作多少有关。
如果不是父亲的病,周芳也许还在美国生活。2007年,父亲查出肝癌,医生说还有3到6个月时间。“以前我觉得可以任性,是因为父亲在那,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家里半边天塌下来也有人顶着,但是他倒下之后,你就突然发现你是唯一要支撑家庭的人。”第二年,周芳回国照顾父亲,到处求医问药。
怀揣希望是一件令人兴奋又疲惫的事。很多年后周芳有机会拍摄中华鲟,看到最后一条被救助的野外中华鲟在北京海洋馆孤独地生活,因为宜昌附近的水域已经不再有洄游的同类产卵。连续三年,无人机在水下来来回回,总是一无所获。
“我们做选题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濒危的,但是我们不断地跟着去调研,其实还是心存希望,希望能够有奇迹出现,希望有更多的存活体。”她又讲到父亲的病,“就像说中华鲟的事情是一样的,医生跟你说还剩下3到6个月的时候,你总觉得没准会有奇迹是吧?我去找新研发出来的药品也好,找所谓的江湖郎中也好,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其实你都是想改写命运,就觉得我不相信他只有这么一点儿时间了。”
她和丈夫甚至决定在事業打拼期要个孩子,也许新的希望可以让父亲久留一会儿。最后,病中的父亲陪伴了她整个怀孕和生子的过程,直到女儿满月,父亲才离开他们,距离确诊过去了一年半。然后她决定留下来照顾母亲,把母亲接到北京定居,她继续读博,重新进入投行。
工作之余,周芳就带着母亲和女儿出去度假。2012年春节,她们去澳大利亚大堡礁,出海的船上有潜水项目,周芳就尝试了一下。“潜导也不管我,我就自己游。但那一刻我才真的知道,哇,原来你只需要轻轻迈出一步,跃到海平面之下,你就可以比别人多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妙。”也是在那一年,她在美国塞班岛的PAUPAU BEACH第一次遇到了鲨鱼,后来她给自己取的微博名就叫“追鲨鱼的PAUPAU”。
周芳喜欢鲨鱼,因为它们与人类想象的残暴嗜血不同,它们聪明又无害。还有另一个原因,她也希望自己像鲨鱼一样强大。
发现水下世界后,周芳常常去潜水,慢慢地也想把看到的记录下来。2015年,她选择辞职,纵身入海。“如果要说是人生的转折点,它算是。但又不是突变,它是一个顺其自然和水到渠成的过程。埋在我心里的一个种子遇到了合适的土壤,然后开始慢慢生长,直到有能力破土而出,而我也愿意顺应它的生长。”
探索,继续探索
在海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水温降低?压强增高?还是重力失衡?周芳一直无法确切描述。
直到看了纪录片《雪豹女王》,她和导演玛丽· 阿米盖产生了强烈的通感。玛丽· 阿米盖在纪录片里说,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由于信息复杂且充满干扰,人的感官大部分时间是收拢的。而到了大自然里,会发现所有的感官都不够用—即便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开,眼睛和耳朵仍然不够用,在城市变得迟钝和麻木的神经会变得极度敏锐。“我们虽然是在不同的区域探索,但切身的感受十分相似,我在海里也是这样的感觉。”
迄今为止,周芳的足迹已经遍布了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但走过的地方越多,越发现“未及之地”在不断增加,于是也走得更多、更远。
如今周芳42岁,与丈夫和平分手后抚养着三个女儿,大女儿8岁时就跟着她去了30多个国家,12岁考了潜水证,两个妹妹看到姐姐可以跟着妈妈下水,很羡慕,于是在今年暑假也考了证。周芳还会带着她们去徒步、爬山,她曾经说:“在女儿的概念里,不觉得只有天天在办公室、在家做饭才是妈妈,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周芳是被未知驱动的人,有时候向内探索自我的可能性,有时候向外探索世界的边界,而最重要的,也是她希望孩子们能耳濡目染的,“要保持好奇心,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成长者,就像爬山一样,爬到一个山头后才能看到另外一个山头。”
“生活要充满各种各样的希望啊,比如希望明天会找到一个帅气的男朋友。”周芳又笑起来,“如果希望破灭,你所憧憬的东西不存在,也要坦然接受不确定性,然后相信还会有新的希望诞生。”
拍摄纪录片如果遇到天气不好,他们只能好几天待在同一个地方。有一天下雨,不能下海,她和潜伴坐在屋里喝茶聊天,潜伴说,“芳姐,我发现咱俩心态都变好了,以前这种情况大家都特别着急,恨不得每天都是晴天,但现在我看你不着急了,我也不着急,好像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大概是在自然待得久了,时间和空间变得没有边际,剩下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声音—探索,继续探索。
今年6月份,周芳和助理在海南渔村住了10多天,每天“无所事事”,做饭、吃饭,给气瓶打气。吃完晚饭下海,每一天都试着比前一天游得更远一些。在漆黑的海洋里游,很久之后浮出水面一张望,原来我们已经离岸那么远了。

叶梓颐星空摄影师、北京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国家天文杂志的签约摄影师、 Discovery 探索频道中国区的首位签约创作人、TWAN 国际摄影大赛一等奖得主,第一位获得“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年度摄影大赛”奖项的中国人,其作品被NASA 收录
叶梓颐:以繁星启示
从一个地理经常挂科的宅女变身为一个畅游世界星空的创作者需要花多长时间?叶梓颐的答案是10年。自15岁在路上邂逅双子座火流星的那一刻起,她总会在迷茫时抬起头看天,日月星辰似乎能昭示着某种隐晦的答案。
从知名广告公司裸辞后,带着旁人的不解和非科班出身的背景,叶梓颐的摄影作品不仅斩获了TWAN“地球与天空”摄影大赛“夜空之美”组冠军,更是凭借《发光的乌尤尼盐沼》登上了NASA APOD天文每日一图,创下了太多亚洲女摄影师的第一次荣耀。“我对星空痴迷,所以我扛起相机说走就走。我很幸运,因为我把兴趣当成工作,创造出生活的无穷可能性。”
把星辰装进相框的叶梓颐,勇敢如她,立志用镜头游览浩渺繁星,用诗意影像将宇宙和人类缔结。星星在哪里,奇观在哪里,她就去那里,捕捉大自然的瞬间神迹。
相信星星
在网络上,叶梓颐的认证除了“星空摄影师”,还有“天文科普up主”和“北京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但她更愿意把自己真正的工作看成是“连接星空和人类的内容创作者”,让大家因为自己的爱好走进大自然。“我们之所以在星空下感觉自己渺小,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当你知道它有多大,就会涌现一种原始的感叹和赞美。我现在的工作就有着一定的科普意义。”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望星而卜,观天而推演总结自然变换的节奏。对古人来说,日月星辰代表的是某种程度的永恒规律,以此制定历法,它象征一种天规的存在,是定数,也是安全感,“它可能是天地间最大的确定性因素。”叶梓颐说。
和许多痴迷研究星盘星象的女生不同,叶梓颐眼中的繁星自有另一番深意,面对它们时,她始终保持着客观的态度。而有趣的是,她最常抵达的“追星圣地”智利恰恰到处充斥着五花八门的“玄学”。“我觉得这些神秘说法的存在都是人类希望跟世界宇宙建立连接的证明,我们希望通过洞悉大自然的一些表象,来说服自己順应某种天理或天命,本质上还是从未知的恐惧演化到一种对自然的好奇和探索。”
一直自学钻研天文学的叶梓颐,在2020年拍出了公益节目《城市观星指南》,希望让更多人抬头去看看自己所处城市的陌生夜空。她说,很多人就像以前的自己,对星空始终保持着可贵的好奇心。“我15岁的时候,北京的天给我的印象就是漫天雾霾和光污染,和大部分生在城里的孩子一样,我对于头顶上的星空毫无概念。那些星体名词只存在于教科书上,直到数学老师带我们去操场上看星星。”正是那位老师,用指星笔在北五环给她勾勒出满天星图,那是她第一次认出仙后座,而那一次美好而特殊的回忆仿佛给叶梓颐点开了一条梦想和信念的星光大道。“除了制定历法的那些人,中国古代诗人也热爱着星体,以星与月作为意象记录着自己的心思和故事,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宝藏。如今,我的相机就是我的表达渠道,我想通过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让大家走近一些遥远和陌生的区域,去感受他们生活中并不熟悉的事情。只要我能把美好的星辰大海带到他们身边来,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让我有成就感。”
学会分享,走出自己的小世界,这是星星们教会叶梓颐的事,也是她想告诉我们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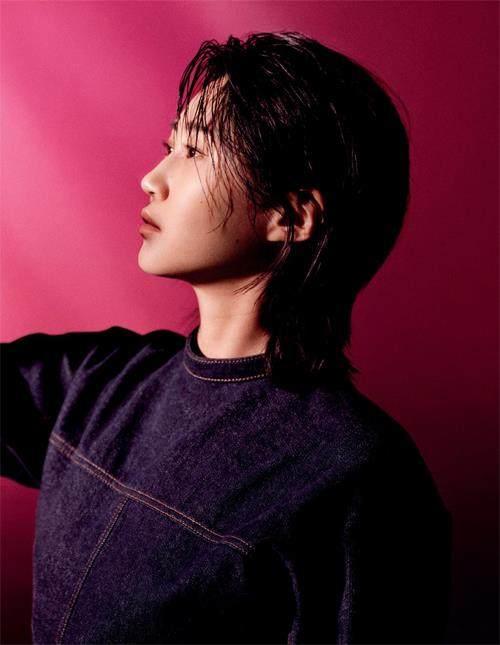
牛仔连身短裙 Fendi
人生一路,就要吃点苦
“虽然真的很辛苦,但极光我拍的,星轨我拍的,银河我拍的,繁星还是我拍的。经历过狂风,体验过骄阳,飞越过雄伟,享受着幸福。从来没有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的标准,只要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就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这是叶梓颐在抖音置顶的短视频里写的念白,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北京大妞的“轴”和“拧”。“我就是个喜欢给自己找别扭的人。人生就是需要不断地给自己找挑战,在自我舒适区里待着是挺舒服的,但人生就这样刷一下过去了。” 很多人问她,怕不怕被时代落下,拍星空这件事情能够做多久,叶梓颐觉得,星空带给她的最大感触就在于广阔,“我是一个不喜欢重复做同一件事情的人,当你产生疲倦的时候,星空又带出新的东西,让我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的认知,让我觉得这还没够,还要继续知道些什么,继续拍到些什么。只要有这种想法就不会被落下了,除非你在人生里做了非常错误的决定。”
叶梓颐喜欢的摄影师星野道夫曾在随笔里写道:“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面临许多选择,我想唯有回到当初的十字路口,才能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吧?”现在回望,自己在25岁时所做的破釜沉舟的选择是何其正确。“2011年我拍下第一张星星的相片,之后我就一直本能地用这种方式去实现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我发现无论一个人的事业有怎样的变化,初衷一直就在那。我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必要为了只是活下去而做没有激情的事。”
这条铺满星光的大道并非坦途,等着叶梓颐的是沉重的器械,极端的环境,身体的不适,还有无法预料的危险,而这些未知和困难在南极拍摄之旅中达到了顶峰:“很多人因为《日食时钟》那组照片认识我,但在南极拍日全食真的是太难忘了。”去年年底,一个人拎了70公斤的行李,在复杂而严格的防疫政策下,几经周折,叶梓颐终于抵达了地球的最南端。那张最经典的《日食时钟》是太阳在高纬度地区处于日不落的状态下拍摄的,记录了在2021年12月4日的极昼状态的39秒钟。在这些不分昼夜的日子里,叶梓颐睡在帐篷里,独自一人在南极大陆露营了5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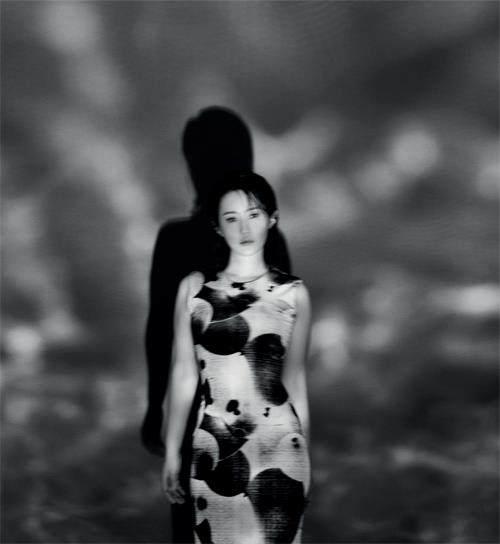
气球花纹天鹅绒连衣裙 Loewe 高跟鞋 Gianvito Rossi
“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如说用特殊的鱼眼镜头,防低温的电池等。我要提前先把相机架好,然后在日全食发生前12个小时找到最佳位置。”她就这样站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的室外,等待着,与不落的太阳为伴。虽然南极夏天没有那么冷,但站上半天还是要缓一缓,注意保暖,同时她还得时刻照看器材的状态,最后在她的“精心照料”下那些电池在户外坚持了28个小时。
作为跑过大半个地球的人,叶梓颐说自己对旅行本身没有太大兴趣,她每一次的“疯狂”或“执著”都是为了完成自己心中想要的作品,那些拍摄时的脏和累在她看来都不是“苦”,而是一种磨练和一种挑战。朋友们调侃地给她取名“铁皮骆驼”—一个可以为了拍照不吃不喝的有执念的人。“有的人穷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喜欢什么,但星空摄影让我感觉到了人生不同的广度,也许身边人不想你走这样一条曲折的路,但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应该是有其自己的味道,这样才有意思,我的人生可能是苦,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是我选的,这才是我走一趟人生的目的。”
成为自己的太阳
“一张曝光三十秒的照片,凝聚的是来自十万甚至百亿年前的那些宇宙的光芒。当我记录的这缕光线从那颗恒星迸发的时候,恐龙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经过漫长的时间旅途,最终达到我的相机里,想想就讓人感动,所以我愿意为了迎接它而耐心地等待。”
等待,是星空摄影的日常状态,你可能只有一次拍摄机会。很多时候拍摄天气不好,要等;为了找到一个好机位,徒步两三天到了露营地,又要等。这些艰苦的滋味,和我们脑海里在辽阔的旷野上架着机器等满天繁星降临的唯美时刻,形成了反差。“很多时候我并不是在‘干等,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比如计算月升的时间,有时候这个过程里我是非常焦虑的。”然而,等待就像一把双刃剑,“后来我把等待当成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没有光和声音的污染,可以慢慢享受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感觉,能带来拍摄时的专注,也会带来独处时难以避开的孤寂。”

周芳 白色背心、花朵装饰半裙、粉色高跟鞋 均为 Prada 叶梓颐 灰色针织衫、钉珠装饰半裙、黑色高跟鞋 均为 Prada
对叶梓颐来说,孤独像是一面镜子,让她诚实面对自己的心,也照到自己的边界。在南极拍完日全食后,她没有直接回国,而是经过了24小时的飞行抵达冰岛,开始了新一段“孤独之旅”。她一个人开着车,在一月份的北极圈内,直面车窗外的风雪呼啸。甚至有时候,夜里她就直接睡在车上,恐惧裹挟着孤独,与风一起怒吼,她承认那时她是害怕的。但一圈又一圈,在极光降临、犹如神域的冰岛,叶梓颐环岛开了40天,足足5000公里的车程。
“这一趟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意义,关于自己的成长。在狂暴的极端天气里,我每天睡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心理层面的强大不安感会让我极其难受。但就是这样的体验是我追求的挑战,超越了拍摄的困难,是对心的一种试探。”
这样一颗坚韧的心,究竟在宇宙中有哪颗星可以与之比拟?或许就像叶梓颐镜头里的太阳,经历了极暗的等待方能展出见证刹那异彩。也就因为是一瞬间,你永远觉得看不够,永远觉得不完美,所以还会一直追逐,就像眼前这位始终没有停下脚步的巡天者— 巧的是,太阳正是她最喜欢的那颗星。
周芳X叶梓颐
周芳:天上和海底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然而它们都在守望着彼此。就像你说不了解水下的生物,我也不知道你那个世界有什么样有趣的知识,我对星空充满了好奇。
叶梓颐:在很小的时候我对海洋也充满了好奇,后来我跟它最亲近的尝试就是潜了几次水,我记得当时是在红海,色彩斑斓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就像看星空一样,不能用语言去形容,是非常独特的不可取代的记忆。那种感觉和陆地上特别不一样,你在做每个动作的时候都要承受很多,所以我觉得你的拍摄难度要远比我更大一些。
周芳:关于星空,我会想到一个画面,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少年一个人躺在船上,夜晚时分海面上出现了荧光海,全是星星,那是我脑海当中最美的一个场景。有时我经常要拍到深夜,出水之后特别安静,但头顶上总有一大片星空,所以我喜欢用仰泳回岸上,感觉到星空一直陪着我,很美很享受。我想问你,国内哪里看星空最好?
叶梓颐:推荐青海。
周芳:我也曾经去过青海,拍青海湖的时候,也在旁边架起相机拍摄星轨,当然我很不专业。我发现我们这两个领域确实会有交集,而最大的幸运是—我们都是长时间在大自然中成长,被大自然拥抱、熏陶和治愈。
叶梓颐:是的。而且这两个世界都特别安静,在没有光污染、没有城市喧嚣的星空下,一个人慢慢享受,仿佛一个人就拥有那整片天空。海底也是一样,没有信号,没有噼里啪啦的微信,没有人跟你说话,不被打扰,你可以完全享受蔚蓝世界的沉静,专注更纯粹的事情,专注在自己的取景框里。我们确实都有挺幸福的职业和生活方式。
周芳:我也觉得,在任何一个有网络的地方,手机就像是个每时每刻嗷嗷待哺的孩子,它一振动,人就会特别紧张。
叶梓颐: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词叫“心流”,我觉得它就是指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感,比如在完全安静的夜里或水下,这是一种回归于人类本真的状态和体验,嗅觉、触觉、听觉……各个感官都被激活了,打开了,这是任何VR或者所谓的元宇宙科技都无法替代的,而且每个人在那一刻所感受到的都是不同的。
周芳:我其实特别开心,看到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根植在小众的、垂直的领域里,做着深入的研究,专注而纯粹,把很多很好的内容传播出去,影响到更多的人。
叶梓颐:其实,我非常想通过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让大家认识星空,了解一些不熟悉的事情,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让我获得成就感。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的文化里、生活中很多都跟天文和星空有关,但现在很少有人去关注,其实其中有很多待挖掘的宝藏。
周芳:我很能理解你的这种想法。我们都是用镜头和自己的故事将看似遥远陌生的领域带进了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扛着器材去南极北极,去雪山海底,我们愿意这样做,愿意把美好的星辰大海带回来,让大家看到。
叶梓颐:水下拍摄肯定要比拍星空更难。
周芳:孰难孰易很难界定,每个领域都有独特之处,都有很多知识要学习。星空和海洋都是个大课堂,我们可能穷其一生也学不到其中的十分之一,更远的星空和未知的星系,更远的海域和更深的海底……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索。
叶梓颐:魅力也正在于此。我是个不喜欢重复做同一件事情的人,大自然和星空总有新东西让我突破认知,可以继续探索,继续拍。即使就像你说的,我们穷尽一生只能窥探一部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不可控的因素,我会发现自己的渺小,但是我愿意接受这种未知和意外带来的惊喜、挑战,甚至是失败。
周芳:没错,对我来说,失败也是一种常态,我和团队拍摄布氏鲸,连续等了两年,一直守着,可惜就是没能拍到,但那又怎么样呢?在外人看来,这是一种失败,但对我们做自然影像的人来说,拍得越多,就会越接受这种状态,我们也不会把它称之为失败,而是看做一种经历,特别是当你身边还有一群可以放心交出后背的伙伴。
叶梓颐:原来我们的身边都有这样的一群人。
周芳:对我来说,水下的伙伴有着特别的意义,潜水的规则是必须要有潜伴,任何时候都要和自己的潜伴在一起,要学会如何一起共享气源,当你遇到危险时如何向他求助,等等。我的伙伴是可以绝对信赖甚至可以交付性命的同行者。我是个有点执拗的人,一进入拍摄状态常常忘了自己的深度、气量,甚至忽略了周围的危险,而我的潜伴会帮我留意到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叶梓颐:对,我的伙伴也一样,不仅是摄影助手或者同事,我们是朋友或者接力的关系。我在拍摄时也非常偏执,团队的人都说我像是一只“铁皮骆驼”,可以不吃不喝,又嘴硬,我很需要他们在我身边。每一次辛苦的工作结束后,都会请他们大吃一顿。有时候我们也会小争吵,在野外连续几晚工作的极限情况下,人的情绪会容易失控,大家都彼此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