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點評“躺平”“內卷”(上)
2022-05-30王五一
王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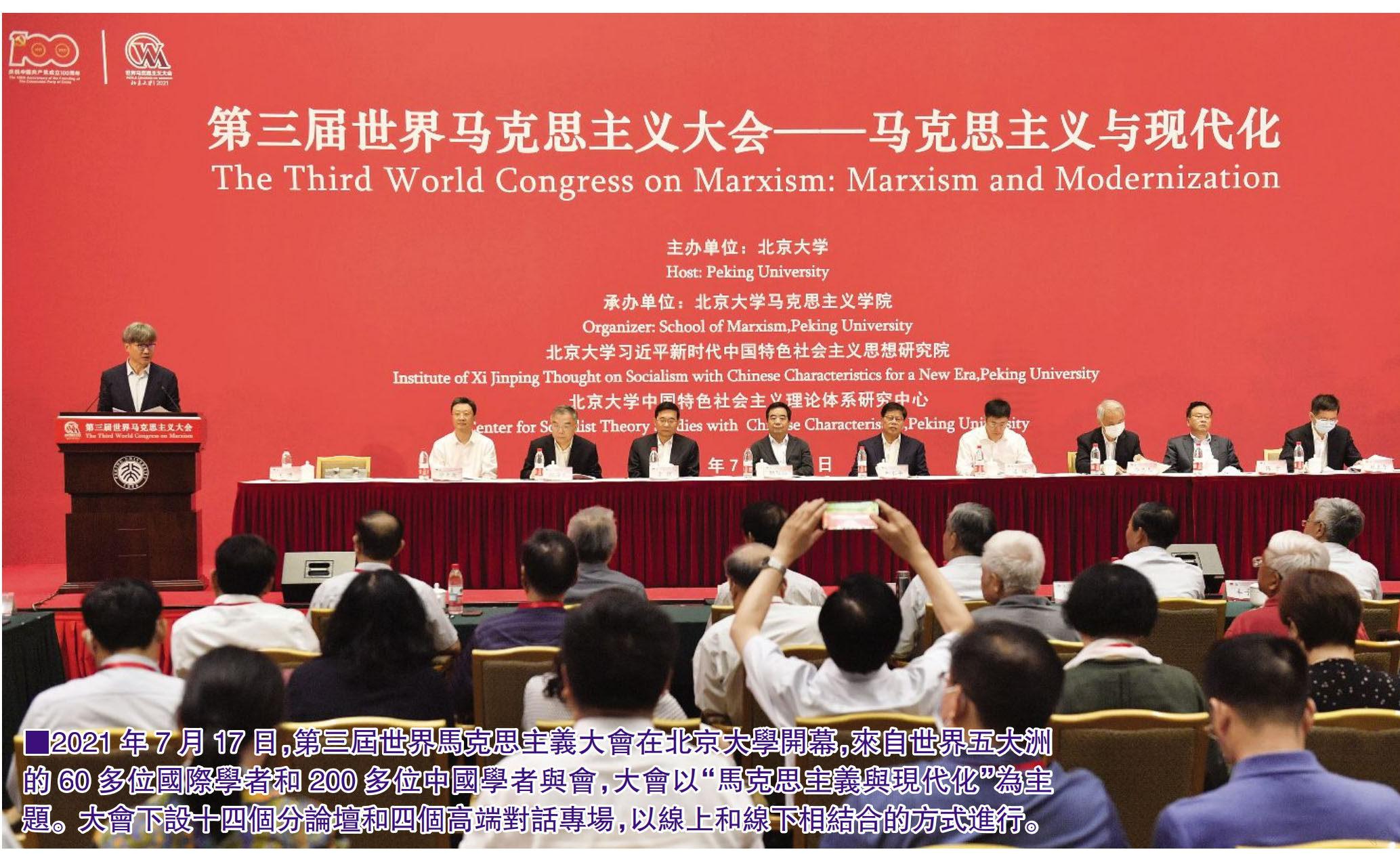

馬克思者,歐洲思想史上的超級學術巨匠,可惜,讓學校裡那些“教”馬克思的給搞臭了,讓官面上那些“信”馬克思的給搞臭了,讓那些對馬克思一竅不通的“馬克思主義者”給搞臭了。在下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例如我不信世界大同),卻是馬克思的學術崇拜者,今天,我把老先生請來,請他為當今中國青年的兩個熱門話題,“躺平”與“內卷”,作個解析點評。
一、利潤率下降
市場,即使像神吹的那樣,是一支“看不見的手”,能擺平人間生活的各個方面,或者換個比喻,是一部萬能動力機,套上什麼樣的工作機它都能拉,工業也能拉,農業也能拉,商業也能拉,金融也能拉,住房也能拉,教育也能拉,醫院也能拉,廁所也能拉,火葬場也能拉,甚至,如中國一度試驗過的,軍隊也能拉,什麼都能拉,那麼,至少有一個問題仍然存在:這只看不見的手本身,有沒有可能有一天得什麼病癱瘓掉?這個萬能動力機本身,會不會有朝一日過了使用年限,“氣數已盡”而壞掉?
煌煌《資本論》,就是專門研究市場經濟的氣數的,它認為,市場經濟必然滅亡。
怎麼講?
市場,作為動力機,其運轉是需要能源的,這個能源就是利潤。市場經濟是利潤驅動的,社會平均利潤率的高低,便相當於這臺機器的油門大小。利潤率高、油門大、商人們都有得賺,機器就轉得暢旺;利潤率低、油門小、商人們的日子都不好過,“低迷”“衰退”“不景氣”一類的詞兒就出來了。如果有朝一日,由於某種原因,利潤能源耗盡了,商人們都無利可圖無錢可賺了,油門關掉,這個動力機就會停下來,相應地,掛在動力機上的所有那些工作機,工業、農業、商業、金融、政府等等等等,自然也就都會停下來。
《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的標題叫“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它指出,利潤能源真會有耗盡的一天。百多年前市場經濟在歐洲如日中天的時候,馬克思便探明了此一制度的生死大脈:市場經濟,以創造使用價值為手段,以創造價值為目的;以生產為手段,以賺錢為目的;它創造使用價值的能力越強,創造價值的能力就越弱;最終,在這個經濟機器製造出了巨大的物質堆積的同時,其運轉的能源基礎——利潤,則會被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一點點耗幹。
商業競爭推動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導致企業的資本底盤的膨脹,即利潤率之分母的膨脹,分母膨脹了,如果分子不變,那就是利潤率的下降——利潤率下降的此一機理,筆者在《市場經濟的死胡同》一文中有個較為通達的描述,刊在2021年第9期《澳門月刊》上,讀者可以找來一讀,以為閱讀本文的基礎,這裡就不複述了。
論證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規律,《資本論》的模型只用了技術進步一個變量,那個時代,資源短缺問題尚未突出出來,資源價格上漲的因素還沒進入馬克思的法眼,若是把這因素也考慮進來,這規律就更好理解了。
當然,分母膨脹並必然導致分數值縮小,還要看分子——利潤額,相應地會怎麼變。這也好辦,馬克思自己有現成的理論工具——勞動價值理論。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當然也是剩餘價值的唯一源泉,當然也就是利潤的唯一源泉,因為,剩餘價值是從社會總價值中割來的一塊兒,而利潤又是從剩餘價值中割來的一塊兒。也就是說,歸根結底,利潤是由勞動創造的,而且僅僅是由勞動創造的,它的高低,本質上與生產的技術水平無關。不管技術、機器怎麼“鳥槍換炮”,在整體意義上、長期意義上,都不會對利潤額產生本質性影響。即,利潤率的分子在理論上是恒定的。分子恒定而分母益大,所以,利潤率不斷下降。當利潤被技術競爭一點點擠光了的時候,當商人們都無錢可賺的時候,市場的機器就會停下來,市場經濟的氣數也就盡了。馬克思喜歡用另一個詞,滅亡。
我們今天來討論利潤率下降理論,與馬克思時代相比,有了一個很大的有利條件——歷史事實。也許有人根本上並不認可馬克思經濟學,尤其是勞動價值理論,但他恐怕很難否認利潤率越來越低的經濟事實。即使他連這個事實也不願承認,他總得承認銀行利息率下降的事實。而無論是哪門哪派的經濟學,誰也不會否認利潤率與利息率在宏觀上是捆綁聯動的。銀行利息率不斷下降的歷史事實,是利潤率下降理論的最有力的證據。
退回一百年前的銀元時代,那時一般私人存款的年息率是四厘。存息四厘,乃是因為銀號可以以七八厘的息率往外放款;商家之所以敢於以七八厘的息率借款,其生意至少得有十厘以上利潤率。利息率是跟著利潤率走的,溯此邏輯線索,不難推斷出那個時代市場上的平均利潤率水平。一百年來,銀行利息率從四厘實息一直降到了今天全面的、不可逆轉的負利率。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從利息率下降的趨勢中得到了足夠的證明。
二、通貨膨脹迷霧
說到了負利率,本節的討論就以它做引子。所謂負利率,就是通貨膨脹率高於銀行存款利息率,百姓存在銀行裡的錢越存越少。
這可能會使一些人產生誤解,以為負利率是通貨膨脹造成的,有人甚至會進而把經濟機體的其他弊病也盡歸於通貨膨脹。先須費點筆墨驅開這層迷霧,以把利潤率下降這個歷史真兇暴露出來。
市場經濟是貨幣經濟,社會每生產出一單位產品,便需要一單位的貨幣供應與之相對應,比例未必是一比一,大原則是貨幣供應必須跟著生產走。從貴金屬貨幣的角度看,這是市場經濟一個天然的生理缺陷——貨幣的供應不可能趕上生產的增長,貨幣一定會拖經濟的後腿。
有人或許會問:貨幣既然只是個價值符號和支付手段,那貨幣供應的增加即使趕不上生產的增長也沒關係呀,讓貴金屬貨幣不斷升值就行了嘛,以前一兩白銀能買一隻羊,現在讓它能買一頭牛,以後再能買一套房,這樣,任憑經濟如何發展,貨幣的供應就都不會成為問題了嘛。
聽上去挺有道理。那麼,歷史為什麼沒有按這個思路走呢?因為,這只是個數理賬,這種賬是不能拿來當經濟賬用的,在經濟生活中起作用的,不是“均量”的道理而是“增量”的道理。設想一下,一旦貴金屬貨幣的升值成為必然性的、制度性的、長期性的,則最安全最可靠最容易的投資經營方式就是挖窖藏錢。一個酒作坊的小老闆花一百兩銀子的成本釀了酒,一年後拿到市場上只賣回了八十兩,因為銀子升值了。誰會去做這種傻子生意?把酒作坊關門,把一百兩銀子挖個地窖藏起來,坐吃白銀升值帶來的“利潤”,那多好。並且,埋錢本身也會使貨幣升值,越埋越貴,越貴越埋,如此,即時性因素與預期性因素疊加,經濟性升值與投機性升值合力,會把社會經濟活活扼殺掉。(中國的明朝,就是被崇禎末年興起的一股埋銀風給埋葬掉的。)
說到這裡,順便說一句,今天仍有一些人在琢磨著恢復金本位制——太不明白貨幣的脾性啦。
所以,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貴金屬貨幣必然退出歷史,紙幣制度必然產生,因為只有紙幣的供應才能跟得上生產爆炸的步伐。
然而,像世間所有的事情一樣,一個矛盾解決了,另一個矛盾跟著來,市場經濟進入紙幣階段後(以五十年前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為標誌),很快被這新的貨幣制度拖向了另一個方向,一個以更快的速度走向滅亡的方向。紙幣,恰恰就像我們給死人燒的紙幣,是來給市場經濟送葬的。
金銀是天賦的,紙幣是官賦的,從這個比較中,其實就可以歸納出紙幣制度的全部弊病。貴金屬是天賦的,所以是稀缺的,所以值錢。紙幣是官賦的,要多少有多少,所以一文不值,貨幣的那些傳統定義,價值標準、抽象財富、儲藏手段等,被紙幣剝得一乾二淨,只剩下了“支付手段”一個角色。作為支付手段,人們接受它僅僅是因為人們接受它。這是一個浮在空中的貨幣體系,即所謂的信用貨幣。
“信用”者,“臉”也。政府“臉大”,所以它印的錢大家都要,僅此而已。而在半個世紀的紙幣制度史上,隨著政府們在貨幣問題上越來越“不要臉”,這個浮在空中的“信用貨幣”體系也就越來越不講信用。
世界分裂成了二百個政府,地球上安放著二百臺“主權”印鈔機。或是為了彌補財政,或是為了貶值競爭,或是為了稀釋債務,或是為了經濟霸權,……,無論出於什麼目的,當政府們基於自身的利益把印鈔機開得越來越快的時候,這為全人類製造出了一個一般性的經濟後果:通貨膨脹。
印鈔機印出來的新錢,是從哪裡獲得價值的?從百姓腰包裡現有的錢中稀釋過去的。印鈔機就是吸血機,通貨膨脹就是政府的巧取豪奪。
表面上看,通貨膨脹無非就是三個字,錢毛了,如弗裡德曼所說的,“通貨膨脹純粹是個印鈔機現象”。然而,如果僅僅是錢毛了,那麼,所有的經濟當事人,所有的經濟變量,都跟著水漲船高不就行了嘛,社會經濟機器就會照常運轉的嘛。銀行原來的存款利息率是3%,現在,來了5%的通貨膨脹率,把利息率提到8%不就行了嘛。貸款那頭,原來的貸款息率是5%,現在10%就行了嘛,等等。可悲的是,歷史沒這樣走,面對通貨膨脹,銀行選擇了裝糊塗,選擇了隨波逐流,通貨膨脹率很快漫過了名義利息率,形成了負利率。
負利率,既改變了百姓的生活,也改變了銀行的性質。
百姓方面,人們沒法掙錢攢錢過踏實日子了,沒法像一百年前那樣辛勤勞動一輩子攢下一千兩銀子靠吃利息而安享晚年了。負利率下,人們或者幹一天吃一天,或者,逼良為賭,參與到各種金融投機和“理財計劃”中。人,沒法做老實人了。
銀行方面,它不再向存戶付費而是向存戶收費了,因為,銀行已不再是一個幫著資金持有人尋找投資門徑而生息生財的仲介機構,而是一個為存戶保管現金的機構了,存戶的利息倒貼,就是現金保管費。
負利率告訴我們:通貨膨脹吸血,隔著衣服也能吸;通貨膨脹豪奪,翻過銀行利息的牆頭也能奪!如此,政府用印鈔機吃經濟,經濟用負利率吃銀行,銀行用負利率吃存戶——社會經濟機器倒著轉了。
這哪裡僅僅是個“錢毛了”的問題!這是社會經濟制度的本質性改變!這個改變的根源不可能僅僅用印鈔機來解釋。
不是印鈔機是什麼?利潤率下降。
三、剩餘價值大鍋
按《資本論》的體系,利潤是從剩餘價值大鍋中舀出來的,利潤率的不斷下降,本質上是剩餘價值大鍋的日益乾涸。
“大鍋”是我的話,不是馬克思的話,馬克思的比喻是“紅線”。為什麼叫“紅線”,這有個經濟學史的背景。在馬克思以前,關於市場經濟中各個收入範疇的理論,工資理論、利潤理論、利息理論、地租理論、稅收理論等,基本是各自獨立一個學術帳戶,各搞一套,相互間無多少邏輯關係——工資是勞動的價格,利潤是資本家經營企業的報酬,利息是那些手裡有錢忍著不花的人所獲得的意志力獎賞,地租是產品中由土地創造的那一部分,等等,五花八門,沒有一個統一邏輯。“庸俗”如薩伊者,想統一下,其統一的理論工具是“要素價格”——所有的收入範疇,都只是與之相對應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工資是勞動的價格,利息是資本的價格,地租是土地的價格等等——跟什麼沒說差不多。在此背景下,馬克思玩了一手學術大一統的絕活兒。第一,先用勞動把價值統一起來——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第二,從價值中把剩餘價值離析出來——價值中扣掉工資,就是剩餘價值。第三,用剩餘價值這條“紅線”,把一切剝削收入穿起來——利潤、利息、地租、稅收,都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是各個資本集團參與剩餘價值分割的經濟範疇。“紅線”喻是這麼來的。
改為“大鍋”喻,理論變實踐——資本階級的一切收入,蓋取自社會總剩餘價值這口大鍋。
剩餘價值大鍋的分配,不但有個比例問題,還有個順序題。按馬克思“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方法論原則,“大鍋飯”先由產業資本做出來,以利潤的形式存在著,然後,地主舀一勺地租,銀行舀一勺利息,政府舀一勺稅收,當然,把產品交給商業企業去銷售的時候,倒爺們也要舀一勺。剩餘價值的分配,是這樣一個概念。
如此說來,顯然,利潤率不斷下降的理論,其實就是剩餘價值大鍋裡的湯越來越少的理論。湯越來越少,相應地,各方面的勺子也就只能越來越小,包括政府稅收的勺子,銀行利息的勺子。話說到這裡,迫使政府在開動印鈔機上越來越“不要臉”的那個背後主凶就揪出來了,導致銀行在通貨膨脹面前隨波逐流裝糊塗的那個主凶也揪出來了,它們是同一個東西:利潤率的不斷下降,或曰,剩餘價值大鍋裡的湯不斷減少。
推動政府濫印鈔票的動機有許多,但最經典的動機就是彌補財政赤字。財政為什麼會有赤字?稅收不夠。稅收為什麼不夠?政府參與分配剩餘價值的勺子越來越小。同樣,銀行的勺子也越來越小,它越來越感到,自己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與通貨膨脹賽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使自己的利息定價跟著通貨膨脹水漲船高,於是,面對現實,任由負利率“無可奈何花落去”了。
“海水倒灌”感覺上也沒有預想的那麼可怕。銀行仍然叫“銀行”,而且,仍然在有效順暢地運轉著。政府的反洗錢制度、小偷的盜竊威脅、殘存著的那點名義利息的誘惑,三股力量聯手,迫使人們繼續老老實實地往銀行裡倒貼存錢。錢越存越少,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了。而銀行家們也並沒有什麼感覺上的壓力,管它正利率負利率,只要能吸收到存款,只要有息差可賺,把斂到的存款再倒貼著貸出去就是了。
於是,原來靠分割剩餘價值為生的各個資本集團(包括政府),在沒有剩餘價值可分的情況下,在求生本能的驅使下,不得不分頭去尋求新的利益源泉,經濟關係和利益結構不得不重新洗牌,市場經濟的機器不得不從根本上改變它的運轉機理——躺平與內卷,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