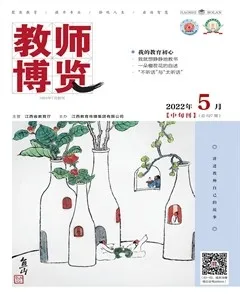我就想静静地教书
2022-05-29顾文艳
顾文艳
一组课堂生活照背后的成长
记得2020年参加“全国十大青年名师”评选的时候,组委会让我发几张照片作为活动手册的素材,可是我发的每一张都不符合要求。工作人员也给我看了其他老师发的照片,大多是在影楼拍的艺术照。
我没有拍过艺术照,找来找去,生活照也很少,我的照片几乎都是在上公开课时同事或摄影师拍的。其实,这些既是我的工作照,也是我的生活照。因为,教学就是我的生活。
我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照片排列,从曾经青涩的我到现在眼角有皱纹的我。一天天,一年年,课堂上的我渐渐成熟,甚至是渐渐老去。
年轻的时候上公开课,特别是赛课,心里还有很多顾忌,也有很多与课堂无关的想法。可是现在,我站在讲台上,心里就只有眼前的这几十个学生,哪怕是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亦是如此。
最后一张照片是2019年12月参加全国新体系作文大赛时拍的,那次大赛我获得了特等獎的第一名。在课堂上,我不会想到这是比赛,也不会想到要争取什么名次,我想的只有一件事——这40分钟,我和孩子们该怎样美好地度过?
源自童年的教师理想,
两个世纪的家族史诗
我的学生曾经问过我:“顾老师,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我说:“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做老师。”
他们问:“真的吗?”
我认真地答:“真的。”
的确是真的。为什么从小就想做老师?这和我的家庭分不开。
曾祖父顾浩然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曾祖母过征宛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她与吴健雄是同窗好友。抗战年代,曾祖父、曾祖母辗转于各地,但不管身处何处,不管职务如何变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教师。
我的曾祖父后来是兴化中学的首任校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化县负责文卫工作的副县长。曾祖母是兴化市实验小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1994年我中师毕业,也被分配到了兴化市实验小学工作。
我进兴化市实验小学的第一天,已退休的周校长就找到我,和我聊起关于曾祖母的往事。“你曾祖母任校长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物资短缺,学校没有课桌椅,也买不到木材。过校长便让校工拆了她家里的吊顶和木地板,制作成一张张简易的课桌椅。过校长常常邀请没有成家的老师到她家里吃饭,那时每年的除夕夜,我们都是在过校长家里吃年夜饭的……”透过他的黑框眼镜,我看到了他眼中闪着的泪光……
曾祖父和曾祖母离开我们许多年了,但他们一直活在同事和后辈的记忆中。记得前几年的清明节,表叔回老家扫墓时,回忆起曾祖父的几件小事。
“我妈妈和舅舅他们念书时,外公总是把自己办公用的墨水和子女用的墨水分开。外公说自己的墨水是单位发的,子女不可以用。我工作的第一个月,给外公写信,用的是单位的信纸和信封。外公回信时批评我不该用单位的纸张和信封给他写信,信里他还夹了十元钱,让我下次写私人信件时得用自己买的信纸和信封……”表叔缓缓地叙述着,我仿佛看到了不苟言笑的曾祖父在灯下给表叔回信的情形,仿佛看到了他正把一张十元的纸币放入信封的动作……
2019年我来到上海工作时,表叔给我发来了一则短信,他是这样说的:
文艳,祝贺你来到上海教书。我想到1942年上海租界沦陷前,你曾祖父、曾祖母也在上海教书。这是两个世纪的家族史诗。
我记得那个时候表叔还特地跑到福建路、宁波路的路口(也就是曾祖父他们办学的地方)拍了几张照片发给我。当年曾祖父他们在那儿创办的是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的分校。表叔发来的照片,已经没有当初那所学校的印迹,但我却可以想象到当年曾祖父、曾祖母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坚守着教育的梦想。
妈妈教师
曾祖父、曾祖母让我看到了老一辈教育人的风骨;母亲,一位乡村教师,让我感受到的则是师者慈母心。
记得我读小学时,一位高而瘦的“不速之客”跟在母亲身后,母亲让我叫他“杏柳大哥”。我知道,他一定是母亲的学生,因为母亲已经不止一次在用餐时间带学生回家了。
前一年的中考,杏柳大哥其他各科成绩都很好,唯独英语只考了2分。英语基础几乎为零的他跟不上教学进度,因此焦灼不安,甚至夜不能寐。母亲和杏柳大哥进行了一番长谈,除了安慰与鼓励,母亲还决定利用课余的时间给他补课,从认识26个字母开始。
“吃吧,鸡蛋有营养,你背单词背得那么辛苦,营养跟不上可怎么行?”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把剥了壳的鸡蛋放在杏柳大哥的碗里。从那以后,杏柳大哥成了我家的常客;吃饭时,母亲也总是不停地往他的碗里夹菜……
时间似乎就在碗边流过。几个月后,中考成绩揭晓了,杏柳大哥英语考了98分,当时的满分是100分。杏柳大哥拿着株洲铁路机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来到我家时,他的脸上写满了兴奋。他说的那番话,至今我仍然记得:“徐老师,我没有考到满分,觉得很对不起您……”那一刻,他的眼里含着泪花。
杏柳是我的大哥,玉平则几乎是我的亲弟弟。
玉平自幼丧父,他母亲改嫁后远走他乡,他跟着年迈的祖父艰难度日,几亩薄田是玉平和祖父唯一的生活来源。母亲不仅关心着玉平的学习,还操心着他的衣食住行。为了让玉平能顺利地完成学业,母亲找到校长,申请为玉平减免能够减免的一切费用。
冬天,玉平衣着单薄,母亲用家中的那台老缝纫机,把父亲的棉衣改小了,给玉平穿上。学习刻苦的玉平如愿考入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兴化中学,可玉平愁眉不展地告诉母亲,祖父负担不起他上学的费用,他不得不面临辍学。母亲一边安慰玉平,一边开始为玉平读高中做着准备。
我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暑假,母亲连续几日带着我穿梭在小商品市场的各个店铺间,箱子、背包,生活用品,铺盖行李……零零碎碎买了一大堆。母亲又找到兴化中学的校领导,告知了玉平特殊的家庭状况,申请减免费用……
开学的日子到了,母亲领着玉平去学校报到。这以后的三年,母亲依旧资助着玉平,从未间断过。三年后,玉平考入了镇江船舶学院,还是母亲送他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我的父亲是医生,温和儒雅。我父母都是工薪阶层,收入并不丰厚,可母亲几十年来一直以各种方式资助着那些家境贫困的学生,而父亲总是尽一切所能,默默地支持着母亲的工作,从无怨尤……
学生生病了,母亲总是陪他们去医院看病。而父亲每次都是一路陪同,帮忙挂号、拿药……父亲默默地做着这一切,似乎这些都是他的分内事。
我想,一位好老师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时是需要家人支持的,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全心全意支持着爱人教书育人的好先生。
母亲被学生们称为“妈妈老师”。她是我的妈妈,她也是我的老师!
父亲的支持
1991年我初中毕业,那时,中师提前招生,录取分数线比重点高中高出几十分。我瞒着母亲,在班主任那里填写了报考师范学校的志愿表。母亲虽然感受着为人师的幸福,却不舍得让自己的女儿再重复自己的辛苦。她有着切身的体会:做教师是辛苦的,做一位优秀的教师更加辛苦。当得知我偷偷报考了师范,她决定到扬州招生办申请修改我的中考志愿表。
1991年夏天的那场洪水,号称百年一遇。当时我们住在教师家属区里面,目之所及,一片汪洋。我记得我们只能一趟一趟地用木桶把家里的东西搬到教室里面,因为教室的地基要高一些。
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母亲依然决心出发去扬州修改我的志愿。但当时公路都被淹没了,和田野连成一片汪洋,自然是不能通车的。
母亲想走水路去扬州,她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父亲担心她的安全极力阻止。父亲劝道:“这是天意,这场洪水阻止了你出行,或许,我们的女儿就是应该做老师的。”
我知道,父亲不便直接反驳母亲的决定,但他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从小到大,父亲总是支持我的一切想法和做法,我梦想做教师,他是知道的。
天意难违,母亲不得已,只能放弃了修改我的志愿的想法。
师范的面试如期而至,绘画、舞蹈、朗诵,一项项比拼过后,我面试的分数名列小组第一。9月,我如愿走进了江苏省高邮师范学校的大门。
这些年来,母亲看到我成了一位很不错的教师,她也庆幸当年那场洪水阻止了她修改我的志愿。
儿子对我的影响
除了曾祖父、曾祖母以及母亲对我的影响外,我的儿子对我的教育观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刚师范毕业时,尚未体会到为人母的辛苦和幸福,那个时候作为老师的我,还是有点小小的偏心眼的——我可能对漂亮的、聪明的孩子会多爱一点。
但是,做了妈妈以后,我体会到每一个孩子,不管是漂亮的还是普通的,不管是聪明的还是迟钝的,都是妈妈十月怀胎孕育的,都是妈妈一小勺一小勺喂大的。这时候的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偏心,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贝。
所以,自从我做了母亲以后,我的学生都会评价我特别公平公正,对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严格要求,对所有的孩子都一樣温柔呵护。这一点,我真的要感谢我的儿子,是他让我体会到母亲为孩子付出的无怨无悔。当一位位母亲把她们的孩子托付于我的时候,我自然不能辜负她们的信任,我也要把每一个孩子当作宝贝。
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
我记得当时他班上有一个孩子做作业特别快,我就对儿子说:“为什么每一次某某做作业都做得比你快,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得快一点?”他这样回答:“妈妈,他做作业是比我做得快,可是你知道吗?他交上去10道题可能有5道是错的,老师要退回来让他订正,再订正可能还会有错的,然后还要再订正。可是我每一次把作业交上去的时候,10道题目我能保证都是对的,只要我会做的,我都可以做对。”接着,他又说:“妈妈,请你不要用别人的长处来和我的短处做比较,我也有比别人强的地方。”
当时,听到他这句话,我真的有一种震惊的感觉,当时就跟他道歉了:“对不起,妈妈的确做得不对。妈妈不应该总是讲别人的好,看不到你的好。妈妈以后一定会努力,多多发现你的优点。”
从那以后,我不仅是努力多发现儿子的优点,也会更多地发现我的学生的优点,用欣赏的眼光看他们。每个孩子,我都可以找到他的长处。
在这一点上,我的儿子,也是我的老师。
盘点我教过的学生
1994年我开始工作了,开始教我的第一届学生。他们是1998年小学毕业的,那时候读三年级。其实他们也就比我小个七八岁,因为我读书比较早,师范毕业的时候还不满18周岁。
记得走进兴化市实验小学的第一天,校长问我们想教什么学科,我赶紧举手说:“我要教语文。”教语文是要做班主任的,于是我被学校安排为三(5)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这三(5)班并不是从二(5)班升上来的,而是从二年级四个班提供的学生分组名单中,任意抽选出一部分重新组合而成的混合班。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抽签的场景:校长室的长条桌边,站着校长、教导主任、大队辅导员,还有我。教导主任把二(1)班的五组名单团成纸球,扔在长桌上。我知道,我选择了哪个纸球,就意味着选择了这个纸球上写着的十几个孩子。就这样,我从一班抽到四班,一共抽了四次,直到四个纸球都被我握在手心,我才在校长、主任的注视下,一一打开——师生相遇也是需要缘分的。
班长朱平平,每次想起她,我就会想到她的作业本——从第一页一直到最后一页,每个字都写得那么工整、漂亮。教了二十多年书,像朱平平这样认真的孩子并不多。如今的她,在大洋彼岸,成了一名汽车工程师。
张瑜,短发,大眼睛,是个漂亮的姑娘。爱憎分明的她,从不吝啬表达对我的喜爱。我记得她到我家玩过,我还记得她送过我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套头毛衣,外套被她甩在肩头,一副很帅气的模样。如今的她,是一位优秀的英语教师。
小吴循,为什么称他为小吴循?去年,他添加我的微信,第一句话就是“顾老师好,我是小吴循”。读到这句话,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小吴循当年的模样:白白净净的,个子小小的。那时候我们都住在马桥街,每天上学、放学都同来同往。如今的他,在上海工作,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陶涛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在苏州工作,他在班级微信群里发过一双儿女的照片,儿女长得都像他。是的,时隔二十多年,我们师生竟然又相聚在微信群里。每次我在群里出现,王争庆就点名喊班长:“老师到了,赶紧喊起立。”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样,那么爱逗乐。
张炀,发给我的近照里,他一身商务正装。真的很难想象,这就是当年的那个瘦瘦黑黑的淘气男孩;更想不到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家在回忆往事时,他这样说道:“当年顾老师家里的蚊帐是白色的。”当年,他们常常到我家玩,他们说怕其他老师,唯独不怕我……
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做老师的特别多,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都有。前几天和我联系上的许啸在大学里教书,已经申报副教授了。我的学生如今分布在各个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泰州……
去年端午节,我去无锡,张瑜来看我。那晚我俩聊了大概四五个小时,聊她学生时期的事情,聊工作,聊家庭。
我记得我对她这样说:“其实想想做老师真的是很幸福的。你看,我和你们已经分开二十多年了,可是你们依然记得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你们依然把我当作最信任的人,把你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与我分享。我想,这可能是从事其他职业都体会不到的幸福。”
一苇是我在无锡工作时教过的学生,她特别有艺术天赋,她手中的陶泥随便捏几下,就成了栩栩如生的作品;随手拿一支笔,就可以画出非常灵动的画。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她特别喜欢画蝴蝶,下课的时候身边总是围着一圈孩子,只要她画出一只蝴蝶,就会被孩子们要了去。我还记得她做过九尾狐小玩具,用那种很细小的铅丝,绕出九个小圈圈,拴上九条尾巴。她做的九尾狐,尾巴都是会动的。每一次看到她,我都觉得无比神奇,这是一双怎样灵巧的小手?当然,她也有让她妈妈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写作业速度很慢,所以她妈妈就很着急。
我记得有一次放假之前,一苇妈妈来问我:“顾老师,假期里我要不要给一苇报一些补习班,买一些学习资料让她复习?”我说:“千万不要,如果你非要给她报班,建议报一个美术类的,因为她对手工、对绘画是那么痴迷。”好的教育,真的不是一味地去补短,而是要尽可能地发现孩子的一些长处。
其实,我觉得教师就像摆渡人一样——我们一直在这儿,而一批批的孩子,他们来到我們身边,和我们相处几年,等到他们变得更智慧、更丰盈,我们又送他们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很多毕业多年的学生,说现在依旧会有每天读书的习惯,依旧会有写作的习惯,还说这一切都是当年受我的影响。很多年过去了,他们早已忘记了我曾经教过他们什么知识,但是这种对阅读、对写作的热爱,是时光无法带走的,也是他们无法忘却的。
当然,我觉得这种影响不仅仅是让你有了对阅读和写作的热爱,这种热爱,可能还让你对一切美好的事物有更敏锐的感知力,对一切生命也会有更深切的悲悯之心,当然,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也会有更真诚的关切。
我记得我的一位学生家长曾经说过:“顾老师,你带给孩子的影响真的很大。孩子说顾老师看到好看的风景都会拍下来和我们分享,我看到好看的东西,也要和老师分享。顾老师,你对美好事物的这份热爱,真的可以感染学生。”
在上海工作的这几年,我和我的家长们一起创建了班级图书角。每当看到孩子们坐在图书角看书的时候,我都觉得那是特别美好的画面。我还常常带着孩子们去图书馆,他们静静地看书,我也静静地看书。我会把精彩篇章分享给我的学生,他们也会彼此分享。这是在纯粹地享受阅读的快乐,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
我还带着他们写观察日记,让他们写种子成长记。每个孩子准备一粒种子,可以是蔬菜的种子,可以是花卉的种子。他们种下这些种子以后,观察种子的生长过程中有哪些变化,比如发芽了、长叶了、开花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写下来,把自己在等待种子发芽时的心情写下来,把自己怎样照顾这盆植物的过程写下来。他们写的一篇篇种子观察记录,后来陆陆续续发表在《全国优秀作文选》——这本杂志当时开辟了一个专栏,发表我们学生的作品。
我还和孩子们一起把他们写的诗搬上舞台。我们节目的名字叫《童诗日历》,从春夏到秋冬,我们把每一个日子过成诗,我们把每一首诗写进日历里。
台上的孩子在表演,台下的孩子和台上的孩子齐诵。我记得当时有家长观摩了这个活动,他们把视频录下来分享给我,说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湿润了眼眶。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孩子们的诗作多么精彩,而是这样的氛围让我们感动;孩子们在舞台上朗读自己诗作的这种自信,以及台上台下孩子互动的这种和谐,让我们感动。
我就想静静地教书
《中国教师报》有个征稿活动,名为“童心绘诗”。我们班的周诺妍画了一幅画,并配上了这样一段文字,发表在《中国教师报》上:
喜欢她,她像一只可爱的猫,但这只猫也有独特的脾气。她不要求我们默写抄写,她带着我们读诗写诗,把我们领进诗歌的海洋。她爱穿中式服装,不爱花哨的图案。她喜欢带我们亲近大自然,给我们写作的灵感。我喜欢她的语文课,她朗读课文时,我仿佛身临其境般被带入其中。我总是想:为什么下课铃来得那么早?
诺妍的这幅画,我前几天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也带回家了。我想我会一直珍藏着它,这也是孩子给我的一个难忘的回忆、珍贵的礼物。
在学生和家长对我心怀感激时,其实,我心里也充盈着对学生的感恩,因为,他们是我热爱讲台的全部理由。
感谢你们让我对这个世界依旧充满好奇。因为这份好奇让我的五官与心灵一直敏锐,岁月的流逝没有让它们产生丝毫钝感,美可以感动我,爱可以温暖我。
感谢你们,让我依旧保持着不经雕饰的真。我不掩饰自己的喜怒,我坦陈自己的爱恨。因为你们,我只敬爱真正值得敬爱的,因学识,因人品,因情怀,不谄媚位高权重者,不怠慢人微言轻者。
感谢你们,让我宽容并悦纳一切不完美。宽容别人的错,不计较、不记仇;悦纳自己的不完美,不哀叹命运不公,在反思中不断提升自己。
“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让这个世界因为我变得更美好。”这两句是我和我的孩子们共勉的话。感谢生命中遇见的所有孩子们,你们让我成为一个更美好的自己。
去年8月,我的新书《我就想静静地教书》出版了,书名是编辑王玉梅老师给我取的,我很喜欢。一开始,我的书名暂定为《静静地教书》,但“我就想静静地教书”比“静静地教书”更有力量,有一种坚定的意味在里面。
2014年评上特级教师以后,我有很多机会离开一线,比如去教师发展中心或教研室,当时教育局的领导都找我谈过,而我婉言谢绝了。我说:“对我来说,我最幸福的事就是带一个班,与孩子们朝夕相处,陪着他们长大,陪着他们在文字的海洋里遨游,让他们感受到文字的美,培养他们对文字的热爱、对这个世界的热爱。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幸福的事。”
我就想静静地教书……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
(插图:谭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