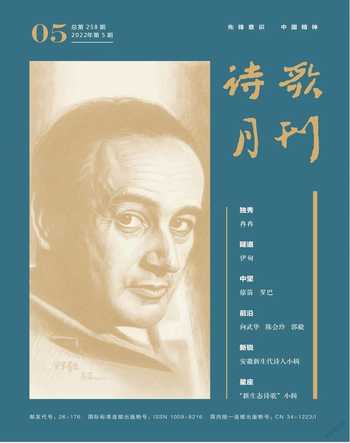交织万物的金梭(组诗)
2022-05-24冉冉
冉冉
鸽子
布谷啼鸣中
鸽子飞出了苞芽。
最顽皮的那只
飞出一小块岩石。
石头开花是它的梦,
这会儿它是自己的果实
披着灰色的锦袍。
它喜欢瓦灰的华美,
昼与夜的中间色——
即便是飞上了云端。
不像某些亲眷,
一靠近梨树就变白,
如果飞上樱桃树,
红得简直像皇后。
从石头里出来的,
它结实的腿脚,发烫的
趾头和附趾,穿越
坚硬时空的翅膀……
它要奔赴邈远的天际。
那永久的巢穴,正发出召唤。
往前走
早起的人没有名字,
她游离在冬与春的模糊地带。
告诉她,往前走五百米,
有一道庄严的大门,
五百尊泥塑盘坐屋里。
最胖的那位把世人的泪水,
全都装进了笑声。
再走四百米,有一道铁门,
屋里对坐着两个母亲,
做媳妇的陪着婆婆啜泣,
每滴泪都攸关儿女的悲欣。
再走三百米,有一道木门,
少年正伤悼自己的恋情,
噙泪的眼盛满了迷惑与懊悔。
再走两百米,有一道小门,
门楣内几粒种子彼此抚慰:
它们仍要開昔日的花,
结往年的果。结果后天各一方,
开花时亲密相依。
再走一百米,有一道
清透圆润的门。一颗露珠
结束了闭关,即将启程。
它要去往天地,融入无垠。
那些石梯
她不说出那些石梯,
是因为心里有更长的梯级
隐入云霄。那一段彩虹之路,
红色的几级取自酒窖,
橙色的几级取自熙和的秋日,
黄色的几级取自漂移的趸船,
绿色的取自崖谷的春意,
蓝色的取自幽暗的梦境,
靛青取自夜的穹顶,紫色
则取自至深的懊恼……它们
一级级上升,像头陀
强行按捺的情欲。
直到时钟敲响
直到时钟响起,她才恢复视听。
键盘的噗噗声,
像葡萄酒在橡木桶内潜行。
葡萄丢弃了皮,离开骨肉,
失却了翅膀——再不能攀援,
也没有旁逸斜出,
只剩下无止境的航程。
葡萄变成了自己的酒,
时间变成了自己的尽头,
飞动的键盘声也寻找到了
各自的归宿。多好的酬劳啊,
十指探测出的浩瀚宇宙,
每个星系,每颗行星,
都有她熟稔的故里和挚友。
最先亮起的
最先亮起的是哪一盏灯,
随后才是第二盏,第三盏?
依次亮起来的前一百盏,
一定有着秘密的约定,
就像新年里秘密躺下的
前一百名有恙的人,雨
依次淋湿的一百座桥。
雾升腾起来,
逆流而上的船,
全都装满了白纸。
可以从头开始书写了——
一个人走进胡同,
他就是路灯,
坐进汽车,就是大灯,
登上轮船就是探照灯,
被浓雾遮蔽,就是无影灯……
他像落地的鹰那样蹒跚地走,
小心翼翼,将人类的秘密,
重叠进生命万物的秘密。
珠宝们
她出差时,首饰盒里的
宝贝儿最兴奋。短暂失踪
是它们最迷醉的游戏。
那条金色项链,
正笼络一个苦笑的女子:
“如果你能回家,我愿献上
储奇门金店的全部首饰。”
这宏愿比较离谱,而它所说的家
不过是某一刻雾散天青,
美丽颈项跟它的须臾亲近。
而她早已习惯了劳碌奔波,
尤其是修补漏洞百出的生活。
同时行贿的,还有和田玉镯——
“来来来,这儿有精致的优雅,
触摸得到的贵气。”受贿者
悄然浅笑,摆了摆头,
她企望的富贵来自手中的
一团乱麻。若讶异她抽出的
缤纷线绳,别出声,她变的不是
魔术,而是被烦恼磨炼的指头。
两只耳钉正黏住一位美妇,
“我是纯银的,比露珠
沉实,比忠诚轻盈。”
她听到的却是别的声音:
亲爱的菩萨,亲爱的菩萨,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新年快乐。
戒指也物色到了目标,
那是个尚未恋爱的少女,
“珍爱自己,不论何时都没错。”
女孩绯红了脸,她的爱
宛若才露尖尖角的小荷,
既非自己也不是他人,
而是一个簇新的世界。
发箍也跑到了某人头上,
犹如一顶熠熠闪光的皇冠。
“你是扮演你命运的第一人,
也是你顾盼自若的自己。”
那光芒炫目,仿佛真有王者气。
还有个天地
关机就寝。想象
短暂的死,在睡姿里弥散。
鸟儿知晓她死去,鸣叫声
没有悲切,反倒有几分喜庆。
从死中破壳而出,没死过几遭,
哪体味得出生的欢悦?
陪伴的车轮,为她驱赶边界,
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寬啊,
她辨识着逆光里模糊的影子——
雪峰的影子,奔马的影子,
迅疾掠过的自己的影子……
降下车窗玻璃,
风在耳道留下另一个天地。
还有个天地,在雾城。
她伸手使劲儿擦拭玻璃,
好奇怪,明知是梦境,
她仍旧告诫自己——
城内的一切都真实不虚,
清晰、致密又确定。
交织万物的金梭
十点,她放下书,
打开手机浏览朋友圈。
稀疏的树掠过车窗
那是小欧去往亚丁旅行。
沿途风景扰乱了心流,
她的上午于是与她们不同。
气温又下降了,
等待瑞雪的故乡很安详。
黄栌与枫叶纷披的群山,
是人们古老的友邻。
有牧羊人风中缩着脖子,
“西北风,我几口就被灌饱了。”
他胸腔和衣袖都装满了风。
她无辜地道了声歉,
祈愿他的耳朵不再寒冷。
“走了就走了。哎!”
走丢的是小羊,猫咪,
抑或不久于人世的老狗?
不想主人伤心,临终的狗
总是悄无声息地离去,
主人的平静也同时被洞穿。
有人摸进邻家,顺走了
巧克力和空调遥控器。
业主叹:“数九寒天,做小偷
也很难,该在客厅放点零钞。”
保安问:“真没丢别的东西?”
当然有,冷漠之外还有怒气。
“羞耻感又回来了。意识到羞耻,
比赢得荣誉更要紧。”
两个男人举起酒杯:哥俩好。
感谢你我的纠缠和成全。
感谢扮演敌手的对方。
交织万物的金梭在哪里?
泪的星光在她眼底一闪。
陌生人之歌
凌晨三点依然无眠的人,
没有被看见。他也看不见
自己的脸,但许多脸自动前来,
做出形形色色的表情。
某一刻,他瞥见了
一位陌生人,面孔无瑕,
还不曾留下酸辛的痕迹。
他不允许自己搭讪他,
他怕不小心说出难堪的家丑。
夜复一夜,他的唇拦截了
太多怨怒,尽管都是对自己。
他忍不住捂紧耳朵——
设若对方开口,如何应答?
对他而言任何致意都是讽刺,
唯有叠合的手让他稍感慰藉。
上床前他曾小声祈请,
愿左手拥有的巧智,
右手也能分得些许。
窗外星光并非来自夜空,
而是源于勾画城市的灯盏。
从它们重塑的街市,传来
发自他人身体的自己的足音:
他正赶往超市,打算购买
洁具和镜子。
目力所能见的幸福
你只专注目力所能见的幸福。
此刻,你的愿望是看清
即将拐弯的溪水和水底卵石。
你看见水流无声地离开,
去往它们倾慕向往的广阔。
那柔弱而无从量化的水,哪怕是
升起在高空,依旧保持哑默。
你相信那些个头儿大小不等,
或光滑圆润或峭拔峥嵘的卵石,
都是溪水的忠实拥趸,也想
追随着去往倾慕的水域。
其实你也不知它最终能否抵达
大江的支流,因为它将流经
太多的天坑地缝,暗洞溶岩——
这是一次又一次反复临渊,
九死一生的凶险之旅,却也是
它的节操,它的宿命和光荣。
被重新忆起的人包围着
“我被重新忆起的人包围着”,
她记不清这句话来自哪里,
重新忆起的又是哪些人,
包围她的气息后来又包围过谁?
后颈感知的吸呼由热变凉,
那嘴唇随后吐露的语词,
是否多过她所见的花朵?
她所谓的花朵包罗万象,
有未污染的云,孩童的笑脸
伴随祝词的杯盏,某人喜欢的
设问句:“我们如果能回到
无忧无虑的童年,洪水会否
携来滔滔的泥沙卵石,
阻断我们的尖叫和虚假的宁静?”
无法替代的哪一个,结果
替代了谁?四处告别的
那个人,最后告别的是谁?
某日她遇见一位神乎其技的
锁匠,音容熟悉恍若来自前世,
可她却始终没能叫出他的名字。
闺蜜和伙伴
他们去了另一个星球,
人数不到十个。通讯录里
她并没有删除他们,
心目中彼此仅只是暂别。
待到再见,背景自然会更换,
不过她坚信自己识别妆容的擅长。
重逢时,两颗星替她同闺蜜紧握,
不是用手,而是用身与灵淬炼
的极光。幼年的伙伴邀约着
穿越极地,那是先行者的驿站。
他们省下的空气正供养着
越冬之物,当她在溪畔俯下身,
似曾相识的菖蒲、水罂粟也将她端详。
那是另一些,通讯录上遗忘的
密友,曾共度过多灾多难的世紀。
他攀爬过七八个天坑
为了一次玩笑,
他把脚印上了摩天楼光滑的幕墙:
“从这个角度可以得见,
整条河流和全部的心。”
他说的河是蜿蜒东流
无法回溯的那一条;
他说的那些心遍被白雾,
没有一颗空置在外。
为了一次玩笑,
他把嗅觉伸进了
城里的每个角隅:
从噩运厄运背运中
嗅出了煤烟和栀子花的气味,
虽然那气息极为淡薄。
没有哪个倒运的人,
如他这般乐观:
他向后绷直左腿,张开双臂,
像鹰隼一样滑行。
他不在意脚下的冰,也不把
晕眩的高度当回事,因为
他攀爬过七八个天坑,
并测量过坑体的大和险。
夕辉照临
夕辉照临后山的峰顶。
这无名的大山,有名的水杉、
润楠、枫香和低伏的蕨类,
林木的絮语蜷缩在球果内,
蝴蝶点亮了杜鹃——“冥想吧,
冥想吧,冥想是完美的剧场。”
声音溢出枯叶的边缘,
温吞如蜗牛,肉乎乎的触须
又软又笨。故乡被小半窝黑蚁
包揽了谜底,相近的烦乱
跟远方的城市一一感应。
回环往复的气流牵引着你
着落处不是地面,而是漂移的
瓦房,墙上布满筋脉与涂鸦。
你仿佛得见父母和长辈,
曾经的初恋,蓄势待发
却从未点燃过的爆竹,
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杜鹃树上。
家乡即遗忘之地,它是
游子心和先人们栖息的所在。
雾霭自看不见的沟壑升起,
驻留的树声,跟母亲逝去的
乡音一样。每次辞别木樨,
你都会默念再见,到来年,
它们开始的却是另外一生。
遇见
一整天,你都隐身在细雨里,
以静默跟所遇之物交换。
槭树的苞芽高低错落,
它示爱的时候全身只剩下嘴——
疯狂的嘴唇,因喋喋不休而鲜润。
积压已久的,无以言表的,
被它说了个透彻干净。
不甘寂寞的是车前草,
“车轮草,车轮草……”
它喜欢喊叫自己的别名。
请倾听一株草在自己身上
疾驰的声音,听它如何越过
乌有的天堑。当它偶或停顿,
那不是与末路和解,而是别辟蹊径。
星天牛说得最为欢实,
同时舞动天线样长长的触须,
谁都会被它当成知音,
语速飞快,因为要宣泄
太多的柔情蜜意。
那片薄薄的云彩也说起来。
为方便听者,它猫下腰,
嘴唇触到了树梢的鸟巢,
灵巧的舌头濡湿亮白,
它转瞬即逝,像一阵晕眩。
玉米
空地上生长的年幼玉米,
单薄羸弱的身姿摇摆不定。
透过窃窃低语,你辨出了
一如往昔的熟悉口音——
这是来自慈爱长辈、亲友邻舍的
亲切面容,以及更多
随缘而至的熟稔之声。
玉米灌浆挂穗,金黄的棒子
循屋檐往下一摞摞倒悬,
自五个世纪前赓续到当今,
乃至五个世纪后籽实的隐喻,
此前的你并未真正留意,
有如火种蛰伏在燧石里面,
觉悟发端于苦难的肉身。
冬日阴冷,静默的村庄边缘,
野草或稀或密,点缀着
小块空地,棚舍栅栏间
虎纹斑斓的流浪猫一闪即逝。
柿子
它发声清脆,类似黄鹂,
飞短流长的嗓门儿煞是迷人。
色相与味蕾的魅惑之核,
悬挂在秋风里的甜蜜陷阱,
在久远时间里缓慢蓄积,
最终生长出明艳的黄金。
多么柔软多么通透的黄金,
你知悉它取之不尽的来路,
怎能不收回旁驰博骛的心?
经过千山万水,你遇见的
所有声音都在述说相同的事情。
你确信,那两枚柿子刚才
停靠在灰褐的枝桠上,
顺便捎来梦与醒的消息。
含泪的苹果花
闭上眼睛,你就是花满枝头的
苹果树。你是那九万九千九百
九十九朵盛开的花儿,也是还未
开出的最后一朵——或者是半途
正在赶来的最后一朵。你承认
自己个儿小速度慢。每走几步
就要停下来,为那些永远也不会
再开的花祈祷,为刚刚绽放
便凋零的花朵祈祷,为一边开花
一边流血的苦难的大地祈祷。
有没有谁在暗中记录大地的花开,
从花的数目,到每朵花的结局?
迟到的花,向近邻打探它的游戏,
不同的规则让每朵花的容颜
都不尽相同。蜜蜂拜访过的那朵
正接待飞来的种子,果实还不见
端倪,它们已开始互换酒的香醇。
世界的灾变在远处加深,难以
寻获片刻宁静。绿风加入进来
它的方言和春的隐喻,不及思量
当你睁眼,只见满树含泪的苹果花。
百里梨花
百里梨花,犹如新家。
那是母亲的新家。
一切都跟曾经有过的相反。
盛开,即是愿望的圆满——
她生前未成就的愿望,每天的
祈请,都以无边的花事现临,
每朵花都展演着她的痴心梦想。
再没有苦难,苦难都掉进了往昔,
再没有屈辱,屈辱都长成了花托。
花被上无字的欢乐,经日月变幻,
并置成了花瓣的吉祥。
一生的瞬间须臾映现,世代的
声色悉数映现——百里梨花,
一树树,一朵朵,多么明净的悲欣。
母亲穿过你,径直走向你的儿女,
那无始无终的套娃——敢问
迎候她的不叫人间又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