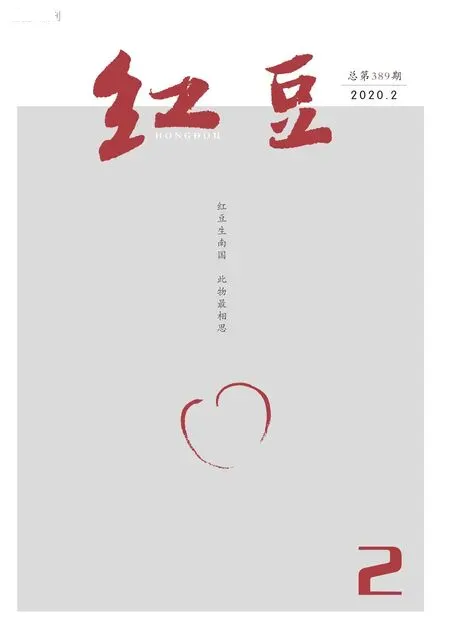遗落的雪国(短篇小说)
2022-05-21房子兮
房子兮
镜中的雪越发耀眼,活像燃烧的火焰。
——川端康成《雪国》
“在世界的尽头是一大片雪地,我们都叫它‘雪国’。”我始终记得这一句话,那是母亲在临走时告诉我的。我依稀记得,母亲用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好几眼,才依依不舍地脱下白大褂,缓缓离去,只留下一滴晶莹的眼泪。我惶恐不安地盯着周围的一切,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离我而去。母亲姓陈,她在研究所工作了很多年,人们曾经尊敬地称呼她为陈博士。但那天之后,她却永远消失了。快十年了,屋里那股发霉的味道至今仍在我的鼻子里游荡,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叫陈雪生,是母亲给我取的名字,母亲最喜欢一种叫雪的东西,那是远去的时代的自然现象,现在早就消失了。
当时我还小,从旁人口中大概知道,我出生前全球变暖,地球上再也没有了雪。瘟疫爆发后,活下来的人在高原建起了无数个巨大半球状建筑——黑白城堡,这是人类最后的家园。城堡一半透明被称为白墙,一半被黑色包裹被称为黑墙,黑白墙之间有一个铁门,据说只有首领才有打开它的钥匙,我甚至不知道白墙里的人长什么样。精英人士住在透明的白墙内,可享受阳光和自由;黑墙区域住着被病毒感染的病人,虽然不会传染,但致死率极高。这里的人都要做一种手术:用阿尔法阻断剂,从上眼眶刺进去。我曾亲眼看到过。我的心一颤一颤,呼吸急促,腿脚发软,看着都觉得疼。可病人似乎没有丝毫疼痛,做完后还嘿嘿地笑,被士兵搀扶着下去。
“看到了吗?这就是科技!你们都是病人,只有做这种手术,脑中的病毒才会消失!首领仁慈,采用的是纳米机器人,针头大小只有头发的千分之一,不会产生任何疼痛!”一个中年男子挺着啤酒肚,穿着黑西装,大声吼道。
人们你推我搡,争相做手术。母亲却抱着我往人流相反的方向跑去……
不过,无论白墙还是黑墙的人们,别说是雪了,连雨都很少见到。人们只知道雪是个白色的东西,很凉。
没做这种手术的,可能只有我和母亲。我不也没死吗?少部分人也曾抗拒,也批评过手术的危害,但影响甚微,他们像蜻蜓点水一样,在这个世界产生微小涟漪,随后就消失不见。
母亲临走前,曾给我留下过一部学习机,我悄悄地跟着它学习,掌握了很多知识。我喜欢文学,在我的家里,偷偷藏了很多禁书,都是过去时代的书。我最喜欢一位叫川端康成的人的小说《雪国》。他似乎得过过去时代的最高奖项,叫什么诺贝尔文学奖的。在他的描述中,我仿佛置身于雪国,那种空灵缥缈的美让我陶醉。非常羡慕那时候的人。我们虽相隔几百年,但我似乎能看到他布满皱纹且充满慈祥笑容的脸,我们时不时在灰暗的房间里交流。我们的心似乎在共同颤抖。
在别人眼中,我是这个世界的怪胎。我不知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其他人别说读书,大字也不识几个。听说过去的时代还有学校这种东西,但首领说这是落后的东西,我们只需劳作,无须学习。精密的仪器随时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有人偷懒,等待的是严厉惩罚。这里的人们,都像失去灵魂一样,每天无休止地劳动,唯一消遣的就是晚上看短视频,视频都是城堡监制的,无非是宣传黑白城堡多么好,科技多发达什么的,年轻工人偶尔刷到美女跳舞的视频,就像发现了什么宝藏似的,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拍着布满茧的双手大笑。
我身体瘦小,不能支撑大量的劳动,挨打是家常便饭。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都这么有力气,即使累死也不会停下。他们好像不知道累。久而久之,我感觉世界灰暗,经常失眠、惊厥,心情低落,有好几次都有轻生的念头。可我还在坚持,我时常想起母亲说过的世界的尽头。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过,雪由无数小雪花和小冰晶构成,北风萧瑟,卷起万千雪,无数雪花像白色的天使在空中漫天飞舞,雪铺在地上,踩起来软软的,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那是真正的雪国。我听得入迷,没注意涎水从嘴角流出。母亲微微一笑,用手绢给我擦嘴角,我也跟着大笑。在那个阴冷破旧的小黑屋,我感到了温暖和光明。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世界的尽头看看。
又是灰色的一天。空气似乎凝结成一个巨大果冻,闷得让人喘不过气。由于资源匮乏,燃油机器早就停用,新能源造价太高,所以大部分机器还是靠人力维持。
黑白城堡的自动控制仪房间,就在城堡的大门旁边。守卫森严,不但有一千多名精锐士兵,还有成千上万的机器,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它们都靠着来自黑墙内的工人手动运行。
突然,有个工人跌跌撞撞地跑来,结巴着报告,好像有仪器坏了。一个士兵懒洋洋地去检查,他打开仪器外壳,脸变得惨白。一台机器的电路板被破坏了。更让他受到惊吓的是,通往城堡外面的大门,居然被推开了一道缝隙,那条缝隙不大,但闪着妖异的光,似乎连接着一个神秘空间……
紧接着,士兵后脑受到一记重击。他昏死过去,倒下之前,他似乎看到了什么……
黑白城堡最顶端,有一间不太大的小屋,屋子虽小但装修得富丽堂皇,屋里几个人正在焦急地讨论什么。他们年龄不小,神态傲慢,岁月在他们的额头上留下蚯蚓般的痕迹。
“你说的是真的?黑墙里竟然有人懂电路?而且还让他跑了?”一个腿残的老议员对着士兵大吼,他似乎要从轮椅上跳下掐断他的脖子。“议员先生。”士兵紧张地吞咽了几下口水,艰难地说,“我当时吓坏了,又被打倒在地,但那小子的确穿着黑墙人标志的套头衫,这点我没有看错!”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黑墙的人也懂电路。”一旁的独眼议员,用仅剩的一只眼,瞥了一下挂在墙上的油画,缓缓地说道。
“这是一条漏网之鱼,看来没做手术。”残腿议员拍了一下额头,“快去追啊,不能让秘密泄露出去!”
“也不用太紧张。”独眼议员说,“没人能逃离,尽头是不存在的,更是坚不可破的。每隔几年,城堡总是会出几个异端,但他们成功过吗?”
残腿议员搔着头,重重地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恶狠狠地说:“那也要追捕!我们要杜绝哪怕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大雨倾盆,顺着我的脸庞流下。不知多久没下过这么大的雨了,是雪融化后的雪水吗?
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滴混着空气中的尘土,像子弹般砸向我。不知为何,母亲在我童年时教的东西,现在全用上了。在学习机上学到的知识,更让我保持着出奇的冷静。我骑着过去时代的摩托车,带着一桶汽油就出发了。
逃离了黑白城堡,我向着心中的目标努力前行,连我自己都庆幸这次行动很顺利,最起码现在是这样。路上寂静得可怕,雨点不断模糊我的视野,到了傍晚,什么也看不清了。耳边只有轰鸣声和急促的喘息声。黑夜正张着黑洞洞的大口,等待着吞噬我。我不知远方有什么,不知道世界的边缘在哪里。我只知道,那里是雪国,那是我的归宿。
猛地,我听到后方有警笛的咆哮,他们竟派出最先进的电子飞车来抓我,看来我被发现了。可是我已别无选择。突然,一个金属小球吸附在了我的车上,摩托车瞬间熄火,我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看到前方有一座小沙丘,我来不及擦脸上的血,踉踉跄跄着往前跑,躲到沙丘边。我大气还没喘一下,就被按住手臂,紧接着一阵剧烈的疼痛瞬间遍布全身,原来我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也被附上了一个小球,球上赫然写着:阿尔法阻断剂。
我狠狠地将小球扯了下来。奇怪的是,剧烈疼痛过后,我又恢复了正常。
飞车缓缓地停在了我的眼前……
“陈雪生,你认罪吗?”黑夜之中,在离黑白城堡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一个身穿红色铠甲的士兵走下来,看着地上的一个瘦弱的少年问。少年被人死死地按在地上,五脏六腑似乎都要裂开了。
铠甲士兵奇怪地看着地上的阻断剂,说:“怪事了,怎么没起作用?”他又大声问,“陈雪生,认罪吗?”少年默不作声。士兵抽出短棒一甩,短棒瞬间变长,每一节都有黄色电流涌过。少年知道,被那东西打一下,必死无疑,但还是恶狠狠地盯着他。
“死不悔改!”铠甲士兵嘀咕几句,举起棒子就打过去。少年缓缓闭上眼睛,任凭泪水夺眶而出,喃喃地低声说:“这残忍的世界!”
“等一下。”一个高大的身影从车里走出,他的左脸带着钨钢面具,穿着黑色金属外衣。少年诧异地看着那人。
“首领,你怎么下来了?”铠甲士兵尊敬地说。“哎呀,难得下这么大的雨,天降异象呢。”首领伸了伸懒腰。面具在暴雨的侵袭下变得锃亮,“既然你不愿认罪,就让你妈替你吧!”首领打了个响指。
少年身体抖动着,下巴合不上了。一个人被麻袋包裹着,被两个士兵从车里抬出来,狠狠地扔在地上。麻袋中的人被粘住了嘴,发出呜呜的声音。听声音,是个女性。少年一下子跪了下来。
“跟我回去,否则你妈就得死!你妈是那个姓陈的博士吧?”首领掏出把老式手枪,“过去世界的人,就该用老式武器杀死!”
“不要——不要——”少年哭喊着,踉跄地站起来说,“我回去!我认罪!”
手枪枪口冒出浓烟,鲜红的血液从麻袋里边汩汩流出。少年不顾一切跑过去,抱着尸体痛哭。他颤颤巍巍地打开麻袋,又愣住了,眼泪挂在脸上,时间似乎暂停了。
“哈哈哈。”首领大笑道,“我根本没见过你妈,你妈十几年前就失踪了,谁知道是死是活?弄个死囚吓唬吓唬你而已。”
少年从悲伤变成愤怒,要不是几个士兵按着,就要去和首领拼命。
“小子,我可以放你走,但一旦离开就再也不准回来,行吗?”首领摸着下巴说,“外面凶险无比,你还是跟我……”“我愿意!我不回去!”少年打断他的话。首领露出惊讶的表情,但很快板起脸来,说:“希望你不要后悔。”
雨停了,飞车卷起阵阵泥泞,绝尘而去,只留下那个孤单的少年的身影。
“雪国什么的,根本不存在,是疯婆子幻想出来的。”首领望着远处,喃喃自语。
“那为什么还放他走?明明是死路还要去?”铠甲士兵褪下战甲,对首领说。“人一旦没有梦想,跟黑墙内那群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那小子既然能逃脱阿尔法阻断剂,说不定还有千万分之一的成功机会。说起来,我们年轻时都为之奋斗过呢。”首领缓缓摘下面具,面具下的那半张脸,有一条似黑蜈蚣般触目惊心的伤疤……
我看着他们离去,全身火辣辣地痛。我好像看到远处冒出的黑烟,它们在大雨中顽强地窜向天空,如同一条狰狞的龙。
我也不明白,首领为什么放过我,但我努力不想这些。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天空忽然亮了一下,似有流星划过。我别过头去,朝着远方继续前进。不知过了多久,摩托车贪婪地舔光了最后一滴汽油,瘫在地上起不来了。我扔下摩托车,继续前进。雨停了,空气中出现了泥土味。我拖着身子,一步,一步……
我的脑海中出现了波澜:为了一个所谓的希望值吗?接受现实吧,你就是这个世界的怪胎,你应该去接受手术。我绝望地使劲摇头,希望把这些声音甩出脑外,但它们异常顽强,挥之不去。就在这些思绪折磨我时,我看到了边缘,这个世界的边缘。我发疯似的冲了过去,瞬间愣在原地,用发红的眼看着眼前的一切。那是一面万丈高墙,四周全是沙漠。
我抬起似灌满铅的腿,慢慢走到墙边。沙漠很厚,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竟有一丝错觉,恍惚间,我把左脸慢慢贴近墙壁,感到了一阵冰凉。这感觉,就像雪在脸上融化。这一刻,我身体的热量,与这雪国合二为一。
迷迷糊糊中,我像是来到了被遗落的雪国,和母亲说的一样,这里是被雪装点的世界。我抓起一把雪敷在脸上,对,就是这种感觉!凉凉的。和川端康成说的一样,这里是那么静谧,那么美好。母亲站在石板上,微笑着向我招手。她花白的头发是用雪染的吗?我的嘴角微微上扬。
我名叫雪生,却终生没见到过雪……
“陈博士,黑白城堡虚拟空间的202号电子实验体,已无生命体征,第五十四次实验失败,请求处理。”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摘下口罩,向陈博士陈述着。
一个清瘦的少年,全身挂满感应器,静静地躺在床上,身体越来越冷,只有那双大大的眼球,还在使劲地瞪着,似乎要挣脱眼眶。在少年的床旁,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摘下连接感应器的头盔,看了看眼前屏幕上那个半黑半透明的城堡,眼圈泛红,叹了口气。她的大衣口袋里装着一本书,是川端康成的《雪国》。蓝白相间的封面,似乎是用雪装点的。
“对不起,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得不牺牲你,不管你是我的雪生,还是202号仿生实验体。下辈子吧,下辈子咱们一起看雪……”陈博士摸了摸少年的额头说,手颤抖着。少年仿佛睡着了,眼睑缓缓地闭上了。
“看吧,外面下雪了。这就是雪。”陈博士刷地拉开窗帘,已经泣不成声。所有工作人员默默起立,似乎都在为这个电子仿生少年默哀。
窗外,大雪纷飞,银装素裹,可是观赏的人甚少。再远一点,一群人站在一个大平台上,他们在试飞新型机器,全然忽视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学校里,一群新入学的小学生在学习一元二次方程,他们都是真正的人类,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类,他们的表情却和那群做完手术的黑墙内的人们一模一样。
陈博士将那本《雪国》放在少年的手心。少年软软的手指,正插在一片书页的中央。陈博士打开,上面赫然写着“无论如何努力,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