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的夹缝里开花
2022-05-20仇士鹏
仇士鹏
这两年,我从一个忙着上课、备考的本科生变成了拥有学术研究、处理横向项目的硕士生。最大的变化就是曾经可以肆意挥霍的业余时间从大浪里的沙变成了黄金。
没时间写作,这是很多非文科专业的文学爱好者总会遇见的问题。
我曾用疯狂形容过我本科时的写作状态——就像是一支笔穿上我的鞋子行走在人间。
为了给老家报纸投稿,我把市里的所有景点都走了个遍,从5A级景区到不为人知的小公园,甚至是一条只有老人才能叫出它的诨名、地图上都无法搜索到的河流,每处草坪上都有我的脚印破茧成蝶,每处残荷旁都有我的耳朵在听雨。采风和写作成了大四保研后的主旋律。每天大脑都会被腾出一部分来思考,所见所闻能否以某种角度写进文章,或是能否提炼出某种生活哲学。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周,每天都强迫自己写上一两篇文章,结果五天后眼睛迎风流泪,手掌弯成鼠标的弧度,僵硬难以屈伸。但心是畅快的,心灵充满了尽情释放后的酥麻与绵软。
不过,这样的随性和纵情注定要一去不复返了。

读研后,出差、做项目与改报告循环滚动,让大脑变成了老式的烧水壶,壶盖转着圈跳个不停,生活则像是被爬山虎层层包裹的墙,看不出本身的颜色和质地。写作,作为在导师眼中会导致不务正业的玩物丧志,不得不转入了地下。
它从一条浩浩荡荡的江河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溪流,成了在泥缝间渗漏的地下水。我在等待程序运行的时候写,在早上起床老师发来消息前写,在把改好的项目发给老师后用余温尚存的夜色写,在地铁上写,在出差回宾馆后躺在酒店的床上写……写作成了见缝插针的活计。但一块岩石,也正是因为夹缝中生出了一朵娇艳的花,才有了下自成蹊的魅力,又怎么舍得把她摘下,重归于平凡和蒙昧。
这种夹缝里的偷闲也改变了我的写作习惯。以前,我习惯用半天的时间去完成一篇文章从无到有、从模具到成品的创作,要么不写,要么就把它写完。而现在,我在空闲时,往往仅写下只言片语,最多是一个段落,然后用多个日夜将各个段落完成,删减、增补、润色后,再串在一起。这样的文章必然是少了“第一时间”所带来的鲜活与绝对纯粹、真挚的抒情——拉长了战线会让人瞻前顾后,对当时的情绪和观点产生怀疑和犹豫,但也因此,让文章有了辩证、成熟和圆融的机会。穿越时间的回眸,往往能在一颗心脏之外看见更辽阔的山川。
不过,这种碎片化的写作肯定不是我本来所期望的。所以刚升入研二时,我时不时就会陷入烦恼与愤懑中。
譬如,当我捕捉到一个罕见的、巧妙的、别出心裁的灵感,并且文章的框架和脉络都水到渠成地在脑海里浮现,让我忍不住想大刀阔斧、挥毫泼墨的时候,老师就会发来项目,并且马上打来电话,强调道:“非常急,无论如何今晚都要发给我!”
等项目做完,已经是夜晚十一点,回宿舍的山路要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才能穿行,并且能见度不超过一米,回去就要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昨日的灵感已经成了黄花,再也想不起来了,即使昨日曾记下些许内容,但是竟然想不出合理的逻辑把它们衔接在一起,忘记的部分让它像粗制滥造的木偶,不再活灵活现。郁悶是一场大雾,在道路两边弥漫,吞噬了树林与湖泊,连橘红色的霞光都无法穿透。
但生活本就是无奈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只能选择和它妥协,无论用怎样的方式,都要和它达成和解。以某种协议停战、握手言和,这是唯一的结果。
我开始学会体验遗憾,抚摸夹缝,沉浸在它带来的纠结、迷茫与痛苦中,感受着它们如何在细小的血管与神经里奔流,如何把血管撑得鼓鼓囊囊,并且在心里源源不绝的牢骚中找出我舍不得放下与坚守写作的根源。
我想,我是要感谢夹缝的。相比于草地上的种子,生活在夹缝里的种子更能知道自己会迸发出怎样的热爱与冲劲,会怎样执着地向往、虔诚地祈祷并最终竭尽全力地投入春天。正是一步步地发现、意识到了这种心灵的倾向,我们才能让生活更加靠近命运在最开始就暗中设置好的倾向。我也渐渐明白,文学可以是一种职业,也可以不是,它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如果说文学曾作为一道光,照亮了我陷在阴郁中的瞳孔,那么现在,我自己就是光源,一个发光体。正是处在夹缝里,我才得以一次次地重新观照文学的初心,并思考在当下人生的阶段,我该如何处理文学与生活的矛盾与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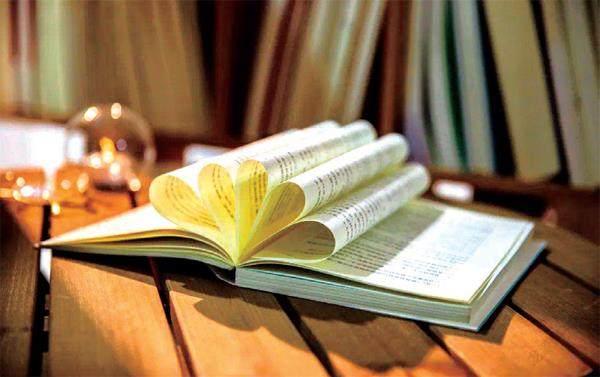
我终于明白,生活的一切和一切的生活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土壤。它未必需要古色古香的书桌、安静的窗子和完整的时间,限制了写作时间的夹缝也可以成为写作的内容。即便是常被批判的物欲、匆忙和浮躁同样可以成为文学的诞生地,只不过是用反省的目光去观照而已。
这株生长在夹缝里的小树,渐渐地把根须伸向了夹缝之外,扎在了生活的全部。原来夹缝虽然是一种限制,但也是一种成全,一种只有依靠夹缝才能产生的指引与庇佑。
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就是自己感动自己,哪怕在旁人眼中你的行为莫名其妙、奇奇怪怪,甚至是矫情、无病呻吟,但只要对自己而言,那一刻的感动是真实的,那么文学就是受孕的,是一颗充满活力的种子,能在夹缝里开出水灵灵的花朵,让平庸的、丑陋的裸岩都成为美的代言人。
(编辑·李泽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