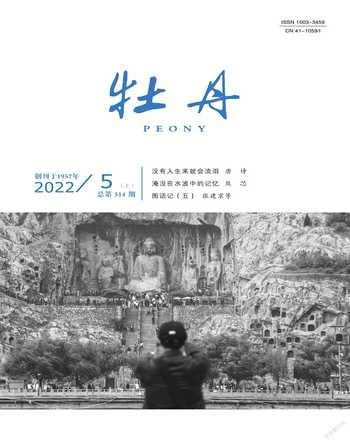倒流
2022-05-17石淑芳

石淑芳,笔名山女,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中国作家》《莽原》《山花》《雨花》《当代人》《天津文学》《黄河文学》《散文选刊》《台港文学选刊》等。出版散文集《长在山间的文字》。获河南省文鼎中原长篇小说精品工程优秀奖、奔流文学奖、延安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河南文学期刊奖。
一
半个月来,母亲像一个高血压药物的试药机器,每天白色、黄色、灰色的药片轮番上阵。但吃了一颗褐色的降压药后,她嘴巴麻木、头晕目眩,她捂着半个嘴巴踉跄着奔向护士站。那个圆胖女孩安抚着她先回病房,随后一群人呼呼啦啦涌进病房,给她吸氧,并上了心电监护仪。
去年春上,母亲肚子痛,在床上蜷缩了两天两夜。疼痛一波一波袭击着她,最终她两手摁着左腹,一步步挪进了村卫生室。乡村医生一番望闻问切后,扯过处方笺写了一封推荐信。让她去县城的结石医院看看。琐碎的农活,早屏蔽了母亲关于汉字的记忆,何况村医的字体手舞足蹈,更加重了母亲的无措。
母亲拿着推荐信站在路边,正午的阳光,虚晃晃从贴满公告的白瓷片墙上反射下来,映衬得母亲单薄矮小。安顿完家里的鸡鸭猫狗、内孙外孙没洗的衣服和要带的东西,她才能动身。她还担心一个人应对不了县城的庞大,眼看班车过去了,三轮车过去了,摩托车也过去了,她还怔在路边。
母亲的肾结石已经有段时间了,曾在县城医院作过B超,医生说结石位于输尿管上端,不好动手术。至于肾积水,先开几副中药回家敷敷,真疼了再来。一年来,母亲身上未尽的“石头”事宜,时断时续跑出来硌着我的心。这次,我坚持让她来市里看病。
母亲能来,实属不易,因为她之前做过胆囊摘除手术,她经历过恐惧和疼痛的折磨。选择乡镇医院是母亲的坚持,因为新农合报销比例高。取出的结石,碰撞在一起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正是这些斑斓的石头,給母亲制造了多次难以忍受的疼痛。
来城的那天,母亲和一篮鸡蛋被马虎的客车司机撂在一座不知名的建筑物旁。建筑物的名称,母亲在电话里只咬准了半个字。这半个字,让我顺着国道边走边寻。我浑身汗水汹涌地找到她时,母亲黝黑泛黄的脸上被镀上了一层被紫外线肆虐的金光。她的花上衣外面套着一件花马甲,她就那样花里胡哨地蹲坐在水泥台阶上,一手护着鸡蛋篮,一手搭起凉在棚茫然四顾。看到我那一刻,她先是释然,然后委屈,最后便是大声抱怨——没了父亲,母亲日子缝隙里的脆弱历历可见。
城里的一切,公交、电梯和自动挂号机,都让母亲表现出不能适应的紧张。她跟着我,眼睛像敏锐的探头一样东张西望,坐电梯时身子也会微微发抖。我抚着她的肩头,试图把那些不安一一摁住。
泌尿科的男主治医生很年轻,还很俊俏。他跟母亲开了一个玩笑,母亲不由笑了,紧绷的神经略略松弛。
左腹重度肾积水,需要住院治疗——主治医生握捏着彩超单说。母亲的表情又绷紧了:西红柿辣椒苗在塑料膜里都长老了,还是栽上再来吧?母亲看着我说。栽不上菜苗后半年我给你吃菜钱——我沉默而坚定地按照流程办手续,我不想给母亲一丝一毫的退缩机会。
夹杂在人流往来的各个科室,一拨又一拨的人,拥堵在电梯口,电梯运载着这些人分散到大楼各层,他们面目模糊,带着不同的酸楚和滋味。医院楼房高得让人晕眩,稠密运送人流的电梯更让人晕眩。医院近处场地有工人在施工,电钻尖锐的声响和堆叠的建材,制造些许喧闹和狼藉,他们需要夜以继日再盖一座楼。人满为患,谁让这是一座有名的地市级医院呢。
二
肾B超,肾扫描,肾造影,每一项检查,母亲都无可置疑的积极配合。她到了怀疑自己身体零部件磨损程度的岁数,从来没有做过检查的母亲对仪器抱有期望。她期望科技含量的参与,能够给予她的身体各项指标客观的论断。
造影室外的候诊椅上,我和母亲默默对望,她头顶华发飘摇。我曾饱盈水分的母亲啊,已经像深秋的树木在渐渐枯萎。从我依赖于她,到她依赖于我,中间只有一步之遥。岁月让她从牙齿、头发、腿脚开始,一点点磨损坍塌了健康,在我面前,她重回孩童时代——牵着我的手,一点儿也不想松开。
当我填好单位突如其来的一张表格,已近下午一点钟。我忙不迭地赶到医院,母亲的脸色堪比风雨欲来的天空:几点了,要饿死人啊。医院门口就有餐馆,可她不会乘电梯。到了餐馆门口,她先看看门口硕大的招牌,再看看招牌上的价目表。饺子,十二元一份,不在她承受的价格之内。于是,拐了几条街,穿过几个十字路口,还是没有找到她老人家认可的饭食。凉皮她胃寒,胡辣汤不耐饥,米饭就菜代价太高,最后还是来到最初的这家饺子馆。
才几个饺子呀,数得过来——她拨拉着盘子里的饺子,不顾小老板的白眼,嘴巴和碟子碰触得呼呼啦啦,迅速吞下了一盘饺子和一个烧饼。我说,下午要去开个会。可母亲说,如果我再这样忙,她就回家,不要我管她的死活。她赌气的话,就像一瓢卤水,点开了我压制在心里的焦躁。我努力把语气变得柔软,声音也降下几个分贝,我亏欠母亲太多了。
母亲没病之前,一直由她在家乡照看的我八岁的儿子转由我独居的婆婆看管。婆婆住在老宅里,东屋的檩条已经脱墙而出,屋顶也破烂不堪,每间屋都堆满旧物和捡来的废品。村干部多次劝她搬离,老人家就是置若罔闻。老人不爱洗澡,身上常年散发着怪味儿。儿子一听说要去奶奶家里,沉默里压抑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悲怆。可又什么法子呢?
回到候诊室,看到一个衣着考究的妇人正在给一个皮肤白皙的女孩揉着眉心,女孩脸色是病态的白。我母亲的神情里立刻充满了同情,我猜想她在对比自己,庆幸还没到被家人搀扶的地步。
听到喊自己的名字,母亲以一个山里人的迅捷走进去、躺下、掀起外衣和报上身高体重。我也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手捉棉签替母亲压住胳膊上冒血的针眼。她褐色松垮的胳膊像一截枯树枝,手背上纵横蚯蚓样凸起的血管,和零落散布若隐若现的老年斑,这双手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此刻被我紧紧地握住。
主治医生拿着片子,指着片子把专业术语转换成通俗道理,给我讲解疏导肾水的方案。我以貌似不明白的茫然看着那张精致的脸,以期从他嘴里知道母亲更多的状况。母亲输尿管狭窄,他决定给她放个导管,相当于尿路支架,用以引流肾水,然后复查时看肾功能恢复程度,如果不行,还有最后唯一果断方式——切除左肾脏。
母亲消除独坐的孤寂是串床和问候临床的病情。她不厌其烦一溜拜访过去,在走廊结识的一位患者,她身材矮小,脸似被秋风挤干水分的倭瓜。她已经切了肾脏,身上挂满管子。镇痛棒的副作用让她恶心呕吐,取了又疼痛不止。母亲去看她时,她脸色苍白,不住呻吟。母亲只默默看她一小会儿,回到病房控制了大约将近两星期、三番五次请心脑专家会诊后降下来的血压,一下子升到二百多。
当时我已回到这个城市的租住处,接到她的电话,公交车是来不及等的,我一边飞速穿上刚刚脱下的外套,一边睃寻来往的车辆,手高高举着,随时让过往司机看见。坐到出租车上,咚咚的心跳声清晰可闻。恼恨路上的红绿灯怎么如此之多,等待的每一秒钟,我几近崩溃。几年前瞬间失去父亲时遗留的惊惧,让我对人世的无常如惊弓之鸟。眼睛跟随身体的流动——掠过医院的门牌、电梯、护士站,我看到母亲的第一眼,惊讶她还没有做手术,浑身上下怎么就已经插满管子?
三
母亲进手术室之前,主治医生已经和我商讨过几种治疗方案。左肾无功能,要不要切除?想到母亲又要被疼痛袭击,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保守治疗:放管子。母亲和我红头涨脸争执起来:如果前期治疗没有效果,早切胜于晚切,如果终归是要切,那前期的治疗费不就白瞎了?
曾经,在灶台边烧火,我添柴的动作过于生硬,被母亲一顿呵斥。我是怕火花溅到我的防晒衣上,母亲则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这么薄还这么多钱,你咋舍得花下去?每次回家,母亲无一例外向我汇报东巷满生给了她几根油条,西院麻神送了一碗凉粉。还会压低声音,神秘兮兮说村里年前给老人发了一张百元大钞——她的神情,让我有一种她身处水深火热而无人搭救的错觉。我给她钱物,她总是推来让去。我有——是她的口头禅。我再次疑惑母亲是因为上了年纪,还是突然没了父亲,从而没了安全感呢?
对放管子的未知,对小摊点麻辣饭食的厌倦,抑或对医院空气的不适,母亲开始咳嗽,太阳色的脸上增加了一层霜色。除了服用医院的药物,她还偷偷喝自己带来的降压药——我无法判断是对谁错。按理该遵医嘱,可她的血压还是很高,她心理上的负载和经济的压力,才让她不得不这样做。每天面对护士送来的计费清单,母亲眯着眼睛要研究半天,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划算。可血压不稳,什么手术也没人敢做。病房里的电视,不停被人调换频道。我抱起校对稿,一页没看完,半边身子斜倚着母亲腾出来的空间,浑浑噩噩就进入梦寐。感觉刚睡着,母亲就推醒了我,是主治医生让我签字。一条条风险术语,扑面而来,我才晓得自己的医学知识多么浅薄。然而,我明白一个道理:那些条条框框告诉我,签了也无法风险转嫁,有的只是简而化之一句话:相信医院,相信医生。
母亲也要签字,笔在她手里迟疑不决。母亲一生,写字的机会及其寥落。和矿上的父亲两地分居,她小学文化的汉字水平被距离激活,她几乎不太能写完整的句子,偶尔间杂着鸭蛋样的符号,但父亲还是用夫妻间多年的默契领悟了。后来电报和电话的取而代之,母亲写字的兴致就被劳作的岁月蒸发了。第一次在手术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目测过去,绰绰有余的位置,可她手里的笔硬是不受控制,丝瓜蔓一样绕出去,绕得拧巴,绕得局促,绕得大处大,小处小,最后一个字和人家的铅印体扭结到一起。末了母亲擦擦额头的汗,像锄了半垄玉米,放下笔,连带把一个歉疚的笑递过去。
四
母亲走进手术室,她身后乳白色的门缓缓合上。门缝渐渐缩小的间距里,她的影子越来越小,融进一片恍惚的白。我摁住自己扑上去的冲动,影视剧总是太矫情,此刻我真实地触摸到无时不在的人生悲苦和伤愁离别。手术外的喧哗,比其他地方力度弱小,但还是灌进一耳朵邻座关于病痛的议论——到某地复查,到某地手术,何时复发,一张一合的大嘴巴里细节详尽娓娓道来。我看了看表,上了一趟厕所。但凡紧张,我就要上厕所。
一个碰面的病友,问候了一句母亲的病情,边打手机边往窗口移动,电话里和淘宝平台上的一宗买卖较上劲。她柔中带刚的斥指责对方的态度,陈述退货的理由。我又看一次表,时间的移动如此缓慢艰难。主治医生推门叫我,向我叙述放管子情形,他口罩外的圆眼睛此刻英气勃勃,让我生出无限钦佩和崇拜。(要知道这两个词我平时用得及其挑剔和谨慎。)
手术顺利,母亲被推出来,护送她到病房,同室的病友家属过来帮忙,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在这个肥硕遍野的时代,她瘦得像一拍两散的纸片人。纸片人很少说话,但她肥硕的妹妹和病床上八十多的老妈却很听她的话。母亲手术前几天和她小公园漫步,她们已经结成无话不谈的盟友。
她是本地人,远嫁山东,她母亲跟她一起生活,她哥嫂不管老妈。失去父亲的几年,娘几个的寻常就是抵挡风霜,突破日子困境。麦子没有人拉,堆到麦场,没有男人支撑暴雨来时起不了场,哥哥被嫂子辖制着不敢来帮忙,姊妹四人在暴雨中的麦场哭成一团。老妈平日绣些荷包儿童帽虎头鞋和枕头套去集市摆摊,供她读完师范,她工作了负担起妹妹们的学费。这次老妈突发血尿,她用平日积攒下的三万块私房钱来看病,家庭主妇的二妹和她轮换守护。放羊的大妹隔日打电话来,跑保险的四妹过几天会来替换。哥哥和他的儿子们住在本市,老妈的事压根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多少年了,她习惯了他们的不闻不问。她担忧着几天后老妈的病检报告,如果不祥,也许就要失去老妈……母亲不知道拿什么话安慰她。回到病房,再看到老太太不知所以然的样子,在一丝不苟做着每天次数固定的头脸和手部按摩,母亲笑着对她说:老太太好福气呢,活到一百岁哩。
母亲先前的病友是一个四五岁的女孩苗苗。她锃明瓦亮的头型让我一开始认为她是男孩。病房的每一束阳光都被她咯咯的笑声点亮,无论扎针还是打针,都没有听到她的哭闹,承受病痛她無声无息。她妈妈——那个满脸孩子气的女人大概二十岁不到。她说她不知道母亲是谁,她是她奶奶抱来给她的光棍父亲延续香火的。奶奶去世后,精神障碍的父亲没有能力供她上学,她到南方打工,在十六岁时生下了苗苗。女儿肾脏肿瘤,做了切除手术,在这里化疗。她眉眼清丽,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悲苦,弯出一对娇俏的酒窝,酒窝里旋起没肝没肺的笑。
苗苗出院和每一个人道再见,嘴角弯起的酒窝里有她母亲的影子。
苗苗腾出的床位入住一个憔悴的妇人,三十出头,人像风干的橘子,干瘪的皮肤、干瘪的乳房从她起身时从悬垂到半胸的睡衣里探头。她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吃,不停地吃。她的床头柜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吃和新鲜的时令水果。麻辣鸭脖、糖炒栗子、盒装杨梅、绿宝香瓜依次堆叠的床头柜搁不下那么多东西,妇人丈夫就又搬进来一个柜子,那个柜子迅速被各种食物占满。妇人除了吃,就是双手攀上男人脖子哼哼唧唧,男人的脖子成了她随时攀援的扶手。女人的哼唧聲,像阴雨天的屋檐水连绵不断,让人平生惆怅。有时整个身子都吊上去,歪在男人怀里任他抱着瞌睡。
后来我听说了她的病情——子宫癌晚期。她出院的时候收拾了许多鲜亮的衣物,跟在大包小包的丈夫身后,挥手对我母亲郑重地说:阿姨再见。
母亲直直躺在床上,口鼻里吸氧,胸口是心电监护仪,床边别着尿袋。主治医生术后巡房,母亲对他说,没啥感觉,啥都不知道,医生真是能人。有病友询问母亲,怎么儿子儿媳不来探望,她神色像风过处的灯焰,只暗淡了一下,忽地又亮堂:儿子开铲车,这两天活路太多,娃们得有妈照顾着,媳妇也是走不开哩,呵呵。
出院时,母亲站在医院门口,门口是大马路。奥迪车过去了,三轮车过去了,摩托车过去了。不少车在进口处拥挤腾挪,医院门口就显得逼仄狭小,一个手里拿一根红小旗嘴里吹着哨子的高个男人在疏通。母亲站一会儿,她说她被车影晃得头晕,我却腾不出手来搀扶她。我提着她出院的衣物、片子、瓷缸脚盆和亲戚看她的香蕉牛奶,这些东西摇摇晃晃重重叠叠摞在我身上,我像一棵披挂了沉重果子的树不能动弹。车辆穿梭的画面,和它们发出的喧嚣,它们混合的气味儿,不想介入却又挣不脱,我屏住呼吸,憋不住了再吸一口气。
再不捋连翘了,医药费太贵,血压升高不划算——她自言自语,像是给自己定心,也像给我许诺。医院真不是人待的地方!最后这句话像是她住院的心得。
回到家,母亲瞒着我,操持着给辣椒苗、西红柿苗和黄瓜苗施肥、起垄、担水——栽种上后,才给我来电话说她又尿血了,让我问问医生咋办。
不用问,你还来医院吧。我说。
再也不上医院了,我和花呀草呀在一起,空气好得很哩……母亲啰啰嗦嗦着。
我仿佛看见母亲坐在阳光弯出一片阴凉的门墩上,朝南的门墩正对着南面的大路。表嫂嘴里嚼着一口馍,边走边咽。馍太干了,把表嫂的嗓子噎得咯儿咯儿响,她向母亲讨水喝。一碗温开水灌下去,表嫂又拿出一个罐头瓶,对母亲说起自己没有烧水的原因——简直是太忙了,一刻不能歇下,歇下的每一分钟都是钱哩。她拿着灌满水的罐头瓶和一个袋子急急奔向后山,她说那里的连翘快被人捋完了。
二憨也挎着蛇皮袋子走过,她是村里最懒手最慢的婆娘,睡到半晌才起床,早饭磨磨蹭蹭能做到中午。母亲问二憨上山能捋多少连翘,她扭着肥硕的身躯慢腾腾地说,能有多少?十斤八斤也中,也值几十块哩,你不去?母亲说,孩子不让干,我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保养身体。
傍晚,山上的人回家来,路上过去说说笑笑笑,后背上背着一天的劳动成果。母亲望着她们,把她们的背影送出去老远。年轻的母亲行走山里的时候,干洋槐树叶二分钱一斤。她头上包块花毛巾,胸前挂着围兜,手里拿着钩镰,每天和它们纠缠在一起。她的衣服是洋槐树叶的气味,手里是,鼻孔出的气是,喂给弟弟吃的奶汁也是。我坐在母亲捋回的洋槐树叶上,叶子上一只毛辣子趁机袭击了我的手指。疼痛从手蔓延到心,再从心反射出去痉挛了手指。我甩着手,眼泪汪汪。毛辣子绿色的身子吸附在某片叶子上,我刨挖半天,敌人的影子也没找见。我告诉母亲,她给了我一个若无其事的表情。
公洋槐树上的叶子刺大,傍晚母亲坐在夕阳斜照的门墩上,我拿一根针对着她洋槐树叶染绿的手掌给她挑刺。混在绿叶汁液中的刺,需要高倍的清晰度才可以看见,见针在我手里滑来滑去,母亲夺了针,一针下去,从指尖剜出断刺,随之冒出一股血来,顶在指尖,像朵小巧的蔷薇花。
连翘的主蔓分出很多小枝,小枝上伸出许多粗糙的小刺,捋连翘时这些刺轻易会挂破人的皮肉。对于母亲这已经不是障碍,她的手经年累月地碰触坚硬的东西,已经结出一层老茧。她拎住连翘果一下子就从根捋到梢。
母亲最终还是加入了捋连翘的队伍。她在电话里声音昂扬地对我说,上山如何锻炼了腿脚,如何降了血压,如何多吃了饭。
国庆节回家探望,和她一起掰河滩地的半亩玉米,抓拢来碎麦秸和泥,补土屋山墙的窟窿,阴雨来临之前,到平房顶和她扯开塑料纸盖住她背回来拢火用的玉米芯,跟她到地里,挖着堤堰上八月正鲜的小蒜,她独轮车推着半布袋新收的玉米,她要找磨面人磨了给我做搅饭,磨面人没收她的钱,她又赶去给人家编了几竿烟叶。
搅饭在干洋槐树枝燃烧的火里泛着新玉米的清香,母亲一边搅锅,一边唠叨着村里谁家刚买了房,媳妇是研究生,下轿礼要了一万一……又感慨谁脑出血了正在医院抢救,回来了日子可咋过啊。母亲絮絮叨叨着,她不知道我正在纠结工作上的事和我想写的几篇文字,但陪着母亲,我不得不适应她的节奏和迎合她的琐碎,这些都是年少时我和她最简单不过的日常。
年少时,我无数次做着冲出去的梦,而今天时光在倒流,一条河流的两端,我选择回归——陪着她,把自己当做儿时的自己。其间我用了很大的耐心和细心,一路走过,我知道了相处的不容易,想想母亲的年龄,哪怕多陪一秒也是一种幸福。
我们说着话的时候,大砂锅里熬着她从山上挖来的血参和鬼针草,砂锅上升腾出草木缭绕的气息,它们的汁液,那些花草的魂魄,也许是她慑服血压的又一次寄望。
责任编辑 杨 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