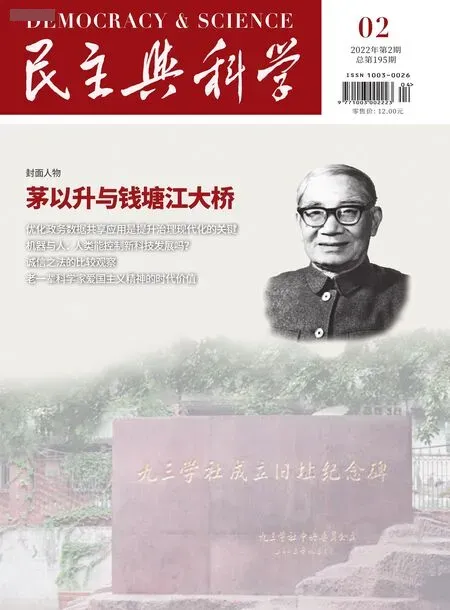最伟大的是思想,最恒久的是文化
2022-05-10李醒民
人生总该有人行,不枉世间走一程。
是非正误泰山重,祸福得失鸿毛轻。
国是学理心中事,鸡毛蒜皮耳边风。
可谴舐痔与乡愿,污染空气遗膻腥。
——李醒民:人行
还是模仿一位伟人的句式作为“作者后记”起首语吧:余致力于批判学派研究凡四十余年,其目的在求学术之创获和思想之创见。这一研究是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起步的:是年我从渭北高原的富平县广播站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前身),从一名电工工人和无线电技术员转变为学术界的一分子。1981年,我下了足够的功夫,完成硕士论文《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17年后才姗姗来迟得以发表)[1]。该文运用翔实的历史资料,梳理和厘清了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物理学危机与革命,有理有据地驳斥了长期流传的、居统治地位的传统观点。此时,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展开,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和保守势力还相当顽固地固守一隅之地,不少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迷信的羁绊,缺乏与时俱进的意识。在这种历史氛围中,我的具有超前意识和某种敏感性的论文迟迟难以面世,就是不言而喻或可想而知的事了。因此,我不得不做一些避讳和修饰,才发表了处女作论文和著作——“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1981年)和《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1983年)。在1980年代,我从已有的起点继续行进,围绕作为一个整体的批判学派及其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深入研究,陆续发表了诸多论文。在1990年代,又先后出版了《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完成于1986年)《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彭加勒》《马赫》《伟大心智的漫游——哲人科学家马赫》《迪昂》《皮尔逊》等著作。进入21世纪,我对批判学派的研究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多篇研究论文相继见诸学术杂志。可以说,在学术生涯的前二十年,我花费大半时间和精力集中研究批判学派,而后二十余年则是拾遗补阙、拓展深化。
由于有早先研究批判学派的基础,最近几年我集中时间和精力又研读了民国时期的科学论资料,这样就有了两相对照、明辨是非的可能,从而比较顺利地完成这本书稿。要是没有此前数十年关于批判学派的研究,我纵使有无与伦比的神奇想象力,也绝对不会想到确立这个“工程项目”,就更不用提建造这个“空中楼阁”了。从这个现实状况讲,我想即使再过二十年,恐怕也无人能写出类似的书稿,因为单单对批判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没有二十年的钻研和体悟是不可能做到的。恕我直言,这是一本填补世界学术空白之作,是前不见往者、二十年后也不会见来者的。有人也许认为,你这是口出狂言,不知天高地厚。此语差矣!待我娓娓道来。作为四十余年潜心研究、笔耕不辍的学人,我向来秉实干为正途,视谦逊为美德,始终反对上蹿下跳、大轰大嗡,尤其是与媒体沆瀣一气,把牛皮吹得比天还大,把脓疮捧得艳若桃花。不过,我也坚信,实话实说不是骄傲狂妄,实至名归应该理所当然。在这种意义上,我的上述表白和估价只是讲出一个真实的事实,并不是信口开河、妄下雌黄。这里有白纸黑字在,是可以经受时间的大浪淘沙和历史的无情检验的——自吹自擂迟早成为笑柄,目空一切难免露出马脚。我觉得,一个长期默默耕耘且有独立人格和自由个性的人,有时狂狷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是充分而必要的。在这里,不妨顺手拈来两首旧作“人生”“读《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其一”,为向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我壮一下胆,助一点威——就算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吧:
人生能有几回狂,降龙伏虎射天狼?
凌霄猛志囊四海,荼火气势吞八荒。
胸藏珠玑任挥洒,笔走龙蛇自成章。
风卷残云碧空净,更现天心慨而慷。
神州自古多狂狷,而今熙熙皆乡愿。
我劝天公重竞择,去曲存直明贵贱。
四十多年来,除了批判学派外,我还紧盯其他十余个课题专门予以研究。[2]读者只要从我改造(旧瓶装新酒)或自造(新瓶装新酒)的相关名词或术语——批判学派、哲人科学家、两极张力论、多元张力论、人文的科学主义、科学精神的规范结构、经验约定论、秩序实在论、综合实在论、基础约定论、纲领实在论、理论整体论、意义整体论、宇宙宗教思维方式、宇宙宗教方法、科学论、科学内论、科学外论、科学元论、科学通论、科学个论、臻美方法或审美方法、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民国学术左派和纯学术派,以及细枝末节的井蛙主义、夜郎主义、六不主义、三不政策、“四项基本原则”、四唯主义或七唯主义等,即可尝鼎一脔,窥豹一斑。
多年前在翻阅苏联一位学者古留加写的《康德传》时,有句话不禁使我眼睛一亮:“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3]其实,在此之前,作为一个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的学术界中人,我就自始至终把执经问难、染翰操觚、思想创新作为自己的高洁而神圣的使命,而把与此无关的其他一切——包括众人趋之若鹜、蜂拥争抢的课题、评奖以及出风头、露脸、应景、凑热闹之类的躁动或妄动一一撇在脑后,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舍方可得,有弃才能获,22部著作、20本譯著、600余篇论文和文章,就是对我最好的报偿,也是对我的心灵的最大慰藉。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地,实惠的红利从身边悄然溜走,耀眼的冠冕从头上荡然滑落。说实在的,实利和虚名并不是我孜孜以求的,甚至被我视之为敝屣一双。这里有我们“酒中仙”“观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为证:
钟鼓馔玉可有无,浮名虚誉任去留。
唯愿酩酊醉晓月,羽化登仙最自由。
人格独立同天壤,思想自由永三光。
虚名实利若敝屣,丈夫立世腰自刚。
在漫长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我与冯友兰先生的下述看法能够强烈共鸣:“学问这东西也很怪,你越是有所为而求它,大概是不能得到它。你若是无所为而求它,它倒是自己来了。作为业余的学术爱好者,为学术而学术尚且可以得到成绩,有所贡献。如果有人能够把为学术而学术作为本业,那他的成绩必定更好,贡献必定更大。”[4]不难看出,这段话与清代袁枚的诗句“我不觅诗诗觅我,始知天籁本天然”[5]是一脉相承的,说的是一个道理。的的确确,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实在是学术繁荣、思想勃发之道。而且,学术是有生命的,学术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与学术的生命已經融为一体:我拥有生命,就顺理成章地研究学术;我失去生命,学术研究也就随之戛然而止;如果我不再从事学术研究,那么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对我来说没有一点现实意义——只不过是丢掉灵魂的行尸走肉而已!在生前,我的著作就是我的肉体,我的思想就是我的精神;在死后,我的著作就是我的幻躯,我的思想就是我的灵魂。
托勒密在《至大论》中说得好:“我知道,我本凡夫俗子,朝生而暮死。但是,当我随心所欲地追踪众天体在轨道上的往复运动时,我感到自己的双脚不再踏在地球上,而是直接站在天神宙斯面前,尽情享用着诸神的珍馐。”[6]同样地,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不仅使我的生命能量和激情得以尽情释放,而且我也从中享受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乐趣和幸福——这就使我更加热恋和痴心学术研究了。我对学术研究的志趣和情愫,可由“写在世界读书日前夕”“古稀自述”“泛舟学海”三诗略见一斑:
手捧典藏细品茶,侵山抱月堂生华。
逢智增识经纶满,见贤思齐格调佳。
创文造化思飞扬,洁身济世气风发。
动问人间何最美,唯有读写乐无涯。
独寐寤言士林间,永矢弗告意拳拳。
心有幽趣慕严斶,身无蓄谋效冯谖。
磊落使才耸天地,慷慨任气睥权钱。
腾蛟起凤寻常事,古稀虽逾梦蹁跹。
泛舟学海卌余年,魂牵梦萦思联翩。
致力广大目光炯,尽心精微功夫全。
登高行远自卑迩,磨金镂石在恒坚。
骏发踔厉永不怠,弄斧方敢班门前。
由于长期与文字打交道,我对中国文字也逐渐生发了一种敬畏和爱恋之情。这里暂且不说仓颉创造的象形文字外形之美妙和内涵之丰盈,而由这些方块字组成的文辞和诗文,简直美不胜收,令人拍案叫绝、击节称赏。请读一读唐诗宋词或《古文观止》中的那些美文吧!那丰赡的内容,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意境,对称的结构,典雅的词语,和谐的音韵,直使你陶醉于其中,仿佛挟飞仙以遨游,竟至不知今夕何夕。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字的敬畏和爱恋,我自己从来不敢率尔操觚,而是含毫邈然,三思而后才敢笔走龙蛇。即便如此,几部汉语词典一直放在案头,以备不时绳墨之需。也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字的敬畏和爱恋,我对那些轻易亵渎、肆意糟蹋中国文字的行为——比如随意生造、广为散播的“粉丝”“小鲜肉”“饭圈”“娘炮”“大V”“大咖”“小确幸”之类——总是本能地反感,且耿耿于怀。我倒不是对丽典华藻的文辞情有独钟,那些出自民间、富有生活气息的俚语土话也惟妙惟肖、别有风味。作为关中人,我乐于向读者推荐电视剧《关中纪事》的歌词作为例证:“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这是多么生动、多么鲜活的文字表达呀,更不必说其中的哲学意蕴和人生智慧,足够你品尝和回味一阵子了。
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是什么?是思想!因为唯有思想才能够囊括整个宇宙。世界上最恒久的东西是什么?是文化!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标志人类进步。思想迸发和文化创造虽然是个人的产物,但是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下才能产生。记得布罗诺乌斯基在《科学与人的价值》中说过:追求真理的人必须是独立的,尊重真理的社会必须维护他的独立性;理性的时代总是渴望超出常情的东西——独立的思想总是超出常情的——但是它必定更渴望保证它们不受打击;科学的社会必须把高度的价值建立在思想独立的基础上。[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向来认为,没有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人,是不会有自由的心灵和创新的思维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为人类的精神宝库增添一粟,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助一臂之力。不保护和促进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社会,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没有前途的社会——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颠扑不破的铁律。因此,每一个社会领导者,每一个社会守望者,每一个社会参与者,都应该深思、再深思这个铁律,从而将保护和促进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理念嵌入意识和无意识,并进而付诸行动和实践。
不管怎么说,人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性的动物——这也许是人与一般动物最大的区别。既然如此,人就应该以精神追求作为主要目标和终极目标,特别是在生产力相当发达、物质生活日渐丰足和充裕的社会里更应如此。在这种与境下,无休止地追逐和攫取实利,对物质享受贪得无厌,像明季朱载堉的《十不足》散曲所描绘的贪婪者[8]那样贪得无厌、永不餍足,实在不足为训。即使在精神追求方面,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所选择和取舍,这样才能真正汲取有价值的东西,不致使自己的思想世界变成冗余信息和驳杂传媒的跑马场。索尔仁尼琴有句名言讲的正是这个意思:“除了知情权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9]
抛弃过度的物质追求的负担,清理无谓的精神错乱的牵累,人才能够有闲暇的时间,才能够有闲雅的情趣,才能够有闲适的心地,才能够真正拥抱闲情逸致,才能够闲云野鹤般诗意地栖居,才能够从天地万物、世事变幻中获取思维的雅兴、审美的妙趣、精神的愉悦、心灵的净化。请看北宋理学家程颢是怎么写的:“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10]请听清代文学家张潮是怎么说的:“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山,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11]在退休之前,我就有如此这般的闲心;在退休之后,我的闲趣更上层楼。当时曾有“午睡”“坐书房南窗前观蓝天浮云”记叙其胜,现不妨将两首小诗附丽于下,权当余兴可遣、余勇可贾吧:
午睡不觉日西斜,随兴卧起细品茶。
待到神清目明时,漫游书海览英华。
白云苍狗幻复翻,人事沧桑更无端。
心中自有一杆秤,稳坐钓台览风帆。
注 释:
[1]李醒民:《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杨玉圣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哲学卷(中)),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247-1285页。
[2]李醒民:《李醒民教授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李醒民:《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哲学)2009年第1版,第174-186页。李醒民:《卌載笔耕不知止,桃李成蹊慰初心——我的学术研究的历史轨迹和思想创新》,《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3期,第182-201页。
[3]https://www.doc88.com/p-747862
7524846.html。
[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版,第363页。
[5]袁枚:《老来》。
[6]https://book.douban.com/review/
12260911/。
[7]J.Bronowski,Science and Human
Values,London: Hutchinson,1961, p. 60.
[8]明代朱载堉的《十不足》散曲是:“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门前无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量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梯还嫌低。”
[9]http://www.kejudati.com/jushow/
600956167d315.html。
[10]程颢:《秋日》。
[11]张潮:《幽梦影》。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