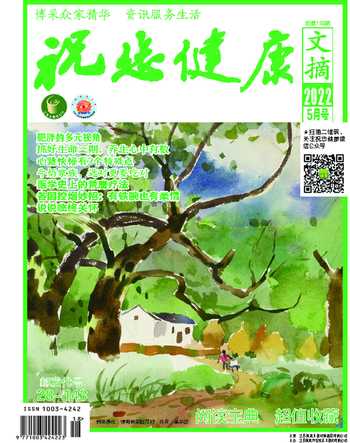说说临终关怀
2022-05-09路桂军
路桂军
社会赋予我们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于患者的生命,但凡有一线生机,一定要全力以赴。当遇到有人溺水,或者突发触电等情况,我们抢救过来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但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我们能做的只是第一次抢救,第二次抢救,第三次抢救……直到患者生命走到终点。
每一位患者临终的时候,都需要一个凝重、安详、温情的告别时间。没有人希望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刻是在救护车上度过的——那时的自己正在经历电除颤,身体被各种导管连接,最终在仓促中死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濒临死亡的患者就毫无抢救价值了。如果真到那一刻,需要整合三方的意见:医生的判断、患者的需求和家属的诉求。在临终的过程中,如何让临终更符合人文精神,这是我们做生命教育的医生对现代医疗模式发起的一种挑战。
在现代医疗制度下,对于脏器衰竭的患者,专家会有专门的复苏流程。心脏不跳动了可以启动心肺复苏,无法呼吸时有呼吸机的支持,肾功能衰竭时可以进行人工肾透析。而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是否应该启动类似的程序,这样做到底还有没有意义,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患者,在住进病房之后马上就进入了临终的状态,家属和患者都对病情非常了解。当时家属表示,只要不让他们的母亲临终过程痛苦就可以了。
有一天,这位患者的病情加重了,当时我正好在病房值班。交接班的时候,我听到一位进修医生、一位本院的医生和一位新入职的护士在谈论这位患者。
其中一个人说:“你看37床的患者,病得这么重,要是今天晚上前半夜走了还好,要是前半夜没走,拖到后半夜,咱们一晚上都不得安生了。上一次夜班就遇到了这位患者,这一次又遇到了,太倒霉了。明天下了夜班,是不是应该去烧个香啊?”
听到这一番说辞,我们一定都会觉得说这话的医生很冷漠。但是说实话,对于常年在临终病房工作的医生来说,他们每天都面临这样的情况,早已习以为常,他们的抢救也都是常规的操作。纷繁的抢救过程会让他们非常辛苦。但是,这位患者的家属和医院事前沟通过,并没有要求医院为患者进行抢救性治疗。那晚,我就在那里听着,也没有多说话。等到夜深的时候,患者突然不行了。
我告诉患者家属:“人在离世之前,最晚丧失的是听觉。她虽然不能动、不能说了,眼睛也睁不开了,但是能听见你们说什么。如果你们想让母亲没有痛苦安详离世,这时候可以在她耳边轻轻告慰,让她安详地离去。”
我特意嘱咐家属,在告慰的时候,不需要问那些需要回答的问题,比如:“妈妈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好点了?”患者此时已经无法也无力回答这些问题了,她听了这些问题会更加挣扎,更加痛苦。与此同时,我让患者的家属搂住她的头,或者拉着她的手,与她的肢体有亲密接触。医护人员在这个时候,只需要默不作声,进行简单用药就好了。
女儿搂着妈妈的头,跟她讲:“妈妈,你不用担心,放心走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爸爸,家里的亲戚我们也会经常去探望。还有您的孙子,我一定好好培养他。”
女儿一边流着泪,一边与母亲聊着天。她的母亲就这样听着,然后悄无声息地走了。她妈妈过世之后,我们医院有规范的遗体处理流程。待遗体被推出来,盖上白色的单子时,我带着值班的医生、护士向患者的遗体进行告别。当我们弯下腰时,逝者的家属深受感动,并深切地感谢了我们。
第二天交班的时候,那个说要去烧香的医生对我说:“路老师,我从来不知道临终关怀是这样的。在产房实习时,我在无影灯下迎接着一个又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感觉自己就像南丁格尔一样。这一次处理临终事件,你给了我另一种感觉,我觉得自己就像提灯女神,引领一个生命走向了另一个世界,而不是在匆忙中进行各种抢救,看着患者在电除颤和心肺复苏中将自己消耗殆尽。”
另一名医生也深有同感:“路老师,我参加工作时间不短了,也快40岁了。我之前没有接触过临终患者的治疗,从来不知道临终的过程还可以这样。”
应该说,即便在我们医生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对临终关怀的认知也是不够的。临终关怀有明确定义是在2014年,那时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缓和医疗联盟联合发布了一份《缓和医疗世界地图报告》。报告中采用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临终关怀的定义:有卫生专业人员和志愿者提供的生命末期照护,包括医疗、心理和精神支持,通过控制疼痛和其他症状,帮助临终患者获得平和、安慰和尊严,同时为患者家庭提供支持服务。
中国目前暂且没有关于临终关怀的统一定义,但根据很多人的研究和界定来看,在中国语境中的这一概念,其服务的对象是临终患者及其家属,服务的内容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等方面,目的是提高生命质量,保证患者安详离世。
在讲我们自己国家有关临终关怀事业的进展时,有必要先了解它早期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脉络。
1600年,法国传教士在巴黎成立的“慈善修女会”是现代临终关怀的雏形,专门收养濒危贫苦的老人和患者;1967年,英国的一位名叫西塞莉·桑德斯的女护士在伦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临终关怀医院——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加拿大于1974年加入这个行列,在曼尼托巴省的温尼伯市建立了加拿大第一家臨终关怀医院——圣博尼费斯医院;1975年1月又在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建立了第二家临终关怀医院——皇家维多利亚医院;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津巴布韦等国家相继建立了临终关怀医院。
说回中国的情况,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有与临终关怀相关的历史,两千多年前在全国各地成立起来的“庇护所”就是临终关怀的雏形。比如宋代时为收养、治疗贫困患者专门设立的“安济坊”,元代忽必烈下令设立的“济众院”,清代康熙皇帝在北京设立的“普济堂”等,都具有慈善和照料老人、患者的功能。
到了现代社会,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在1988年起步,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所研究临终关怀的机构;1990年,天津医科大学的崔以泰教授建立了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病房;1992年,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成立,专门接收濒危患者;1995年,上海市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临终关怀病房,开展相关研究和实践。与此同时,港台地区也开始关注临终关怀。1998年,李嘉诚捐助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宁养院。而后,李嘉诚基金会又建立了三十多家宁养院。2006年,中国生命关怀协会成立,这是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里程碑。
到今天,我们应该对临终关怀的理念有所调整,当一位患者医治无望时,我们能做的是帮他们处理症状,疏导他们的心理痛苦,然后对患者的家属进行人性的抚慰。这个环节更符合现代社会在家族情感上的需求。当然,有些医院出于利益的考虑,会鼓励医生对患者进行抢救,这样能够为医院带来利益最大化。作为医生,我也不能说医院不应该这样做,每个科室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医生也需要保证基本的生活,实现自我价值,毕竟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不受外力作用的真空中的。
另外,从患者家属角度来说,他们往往认为如果患者生病了就必须抢救,否则就是做了大逆不道之事。这样来看,承担在家属肩上的责任感或是孝道等十分坚定的道德规范大多优先于患者本人的意愿,对于一些已经难以忍受身体或精神痛苦的患者而言,生命的长度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只想安静离去,不愿再遭受抢救之苦,但家属的苦苦挽留只会让他们更加痛苦。这样来看,我们文化中这种临终关怀的精神还没有十分普及。
我们做临终关怀,或者是安宁疗护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有很多医学界的同行提出了适合在中国推广的临终关怀模式。我的朋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景军教授一直在研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他的一些研究工作和研究发现对我也有启发。他认为目前中国临终关怀有五种模式做得比较好,分别是李义庭模式、施榕模式、宁养模式、“死亡咖啡馆”模式,还有安养模式。
第一种是李义庭提出的可表达为“1个中心,3个方位,9个结合体系”模式,即以解除临终患者的病痛为中心;在服务层面上,坚持临终关怀医院、社区临终关怀服务与家庭临终关怀相结合;在服务主体上,坚持国家、集体、民营共办临终关怀事业相结合;在服务费用上,坚持国家、集体和社会投入相结合。
第二種是施榕模式。该模式又被称作“施氏模式”,施榕目前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院长,他提出了应该全面培养乡村医生。中国有70多万个乡村,有100多万名乡村医生,大多来自农村,而中国农村绝大多数的患者临终在自己家里。相对于城市的临终病患,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所以需要培养更多的乡村医生,去关照农村的临终患者。
第三种是宁养模式。1998年,李嘉诚基金会出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宁养服务计划,目前全国的宁养院已有30多家。这种模式关注到了社工、志愿者和义工团队的力量,重点为对其提供一定的培训后,将他们派驻到各个社区开展居家服务,让癌症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得到照料。
第四种是“死亡咖啡馆”模式。这种方式借鉴了国外的经验。顾名思义,临终关怀是在咖啡馆里进行的,来这里的人通常是患者的家属、从事临终关怀相关工作的人员等,他们可以共同聊天,谈论死亡。2011年,英国伦敦开设了全世界第一家“死亡咖啡馆”,之后欧洲其他国家、美国也相继开办。2014年中国开始设立这种咖啡馆,现在也在定期举办活动。
第五种是安养模式。这一模式主要关注佛教寺院介入社会化养老领域,以宗教为纽带,逐渐为佛门之外的老年人提供安养服务。
这五种模式其实充分考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以及很多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方。比如我们国家农村人口多的现实;社工、志愿者团队的强大,他们多以大学生和爱心人士为主,这些力量可以为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
(节选自《见证生命,见证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