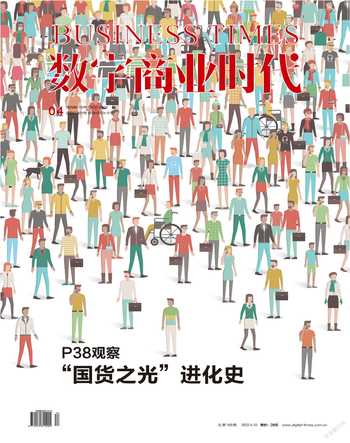别让地域黑和城市吹“赢麻”了!
2022-05-07虫二
虫二
去年,冰川思想库有篇奇文叫做“幸好我们还有上海,我一个外地人,是怎么变成沪吹的”,被认为是同类作品的扛鼎之作。
文章没有高屋建瓴的分析,全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感受。
比如迪斯尼焰火晚会照常;菜市场卖口罩,5毛一个;进小区畅通无阻;工作人员礼貌客气;诸如此类。
文章的结论很简单,措词却是字斟句酌:从来没有“干扰、强制、胁迫我做过任何一件方便于他们管理的事情”。
在这里,管理被感知的程度,成了左右公众情绪的重要标准。
最近,上海疫情出现反复,抗疫“优等生”的光环多少受损,但大多数人仍然倾向于肯定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
“你可以永远相信XX”的句式背后,本质是对大城市基础设施以及统筹、协调和配置资源能力的信赖。
时光倒流一百年,人们就远没有这么感性和实际。
1927年沈从文初到上海,办了本杂志叫做《红黑》,希望干掉市井文化的“鸳鸯蝴蝶派”,可惜事与愿违,既不叫好也不叫座,很快停刊。
對沪式审美感到绝望的沈从文转战天津《大公报》,以春秋笔法写出一篇奇文《文学者的态度》,绘声绘色描述了京派和海派两大文学阵营,直指海派文学就是附庸风雅,风花雪月,是所谓的“名士才情”+“商业竞卖”的结合体。
这玩法今天叫“带节奏”,天生有流量,文章发出之后,京沪两派人马应声站队,开始对喷,最后盟主鲁迅亲自下场,以栾廷石的笔名发出《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两篇文章,化用顾炎武的典故,说北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把自以为是的两派“一勺烩”了。
但笔下犀利的鲁盟主,生活上却是深坑的沪粉。
当年他初到上海,嘲笑这里的人们“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裤子却必须每晚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视角刁钻,尖酸刻薄。
不过真正安顿下来,大文豪却被四马路小贩的叫卖声“洗脑”了,觉得玫瑰白糖伦教糕、薏米杏仁莲心粥这些名字“既漂亮又有艺术性”,全不管伦教糕其实是一款粤式糕点。
鲁迅客居北京十四年,光是琉璃厂就去了480多次,买了3800多册古书,4000多片的碑拓和墓志,就没有培养出这种感情。
文化基因敌不过口腹大欲,太正常了。
人总归是感性的,最初争执的再怎么阳春白雪,最后影响个人好恶的还是柴米油盐,真不是城市的历史越悠久,经济越发达,越讨人喜欢。
这么说来,沪黑沈从文和吃货鲁迅,并不比我们高明多少。
地域控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但上升到“吹”和“黑”,就有不易消除的副作用。
比如三亚的天价海鲜,雪乡的宰客方便面,无论解决与否,当事人是否满意,公众影响都是不可逆的,甚至拉低了外界对特定城市及其原住民的风评。

地域之争的最大特点是非吹即黑,基于家乡情结或是个人立场的天然站队极难改变,比如深圳的高房价,本地人也身罹其中,但叫板沪粉时就成了自嗨的谈资。
最近,上海和深圳同在疫情中饱受煎熬,但评论区仍然吵得沸反盈天,花式互怼的戾气让人觉得既可笑又可悲。
屁股决定脑袋,自古使然。
西晋末年,北方人为避战祸大举南迁,盘踞要津,仕途受限的南方人大骂北方人是“伧子”,“伧夫俗子”这个词就是专黑北方人的。
地域矛盾第一次被无限放大。
随着时间推移,相对安宁的南方支撑了农业经济的崛起,到明代已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但纯经济竞争必然是极度内卷的,在BAT最鼎盛的那些年里,保持了上百年优越感的上海,一度被讥为“环杭州城市”,算是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在话语权下沉的流量时代,吹和黑的门槛都降低了。
首先,个体观察很容易变成群体断言。
大V仍然有流量,却无法左右舆论倾向了,大数据谁都会看,在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中,广州第3,深圳第9,上海第18,北京第30。
评论区里洋溢着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优越感,但幸福的定义既抽象又空泛,普通的吹和黑都难以下嘴。
个人经历则不同,随时可以轻松吐槽。
此前的西安和北京疫情,很多本地人经常拿上海的“精准防疫”说事,没想到,几个月后“浓眉大眼”的上海也沦陷了。
其他可以拿来攀比的硬指标更多。
比天际线数量,是典型的摩天大楼情结;比购物中心数量,拼的是消费氛围;比酒吧数量,拼的是吸引青年人;比便利店数量,楼下的711总比CBD的米其林好;比人口,比GDP,比房价,比财政收入等等;最奇的是还有比吃肉数量的。
比如这条微博,北京每人每天只吃0.8两肉,一天3小片,一顿一小片。听起来很有槽点,但作为吹或黑的论据,就大成问题。
首先,吃肉的数据,农业部和统计局大致可以佐证。
2019年广东人均肉类消费量93.2公斤,远高于北京的42.3公斤,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存款也可以提出反证。
2020年北京人均存款是207052元,广东是7723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北京是69434元,广东是64878元,北京人似乎不应该吃不起肉。
其次,恩格尔系数的逻辑是食品支出越高,生活水平越低。
这套评价体系未必适用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现代社会,毕竟大嚼M9牛排的土豪,与小饭馆狂啃猪头肉的人,根本无法类比,但放在一个漫长的历史周期中,底层逻辑还是相对靠谱的。
此外,全球城市实验室(Global City Lab)在估算城市的品牌价值时,虽然创造性引入了城市声誉的概念,但主要还是依托经济、文化、治理、环境、人才和声誉等六个维度的CBV模型,核心指标包括GDP、就业率、文化积淀、生活环境、生活质量、人均收入、平均寿命、医院数量等等,无关于特定群体的主观印象。
喜欢或讨厌某个地方无伤大雅,变成吹和黑就有两个危害。
第一,群体情绪都是自带攻击性的。
大部分是从社会刻板印象开始,再发展到证实偏见,比如女司机一定手潮,女博士多半单身,码农都是宅男等等,明明毫无科学根据,却都言之凿凿。
这种情况大家习以为常,甚至乐于玩梗,并不觉得是一种冒犯,但身在其中者,都会感受到浓浓的恶意。
地域之争更是如此,都是“非吹即黑”,几乎没有中间情绪。
2012年有个内地小女孩在香港地铁吃东西,在微博从讨论升级到激烈论战,甚至成了中国互联网语境的标志性事件。
深圳标语“坚决打击XX籍犯罪团伙”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好在深圳毕竟是改革开放的旗帜,到处刷墙的标语很快换成“来了就是深圳人”。
第二,攻击性的次生灾害是强迫站队。
此前北京丰台冷链疫情突发,健康宝弹窗一度风声鹤唳,很多北京人选择站队上海的“精准防疫”,尤其是20平米奶茶店成为“最小中风险地区”迅速刷屏,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存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抗疫优等生”!
但站队又是有条件的,本地人自嘲并不意味着容忍外来者的轻谩。
北京人可以抨击家乡是美食荒漠,上海人可以吐槽抢咖啡比抢菜重要,但互动中出现哪怕是一丝来自其他城市的傲慢,所有槽点马上就成了本地人引以为豪的资本。
站队可能是纯朴的家乡情结,可能是本能好感,也可能是舆论裹挟,唯一能确定的是一旦站队就终生难改了。
对地域黑的厌恶“成全了”城市吹,两者互为镜像。
个人观感都是“谁讨厌我,我讨厌谁”,外地人不喜欢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无非是先入为主,脑补了自高自大、盲目排外的原住民形象。
对应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在你讨厌我之前,我先讨厌你了”,这大概是所有地图炮的思维定势,然后寻找佐证自己观点的猛料,哪怕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
互联网大数据也在推波助澜。
以前曾有银行拒绝福建某地的信贷需求,理由是该地区的骗贷及坏账风险高于其他地区,到网络风控时代,用户画像更是变本加厉。
试想,如果芝麻信用出具一份报告,宣称北京用户的整体信用水平高于或低于上海,评论区定是腥风血雨,哪怕是今日头条出具一份数据,指出某个城市对香艳信息的兴致高于另一个地区,都会引发轩然大波。

但数据里未必有真相。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达莱尔·哈夫就写过专著《统计数字会撒谎》,揭示了选择性运用数据的欺骗性。
地域黑和城市吹的成因更复杂。
首先,真不是经济失衡这么简单。
这经常被认为是地域歧视的根源,城乡差异,南北差异等等,上海人觉得全国都是乡下,北京人觉得别人都是外地人,京沪同为中国城市的泰山北斗,彼此就会星星相惜?更加CUE才是常态吧!
其次,也不是素质问题。
北京、上海常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领先全国,每10万人的大学学历比例最高,但因此斷言这是中国最包容、最开明的两座城市,相信很多人并不同意。
吹和黑就是一种主观心态。
对已经选好站位的人来说,特定城市之于他们,既不是精神故乡,也不是赖以谋生的舞台,更不是人生规划的未来寄托,只是可吹可黑的工具。
不论吹黑,都是一种差异化的个体观感,真正要消灭的不是观感本身,而是背后的侮辱性和攻击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