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美术:再释人民性
2022-04-28■郑工
■ 郑 工
一、历史与当下的双重表达
2021年度中国美术最突出的现象,就是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此时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当下的表达,使得美术家们在进入创作时不得不重新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同一历史题材,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艺术家创作,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2021年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创作,有不少历史题材由新人重新创作,作者不一样,视角也必然有差异,作品的立意及观看效果也会全然不同。这一切取决于创作现场,但没有一件历史题材或现实题材的创作可以完全回到现场。所谓历史的语境,都是在创作者理解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所谓历史的真实,都是在不断甄别事实材料的基础上被重新认定。
人的认识总存在着局限,而历史材料一直在被不断地发掘。不是离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越近,就越接近真相;若只具备一个视角,则更加难以统观全局。历史往往被造型艺术家定格在某一瞬间,可这一瞬间的意义空间又有多大?因此,在建党百年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中,艺术家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深入挖掘题材中的主题。这一事件的主题是什么?这一时段的主题是什么?这一时代的主题是什么?而解读一件作品时,也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获取不同的意义。艺术作品的意义是多层次的,而艺术创作中对主题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多方位的。认识的深刻性与广泛性并不矛盾,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在主题性问题上,认识的广泛性在于如何贯通,即是否能将此时与彼时贯通,将此地与彼地贯通,将此事与彼事贯通,将此物与彼物贯通,将此在与彼在贯通。若能抓住建党百年的总主题,落到具体的某一创作主题上,则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有作者如此,自是高手。而作为批评家,只是隔岸相望,且隔年相看,看看其能否穿越不同题材与不同时代,在不同作品之间看到一条共通的脉络。
这一百年,将一个政党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2021年的中国美术家,将一个政党与百年中国的视觉历史联系在一起,让我们通过美术作品看到一个大写的中国人的存在。虽然在创作的方法论上,主题性美术创作都是采取写实手法,或者说遵循的都是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这已形成近百年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传统,但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画家创作的作品,风格手法还是不同的,阐释的角度也不一样,毕竟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环境不同。每一件历史题材的作品,都是当下的创作,是彼时人们对历史的解读。
2021年6月27日开馆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以下简称“党史馆”),推出了一批近30年来组织画家创作的百年党史题材作品。有些作品直接配合党史陈列,与实物、文献等历史资料共同构成一部较为完整的视觉化的历史。如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组建同盟会,这一事件即由沈嘉蔚和陈宜明合作画成油画,时为1988年;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平前,与李大钊商量创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瞬间由陈坚画成油画,时为2010年;1920年初,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一事件由张峻明画成油画,时为2018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召开,庞茂琨、何红舟与黄发祥分别将两个会议场景画成油画,分别创作于2021年和2009年;1984年10月1日国庆游行,北大学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打出横幅标语:“小平您好”,这一事件由何红舟、黄发祥、江帆、余琛潇合作画成油画,时为2021年。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也在党史馆开幕。展出作品近180件,主要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以及近年各地部分党史题材及现实题材的作品。其中2021年创作的占多数,如龙翔的浮雕《古田会议》、王吉松的油画《古田再出发》、袁庆禄的版画《广州起义》、于振平的水墨画《过雪山》、王冠军的工笔画《热情洋溢的代表委员们》等。其他两个重要展览,一是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伟大征程 时代画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于2021年6月16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作品四百二十余件,既有历年馆藏作品,也有近年来的新作。二是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无声诗里颂千秋——美术经典中的党史主题展”,展出了不同时期与党史相关的100件美术作品,创作年代最早的是一批20世纪40年代的木刻,如胡一川、罗工柳、邹雅、刘韵波等创作的套色木刻《抗战十大任务》,还有古元的黑白木刻《减租会》(1943)、《人民的刘志丹》(1944),这些在当时都是现实题材作品,时至今日,已成历史题材。罗工柳的油画《地道战》(1951),表现的是亲身经历的那段战史,但不是亲历的事件。2021年创作的作品如黄启明的木刻《北京奥运》、董卓的综合材料绘画《智造速度》、李继飞的雕塑《帕米尔雄鹰——拉齐尼·巴依卡》、韩晓冬的雕塑《杂交之父——袁隆平》,这些都是现实题材作品,也被载入了历史。任何创作都具有当下性,无论表现的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其中并没有绝对的界线。对于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当下性读解,正在于创作主体。

图1 董卓 《智造速度》 综合材料绘画 300×480cm 2021年
三大展馆庆祝建党百年的专题展各有特点。党史馆以历史题材为主线,重在新人新作;而国家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重在历年馆藏作品的经典性,也有近年中青年艺术家的新作。不同年龄的作者及不同创作年代,各自呈现出不同的创作观念与时代气息,视角不同,手法各异,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同时也是一部百年中国美术的风格史。尤其是党史馆的作品,多是由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艺术家们所作,其画风及观看历史的角度与董希文、罗工柳、刘文西等人已然不同,呈现了两代人不同的创作意识。概而言之,即从人民的英雄转向英雄的人民,由典型的塑造转向日常的叙事,人民性的话语被重新阐释。

图2 中央美术学院集体创作 《信仰》 汉白玉石雕 800×450×1500cm 2021年
二、重构观看视角再现历史
以具体形象推演出抽象概念,再以抽象概念演绎百年历史。党史馆西侧广场的四组群雕《信仰》《伟业》《攻坚》《追梦》,分别由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鲁迅美术学院组织团队集体创作。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不同,党史馆广场雕塑的碑体形式被群体性的人物雕像所取代,将“基础”和“丰碑”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强调横向性的展开,而不做纵向性的提升,拉伸了时间维度,使得每组雕塑具有更大的包容度。同时,以观念性传达其象征意义,方向高度统一,形象直观、易懂也易解。
如《信仰》的主题是“初心”,以“入党宣誓”的人物形象,表述了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念。握拳宣誓的动作虽然具有典型意义,但作者并没有着意刻画某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群雕中的71个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与年龄差异,而重复性的宣誓动作,从外部形式到内在理念使得党员这一特殊群体获得了一致性,贯穿了四个历史发展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终体现百年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历程。《伟业》的主题是“建设”,贯穿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发展阶段的历史主题。作品塑造了65个人物形象,注重人物的职业身份与场景道具,注意社会分工及行业特征,在差异化的个体形象的基础上,以“坚毅”与“向往”的神情统一了作品。《攻坚》的主题是“奋斗”, 群雕人物共67个,分12组,以语境化的方式再现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性场景,如开路先锋、高原蓝图、抢险救灾、石油会战、红旗渠、南极考察以及黄河纤夫、飞夺泸定桥、东北抗联、淮海战役等,每一事件各有主题,每组人物各自成峰,起伏错落,意气飞扬。《追梦》的主题是“和谐”,是“欢乐颂”,73个群雕人物以其不同的服饰表明其民族身份,没有具体事件,也没有规定动作,只见鲜花与哈达,人物随风起舞,随声歌唱,团结前行,一片喜庆。
个性与普遍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并不矛盾,但曾有一度时间被理解为追求普遍的典范意义,个性被消解了。虽然这四座雕像也没有完全避免这一问题,甚至在艺术手法上,他们还在避开过于个人化的表达,寻求共性。可回到个体,尤其是回到“身边那些朴实无华的人”,更有利于创作者的自我体验,唤起真实的情感,表达对象的精神气质,而不是停留于面上或形式上,这是创作的新迹象。小我与大我,可以相互转换。从个体入手,贴近生活,真实性强,又不完全个体化。如《攻坚》中“石油会战”的人物原型是王进喜,但并没有照搬其形象。无名化是大型纪念碑雕像创作常见的手法,可在人民性的问题上,则让创作者的视角深入到底层群众,“唤起工农千百万”(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彼时的“工农”而今替换为“民众”,政治化属性被职业化属性所替换,人民性的内涵扩大了。
同一题材,乃至于同一主题,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视角与表现方式,从而体现美术家的个性。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美术家如何以艺术的方式进入历史。“进入”是一个关键词,其前后带着“艺术”与“历史”。美术家只能以艺术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同时与历史对话,而“历史”对艺术家而言,意味着什么?那是由艺术呈现的“历史”,或者说是“由艺术家书写的历史”。因此,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就是一个特殊的视觉文本,是美术家个体言说的形象文本,其中包含着美术家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及认识、体会与想象、情感和评述。美术作品中所有的形式因素,都在于论证观看主体的独到性,以至于其中存在的观念与意识。当一种视角不约而同地出现,渐成风气,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平行”构图中的观看意识就是一例。在这一视角下,丰富的历史现象是否被扁平化?

图3 庞茂琨 《开天辟地》 布面油画 300×450cm 2021年
比如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关键性的情节不多,横幅标语、游行队伍、街头演讲、呼喊口号,等等。1951年,周令钊创作的油画《五四运动》将游行现场置于天安门前,强调空间的纵深感,画面中的一个典型动作就是振臂高呼。2009年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刘国辉、袁进华、盛天晔合作的水墨画《五四运动》已是平行构图,背景略去了,只见一列列游行队伍,侧面横向行走,还是那典型的动作——振臂高呼。2021年,“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展出的油画作品《红潮——五四运动》也采用平行构图,不过是正面的,直视观众,典型的动作改为“手挽着手”,形成一堵密不透风的人墙。一个动作,既非场景亦不关涉人物形象,却直指作品主题。“手挽着手”解决了个体人物间的连接问题,以形象落实了“联合起来”的概念,个体的觉醒转换为群体的力量。

图4 许江、孙景刚、邬大勇 《红潮——五四运动》布面油画 400×540cm 2021年
又如平型关大捷,因为是伏击战,美术创作可选择的表现瞬间比较多,自由度较大。1959年,任梦璋、杨为铭合作的油画《平型关大捷》,采用竖幅构图,居高临下,依托山形,呈绝对优势,火力全开。其关键词是“围歼”,视觉中心是一位用手枪射击的八路军指挥员。2009年,孙浩的油画《平型关大捷》则取低视角进入峡谷的山洼坡地,敌我双方刀刃相见,战争的残酷可见一斑。其关键词是“肉搏”,视觉焦点是两人对峙——一位手挥大刀的八路军士兵与手持指挥刀的日军怒目相视,四周一片砍杀,人性与正义的问题同时被提出。2021年,窦鸿再画《平型关大捷》,同样是低视角,还是峡谷的山洼坡地,却是在战斗结束之后,八路军清理战场,收拾战利品。日军的尸体横七竖八,间或也见战死的八路军士兵。视觉中心是一位胸挂望远镜的八路军指挥员,凝神远望。画面整体处于平视状态,作者着力刻画人物的心理,神情微妙。其关键词是“善后”,生命之思,倏然而起。
艺术不是历史的图解。美术作品的图像阐释,不应拘于图像本身的内容,而在于对意义的追问:此处为什么是这一图像而不是其他?图像出现的理由和意指何在?历史是多面相的,作者有多种选择,这就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各种表现的可能性。对创作动机的理解,强于对事实本身的陈述。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真实性都抱有一种警惕性,担心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无法探及历史的真实,但历史学家又期望学术界对历史作出客观真实的描述。再严谨的文字也存在着缝隙,为不同的阐释留下机会,而同一事件或同一事实遇到不同的解释与评价时,人们怀疑的不是历史文本而是事实本身。“这事情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是那样?”因为历史文本的写作者总会给我们许多理由,而且总以事实为依据,证明他对历史事实的判断。当历史被不断地重写与重构时,就会越来越加深人们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这时,返回图像文本是否又会获得另一层面的认知,改变我们对历史真实性的看法?

图5 窦鸿 《平型关大捷》 布面油画 300×600cm 2021年
以艺术文本建构的历史,首先让人感受到的是艺术的存在,进而借助艺术家的眼光进入历史,以沉浸的方式感受历史。历史成为一面镜子,既映射着过去,也映射着现在;既映射着他人,也映射着自我。在现象与镜像之间,恍惚的主体,总是以与作品主题相关的方法存在着。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创作主体带来了不同的艺术阐释方式,作为观看者的我们,也不会纠缠于何为其历史存在的唯一性问题,不再狭隘地看待历史。
三、另觅表现方式反映现实
2021年的现实题材,同样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一大板块。这一年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一是防疫抗疫,二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文艺创作上,这两项也被纳入到建党百年的整体历程,成为重要表现题材。特别是各省区市组织的庆祝建党百年美术创作及其展览,都结合地方实情,在题材上有所偏重,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与2020年抗疫主题作品相比,2021年的创作标语口号少了,在人性以及生命关怀的主题上阐发意义的多了。相对于其他省份艺术家创作的同类主题作品,身处武汉以及湖北的艺术家、有过“封城”经历的艺术家,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其人生体验非他人可比,其艺术创作更有着他人难以企及之处。2021年6月18日,“壮丽航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湖北优秀美术作品展”在湖北美术馆开幕。展览中有三件抗疫主题作品值得关注:一是肖丰、吴青合作的油画《穿过黑暗的那道光——武汉庚子年春》,二是曹丹的版画《战疫,战疫》,三是杨明清的油画《公元2020年1月23日10点整》。

图6 曹丹 《战疫,战疫》 版画 150×160cm 2021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件作品独到的观察视角与表现方式。肖丰和吴青的油画以及曹丹的版画,都是表现抗疫第一线的场景。“穿过黑暗的那道光”,这诗意般的话语抚摸了抗疫这一充满悲情的题材,大面积的冷灰色调,将一束希望之光赋予了白衣天使,画面沉静、温馨、平和。作者很强调质感,手法写实细腻,充实而丰满,给人的联想空间较大。相反,曹丹的版画《战疫,战疫》中,强节奏的语速一直拍打着画面,使观者的心被揪着无法放下。那是一个临床抢救病人的场面,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紧张工作,人的神经都被画面的线条牵动着,关注着病床上的那个人。如果说“呼吸”是这一时刻的关键词,那么画面上让人喘不过气的就是拖泥带水的笔触。画家在这里没有留下一处空闲的地方,赶来的医生甚至还没有穿好防护服就上阵了。画面的折叠感特别强,这一形式似乎意味着人生的某种状态,我们能感同身受的那种急迫状态,或者说是生命的危急状态。艺术,就是以特定的形式让观者与它互动、一块遥想、一起行走、一并感慨、一同呼吸。由艺术方式呈现的历史或现实,都是有温度的。作品《公元2020年1月23日10点整》选取了关闭所有进出武汉通道的时间,时间的数字表述趋向于概念。画面中,我们视线所及的是城市公共交通停止运营,街道行人稀少,车站准时封闭,城市变得十分单调。作者放大了武汉高铁站前屋檐下的黑影,以此压住画面,锯齿般的边缘线切开了灰色的天空,只有一束耀眼的光投射到玻璃幕墙上。画面中的颜色被清洗了,只有红色在闪烁,色彩的情绪被唤醒,传递着抗疫的声音。艺术家在动用各种形式的时候,往往将形式或形象都转换为符号,并暗示其意义指向,从而将画面变成可阅读的视觉文本。
无论是艺术的真实还是历史的真实,都是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将问题逐一打开。艺术家的在场,不仅在精神上要融入其创作语境,还要在情感上与作品的形式同频共振。前者可催生艺术的意境,后者可增强形式的力度,让主体亲近——亲近对象,贴近形式,放逐精神,让主体无处不在。亲近,是人民性在艺术方面的具体呈现,也是“共谋、共创、共享”的具体表达。换言之,即以人民性重建主体性,由主体的介入谋求形式语言的发展变化。承认主体精神的独立性,必然带来艺术形式的多样性。
主体在场的创作意识与当代艺术的在地性相关,但不完全等同。当代艺术的在地性,指的是脱离常规的展览空间,作者直接来到某一现场,利用现场材料进行创作,无预设无框架,随机性强,其作品的结构是开放的,观众容易进入,又因为媒介材料的关系,易于和观众互动。而主题性创作的主体在场,针对的是创作者自身的体验问题。还是在常规的展览场地,作品是预设的,有既定框架,只是在创作过程中强调主体与表现对象(题材)之间的亲近度,就是我们常言的“深入生活”,不走马观花,不局限于简单的情感交流,而是着眼于一种专业眼光的介入,即在艺术家的关注下,呈现被某种形式整合了的对象。题材引发了艺术家在场,而在场的艺术家处理了个人风格与对象表达之间的形式关系。那是“身临其境”的创作方式,可破除艺术家固有的表现程式,激发新的创作欲,以形式解读的方式另辟蹊径。同一题材或同一事实,在艺术那里可以获得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形式,其实就是不同的观察与理解。实地观察或实时介入,感觉与体会自是不同。因为实时介入是鲜活的,也是变动着的,而且可以随时被主体确认。
“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句话在创作上肯定了每一位创作者的主体性。主体的差异决定了艺术表现风格的多样性。不过,艺术创作中的个体差异毕竟有限,难以超出某种知识的范型而自行其是,独创性空间并不大,特别是遇到特定主题的创作更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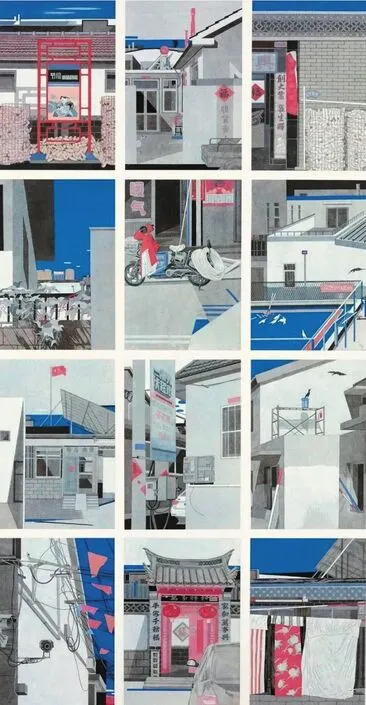
图7 李英建 《美丽乡村·幸福小康》 纸本彩墨186×120cm 2021年
四、主体转向与大众化实践

图8 “人民的纪程——主题性与纪念性雕塑大展”之“童年塑记”(图片来源于网络)
此次展览的策划颇具特色,将主体项目与公共教育部分分开,穿插进行。如展览的主体项目在第一站(杭州)和第三站(北京);第二站(上海)和第四站(深圳)则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共教育,即如何通过受众的个体体验,运用雕塑这一特定方式,让受众接触材料,打开想象空间,培养审美意趣与动手能力。大众的审美教育从小抓起、从个体经验入手,这并不新奇,有意思的是其如何结合项目主体,由此去亲近雕塑的历史与文化。其环环相扣,建立起展览的整体逻辑框架,让人民性与历史性的书写结合,又与每位参与者的双手联系起来。这个展览策划的意义在于让公共教育走出展览馆,进入社会基层教育机构;同时走出既定的知识体系,通过感性的、直观的审美活动,让个别的生命活跃起来;更重要的是面对少年儿童,让其接触经典美术作品,从而认识文化的价值和创造的意义。在人民性问题上,少年儿童这一群体所具有的社会广泛性,在新时代的艺术教育中尤其不能忽略。
艺术的创造和艺术的传播,都是在社会化的审美教育体系中交互进行的。创作中有传承问题,那也是传播的一种路径;传播以观看者的消费为主,也存在着创造问题。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网络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方式,虚拟空间及虚拟技术也进入到艺术创作与传播领域,这对以人工技术为基础的传统美术影响很大。如此一来,人工智能中的人性问题、人民性问题如何论述?数字建模、声光电通过软件编码进行操控,所运用的工具是计算机,其所带来的沉浸式的审美体验基本上都属于虚拟的异化现象,可我们想到的还是关于人的自身。对此,我们接受了什么?放弃了什么?如果只靠观念,我们是否还能做艺术?如果不靠观念只凭技巧,我们是否还能做艺术?
一旦放弃艺术中人的主体性,我们将无法谈艺术的人民性。或者说,我们对艺术中的主体需要重新定义。比如观看者的主体性,在特定场域中就带有权力投射,新媒体艺术中的链接性与互动性,都涉及到主体的转向。其解放了受众,让艺术在人的实践层面上往大众化方向去,人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被重新认识。比如,在一个艺术行为场域,人的主动性就成为评判的依据,包括那些以身体直接感知的体验空间,人的意念或行为动作会转换为各种信息被接收,再通过相关的设备反映出来,直接作用于人本身,同时也影响同一场域中的人。
由于科技的不断介入,新媒体艺术发展趋势渐长,其互动性越来越强,特别是人与作品间的互动呈现出全新关系,改变了作品的造型、影像及意义,引发了人的意识、思维及经验的转化。手工性消失了,人的个性保留在意识层面,与思维有关,与个体的知识和经验相关。当然,我们对人的认识、对艺术中人民性的理解也将会随之改变。
五、结语:被扩展了的人民性内涵
再释人民性,就是对人民性内涵的重新设定,或者说,不改变其基本性质,只是扩展其边界,延伸其意义。从2021年中国美术主题性创作的整体趋势看,有三个可延伸的维度:第一,主体的职业身份;第二,题材的社会属性;第三,语言的时代特征。无论何者,其延伸的意义空间都受限于时间。时间是流动的,主体身份是变化的,意义阐释是因人而异的,流行话语是无法固化的。存在的时间决定了话语场域,也决定了存在者存在的正当性。
近百年来艺术家的社会身份变化很大。从自由职业者到艺术专业人员,从小资产阶级到劳动人民,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身份的转变有两个时间点值得关注,一是1949年,二是1992年。特别是1992年以后,艺术家完全以劳动者的身份进入艺术创作,与表现对象之间的隔阂渐次消除,主体意识越来越明确,主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
这种变化不是一日形成的,只不过在2021年,因为大规模的主题性创作,凸显了这一变化。那些出生于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艺术家,是2021年创作群体的主力。他们的成长经历都在1978年之后,能与时俱进,认同时代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经过较为完整的专业训练之后,对自我身份有着自觉的认同。专业不断细化,同时也不断泛化,跨学科现象越来越多,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增加,多重身份现象比比皆是。聚合流变,使得艺术创作越来越多元,主体意识在材料与技术的夹击下,隐蔽沉潜,随之而动。艺术家对自身的专业定位,其时效也越来越短。例如新媒体艺术创作就没有明确的主体定位。农民画家的主体性也是一例,行业化现象更加速了主体身份的异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70年代的士兵画,现在几乎不存在了,工人画同样如此。随后,主体的职业身份被专业话语所掩盖,如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等。直到公共艺术的出现,这些基于材料与技术层面的专业划分又被消解。现如今,统合的趋势让所有从事艺术的人回到人的本位,不论是创作者还是消费者,可以互换也可以互动。艺术的过程所生发的意义逐渐大于艺术品本身,而艺术品的意义空间也重新开放,面向大众,使得变数迅速加大。

图9 赵建成、赵晓建 《开国大典》 纸本彩墨 420 ×1200cm 2021年
可是,通俗话语不等于流行话语,流行话语带有时尚的意味。这样,问题将被引到现代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上。对于2021年度美术,民族的、大众的与现代的,三者互融互通,而且其融合程度较高。现代文化的在地性,本身就有大众化与民族化的趋向,有通俗化的趋向,并且注重推出流行的文化浪潮,从一地涌向另一地,形成时代特征。流行话语的时效性强,民众的参与度高,影响面较广。比如在艺术设计领域,有流行色与流行样式,而在美术主题创作与展览方面,也会出现一些流行观念与相关操作模式。比如“正面”“团聚”,一字排列、中心构图、三联画等。凡是贴近流行话语的作品,其个人的创造力相对减弱,出现对群体模式的依赖。群体模式容易被类型化,当大规模地组织主题性美术创作时,“类”的特征往往掩盖了个体特征,“民”的意识往往冲淡了个人意识。比如党史馆前面的广场雕塑,是不同单位的集体创作,有主创人,其单体雕塑的风格是统一的,依稀可见主创人的影响,会与主创人平时创作中的个人手法与创作理念有联系,其他参与者的个体因素基本是被阻断了的。四座群雕,艺术语言完整而统一,在内容上印证互补,形成特有的“广场作风”。这是动用整个中国雕塑界的力量共同营造出的一个新的艺术空间。“群众”,就是一个流行话语,是一群咤叱风云的革命群众,体现出无产阶级“新人”的基本特征。
人是可以被塑造的。从自然人到社会人,为生活所形塑,在艺术创作中则为艺术家所塑造。人和人民,前者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而后者就是一个集群概念。对于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无论个体还是集群形象,人民性的话语向来没有缺席。2021年,从新兴木刻运动至今已90年,人民性的内涵变化非常大。再释人民性,是在建党百年这一背景下自然被引发的话题,因为人民性与革命性的话语牵扯不断,有的侧重于题材或主题,有的侧重于形象塑造,有的通过语言方式表示其意向,至于其变化与延展的空间,在不少美术作品中都能体现,而对其意义的解读,还在于个人的理解和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