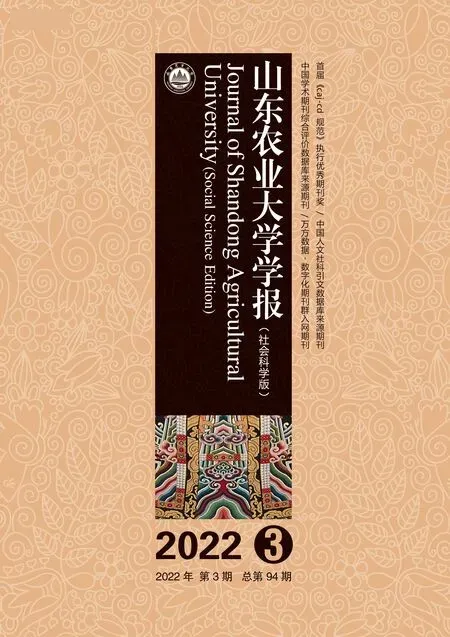论池莉《大树小虫》的“时间和空间”
2022-04-16李贤
李 贤
[内容提要]池莉的《大树小虫》书写了三代人近百年的日常生活,内容上延续了作者之前的以世俗烟火书写时代变迁的风格,叙事艺术有了大的突破,尤其体现在文本中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运用上。主要有三点:一是打破情节时间,以流动的时间控制故事节奏,塑造圆形人物;二是以外延的空间讲述历史故事,不断颠覆既有的形象;连缀起历史片段,拓展文本内涵;三是在时空交错中书写当下,以个体书写群体;反思了人与环境、代际沟通、人类繁衍等永恒话题。
从1987年的成名作《烦恼人生》到2019年出版的《大树小虫》,池莉的作品总是能吸引一大批读者,她书写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人和事,几乎每个人都能在她的作品中找到某些共鸣。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缩微的人生,每一个人生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每一篇作品都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她以细腻的文字描绘了世俗众生相,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不追求深刻的思考、犀利的批评,但记录了时代和时代中的人们。或许是长篇的缘故,《大树小虫》的叙事艺术和以往有些不同,除了隐喻的人生书写之外,尤其表现在对文本时间和空间的运用上。她把同一情节时间剪断,把不同的情节时间揉碎重组,既有中国古代文论所强调的演述时间,也借鉴了西方小说中的情节时间,构成了多层空间。每一节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每一章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整个文本环环相扣,时间和空间转换自如。不仅呈现了三代人的故事,塑造了圆形的人物,书写了普遍的烦恼人生,还有对“人生代代无穷已”和生态环境的思考。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固有的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法都有了新变,打破了她既有的小说艺术成就。《大树小虫》中的“时间和空间”艺术主要有三点:以流动的时间控制故事节奏,塑造圆形人物;以多重的空间讲述历史故事,拓展文本内涵;在时空交错中书写当下人生,融入生活万象。
一、以流动的时间构成叙述节奏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是则人物形象和故事发展的背景。作家运用时间因素营造不同的空间或转换空间形成不同的时间是两种常见的“时空”艺术,时空的自由转换不仅有助于圆形人物的书写,还极大地增加了文本的意蕴。“凡是我所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的”。[1]190-216相比较而言,早期《口红》《来来往往》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所以》中的文本时间大都是直线型,较少循环往复,阅读思维很少被情节时间打乱。《大树小虫》则不然,非静心读不懂其中的内涵,一个谜语套着一个谜语,一个谜底隐藏着一个谜底。叙事时间上的时空交错是《大树小虫》的显著特征,以流动跳跃的时间速写人物表情,让故事呈现出快进、暂停、后退的节奏,形成奇特的阅读体验。从表层看小说分为两章,第一章是人物简介以及人物关系概述,以人物名为标题名。先着力叙写第三代人俞思语、钟鑫涛,留下一个悬念,依次介绍他们的父母以及第一代人俞奶奶、俞爷爷,讲述他们在不同时间的生活。第二章是故事,借鉴了日记体小说的书写方式,以年、月为标题名,文本的表层是写年轻的第三代在2015年的生活状态,实际上讲述了这一年十二个月中发生在两个大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故事。结尾的第十二个月看似“真相大白”却是结局留白,作者以“翻开了新的一页”结束。新的一页会怎样?这里又宕开一笔为读者开拓了一个虚拟时间和想象空间。
小说第一节,俞思语、钟鑫涛已经完成了人生蜕变并面临新的问题,作者加快讲述时间的节奏,从他们出生的惊心动魄写起到成为父母的种种曲折后;转而讲述另一个故事,故事同时发生,一个故事时间的暂停是另一个故事时间的开始;小说的最后一节文本中的主要人物大团圆,俞思语、钟鑫涛还在为“做父母”、完成父母的心愿而烦恼,即小说第一节中提到的人生困境他们还未得以解决。文本时间快进而故事时间后退。这种表现手法不仅体现在男女主角的故事中,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形象上,如格瑞斯的经历,俞、钟两家父母的人生等。一个个环环相扣的人生、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不断冲撞却有首尾呼应的文本中似乎有一个“循环往复”的主题,是对生命循环的洞悉?是对自然生态的思考?还是对人生百态的参悟?作者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文本的表层以时间为顺序,择取人物表情的关键点即时间点有节制、有节奏地讲述着几代人的故事。“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2]562-572小说第一节,主要人物或者说重要人物全都出场了,作者着力于书写这些人物出场的“现在”状态即人生表象。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相遇,不同的故事在同一时间发生,不同的形象有了交集,同一形象也因为立体的故事时间有了更全面的呈现。格瑞斯在文本中虽然是配角,她的形象却最丰满,最能体现复杂的人性,她是俞、钟两家的连接点,也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两家人的生活。她先以俞思语闺蜜的身份出场,是时尚、洋派的法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创业的商界精英;依次是俞亚洲的忘年交;钟永胜的知音;任菲菲、高红的好朋友;在不同的时间里她的形象也不同。作者以流动的时间表现了一个人的成长,还书写了人性在个人不同成长阶段的奥秘。让时间诉说光阴的故事,不拘泥于单一的线性叙述。如果说在讲述第三代人的故事时是直线型的时间,那么讲述第一代、第二代人的故事则是利用追叙和回想,能让几十年的事情在极短的时间内再现,也就是说,这一叙述是由线段型的时间和时间点构成。在写两家父母曾经惊心动魄的爱情时,以特定的时间段为界限,择取俞亚洲二十三岁那年的暑假,任菲菲做讲解员的时期;高红、钟永胜传奇的初相见;在叙述第一代人之间的离合悲欢时,文本用时间点表达,选取家庭生活中看似不经意发生却有重要意义的关键事,如钟父在五四青年节去世,钟母早年对家庭卫生的执着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矛盾等;俞爷爷、俞奶奶之间的敏感词“彭厨子”。直线型时间、线段型时间、时间点视域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立体、多面、完整的。
人物塑造的成就很大一部分源于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的自由切割,跳跃的时间隐匿了故事时间的逻辑性,但却建立了形象的内在联系,不同时间里的形象有着不同的言行,不同的言行从不同层面聚焦式塑造同一形象。有时是遥远的历史,有时是切身的当下,有时是“过去”与“现在”瞬间重叠。人物性格不断被补充,甚至是颠覆,阅读期待不断被打破。在故事开始的地方也是故事的结束,在文本的结尾又回到了故事的开始,形成交相辉映和互文的效果。强调“时间”的叙述价值,利用“时间”因素书写形象,在池莉之前的作品中并不明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她的小说对历史与当下的表现较多,很少书写未来,更不会为作品中的人物选择未来,也因为这一特征,她小说中的时间形态以“过去”“现在”为主,小说中的形象是过去和现在的集合。《大树小虫》中不仅有对“未来”的呼唤,还有未完成的“现在”,开放式的结尾由读者去判断。以流动的时间掌控叙述节奏还意味着“一种简约、浓缩的技巧”,[3]91以简洁的手法书写了包罗万象的生活空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立体的人物群像。
二、以多重的空间丰富文本意蕴
具体的场景描写是空间的主要呈现方式,具体的地点是空间的载体,每一个地点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大树小虫》中的空间并不受时间的制约,两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它和时间在文本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概括来看有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下的书写:一是客观的地理环境空间。如上海、武汉近百年来的地标性建筑,选取了铁路、火车、招待所、军区大院等公共“地点”进行细描,带有时代的烙印和老一代人的青春。二是微观的生活环境空间,如三代人不同时期日常生活中所处的场景、场面。筒子楼、高档住宅楼,居住环境不断改善,每一个空间里都有一个故事;轿车、游轮,交通工具的更换诉说着时代变迁以及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商城、广场与时尚、现代化密切相关,是文本中第三代人实现生活仪式感的空间,这一空间见证了他们人生中许多关键场景,也造成了污染并影响到个人健康。三是作者在讲述故事时为打通代际关系而建构的话语空间,以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为中心,两种视角交叉进行。
两种视角下的书写构成了多重空间,情节在一个又一个场景的转换中快速发展,以第一节为例来看,细描俞思语的片段有:出生时的她;成为大学生的她;高级写字楼里的她;参加同学聚会获得“最成功女生”称号时的她;五个家庭聚会时的她;婚礼上的她;为人母的她;重返职场的她;马尔代夫归来期待二胎的她。她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言行,作者让形象在不同空间里自由活动,实写与虚写相交,看似杂乱无序,实际是充分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实际上是人类依靠想象和虚构,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与人生进行秩序化构建而呈现意义的艺术”。[4]118作家用不同的空间对钟家、俞家、高家三代人近一百年的历史进行了秩序化构建。每论及一个形象,都会追溯家庭历史,每一个家庭自成一个“空间”,为了情节的需要,常常会中断对过去历史的回忆跳到当下场景,甚至是在同一时间里营造不同的空间。例如在俞思语和钟鑫涛的成长轨迹里,时间相同,但所处环境和空间不同;在格瑞斯与高红的平行时间内,所处空间也不同。在讲述高红与钟永胜、俞亚洲与任菲菲的故事时,时常插入各自原生家庭状况,直接或间接勾画了上一代人的生活空间。每当他们在面对人生抉择时,作家就让他们陷入对过去场景的回忆,让大段的内心独白去表现真实的他们。而在讲述俞爷爷、俞奶奶时,又把读者带回到久远的过去,从1949年谈起。这一叙述方式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扩展了文本内涵,不同时空的场景、不同时空的地点互映,历史深度与当下生活广度凸显。
作者的话语空间像一个迷宫,文本中实际上是讲述了九个小家庭的故事,相对应的事物琐碎烦乱但又条理清晰。选择合适的空间表现人物,有时是强调人的外在环境——所处都市,有时关注人的私人空间——家居环境,并有一定的隐喻在其中。前者仍以格瑞斯为例来看,她辗转多处,作者选择了三处重要的“地点”进行细描。她在广西桂林的生活片段,她身份证上的姓名是韦大姑,因为会唱歌而成为刘三姐景观园中的经理;法国读书期间她到川菜馆打工时与钟永胜的偶遇,“个子小,皮肤黑,一点也不起眼”的她以一曲《梦里水乡》而巧遇知音;她在武汉的八年是“风华正茂,神采奕奕的格瑞斯”。作者详细地描绘了每一个“地点”的格瑞斯及其生活空间,不断转换她在各种场合的情景:在俞思语、钟鑫涛两家初次聚餐的地点,汉口西北湖广场的好世纪大酒店,她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法国留学生、是运筹幕后的主持人;在武汉天地商业街,她是保罗木梳酒庄的主人。这其中既有客观环境的表现也有对人物心理空间的表达,同时也隐喻了格瑞斯漂泊的命运。对家居环境的细描有多处,有意味的是对高红、钟永胜和俞亚洲、任菲菲两家私人空间的叙述。一个是两套打通、带有庭院和秋千、费尽心思豪华装修的家;一个是四室两厅高规格装修的家,但“大面积的空白墙壁……大小相框就自己待在储藏间一待几年灰头土脑,让俞亚洲看到就心塞”。[5]269高家的厨房里一年四季、一日三餐都是热气腾腾、各种美食层出不穷,人间烟火中透出家的温暖,尽管也有不断的争吵;而俞亚洲家的厨房是冰冷的摆设,精美的餐具只做泡饭和速冻水饺,两人相敬如宾。文本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细节,以客观的场景、地点营造出另一个“空间”,多重空间的组合扩充了文本意蕴,有限的文字建构了溢于言表的另一空间。有时是单一的地点,有时是重叠的场景,有时是交错的地点和场景共生,形成了一种别致的空间感。
三、在时空交错中反思永恒的话题
小说的封面上写道:“人间城郭是苍穹之下的微缩景观”,扉页上则引用了爱因斯坦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解释,是《大树小虫》的隐喻,在日常琐事的书写中隐藏着对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未来的思考。与早期作品里一半烟火一半清欢的人生片段相比,这部长篇写了三代人,关注了代际差异、代际沟通甚至是人类繁衍这些永恒的话题,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时空怎样改变,总有一些相似的问题存在于人生的某个阶段。作家的语言一如既往的清爽、轻快,作品中的每一个人在面对困境时都是乐观豁达的,都擅于接受并顺应人生的种种改变。然而这轻盈的背后却有无法忽视的沉重:在历史的河流里,在短暂的人生中,所有人都无法真正掌控不期而遇的悲欢离合。
与其说第三代人是文本的主角,不如说是以第三代为焦点透视其他形象和现象,以便情节在历史与当下自由转换。文本直接表现了第一代独生子女与父母和祖父母之间的错位关系,间接反思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父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祖父母负责照顾,孩子与父母的情感隔阂由此产生,隔代亲现象凸显。代际沟通问题不是因为科技等客观因素而是因为主观情感,是童年经验的缺失,并影响到个体性格的形成。四岁前的钟欣婷是远离父母在“猪鸭鸡狗的相伴”下度过,回到父母身边后依然是被全家人忽视的那一个,和哥哥钟鑫涛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小时候“恨她全家”,青春期时叛逆的她成了全家人的心病,或者说她最初只是想以叛逆获取家人的关注。俞思语的成长过程中从不缺爱,但父母的陪伴是缺失的,幼年时她以“叔叔、阿姨”称呼父母,成年后的她和父母依然无法亲近,彼此都意识到那份无形的距离。钟鑫涛、钟欣婷、俞思语的成长过程中都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良好的家教,作者微妙地写出她们性格中的另一面,不动声色审视童年经验对个体性格形成的影响,剖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现象,溯源式探究代际沟通。然而,人生阶段总有相似,成年后的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又一定程度上重复着父母的步伐,孩子交给保姆和爷爷奶奶,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工作而是“三朋四友一大群”和“街上流行什么”。俞亚洲、任菲菲把退休后的美好生活寄托在“抓住外孙子”,“说来可笑,曾几何时,俞亚洲很是鄙视那些带孙子的老干部”;[5]293钟永胜、高红亦是如此,他们都不自觉地走上了特定的人生阶段,隔代亲将继续上演。小说中设置的人物有婴幼儿也有八十多岁的老人,这些形象的年龄段恰好与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个阶段相一致,即:构成一个循环的周期,并形成一种参照和呼应。
在文本的第二章,作者以“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隐没”作为题记,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第一代、第二代人的人生已经定格,他们这一阶段人生的共同目标是二胎,文本情节是围绕一个未出生就已引起两个大家庭关注和无限畅想的宝宝,两家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待新生命的降临,因为“思思再生一个孩子就是对老人最大的孝敬”。[5]426这一年年底,俞思语的外公外婆、俞爷爷去世了,新生命还未到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是“全球问题”。小说在家庭聚餐的热闹气氛中结束,体检单的问题大家都积极面对。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道出一个真相:个体的人无法改变人生自然规律,全球的科技发展、环境变化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个体的人。
《大树小虫》在人物形象和语言上延续了作家以往的风格,而在对“时间和空间”的运用上有很大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自由组合、切割、拼接不仅让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也增加了文本的深广度。在历史范畴中写人,以人反观时代和历史;从童年经历反观个体性格的形成,反思代际沟通;以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表现当下一些生活现象和时代热点。小说因此而意味无穷,时间和空间在文本叙事中的价值因此而凸显,是作家叙事艺术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