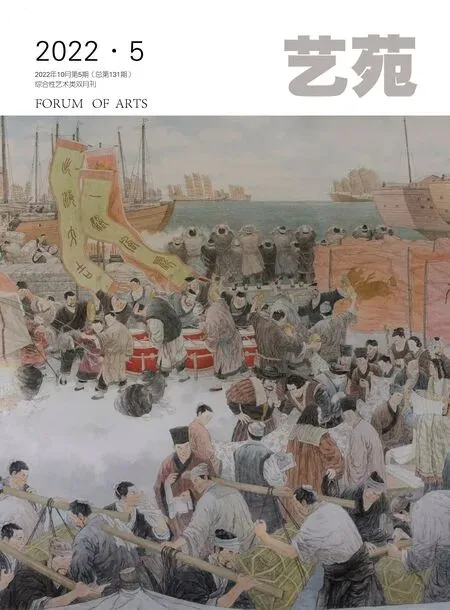从《敲门叩问》看纪蔚然戏剧创作的变与不变
2022-04-16胡明华
胡明华
2022年5月,福建人民艺术剧院陈大联导演与台湾剧作家纪蔚然合作的多场次戏剧《敲门叩问》在福州人艺黑匣子小剧场上演。作为继《盛宴》(2019)、《12.3坪》(2020)之后的家庭伦理三部曲终结篇,纪蔚然提到:“第一部写一个家庭,第二部写两个家庭,最后一部想从实体的家谈到精神的家,借此探讨人的困境与憧憬。”[1]从剧本内容和舞台演出呈现来看,这是一部实验性较强的小剧场作品。其实自《安娜与齐的故事》《衣帽间》以来,纪蔚然的戏剧创作已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敲门叩问》处理的仍是他熟悉的家庭题材,仍保留他对当代台湾社会流行语言现象的敏锐捕捉和呈现,对于台湾社会乱象的映照与反讽,但是新的剧作主题及人物形象类型的出现,剧情编排上对于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美学追求,让纪蔚然的戏剧在似曾相识中多了一些陌生和奇异感,它们体现了纪蔚然在创作追求上的自我反省与创新意识。
一、从家的崩解到家的联结
同《12.3坪》一样,《敲门叩问》聚焦的仍是当代台湾社会的两个家庭两代人,即汪家爸妈和儿子小明;作家永嘉、妻子方萍和儿子阿明。这两个家庭仍共享同一个空间,但是在时间上却跨越了40年。作家一家生活在40年前台湾新北市深坑乌月山脚下的偏僻乡村,汪家虽是同一空间,却是现在已变成高档社区的——祥瑞聚落。无论是深坑乡村还是祥瑞聚落,它们都是与都市保持一定距离,较为亲近自然的生活空间。两个家庭从都市搬到这里之后,却发现他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并不尽如人意,陷入了各自的困境之中。
作家虽然是歌颂自然的田园诗人,但是并不具备在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妻子对他偏执的生活态度产生不满,家庭矛盾升级,最终儿子在池塘中溺水身亡,妻子离去。汪家则是因为发了一笔不义之财,搬到了祥瑞聚落。儿子小明不仅发现这里曾经是凶宅,还在梦中与以前住在这里的作家对话。几个月内,聚落里出现了各种男盗女娼的事情,邻里之间不再来往。最终小明发现爸妈原来是因为做伪证诈骗了一笔巨款,才买了这里的别墅。他劝说爸妈去自首坐牢,自己留在家中等待爸妈的归来。
纪蔚然对该剧的创作定位为“一则关于家的寓言”。该剧由序场、尾声和十个场景组成。汪家的生活场景侧重于外部的社交功能呈现,包括买房,汪家父母与聚落其他住家的交流等,揭示家庭与外部社会的关系;而作家一家的生活场景侧重于家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夫妻争吵,亲子矛盾,揭示家庭内部的关系。两个家庭碎片化的生活场景交叉呈现,营造出家庭内外共存的矛盾和危机感。在写实性的生活场景之外,纪蔚然还加入了超现实的场景,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与变化。比如剧中的小明在地下室遇见了过去生活在这里的作家。两人的相遇和对话似乎发生在梦中。作家的家庭遭遇为小明打开了视野,让他认识到自己不能像作家一样活在自己织就的理想之网中,尽管现实人性不断暴露出丑陋鄙俗的一面,但他需要这种实在而平凡的生活。
作家与汪家父母都以现代文明人的身份去接近、融入自然,但是他们无法做到以平等的姿态与自然相处。作家养猪养鱼,都以失败告终,并不适合农村生活的他矫情刻意地远离城市,以致于手拿镰刀威胁妻子的生命;祥瑞聚落的人们刻意追求平等民主、夜不闭户的生活,却难以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身份偏见和歧视,导致居民纷争。最终他们对理想家庭的打造都遭遇了失败。
这两个家庭的故事揭示出,无论是40年前还是40年后选择田园生活的现代人,无论他们进行怎样的尝试和努力,乌托邦式的家庭理想最终都遭遇了失败。只要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无法消除,理想家庭就只能是梦幻泡影的存在。剧末,小明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坦然地面对人性与现实中的缺陷,或许这样才能在废墟之上重新开始并建构新的家园。
从1990年代的家庭三部曲到21世纪的家庭伦理三部曲,纪蔚然在剧中所呈现的家庭总是缺乏安全感的所在,不仅有家庭成员之间的背弃和不信任,也有家庭外部所受到的干扰和侵害,且最终都会走向崩解。《12.3坪》和《敲门叩问》也毫不例外。但是《12.3坪》和《敲门叩问》的家庭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不仅有两个家庭的对比或并置,而且这两个家庭最终都以某种形式实现了联结。《12.3坪》中两家的下一代儿女原来只是通过微信交流,剧末他们终于鼓起勇气在现实中相见;《敲门叩问》中,先是小明和作家在梦中相遇,最后小明在聚落废墟上与老年的作家妻子方萍相遇。崩解后的家庭成员似乎都在家庭外找到了各自的精神支撑和救赎勇气,这也为全剧的结尾带来了超越现实的希望和可能。
从以上的变化可见,纪蔚然不再像早期的家庭三部曲那样聚焦于一个家庭,集中强化家庭中的离散主题和黑色情绪,而是通过两个家庭,甚至在《敲门叩问》中还通过聚落内更多的家庭离散遭遇,来表现家庭并不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无论在都市还是田园式的乡村空间内,无论是过去的1980年代还是当下的社会,家庭始终都面临着不同的危机和困境。家庭原本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组合性和动态性存在,与其执着于追求它内在的稳固性和安全性,失落于理想性和现实性的落差,像作家一样为其所困,还不如面对并接受它的平凡庸俗,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剧中的小明不愿意成为作家那样的人,为了自我的理想主义而脱离现实,他还是选择了包容自己有过错的父母,在家庭的废墟上守候,等待父母归来。而方萍遇到了和自己儿子同名的小明,也愿意和他一起携手,在这个废墟上与她悲痛的过去进行和解。由此可见,纪蔚然不再满足于书写家庭的崩解,而是在这两个家庭解体之后,特意安排小明和方萍携手开拓新的家园作为结局,代表着他在家庭之外寻求精神联结和救赎性的展望。
纪蔚然在剧作题记中曾指出该剧:“探讨‘门内’与‘门外’、‘自我’与‘他者’、‘家内’与‘家外’的复杂关系。如果‘家’是‘最后的堡垒’,家门之外不就成了战场?如果家是‘心灵的港湾’,家门之外是不是狂风暴雨的潜意识?如果家为枷锁,离开它是不是代表自由?”[2]这段话揭示了剧作家对家内与家外是否存在二元对立关系的反诘与疑问。结合剧情可以看出,家庭内外不仅有崩解,也有重建和联结的可能;像小明那样不被家庭所困,积极地向内自我反省并向外建构联结,同样能给濒于崩解的家庭带来新的救赎希望和可能。
二、象征手法的运用
同《12.3坪》一样,纪蔚然在剧中也使用了丰富的象征手法。该剧的剧名原为《门禁社区》,后来改为《敲门叩问》。从《门禁社区》到《敲门叩问》的剧名更换,“门”的意象得到了重点突出。《敲门叩问》中并没有敲门的具体动作,但是门的意象得到了重点突出,即“五扇同样大小的门不规则地竖立于舞台。主要表演区有一桌二椅”。舞美设计师马连庆以“门”为切入点进行空间建构与延展设计。他在舞台前方设置了一个大的LED透明显示屏幕(带有黑色的网格边框线)。这个屏幕既能用来投影,比如剧中的蜘蛛网和“川普”墙通过投影来呈现;又可以把舞台表演区域分隔为前后两个空间。从观众视角来看,仿佛通过一个封闭的围栏在窥视别人家发生的琐碎日常;从演员视角来看,则如同被围在第四堵墙内进行表演。在舞台左右两侧都有不同大小的门,方便演员在屏幕内外进出表演。舞台后方也有推拉的网格门设计,交待不同的室内空间转换。多个不同的门形成了对封闭空间的切割与组合。
剧中小明也不断地提到门的意象,比如他对作家说:“我最近领悟了一些事,发现人生里有很多扇门,只要有勇气打开,就可以踏上一段旅程,进入另一个境界。但是那么多扇门、那么多选择,要打开哪一扇呢?打开这一扇而不选择那一扇,到底是命运还是意外?”[3]这里的门既可以看作是家的入口或出口,也可以看作是人与人沟通的心门。无论家庭内外,还是人与人之间,都渴望平等友善的交流和沟通,但隔阂与疏离却是常态,所以门无处不在。作家一家搬入农村,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农民,所以他们与周围的环境并不和谐;小市民背景的汪家父母搬入高档的聚落,却难以成为真正的精英阶层,他们与周围邻居的关系并不融洽。而两个家庭的内部成员之间在沟通上也出现了隔阂与断裂。所以在各种门的阻绝之下,家庭的崩解不可避免。令人意外的是,作家和小明虽属两代人,他们无法与家人沟通,却能够彼此打开心门,化解各自所面对的困境和内心纠结。剧作家通过这个情节揭示人只有勇敢地向外或向内打开闭锁隔绝的门,才能摆脱门的枷锁,找到新的出路和救赎希望。
除了门,镰刀、蜘蛛网的意象也在舞台上多次出现。剧中先是作家与妻子出场时,手里拿着镰刀;最后的废墟场景中,镰刀又出现在小明手中。而且纪蔚然还特意在人物介绍中把作家一家称为“镰刀之家”。镰刀作为欧洲文化中死亡的经典意象,既是用来收获粮食的农具,更是死亡降临的象征。作家出场时,他手里拿着镰刀威胁妻子的性命,并让儿子阿明在爸妈两人之中只能选择一人活着。在这样的暴力家庭氛围中,其子阿明的存在感很低,所以剧中这个孩子以“只闻其声”的形象出现。阿明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会游泳,在池塘中溺水身亡,而妻子方萍认为儿子是自杀,因为他感受不到父亲对自己的爱和温暖。小明的父母做伪证获取了一笔不菲的赔偿款,买了别墅,认为可以重新开始并跻身精英阶层,却以失败而告终。无论作家还是小明的父母,人性深处的自私贪婪让家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镰刀作为农耕文明和死亡暴力的象征,隐喻了家庭所兼具的文明和野蛮的双重属性。
全剧开始,舞台上方就挂着一张小的蜘蛛网。在第四场,舞台多出一张蜘蛛网。第八场,舞台又多出一张蜘蛛网。尾声,舞台布满蜘蛛网。舞台上的蜘蛛网通过LED显示屏得到了由小变大的动态呈现。蜘蛛网在剧中的象征是多义的。它既可以看作是剧中角色的隐喻,也可以被理解为家庭人际关系的象征。比如小明把作家看作是他要寻找的蜘蛛,因为他是在地下室发现了作家,而作家的个性与独居生活的蜘蛛很相似。他喜欢离群索居,追求自我发展的极致体验,像蜘蛛一样通过创作来吐丝结网,不甘于过平凡务实的生活。对作家而言,家庭就像蜘蛛网,让他感到束缚和不自由,所以他觉得自己不是蜘蛛,而是一只被困在网中的飞蛾。
汪家父母似乎与蜘蛛无关,但是联想到他们欺诈法拉利跑车母子的行为,又何尝不像等候在旁边猎食的蜘蛛?汪家还认为他们在聚落的新家是一张新网,借此可以与社会菁英建立联结。但是这个网最终也破散了。小明原本生活在父母编织的谎言之网中,他无忧无虑,以为父母是做生意赚了大钱,才搬来聚落生活。但他在地下室里遇到作家后,才发现有很多隐藏在门后的危险真相等待自己去发现和确认。
蜘蛛网作为家庭的隐喻和象征,揭示了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纠结、难以分离的伦理关系。这个网可以让人感觉压抑束缚,也可以让人感觉安稳可靠。它可以是温暖的港湾,也可以是陷阱和捕猎的战场。在剧中越来越大的蜘蛛网既象征着家庭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个成员的重要影响,它让人难以挣脱或逃离,因此剧末即使身受家庭重创,方萍在老年还是回到了她这个曾经的家园,难以忘却她在这里的回忆;它又象征着每个家庭其实都不是一座孤岛,它还有向外延伸或扩展的功能,联结着外面的不同个体与社会。所以看似个别的家庭问题也是某种社会问题的折射与暴露,值得人们对身处其中的社会进行忧思并反省。
纪蔚然在《敲门叩问》中所使用的象征意象具有两个作用:一是用蜘蛛和白蛾这些动物意象来隐喻家庭成员的生存状态,如同《12.3坪》中用斑马、孔雀等动物隐喻家庭成员的个性一样,通过动物的隐喻能更好地揭示现代人所身处的半文明半野蛮的进化状态;二是小明梦境中所看到的门、蜘蛛网和白蛾等意象构成了一座充满象征符号的迷宫,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反日常的新奇组合与可能。基于“戏剧,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形式,不时呈现异于‘正轨’或‘常态’——介于秩序与崩解之间——的情境”[3]15的认识,纪蔚然在剧中设置了异于“常态”的意象,让观众从另一种视角感受戏剧情境里逸出“日常现实”的时刻,以及那个时刻对剧中人物所代表的意义。
三、纪蔚然戏剧创作的变与不变
《敲门叩问》不是一部很容易理解的小剧场作品。尽管它属于写实的家庭生活题材,导演也最大限度地对原作进行客观忠实地呈现,但是由于剧作家在原有的编剧理念和风格上进行了调整和创新,执意避开了易于讨好观众的情节剧构思,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以及戏剧艺术功能的设定上,《敲门叩问》和以往的剧作相比有保留也有变化。在变与不变之中,纪蔚然戏剧的独特风格得到了彰显。
首先,从纪蔚然对家庭题材的传承和创新来看。1990年代至21世纪的家庭三部曲(《黑夜白贼》《也无风也无雨》《好久不见》)中,纪蔚然多以青年人(下一代)的视角来呈现并处理他们与上一代父母之间的关系,包括父母、家庭及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压抑和创伤。在21世纪新的家庭伦理三部曲中,如果说《盛宴》与《黑夜白贼》还有创作视角上的承接和关联,那么《12.3坪》和《敲门叩问》中,纪蔚然把创作视角和关怀更多地转移到了家庭中下一代儿女形象的塑造上。在家庭身份上已经由下一代变成上一代的纪蔚然开始以中年人(上一代)的视角来反思他们对下一代的影响与责任,所以剧中出现了新一代的人物形象,比如《12.3坪》中的牧群和小凤、《敲门叩问》中的小明等。尽管在他们身上也有脆弱敏感的一面,比如《12.3坪》中的牧群不为虚伪世故的父母所容忍被逐出家门,《敲门叩问》中的阿明不堪忍受父母之间的争吵和暴力相向溺水身亡,但是剧作家以宽容和信任的态度在他们身上寄予了改变的希望和可能。他们同样要承担或背负父母一代的过失与伤害,比如《12.3坪》中的小凤差点被父母的朋友四海叔侵犯,小明发现了父母为了金钱做伪证的真相,但他们在接触了现实庸俗丑陋的真相后,依然能够勇敢地面对并接受现实,使濒临离散的家庭有了修复重建的希望。
为了生动地塑造新一代的人物形象,纪蔚然在剧中采用了象征和梦的隐喻等手法来表现他们的心理世界。这些形象多富有想象力,内心敏感而彷徨,符合青年人的心理特点。比如《敲门叩问》中的小明就是一个兼具诗人与哲学家气质的青年人,剧中他有较多的内心独白,比如:“有一回,我走进一扇门,里面的空间很窄,只有一个螺旋阶梯,阶梯往上无限延伸看不到尽头,我一直爬一直爬,越爬越亢奋,以为会到达一个新奇的世界,最后却来到这个阴暗潮湿的斗室,看到你这个坐在角落的孤独老人。还有一回打开门之后,换成无限往下的螺旋阶梯,我一步步走着,感到晕眩,仿佛顺着一股漩涡往下沉没,没想到走到了尽头还是遇到你。”这段充满诗意的独白揭示了人性在向上升华与向下沉沦之间的挣扎,也是人类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所恒常陷入的精神困境。从新一代家庭成员形象可以看出,已进入耳顺之年的纪蔚然已然从一个冷眼旁观,甚至有些“尖酸刻薄”的剧作家变成了一位能够接纳庸俗平凡的“纪伯”。
其次,从剧作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来看。剧中仍能看到纪蔚然以往所擅长的对于当代台湾时事乱象的揶揄与反讽。“场四”“美美地丢垃圾”开头部分,剧作家安排了两位舞者跳芭蕾倒垃圾的动作表演,其构想就来自于几年前台湾的一则环保广告(1);“场八”中汪妈提到的邻居蔡妈妈和曹爸爸在丢垃圾时眉目传情,最终私奔的情节显然也是对该广告片的戏仿; “场十”中,汪家父母正在家中吵架,忽然一辆跑车闯进汪家客厅的情节也并不是剧作家的脑洞大开,而是来自于台湾真实的社会新闻,纪蔚然在此基础上对后续情节进行了更戏剧化的延伸补充,让汪家爸妈趁机敲诈了醉驾肇事者,发了一笔意外之财。以上充满无厘头与意外的台湾社会乱象成为纪蔚然戏剧创作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在这样一个缺乏秩序和规律、充斥着混乱和意外的社会中,家庭能够独善其身,并且为其中的家庭成员提供充分的安全和归属感吗?作者显然对此是质疑的,所以剧中的小明会疑惑: “到底是命运还是意外?很多人把意外当作是命运,他们可能很蠢,但反过来说,把命运误以为是意外不是很恐怖吗?”
最后,从纪蔚然戏剧的创作转向来看。近年来,受朗西埃美学观和人类学家特纳“阈限”(2)概念的影响,纪蔚然对戏剧的批判功能及作用产生了质疑,其戏剧创作意欲摆脱先前“带刺”的现实批判路线,超越批判,转向更具开放性和参与性的美学路径探索。这种尝试从《安娜与齐的故事》《衣帽间》就已开始。在《敲门叩问》中,观众可以看到剧中的人物对白与剧情设置越来越趋于“不可靠性、歧义性、多义性”[4]41的风格转换,比如阿明的溺水身亡在作家口中是意外,在妻子方萍的口中则是自杀。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剧作家在剧中没有做任何确认。而作家这个角色,他怎么会和小明在地下室相见,妻子离开后他又去了哪里?小明与作家一家又是怎样的关系?对于这些内容,剧作家也不做明确的交待,观众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猜测或补充。由此,观众在观剧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未知的历险挑战,不得不成为剧作主动的诠释者。纪蔚然不再以全知的上帝视角和启蒙大众的姿态去创作,因为他深切地认识到,在这个后布莱希特的年代: “实在轮不到剧场工作者站在‘知’的高位,来‘教化’那些他们以为‘无知’的观众。剧场能做的,其实不多,除了故事与声色带来的娱乐,就是呈现新的想象,让理所当然的事物变得奇怪,让不可能的事物仿佛稀松平常。换言之,就是让平常紧密关联的事物失去连结,让平常毫不相干的事物得以连结。此为雅各布·朗西埃所谓艺术对惯性感知造成冲击所导致的‘悬吊’。”[5]23同样,特纳也指出,阈限里的象征符号有些是正常社会的倒置,这些经过重组、怪诞化的意象会强迫观众重新思考平日习以为常的事物,包括人际关系、所属社会、他们的宇宙等等,其目的是让“观众在观剧时更需保持着一种时刻准备着去分析、判断、揣摩人物和剧情的客观态度,从而使剧场演绎达到双重的客观性”[4]41。可见,《敲门叩问》体现了纪蔚然身为剧作家在创作理论上的自觉及创新意识。
四、结语
从《盛宴》到《12.3坪》和《敲门叩问》,在福建人艺和陈大联导演的努力下,纪蔚然的家庭伦理三部曲在福建人艺小剧场的上演,因贯穿了整个疫情期间,显得极为可贵。只有像这样极具当代关怀和探索意识的现实题材原创作品不断推出,才能形成一定规模和现象级效应,推动当代小剧场艺术的发展与前进。由福建人艺探索出的这条以著名剧作家为创作核心、以海峡两岸合作为基础的发展道路不仅切实可行,其经验和成果也值得进一步的总结分析。
注释:
(1)可参见腾讯视频网站上“美女跳芭蕾倒垃圾,宣传环保人人有责”的广告宣传片。
(2)“阈限”意指门槛,一个存在于‘之间’的时空,一个既不属于这,亦不属于那的尴尬情境。可参见纪蔚然的论文《阈限概念与戏剧研究之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