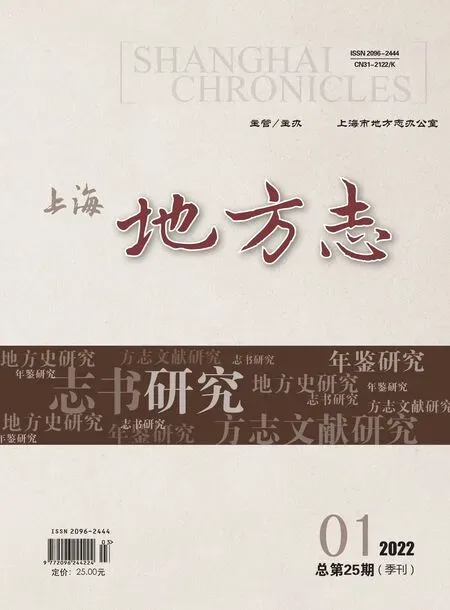《西藏志·附录》的资料来源及价值*
——兼论《西藏志》与《西域全书》《西藏志考》的关系
2022-04-16赵心愚
赵心愚
乾隆初年成书的《西藏志》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抄本流传颇广,影响也颇大,清代不少西藏方志以及一些研究西藏的著作都从中大量采择材料。邓锐龄先生在《读〈西藏志〉札记》中认为,《西藏志》“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可谓在旧新唐书吐蕃传后数百年间罕见的巨作”。由于《西藏志》资料宏富,记述较详尽,体例亦较完善,《中国地方志辞典》将其列为中国方志史上的“著名方志”。近年来,已有学者对《西藏志》做全面审视与评价,并对《西藏志》资料来源及与其他早期清代西藏方志的关系进行探究。《西藏志》由诸多篇目构成。相对而言,对此志篇目的研究目前却显不够。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拟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西藏志·附录》的资料来源、价值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并分析和阐述《西藏志》与《西域全书》《西藏志考》的关系。
一、《西藏志·附录》的资料来源
《西藏志》体例为清初流行的“平目体”,即全志平列多目互不统属。在全志30 余目中,“附录”列“程站”之前。从内容看,“附录”分为三部分:一是与西藏相邻的白木戎相关情况及西藏种类。先记由拉萨至后藏塞尔地方再到白木戎的路程;其次记白木戎部落社会及民俗、物产与宗教;之后又记白木戎东、南、西、北四至各地及以西的大西天、小西天地区;最后记西藏各种类。二是有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郡王颇罗鼐的有关情况。先记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住地及郡王颇罗鼐、班禅管辖寺庙、喇嘛、城池、百姓数;再记由召(拉萨)、阿里至各方向不同地方路程的资料。三是布鲁克巴、巴尔布有关情况。先记布鲁克巴部落、城池、百姓、寺庙、喇嘛数与四至地方与路程;再记巴尔布部落、百姓数以及东、南、西、北四至地方与路程。值得注意的是,其第二部分前有“乾隆二年造送理藩院入《一统志》”一语,记有明确年号。分析此语及出现的位置可知,“附录”第二部分资料的来源应如邓锐龄先生所言是“藏臣衙门遵理藩院下达之命写成的调查材料”。
分析“附录”三部分内容,其资料形成时间可认定为清初。《西藏志》成书前能见到的清初有关西藏的著述主要有两类。一类为纪程类著作。此类著作康熙末年出现,主要记内地、西藏往返路程及沿途情况。另一类为方志著作。李凤彩所撰《藏纪概》成书在雍正五年(1727年)或之前几年。雍正《四川通志》成书刊印于雍正十一年(其卷二十一为主要记西藏的“西域志”)。以上两类有关西藏的著述,从体例到内容以及行文特点,均与《西藏志》存在着明显区别,也并非系统全面地描述西藏各方面的情况。《西藏志》于乾隆初年编纂时在以上两类西藏著述中可利用的资料实际上很少。“附录”一、三两部分资料在这两类西藏著述中亦未见,应另有其来源。较早注意到《西藏志》“附录”的是何金文先生。他认为此“附录”带“补记”性质,文中引了“附录”的一条资料,但并未言及资料来源问题。邓锐龄先生的《读〈西藏志〉札记》最早对“附录”资料来源作了探讨,认为编纂者“必在拉萨驻藏大臣衙门多年”,并提出“附录”中的三条资料“是藏臣衙门遵理藩院下达之命写成的调查材料,被作者全部原封不动地采录”。
近年来发现,《西藏志》成书前已有《西藏志考》及与之存在密切关系的《西域全书》。这两部新发现的志书为清代西藏方志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但是,对这两部志书,各种方志目录均无著录,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方志辞典也无辞条,清代西藏方志研究成果中也未见提及。《西藏志考》体例为“门目体”,分为四册。观其篇目并与《西藏志》比较可知,《西藏志考》第四册“程途全载”首页上在前三册书“西藏志考”的位置却书“西域全书”四字,再提行才书“程途全载”。为何书“西域全书”?因资料所限暂作“原因待考”。后《西藏志考》篇目中没有“附录”目,由此可知——《西藏志》虽与《西藏志考》关系密切,但其“附录”资料应不是来自后者。2014年,刘凤强教授在南京图书馆发现了《西域全书》抄本,并在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比较分析了《西域全书》与《西藏志考》及《西藏志》的相关内容,首次指出《西藏志》“附录”资料来自《西域全书》抄本中的“略笔杂叙”“考遗”及“附录”等。2019年,杨学东博士在论及“《西域全书》对清代西藏方志编纂影响”的研究论文中,也将《西域全书》抄本“略笔杂叙”“考遗”等与《西藏志》“附录”作比较,并指出前者对后者的资料影响①。这两篇《西域全书》研究论文,积极推动了《西藏志》及“附录”资料来源的研究。细读南京图书馆藏《西域全书》抄本并比较《西藏志》“附录”内容,笔者认为,后者的资料来源问题仍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首先,《西藏志》“附录”资料虽然发现于《西域全书》乾隆七年(1742年)抄本之中,但实际上应主要为《西域全书》乾隆元年(1736年)稿本中的资料。《西域全书》此抄本前有三序,“撰辑”者锦城“玉沙道人子铭氏”所作“志序”署时为乾隆元年(1736年)“暮春月之朔”(三月初一),故《西域全书》成稿时间也应在当月。但是,目前所见这一抄本中,的确又有几条乾隆元年后的资料,最晚为第四册“道途全载”后明确提及“乾隆壬戌年”及“乾隆七年”的记事刻石条。以此条时间看,这一抄本时间应为乾隆七年(1742年)或稍后。《西域全书》这一抄本体例同样为“门目体”,从首册目录看,除列前面的舆图、人物图形外,平列34 目。通观其各目内容,可发现此抄本中多见雍正年号,绝大多数篇目记述的是雍正年间事,“封爵职衔”“设隘防边”“招徕土地”等记事亦止于雍正末年;记述中乾隆年号鲜见,乾隆元年的资料少,乾隆元年之后的资料虽有几条但均列所在篇目内容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及颇罗鼐的“寺庙名色”“年节时令”“衣冠饮食”“交接礼仪”“文书征调”“表章贡赋”及“封爵职衔”等目及人物图形题词中,皆称颇罗鼐为“贝勒”。而清政府封颇罗鼐为贝勒时间为雍正九年。结合绝大多数篇目记事内容及截止的时间,笔者判断:《西域全书》此抄本应主要为乾隆元年稿本的内容,乾隆元年三月后至乾隆七年的几条资料应为后人补缀。在中国历史上,史志著作后人补缀者不少。司马迁《史记》流传版本中就有一些补缀文字,有的内容已是司马迁逝世之后的事情。尽管存在补缀,但由于稿本的基本框架、篇目和内容并未作大的调整改动,南京图书馆藏《西域全书》仍应为一种抄本。
其次,《西藏志》“附录”资料虽主要为《西域全书》乾隆元年稿本中的资料,若再探究其最初的来源,则应为清驻藏大臣衙门档案及相关人员雍正年间在拉萨及西藏各地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关于清中央政府建立驻藏大臣制度及正式派遣驻藏大臣的具体时间,学界目前仍持不同看法,但主要为雍正五年与雍正七年两种说法。驻藏大臣入藏,代表清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要稳定西藏、管理西藏以及防准噶尔部军队的武力袭扰,均需要了解西藏各方面情况。从其基本职责看,正式派遣驻藏大臣的当年或稍后,驻藏大臣衙门应已开始存有包括驻藏大臣等官员到任与离任、西藏地方官员的赏赐与封爵、西藏各地城池与所属百姓、各地寺庙及支粮喇嘛、清在藏驻军及换防、驻藏大臣带兵分防各要塞及行军路线、西藏与川、滇、青行政分界等档案资料,其相关人员也已开始在拉萨及西藏各地开展了社会、自然诸多方面的调查,并形成了一批调查资料。分析文献中有关记载可知,驻藏大臣衙门设立后其相关人员在拉萨及西藏的调查,应还与雍正帝对《一统志》编纂的推进有关。雍正帝即位后,重组一统志馆,并向全国发出《行查事项》,对各地调查门类及采访内容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详查造册送馆”。西藏地区虽不能等同于内地行省,但驻藏大臣衙门也应按《行查事项》派出相关人员进行调查采访,形成的资料亦“造册送馆”。从“四至疆圉”“山川形势”“土地蓄产”“年节时令”“风俗好尚”及“婚姻嫁娶”等篇目内容推断,《西域全书》乾隆元年稿本中此类资料应相当多。这些资料一部分应是玉沙道人子铭氏到达拉萨前就已形成,也有部分是雍正十年后写成的,当然应还有玉沙道人子铭氏到达拉萨之后至乾隆元年三月“撰辑”《西域全书》时调查收集所得。
总之,分析《西域全书》抄本内容可知,《西藏志》成书前已有因人为修志而采录驻藏大臣衙门档案及调查资料,雍正年间驻藏大臣衙门也已经在西藏开展调查。《西藏志》“附录”第一、三两部分可肯定为雍正年间的资料;第二部分资料前虽有“乾隆二年造送理藩院入《一统志》”一语,但其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实际上也应是雍正末年的。
二、《西藏志·附录》的价值
截至目前,《西藏志》“附录”的价值在《西藏志》的研究中鲜有人谈及。但此志及其篇目的深入研究,均需要关注这一问题。笔者以为,“附录”的价值可从篇目设置和资料保存两个方面去审视与探讨。
首先,“附录”成为“门目体”清代西藏方志篇目之一,在篇目设置上反映了乾隆初年清代西藏方志的发展,对之后的清代西藏方志又产生了一定影响。“附录”目一般被认为出现于北宋时期,内容多为具有价值且应入志但又不便划为一门类或一时难定其归属的资料。设置“附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这样的资料。此目最初称作“杂志”,别称“杂记”“附录”“杂录”等。随着方志的发展,这些别称逐渐也成为方志门目名。前文提到的成书早于《西藏志》的李凤彩所撰《藏纪概》和雍正《四川通志》,从体例上看,这两部最早的私撰和官修清代西藏地方志虽也做分目记述,但总体上讲并不是“门目体”志书,所设篇目中尚无“附录”目。《西域全书》抄本第三册中虽然有“附录”标题及内容,但首册目录中并不见“附录”目。这就反映出《西域全书》“附录”与其他篇目有所不同,应当不是平行设置篇目时所设的一目。目前已知的两种《西藏志考》抄本所设篇目,均不见“附录”目。因此可以认为,在“门目体”清代西藏方志中,《西藏志》实际上最早设置了“附录”目。《西藏志》不仅正式设置了“附录”目而且将其置于篇目最后,说明编纂者了解历代方志中的“附录”目设置传统,在充分认识“附录”资料价值基础上,将清代西藏方志视为中国地方志的一部分,按中国方志传统进行编纂,也反映了西藏方志在乾隆初年的发展。随着《西藏志》抄本流传,所设“附录”目对之后的清代西藏方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成书时间为乾隆十六年左右的《西藏记》,亦设有位列全志最后的“附录”目,显然是受《西藏志》的影响。

三、《西藏志》与《西域全书》《西藏志考》的关系
前文提及的两篇《西域全书》研究论文已指出,《西藏志》是在南京图书馆所藏《西域全书》抄本基础上编成。笔者基本赞同这一看法。《西藏志》虽对《西域全书》原有篇目进行了调整,并对内容有所增删和修改,但比较后仍可看出二者的确存在密切关系。《西藏志》“附录”三部分资料,在《西域全书》乾隆七年抄本的“略笔杂叙”“考遗”及“附录”之中有所发现。而《西藏志考》却无与《西藏志》“附录”类似的篇目。这是否意味着,《西藏志》与《西藏志考》无直接关联呢?
讨论清初西藏方志著作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其成书时间。《西藏志》的成书时间近年来学术界有所考定。邓锐龄先生在《读〈西藏志〉札记》一文中指出,《西藏志》最后成书时间应在“乾隆七年之际”。这一看法确有文献记载依据。
目前国内已发现两种《西藏志考》抄本,一为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以下称民大抄本),一为国家图书馆所藏(以下称国图抄本)。这两种抄本篇目数与顺序以及内容均存在一些差异,但又存在明显的一致性。从国图抄本与民大抄本“居住房屋”目、“寺庙名色”目最后所举大房、著名呼图克图数与其名多一致,而与《西域全书》抄本则差异较大来看,民大抄本应是以《西域全书》为基础改编整理而成,国图抄本则当是以民大抄本为基础整理而成,内容又有所删改。
从两种《西藏志考》抄本所记内容来看,记事多为雍正年事,最晚止于乾隆元年春三月(“略笔杂叙”),提及颇罗鼐的各篇目中皆称其为“贝勒”;而《西藏志》中有数条乾隆年资料,最晚止于乾隆七年(“朝贡”),各有关篇目中均称颇罗鼐为“郡王”。这也证明《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在乾隆初年,的确早于《西藏志》。两种《西藏志考》抄本的成书时间,显然要比邓先生提出的《西藏志》最后成书时间早。《西藏志》编纂之时,《西藏志考》应在流传中,因此《西藏志》编纂者看到《西藏志考》是有可能的。
下文中,笔者通过比较《西藏志》与《西藏志考》《西域全书》几个篇目中的部分记述内容,来进一步探讨《西藏志》是否与《西藏志考》存在关系以及存在何种关系。
《西藏志》“粮台”目中,简要记打箭炉、理塘、巴塘、乍丫、昌都、西藏六处。但只记所设地点,不涉及粮员。《西藏志考》(民大抄本)列“台站粮务”目,其“粮务”指粮台,也是简要记打箭炉、理塘、巴塘、乍丫、昌都、西藏六处,亦只记其地点。《西域全书》抄本列“台站粮务”目,其“粮务”的记述是先记粮台设置地点及粮员为何人,再用小字注粮员的相关情况。如,“打箭炉,驻雅州府同知一员,张泰国”,其后小字注“原管炉雅同知事”“西藏,驻陕西靖远同知一员,杨世禄”,其后小字注“雍正十三年,特加道衔”。可以推断,《西藏志》“粮台”应主要参考、借鉴《西藏志考》“台站粮务”的记述方式。
《西藏志》“程站”目首列“自四川成都抵藏程途”。记述方式是,先记出发地,后记其里数,再记到达地,并在适当之处加小字注。如,“成都府四十里至双流县,五十里至新津河”。“五十里”后有小字注“过黄水河、新津河”。从小字注提及的新津河看,前“至新津河”应为“至新津县”。《西藏志考》(民大抄本)“程途全载”目首列“自四川成都进藏程途远近崎岖道路”。记述方式是,先记出发地,后记到达地,再记其里数,适当之处亦加小字注。如,“成都府至双流县四十里,双流县过黄水河、新津河至新津县五十里”。“双流县过”后小字注“过黄水河、新津河”。《西域全书》抄本“道途全载”目首列“壬子年进藏程途远近崎道路”。“七月,十六日自成都起程至双流县四十里,十七日过黄水河、新津河至新津县五十里”,仅从以上两天所记即可发现其为逐日记述方式——明确月份后,每天所记均先标明为何日。其后的记述中,每天行程后多有加小字注者,写天气、道路与有无人家、寺庙、瘴气及土司、粮草、住营等,有的小字注达三十余字。比较三者所记,《西藏志》与《西藏志考》(民大抄本)未明确月份,每天所记行程前也均未标明为何日;住营等候、会合前营等语均删去;每天行程后的小字注也与《西域全书》抄本有所差异,重要的是二者的增删文字等颇为相似。如,“泥头至林口三十里”后,《西域全书》抄本小字注为“路崎,是夜小雨”;《西藏志》与《西藏志考》小字注为“路崎”,均删去“是夜小雨”。又如,“莽里过漫山至南登六十里”后,《西域全书》抄本小字注中有“其山名宁静山,有分界碑”语;《西藏志》与《西藏志考》小字注均为“其山名宁静山,上有分界碑”,增一“上”字。再如,“阿兰多至甲贡八十里”后,《西域全书》抄本小字注最后为“路窄。李大人病住此”;《西藏志》与《西藏志考》小字注最后为“路险窄崎岖”,增三字后又均删去“李大人病住此”六字。综上,可以认为《西藏志》“程站”目首列“自四川成都抵藏程途”也主要参考、借鉴了《西藏志考》这段路程的记述方式,删去了一些文字,也略增加了小字注内容。
《西藏志》“程站”目第五为“自藏出防腾格那尔路程塘口”。记述方式也是先记出发地,接着记其里数,再记到达地。开始几句为:“西藏三十里至夹普,四十里至浪子,四十里至奔里,四十里至德庆”。此路程共十站,均如此记载。《西藏志考》(民大抄本)“自藏出防腾格那儿路程塘口”,开始几句为:“西藏至夹普三十里,夹普至浪子四十里,浪子至蟒里四十里,蟒里至德庆四十里”。此路程十站也都如此记载。《西域全书》抄本“自藏出防腾格那儿路程塘口”,开始几句为:“头站,西藏至夹普三十里;二站,夹普至浪子四十里;三站,浪子至蟒里四十里;四站,蟒里至德庆四十里”。此路程共十站,每站前都一一标明站次。比较三者所记,可以认为《西藏志》“自藏出防腾格那尔路程塘口”亦主要参考、借鉴了《西藏志考》此段路程的记述方式,删去了每站前标明的站次。
《西藏志》参考和借鉴《西藏志考》的情况还见于其他篇目。如,《西藏志》“婚嫁”中有“女家父母、亲友喜允,则饮其酒”语。《西藏志考》(民大抄本)“婚姻嫁娶”中亦有“女家父母、亲友喜允,则饮其酒”。《西域全书》抄本“婚姻嫁娶”中则为“女家父母、亲友喜者,则饮其酒”。再如,《西藏志》“疆圉”中有“西藏东至打箭炉八十四日”语。《西藏志考》(民大抄本)“四至疆圉”中亦有“西藏东至打箭炉八十四日”。《西域全书》抄本“四至疆圉”则为“西藏东至西炉八十四日”。“西炉”即“打箭炉”,但用字毕竟不同。
上述所列《西藏志》与《西藏志考》中颇为一致的内容,应不是巧合。足以说明《西藏志》编纂者虽主要在《西域全书》抄本基础上调整和增删,但部分内容也参考、借鉴了《西藏志考》的记述方式,并采用了某些资料。即《西藏志》与《西藏志考》也存在一定关系。
四、结 语
雍正年间,清中央政府派驻藏大臣入藏,代表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国家主权,加强对西藏的治理。驻藏大臣衙门的设立,也有力推动了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驻藏大臣衙门设立之后,按例保存相关的档案资料;其工作人员按管辖施政需要并在《一统志》编纂的要求下在拉萨及西藏各地开展了社会与自然、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系统调查,也形成积累了一批调查资料。这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西域全书》的编纂有了坚实的基础。几年之后,在《西域全书》抄本基础上,按乾隆初年造送理藩院入《一统志》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和增删,并参考借鉴《西藏志考》的某些记述方式,最终编成中国方志史上的著名方志——《西藏志》。需要指出的是,《西藏志》在“门目体”清代西藏地方志中最早设置了“附录”目。“附录”目虽只保存了三部分资料,但其设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西藏地方志的发展及高潮的到来,对之后的清代西藏方志以及清代西藏史地研究著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