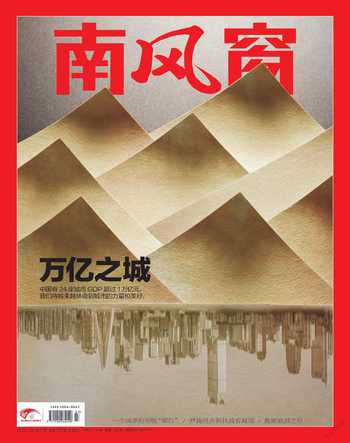北方有个青岛
2022-04-16杨闰然
杨闰然

中国万亿GDP城市有24个,南方18个, 北方6个。除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外,青岛是北方唯一入选的非省会城市,其GDP是靠着实实在在的产业支撑起来的。
青岛,这座海滨“岛城”,其崛起、落伍、突围之路,跌宕起伏,每一个阶段都反映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变迁,同时也能给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诸多启示。
超越大连
2021年青岛外贸进出口表现突出,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8498.4亿元,连续5年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2.4%,一年内跨越了两个千亿元台阶。
在此基础上,青岛2021年经济数据表现不错——全年生产总值为14136.46亿元,比上年增长8.3% ,两年平均增长6.0%,排在全国第十一位。
城市经济就是你追我赶。在GDP数据上,青岛领先了郑州、长沙、济南、合肥等省会城市。GDP体量1.4万亿级的三座城市分别为宁波、青岛、无锡,它们都加紧了对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的追赶步伐。
大连也是北方著名的滨海城市,计划单列市之一,地理位置与青岛相近,和青岛并称为北方的双子星。青岛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GDP滑落时,还曾提出“学大连,赶大连”。最终,青岛在2000年超过大连,GDP排名也提升到了第13名。
但如今,青岛与大连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大连2021年的GDP为7825.9亿元,并未站上8000亿,全国排名29名。在北方城市GDP排名中,大连只能屈居第十,但它已经是东北唯一在全国能排进30强的城市。从经济数据上来看,现在大连对标的北方城市也早已不是青岛,而是烟台、徐州等。
大连的经济何以至此?上世纪90年代,大连就大胆地提出建设“北方香港”,为了实现转型,这座城市曾依靠强力的政府干预手段,将市内重工业企业外迁。在大力改造大连的经济体系和城市面貌的同时,本土制造业壮大的空间却被毫不留情地挤占了。
“自上而下”地领导城市转型之路,与其他城市“自下而上”依靠市场的路径全然相反。由于经济的内生动力不强,大连很快就被那些搞外向加工型企业的城市甩开了距离。加上大连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经济腹地东北的大环境,东北经济不振,过于倚重石油、化工等传统工业的大连,出现了明显的后劲不足。
大连市中心摩天高楼林立之时,相比之下青岛市中心的城市建设就显得落后了许多。但相反,青岛抓住了国家在沿海地区重点发展的先机,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中心,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在扶持本土制造业上。
为了培育一批拳头产品,1989年,青岛在工业系统开展争创“青岛金花”活动,评选出了11个“金花产品”。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青岛抓住了国家消费品工业产品的市场机遇,以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啤、双星为代表的“五朵金花”叫响全国,成为了中国制造发展历程中独特的“青岛现象”。
可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价值与企业价值已经深度绑定,青岛品牌的构建和成长是政府与企业形成合力的结果。
“金花”的能量
与其它城市相比,青岛市的资源优势并不突出,如何扭转资源薄弱的劣势,一直都是青岛面前的一大问题。所以因开放而强,成了根植于青岛基因的一种意识。
谈及青岛企业的“进化论”,从市场化、资本化,再到国际化,不得不提到青岛啤酒。自1987年,青岛啤酒拥有了进出口权后,就开始不断拓展海外业务。1992年青岛啤酒在意大利成立欧洲办事处,勾勒出了中国啤酒行业的世界版图。
拥有近百年历史的青岛啤酒由此发展成为了中国品牌名片,在国际市场上大获成功。这让青岛的企业都意识到了品牌的能量,包括海尔。
青岛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GDP滑落时,还曾提出“学大连,赶大连”。最终,青岛在2000年超过大连,GDP排名也提升到了第13名。
海尔創始人张瑞敏曾回忆自己在初期做品牌的日子,“那个时候,中国企业都采取代工,我们大概是唯一一个做品牌的,他们是出口创汇,我们是出口创牌,我们那个时候赔了很多钱,整个集团的利润率降到1%,平时应该在百分之八九。所以这个是非常痛苦的过程”。
做品牌,然后走向国际,海尔的路子也是这样。虽然现在看来一切好像顺理成章,但在90年代,拥有国际化视野的人并不多。1999年,当张瑞敏决定投资3000万美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立海尔美国工业园生产家电时,很多人都指责他是盲目扩张。
尽管当时市场的声音很难听,但张瑞敏却提出“国门之内无名牌”“下棋找高手”,海尔必须走出去,“与狼共舞”。
2006年,海信创始人周厚健也正式提出“海信未来发展,大头在海外”的国际化战略,并于当年正式成立国际营销公司,把科龙的冰箱、空调海外业务并入其中。今年3月,海信换帅,周厚健将“大权”转交林澜,对此周厚健的解释之一也是海信正在快速成长为“世界级企业”,需要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带头人。
“五朵金花”支撑了青岛在全国工业的垂直崛起,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青岛为人熟知的还是这些企业。也就是说,青岛的产业更新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新消费、汽车、全球电子、信息等相关产业中所诞生的青岛知名品牌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在艰难地向新一代新兴产业迈进。
青岛还需要更多的新一代企业。时隔多年,青岛在2019年启动了新一代“青岛金花”培育行动,次年就发布了培育企业名单,2021年青岛又发布了一批“青岛金花”的培育名单,制造业占比最高。连续性的动作和力度,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青岛发展的焦虑。
青岛选择的路径是以产业集群来引领品牌。入选了新一代“青岛金花”的赛轮集团,其董事长袁仲雪曾谈到,青岛的轮胎品牌之所以能逐渐走向世界,获得越来越多用户认可,最根本原因是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2000年以前,国内的子午线轮胎产能才3600万条左右。到了2013年,轮胎企业遍地开花。2019年我国子午线轮胎的产能达到了6亿多条。”只有做大做强,形成产业集群,才会有更多的资源、市场、信息和技术。
在其他入围的企业中,也出现了多家有海尔以及海信背景的企业。比如如聚好看是海信集团旗下的家庭互联网AI公司,雷神科技、卡奥斯以及日日顺,则是来自“海尔系”。对于薄弱产业,更是需要产业集群的建设以及优势产业的“先强带后强”来拉动。

拜师上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谈及青岛发展的报告中,指出了青岛所面临的发展困境:“重抢牌子、轻用牌子”以及开放平台首创措施少、开放平台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制约了开放平台作用的有效发挥。
此外,发展空间和重点上不聚焦和多变的问题,也使得空间发展上四处开花,没有形成集中集约集聚的发展效果。
2012——2018年,青岛工业投资增速几乎逐年下降,分别为35.7%、29.8%、16%、16.5%、10.1%、9.3%、9.1%。在这个过程中,青岛没有认清后工业化的发展逻辑,而出现了去工业化的倾向,也使得青岛错过了一些风口和机遇。
尽管青岛比大连等北方城市发展得好,但其综合竞争力在全国城市的对比下,仍然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前面的苏州、杭州、成都,领先优势在不断扩大;同行的南京、宁波,在反超后的优势也逐渐形成,无锡、长沙、郑州等城市仍在紧追不舍。
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报告来看,青岛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在2004年排第12名,在 2010年排第10名,而2013年则开始跌出前十,2015年全国排第16名,2021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仅排第20名。
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内唯一迈进“双万”门槛的城市,青岛崛起的价值就是发挥龙头作用,协同带动山东半岛的整体发展。
北方工业重镇逐渐褪色,南方创新城市强势崛起,“南北差异”逐渐赶超“东强西弱”,成为当今最令人关注的区域问题。在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条件下,青岛的发展也面临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但青岛这座城市很重要,尤其在城市群时代。“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明确提出19大城市群建设,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
在这19大城市群中,几个发展较好的城市群都在南方, 如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如何实现南北均衡发展?这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作为北方第二大城市群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将在提升北方经济的活力中发挥极大作用。
而青岛正是该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它。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内唯一迈进“双万”门槛的城市,青岛崛起的价值就是发挥龙头作用,协同带动山东半岛的整体发展。
目前,整个山东正着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形态已经在发生深刻变革,青岛也在科创方面发力,想要打造自立自强的产业链和高附加值的创新产业。2021年,青岛的多指标在全国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比如截至2021年12月20日,青岛市场主体数在190多万户,位居全国第八名,人均拥有的市场主体数在大中城市仅仅小于深圳和苏州的对应数据。
为了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加快“补课”速度,青岛还“拜师上海”,城市主政者主动带队去上海考察,搭建起资源流动的平台。海尔也抢滩上海,落地了海尔智谷工业互联網项目。即便上海的要素成本有些高,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能在最先进的城市里寻找到最优秀的生态伙伴和人才。
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青沪企业家联谊会会长郑永刚曾感慨说:“我之前对青岛了解甚少,也没有在北方投资的打算。最近两年,我身边的企业家朋友常常念叨青岛的变化,纷纷来到青岛,有的投资,有的在投资的路上,这深深触动了我。”
青岛还是那个青岛,从上世纪的“学大连”到如今的“学上海”,青岛再度开始进击。于这座城市而言,在新的时代机遇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