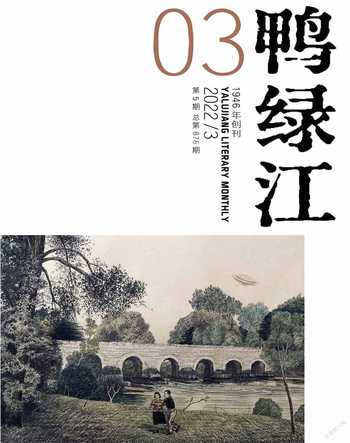空无一字的信函( 组诗)
2022-04-13宋晓杰
宋晓杰
妈妈
妈妈,总有一些汉字让我过敏
我羡慕别人喊“姥姥”
因为你六岁就没有了妈妈
我还羡慕别人喊“大姨”
因为你会绣花鞋的姐姐马上嫁人了
却死在去往18 岁的路上
妈妈,我们越来越像
不仅是指贼眼皮儿、拇指的形状,洁癖
饭菜的咸淡,半袖衫喜欢圆领还是鸡心领
而且,我们喝一样的保健茶、蜂蜜
我们一起洗澡、做足疗
皮肤起疹子的时候,用同样的药膏
更要命的是,我每每从沈阳下班回来
总能准确地接到你问候的电话——
不是我刚在小区停好车
就是刚打开家门,还没来得及脱鞋
有一次,我乘坐的虎跃快客刚刚进城停靠
你的电话就来了:“我猜你快到了。
原以为你开车上班,后来想起你坐车,哈哈。”
像个狡黠、调皮的孩子
那天,你拿出自己的一件绿花半袖绸衫
说现在我穿正好——
你把它雪藏了二十多年
才让我俩的中年,完美相逢
可是妈妈,你不知道
经过半个世纪,我们活成了同辈:
你是80 岁的老人,我是53 岁的老人
——终于,我们彼此成全
成为今生最亲爱的姐妹
这是我平常的一天
这是我平常的一天
很有可能是别人难忘的一天
一些鲜花,开始失水
一些火焰,刚刚熄灭
大苇莺的叫声,传自萧太后河
园林工人穿着雨靴,在河边除草
我在读一本关于猫的书
说不上喜欢,但写得有趣,来自异域
编辑与我,沟通新书的某些细节时
书中的陷阱,让我巧妙地躲过
窗前停车场上,多数车位空着
院门外的消防车,却整齐地停着
楼口的两棵稠李树间,挂着花床单
奶白的一只小狗与一个小男孩,在练习飞盘
听声音就知道,遛鸟的大爷在夸赞他的鸟
另一个摇着蒲扇的方脸男人
习惯使用书面语,却是地道的京腔
一个姥姥一边劝阻奔跑的孩子,一边惊呼:
“这树是核桃啊!一直以为是苹果。”
年轻女人说:“生出来,才知道是男是女。”
她笑着,瞥一眼婴儿车里熟睡的“小糖果”
这是无风无浪的一天。萱草、凌霄、玫瑰
陆续衰败;不过,菊和旋覆花正在盛开
阳台上的多肉植物,生出细软的新芽
没有喜讯,也没有悲伤传来
快递小哥车轮飞旋:每个电话号码
都在亲人般等待,生活中已知和未知的
终将要被逐一签收
给未出生的孩子的第一首诗
不知道你是我的孙子,还是孙女
但我知道:借由你,我的孩儿
我将成功晋级为宋奶奶
人类生命科学中较高级的职称
与诗人的冠冕,等同
我小声说话,蹑足前行
欢天喜地,贪生怕死
对陌生的孩子微笑,揉揉他们的头
素不相识的孕妇,我也多看几眼
我停下来,让他们先走
——为未来让路,我退到幕后
如果需要,我再一个箭步冲到前头
我原谅自己:每天无所事事,专注地等待
那些“不可饶恕”的错误,一笔勾销
一笔勾销吧,牛年也不钻“牛角尖儿”
静候秋风飒飒,金黄的田野
晃得我眼花,天空蓝得像一场美梦
我肯定会大笑,也可能痛哭
缺氧,难免头重脚轻
这个秋天,只等这枚沉甸甸的果实压舱
早已准备好托举的双手——我是上等水手
古铜的臂膀,岸——哦,我就是岸
即使在湍急的洪流中
也要準备好:慈祥
台风过境
飞机开始下降高度
她从两千公里之外归来
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有了烟火
他们开始扮演自己
说简短的话,在手机上
发字符、表情图,打趣儿、调侃
掩饰内心的戏剧冲突
有时说长长的话,没完没了
有时,则是大片的空白
各自发呆,心照不宣
气象预警说:台风正在过境
一头发疯的巨兽,身披青铜的铠甲
扫荡。吃土,吃树,也吃人……
在屋子里,她不安地走动
疾风骤雨的窗外,忽然电闪雷鸣
她赤足奔向呼啸的阳台,转而颓圮
像倒塌的墙,摊倒在角落——
通透的落地窗,影音效果的宽银幕
一顾,倾城……再顾,烟雾蒸腾
指间灼烫。波斯地毯上
缠绕的藤蔓间
多了一个,黑洞……
这个时节,很容易想起民谣
再也看不到炊烟了
如果有,那一定是人类干预了自然
烧荒的人,终于卸下了疲累
空风景,真的空了
一个个干草垛的出现,实属意外
在下午三四点钟的余晖中
空旷的田野里,它们像巨大的蛋卷
——大排筵宴的,是谁?
雁北乡,鹊始巢……暗流涌动……
高速公路两旁的白杨,集体倾倒——
这个时节,很容易想起民谣
怀抱吉他的逆光歌手
懒懒地弹拨,如鬃的长发
有干草的气味儿
肩膀上,茸毛一样的光
河水般流淌……
腊月二十五的北陵公园
已经有几个月没来了
夏夜里跳舞、嬉戏、发呆的人
各自回家找乐
傍晚的北陵公园里
皇太極披挂整齐,站在原地
一间售货亭,兀自亮着灯
迎面遇到的两位老人
有一刻,停下来,认真地谈论
年货、孩子们的压岁钱……
从东门进去,转了一圈
又从东门出来:分开的寂静
重又合拢,还给松柏和鸦
晚霞似追风的纱裙,薄厚不均
——那速度,太快了!
如冰面上的三个男孩
岁月庄重、安稳
而年轻人还是喜欢冒险
浑圆的落日,日夜飞驰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落日
是在新疆的旷野中,快二十年了吧
我们乘坐四处漏风的老巴士
沿着准噶尔盆地的边沿儿
颠簸了十七个小时
一天当中的另外七个小时
几乎用来回忆——
那落日橘黄,圆满,迫近
无枝可依,却一动不动
谁大咳一声,说不定就会震落
一车叽叽喳喳的人啊
站在无边的天幕下
瞬间,集体失声
某个傍晚,我驾车转下高速公路
忽然泪涌……在丛丛晃动的白桦后面
跳跃的,不正是它嘛!
——那满满的一车人呢
怎么,只剩下我?
落日如硕大的磨石、利器
耗损,收割,林木和人,四散……
不由自主地眩晕——
它急于挟持那些早逝的人
日夜飞驰:吃燃烧的火
喂养它的荒、它的凉
空无一字的信函
会不会有一封信
把我寄回过去——
三十多年前的海岛
呼啸的三轮车,不认识的大叶蔬菜
和水珠,新鲜而慌乱的清晨
电报,单行道,大东海,秀英码头
那个死去多年的诗人,孩子的笑
摔碎的几朵浪花儿……
我借助铁器冰凉的翅膀
回到空无一字的温热信函之中
——其实,它们一直居住在体内
邮票,细密的针眼儿、圆孔和耐心
绿色的邮筒和它沉重的门
“吱扭”一声打开,倾泻而下的
故事,也有可能是事故……
在春天和幽静之夜,一次次抽芽
——抽:抽打的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