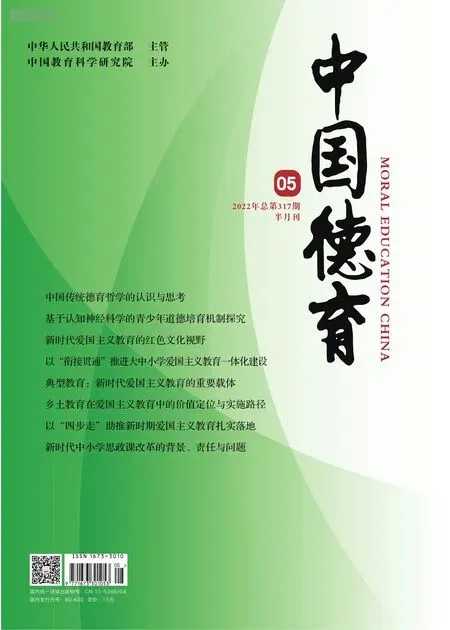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青少年道德培育机制探究
2022-04-13钟振华徐洁
钟振华 徐洁
摘 要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将道德教育的视野扩展至大脑层面,其研究成果揭示了道德形成的神经学基础,探明了道德认知的神经加工机制,阐明了道德判断的认知—情感双加工理论模型,探究了进行道德决策时的脑域激活状态。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将认知神经科学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诉求日益增长。认知神经科学视野下的道德教育,即教师依据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以道德活动的神经激活、神经环路生长为基础,设计一系列针对性干预方式,以帮助学生培养正确的道德认知、完善的道德情感以及矫正学生不良道德行为。
关键词 认知神经科学;神经机制;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 钟振华,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徐洁,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副教授
认知神经科学兴起后,道德成为其研究重心之一。随着神经科学对道德相关神经网络的定位以及道德脑域功能的厘清,关于认知神经科学应用于道德教育的诉求逐渐明晰。认知神经科学关于道德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如道德认知、道德情感等。这些方面的研究为认知神经科学与道德教育的结合提供了神经学基础,并为认知神经科学应用于道德教育提供了可能。
一、道德形成的神经学基础
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对道德认知、道德判断以及道德决策进行了深入探究。在道德认知方面,具身德育概念的产生明确了身体和环境对道德的影响,为促进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统一提供了新思路;在道德判断方面,认知—情感双加工理论模型的出现打破了道德产生于理性的传统概念;在道德决策方面,意志参与决策的3W(What,When,Whether)模型揭示了道德决策过程中脑域的协同过程。
(一)道德认知:具身隐喻的神经加工机制
道德认知能力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德育研究的重心。有关道德认知是如何运作的议题,向来都是争论的焦点。认知神经科学认为,认知的产生以身体为基础,意识的运作有赖于神经网络。道德认知作为意识的一部分,同样受到大脑神经网络的制约与影响。近年来,在具身认知思潮的影响下,有学者提出了具身道德理论,即身体及其活动方式与道德心理和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强调身体经验以及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对道德的抽象概念认知的影响。[1]其中,具身隐喻概念被应用于道德认知,所谓具身隐喻(Embodied Metaphors)是指个体自动将身体经验相关的具身概念(视觉、触觉、温度觉等)与抽象概念(明暗、软硬、冷暖等)形成连接的过程。[2]具身隐喻在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清洁隐喻和空间隐喻。在清洁隐喻的实验中,Denke、Schaefer等人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揭示了人在进行不道德行为时的脑域活动。当人在进行不道德的行为时,大脑双侧感觉运动区域被显著激活,且显示出躯体特异性和双重分离效应。[3]在空间隐喻的实验中,Meier等人通过IAT范式的研究证明了道德概念与垂直空间线索具有内隐联结关系,其道德的垂直隐喻表征规则是“道德在上”“不道德在下”。[4]这些实验均指出了道德认知的产生与运动皮层具有相关性,个体道德概念的建立与身体经验有关的具身概念存在关联性。具身隐喻概念的提出为当前的道德教育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道德认知的产生提供了神经学的理论基础。
(二)道德判断:情绪和认知加工的协同作用
学术界关于道德的产生是否依循于人的情绪存在诸多争论。在传统认知中,道德产生的理性基础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人们的共识。但是,如若道德判断只存在理性而不包含情感,其判断会充满功利性,如此便失去了道德本身的含义;反过来说,若道德判断仅仅依靠情感来进行,面对道德两难问题时便会陷入无法取舍的窘境,可见道德判断也需要理性的存在。现代认知神经科學的研究成果表明,理性在道德中并不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单纯的理性无法构成道德认知,道德需要情绪的参与。Haidt通过调查人们对不道德事件的快速判断,提出了道德的社会直觉模型(The Social intuition Model),即道德判断是在短时间内由情绪作为驱动力完成的。在其后,Haidt等人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在外源性厌恶刺激的条件下进行道德判断,被试皆认为自己并未受到外源性厌恶情绪的影响,但道德判断结果相较正常情况下更为苛责。[5]这一实验也进一步证实了情绪是影响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判断完全是由情绪驱动的。事实上,道德驱动是在认知与情绪的协同之下完成的。Greene等人提出了认知—情感双加工理论模型,并通过将被试卷入两类道德两难问题(易调动情绪与不易调动情绪)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当被试在卷入不易调动情绪的道德两难问题时,脑域中的背侧前额叶和顶叶会被激活,这一区域主要与认知加工有关;当被试卷入容易激起情绪的道德两难问题时,脑域中的内侧前额叶和扣带后回会被激活,这一区域主要与情绪加工有关。[6]这一实验证明了人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情绪与认知系统会同时运作,共同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因此道德判断的理性与否是由个体的情感参与程度所决定的。
(三)道德决策:经由颅脑刺激人的大脑区域
在道德运行机制当中,个体依据道德认知对事件完成道德判断以后将进入道德决策阶段,道德决策与前两者的差异之处在于,道德决策实质上是一种意愿行动能力,意愿行动在意志努力中实质上是一种“决策”过程。[7]道德决策是道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责在于决定是否将道德判断付诸实践,在道德决策过程中意志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个体在作出道德决策时会受到利益、压力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意志能够帮助个体克服阻碍因素完成道德行为。当前有关意志参与道德决策的神经标准模型主要为3W(What,When,Whether)模型,且这一模型得到了神经科学的支持,该模型将意愿行动的发生分为三个部分,即“做什么”“何时做”“是否做”。[8]在“做什么”的神经表征中,被试自主作出决定时喙部扣带回区域激活程度较高,眶额叶皮层激活较低,若决定是在被引导情况下作出,则激活区域相反。[9]在“何时做”的神经表征当中,被试的前补充运动区、顶内沟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区域被激活。[10]在“是否做”的神经表征中,发现被试决定抑制自身行为时,其背内侧额叶皮层和前脑岛会被激活。由以上的实验结果可知,道德决策的进行并非是由单一的脑域来执行的,而是在多脑域的合作之下共同完成的。[11]
二、青少年道德教育与认知神经科学的
深度融合
认知神经科学通过对被试进行功能性核磁共振测试,进一步揭示了个体进行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等活动时的脑域激活状态,厘清了不同脑区对个体道德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将道德教育的视野扩展至大脑,为道德教育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性。
(一)基于提升青少年道德认知的生理学诉求
近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道德认知的神经运作机制逐渐明晰。依据Greene和Haidt对个体进行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测试结果能够得知,道德认知与个体的前额叶、颞叶、脑岛、眶额叶、楔前叶以及前扣带皮层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前额叶与个体的认知、情绪存在相关性,该区域的损伤会导致患者道德行为的变化;而前颞叶的颞上沟区域与个体的社会感知相关,该区域的损伤会导致个体的归因困难;边缘和副边缘结构则与个体的基本动机机制(社会依恋、攻击性、性欲等)相关联,其损伤可能会导致极端的道德违反(无端的身体攻击、恋童癖等);前额叶亚区、边缘区和颞叶皮层在文化塑造的道德价值观和规范方面有独特作用。[12]道德认知是由大脑多区域共同协作形成的一种意识,其中任意区域结构发生改变,都会造成个体道德认知的转变。此前道德教育的窘境在于其忽视了促进具身概念与抽象概念的联结,造成了学生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割裂。人的认知能力与身体经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身体与外界交互所带来的经验是帮助个体建立心理认知的基石。个体在原有的认知结构上建立新的认知体系,而最初的认知结构正是通过身体经验建立的,若在道德教育中忽视具身概念的培养,那么德育成效必然不佳。认知神经科学的引入能够引起大众对具身概念的关注,并对如何促进具身概念与抽象概念相联结的问题给出些许启示。
(二)基于陶冶青少年道德情感的情绪性机能
有关道德观念是否完全依循于理性的论争从未休止,直至Greene提出道德观念并非完全依循于理性。Greene从认知神经科学维度提出了实质性证据,即认知—情感双加工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的道德判断是由情感和认知共同驱动的,Greene在对个体进行功能性核磁共振的实验中发现,被试在回答道德两难问题时,有关情绪的诸多区域被激活。随后其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个体在进行道德判断时,被激活的区域包括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左内侧眶额叶皮层、后侧颞上回、前扣带回、前脑岛、镜像神经系统、扣带后回以及杏仁体。[13]其中,腹内侧前额叶与社会情绪背景知识相关,当该区域损伤时会表现出情绪钝化、共情能力丧失、情绪不稳定等症状;[14]前扣带回、前脑岛与镜像神经系统与共情有关;扣带后回负责加工与自我有关的情绪性心理意向,可能与道德判断中的情绪性心理意向的产生有关;杏仁核负责社会性情绪的加工,對道德情境诱发的消极情绪尤为敏感,并与奖惩信息的快速编码有关;[15]颞上回与个体的“人格”相关联;[16]眶额叶则涉及奖惩价值以及控制不好的行为。[17]道德情感是影响个体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个体道德行为实践的内驱力。当前学校德育更多地侧重于伦理知识的传授,希望借此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学生,然而这本就是一种悖论。道德情感的培养并非依靠伦理知识的灌输,而是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情感需要来设置情境,以此唤起学生的道德情感体验。认知神经科学的引入揭示了情感是道德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人们对道德情感的重视,并通过揭示在道德活动中不同大脑区域的作用,为道德教育提出指导意见。
(三)基于优化青少年道德行为的内隐性机理
道德行为向来是道德研究重心,而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为道德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大量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道德行为与大脑的腹内侧前额叶、脑岛、眶额叶、后颞上沟、颞顶叶交界区、前扣带皮层、杏仁体以及额下回等区域存在相关性。其中颞顶叶交界区、杏仁体、腹内侧前额叶和脑岛与个体的情感相关,杏仁体负责社会情绪处理,而颞顶叶交界区与腹内侧前额叶负责理解他人心理状态情感成分,脑岛则与个体共情能力具有相关性。[18]眶额叶与额下回具有行为控制作用,二者均能抑制个体的不道德行为。但二者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区别在于眶额叶是通过奖惩机制为个体行为带来持续变化,额下回则在反应抑制和行为控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19]杏仁体与后颞上沟则与个体的社会信号和理解行为相关。[20]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道德行为的神经学基础,这为道德教育中解决青少年道德行为与道德认知相分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道德教育能够根据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设计相应的教学方式,将其组合后,形成一种多维度干预青少年道德行为的方法。譬如,根据眶额叶与额下回对个体的行为控制功能以及腹内侧前额叶、杏仁体、前扣带皮层等区域对共情能力的影响,开发相应的德育方法,在增强学生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从增强控制力以及培养共情能力两个维度影响学生的道德行为。
三、基于认知神经科学提升青少年道德教育实效的对策
认知神经科学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够为道德课程的设置、道德情感的培育以及不良道德行为的干预提供新思路,并推动学校道德教育的科学化进程。
(一)落实具身思维,塑造青少年良好道德认识
具身德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构建具身思维,这是一种促进具身概念与抽象概念相联结的思维方式。在道德教育中,具身思维的落实能够有效帮助学生培植正确的道德认识。认知神经科学对具身隐喻的研究发现,个体在进行不道德活动时,其双侧运动皮层被显著激活,且呈现出躯体特异性和双重分离效应,即具身隐喻与双侧运动区域存在关联性,且不同的不道德行为会激活不同的大脑区域。当前与道德有关的具身隐喻主要包括清洁隐喻、空间隐喻、颜色隐喻以及触觉隐喻。基于具身道德的认知神经科学成果,道德教育能通过两方面举措促进学生道德认知的塑造。其一,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身体的参与,在道德教育方式上做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结合,将实践活动融入道德的培养过程,实现具身概念与抽象概念的联结。例如:将情境式教学引入道德教育,在德育过程中设置贴合实际生活的情境,通过实例中的感受增强学生对道德行为的认知,进而构筑完善的道德认知。其二,依据具身隐喻的躯体特异性和双重分离性,在德育中采用多种具身隐喻的方式,培植学生的正确道德认知。譬如,采用颜色隐喻,以黑白来象征行为的道德与否;采用空间隐喻,以位置高低来表征道德知识;采用温度隐喻,以冷暖给予学生行为反馈。
(二)推行情境体验式道德教育,培植青少年正确道德情感
情境体验式道德教育是指在道德情境中以渲染、引导等方式培养学生道德情感的教学方法。认知神经科学认为道德情感与道德判断之间具有内部关联性,个体的道德情感是道德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推论得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证明,个体的道德判断由情感与认知共同驱动。个体在解决道德两难问题时,大脑中与情感有关的腹内侧前额叶、左内眶额叶皮层、后侧颞上回、扣带后回以及杏仁体被激活。其中眶额叶和杏仁体都具有对奖惩编码的功能,眶额叶能够抑制不良道德行为,杏仁体则对道德情境中的负面情绪极为敏感;镜像神经系统、前扣带回、前脑岛和腹内侧前额叶与共情有关;扣带后回则与情绪性心理意向有关。基于情感相关的脑域功能,遂提出情境体验式道德教育。情境体验式道德教育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根据腹内侧前额叶、前岛叶、前扣带回以及镜像神经系统的共情功能,在德育中设置贴合实际生活的情境,通过实例中的感受增强学生情感感受,进而塑造完善的道德情感。其二,眶额叶与杏仁体对情绪敏感,且包含奖惩机制的功能。因此需要在情境中设置问题,并根据学生的反应予以奖励或惩罚,且在训练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在学生进行不道德行为后予以负面情绪的体验,该举措的核心在于以奖惩机制为学生建立对行为的基本认知。
(三)实施多维度行为干预,矫正青少年不良道德行为
青少年道德行为矫正是道德教育的重心,且道德行为难以通过外力直接进行干预,因此矫正青少年道德行为需要从动机机制形成、共情能力培养等维度同步进行。现代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证明个体的道德行为与腹内侧额叶、脑岛、眶额叶、后颞上沟、颞顶叶交界区、前扣带皮层、杏仁体以及额下回等区域存在相关性。这些区域与影响共情的脑域分布存在重合之处,即个体的共情能力能够影响道德行为的产生。此外,个体的道德行为与影响个体动机机制的脑域也存在共同区域(腹内侧前额叶、脑岛、前扣带皮层等),即个体的动机机制是制约道德行为的另一大因素。依据上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对青少年道德行为的矫正可以从动机机制构建以及共情能力培养着手。在道德动机机制构建方面,教师可以通过培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塑造正确的归因方式以及建立信息反馈机制的方式培养学生的道德动机机制。在学生共情能力培养方面,共情能力与个体的镜像神经系统存在关联性,而镜像神经系统参与了行为的模仿,还可能参与了对他人意图的理解。[21]因此,在德育中应利用镜像神经元的效能培养学生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譬如,以情景剧、心理剧等方式将学生代入具体场景,培养学生对他人情感的敏感性。
參考文献:
[1]方溦,葛列众,甘甜.道德具身认知的理论研究[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6,14(6):765-772.
[2]王继瑛,叶浩生,苏得权.身体动作与语义加工:具身隐喻的视角[J].心理学探新,2018,38(1):15-19.
[3]Schaefer M,Rotte M,Heinze H J,et al.Dirty deeds and dirty bodies:Embodiment of the Macbeth effect is mapped topographically onto the somatosensory cortex[J].Scientific Reports,2015(5):18051.
[4]Meier B P,Sellbom M,Wygant D B.Failing to take the moral high ground:Psychopathy and the vertical representation of morality[J].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7,43(4):757-767.
[5]Schnall S,Haidt J,Clore G L,et al.Disgust as Embodied Moral Judgment[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8,34(8):1096-1109.
[6]Greene J D.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J].Science,2001,293(5537):2105-2108.
[7]曾文婕.德育课程创新何以可能:来自脑科学的启示[J].南京社会科学,2021(2):141-149.
[8]Brass M,Haggard P.The What,When,Whether Model of Intentional Action[J].The Neuroscientist,2008,14(4):319-325.
[9]Walton M E,Devlin J T,Rushworth M.Interactions between decision making and performance monitoring within prefrontal cortex[J].Nature Neuroscience,2004,7(11):1259-1265.
[10]Lau H C,Rogers R D,Ramnani N,et al.Willed action and atten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action[J].Neuroimage,2004,21(4):1407-1415.
[11]Greene J D,Nystrom L E,Engell A D,et al.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J].Neuron,2004,44(2):389-400.
[12]Moll J,Zahn R,Oliveira-Souza R D,et al.The neural basis of human moral cognition[J].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2005(6):799-809.
[13]Valdesolo P,Desteno D.Manipulations of Emotional Context Shape Moral Judgment[J].Psychological Science,2010,17(6):476-477.
[14]Ciaramelli E,Muccioli M,E Làdavas,et al.Selective deficit in personal moral judgment following damage to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J].Soc Cogn Affect Neurosci,2007,2(2):84-92.
[15]谢熹瑶,罗跃嘉.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因素——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进行探讨[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6):1250-1256.
[16]Brothers L,Ring B.A neuroetho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nds[J].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1992,4(2):107-118.
[17]Fricchione G L.Descartes' Error: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J].Psychosomatics,1995,36(2):151-153.
[18]Costafreda S G,Brammer M J,David A S,et al.Predictors of amygdala activation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stimuli: a meta-analysis of 385 PET and fMRI studies[J].Brain Research Reviews,2008,58(1):57-70.
[19]Osborne-Crowley K,Mcdonald S,Francis H.Development of an observational measure of social disinhibit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J].Journal of Clinical & Experimental Neuropsychology,2016,38(3):341-353.
[20]Yang Y J,Rosenblau G,Keifer C,et al.An integrative neural model of social perception,action observation,and theory of mind[J].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2015(51):263-275.
[21]魏高峽,满晓霞,盖力锟,等.人类共情领域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展望与应用启示[J].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21,51(6):702-716.
责任编辑︱何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