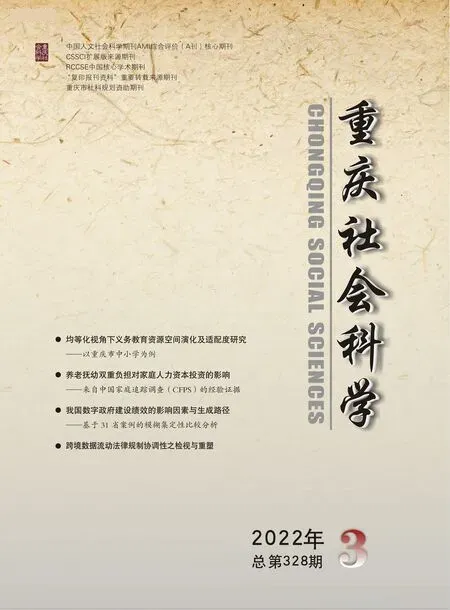试论康德《法权论》之阐释路向
2022-04-12贺梓恒
贺梓恒
摘 要:学界对康德法哲学的研究主要以《法权论》为核心文本,但对《法权论》阐释路向的判定存在较大争议。康德的法权是一种先验的法权,法权之所以为法权的先天条件是人的实践的自由,对《法权论》的阐释理应以实践的自由为前提。康德将实践的自由,也就是人的欲求能力,划分为意志与任意,意志自在的为目的,承担着立法的机能;任意仅与行动相关,承担着执行的机能。当后者完全以前者为规定根据时,人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是能够自我立法的意志的自由。契约论阐释路向以任意作为道德之本质,将公民状态的形成建立在基于理性选择的社会契约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视角。先验阐释路向抓住了康德法哲学的先验本质,将法权的演绎建立在人的先天自由,即意志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意志论与理性主义的超越,并且打通了国家法权、国际法权以及世界公民法权的论证逻辑,回答了“永久和平”何以必然的问题。
关键词:康德;法权论;实践自由;先验;永久和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法治与德治的治理机制研究”(20AFX002)。
[中图分类号] B516.3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3-0097-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3.007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界重新燃起了对康德法哲学的兴趣。学界对于康德法哲学的理论推进以及批判,大多以1797年出版的《法权论》①作为核心文本,但就目前来看,学者们对《法权论》的阐释路向的判定存在较大争论,难以形成共识,这直接影响了后续理论的解读方向。
法权(Recht)是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它不单指主体拥有的具体的权利(right),而是意味着一种外在合法则性的整体公民状态②。《法权论》不单是对法律的讨论,而且是一种政治学说,对它的阐释包含着对康德关于政治合法性之形式与范围的理解[1]52。就政治合法性之形式而言,学界的阐释路向大体包括以墨菲、凯尔斯汀为代表的契约论阐释①与以路德维希、马尔霍兰为代表的自然法阐释②,两者的分歧在于,康德的法权思想更接近于社會契约论传统还是诸如格劳秀斯的自然法传统。契约论阐释路向采取的是经验主义视角,显然与康德哲学的“先验性”相悖,并且在康德文本的处理上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自然法阐释路向虽然选择了意志作为法权之根据,但其论证是从细节入手,鲜有提及康德关于人的先天实践能力的批判性预设,缺乏整体性关注。对康德而言,实践领域的批判对象是人的欲求能力③,目的是为人的先天实践能力重新划定界限,并试图在意志(Wille)与任意(Willkür)的实践的自由的划分基础上展开道德学说的演绎。法权与德行同属道德问题,都建立在实践的自由的基础上,因此,康德《法权论》的阐释无法绕过这一前提,应当采取一种先验路向。
本文尝试阐明康德《法权论》之阐释路向,拟从实践的自由着手,厘清它在康德法哲学语境下的功能定位与准确含义,随后说明契约论阐释与自然法阐释的局限性,以及何为先验阐释路向,它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对意志论与理性主义的超越。由于主题所限,本文主要探讨《法权论》关于政治合法性之形式的阐释,政治合法性之范围(即“永久和平”)仅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有所提及。
一、实践的自由:法权何以可能的先天条件
康德的《法权论》是对外在合法性行为之形而上学的要素阐明,对它的阐释首先找到它的逻辑起点,也就是法权之所以为法权的先天条件。实际上,法权可以被视为一种先验的实践知识,并且实践的自由,更确切地说,自由的意志充当了其演绎的最终根据。
(一)法权本质上是一种先验的实践知识
康德哲学是批判哲学,批判的本质就在于获悉关于人的诸先天能力的来源、范围以及种类的先验知识。“先验”(transzendental)在一般意义上与“先天”(a priori)相同,指先于经验的(逻辑上而非时间上在先)。但康德明确指出,“先验”与“先天”这两个术语是有区别的:“不是说任意一种先天知识都须称为先验的,只有那种使我们认识到某些表象(直观或概念)只是先天地被运用或只是先天地才可能的、并且认识到何以是这样的先天知识,才称之为先验的(这就是知识的先天可能性或知识的先天运用)。”(A56=B80-81)①先验知识也是先天知识,但先天知识并不都是先验知识。先天知识指那些没有掺杂任何经验性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先验知识是对先天知识本身加以研究的知识,探究这些知识成为知识的条件,即必须运用于经验之上,以及如何运用于经验之上②。
先验知识在理论领域的考察对象是人的先天认识能力,在实践领域则是人的先天实践能力,前者回答“这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回答“这应当是什么”的问题③。经过康德批判的人的实践能力作为实践行为的先天根据,是他的整个实践哲学的根基,那么,依据其所确立的实践法则,也就是最高的道德法则,自然而然应当适用于法权与德行领域,这也是《道德形而上学》由《法权论》与《德行论》两部分构成的原因之一。但有学者质疑,法权并不建立在道德法则的基础之上,《法权论》可独立于《道德形而上学》[2]。这一观点(分离命题)有两个最主要的论据:其一,法权的最高原则是“分析的”(analytisch),而德行的最高原则是综合的(synthetisch)(6:396)。“分析的”指法权原则可以从法权概念(外在自由概念)中直接推导出来,无须借助其他东西,因此,法权独立于康德的道德理论。其二,康德在“法权论导论”中指出,法权的普遍原则是一个“根本无法得到进一步证明的公设”(6:231)。这意味着,法权的普遍原则自身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它无需道德法则即可证明自己。那么,是否康德的法权就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呢?下文的观点将表明,康德的法权的确一定程度上独立于道德理论,但它的有限的独立性并不能消除其终究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事实。
第一,根据《道德形而上学》的结构安排,康德在导论中提出了一些法权与德行共有的“预备概念”,例如,自由、义务、法则等,这些概念内在于(广义的)道德之中。根据法权与德行领域的性质差异,自由被划分为外在的自由与内在的自由,两者都属于道德形而上学的整全性的自由。此外,康德由自由概念引出了义务、法则,自由主要表现为一种普遍性的义务,普遍性指的是法则的普遍性。自由或道德的普遍性法则,即意志的普遍立法法则,被视作法权义务与德行义务共同遵循的道德领域的最高法则。
第二,法权成立的最高标准是道德的,而非自然的。根据康德的阐述:“就这些法则仅仅涉及纯然外在的行动及其合法性而言,它们叫作法学的;但是如果它们要求,它们(法则)本身应当是行动的规定根据,那么,它就是伦理的。这样一来,人们就说:与前者的一致叫作行动的合法性,与后者的一致叫作行动的道德性。”(6:214)就规范的对象而言,在法权的领域中,行为的允许无关乎道德与否,只需要符合法权法则的规定。然而,法权的规范有效性,也就是其强制力的成立,是建立在行为的道德性基础上的。如果一个行为,它是一个自然而非自由事件,即它不具有道德意义,那么,法权就无法对其产生规范力,进而无法将这一行为归责于任意主体。人区别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的关键就在于,他是一个自由的存在者,是可以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存在者。人之所以是自由的存在者,就在于他是理性的,服从于理性的法则,其行为表现为“應当”。因此,尽管法权仅要求外在行为的合法性,但法权最终是道德的,是人的自由本质赋予其规范性。
第三,所有外在的法权以自由或者道德为最高标准,还表现在康德对法权的类型划分上。康德首先在形式上对法权作出了一般划分:“法权分为自然法权和实证法权,前者建立在全然的先天原则之上,后者来自立法者的意志。”(6:237)在康德看来,法权的划分还能在“功能”上进行阐明:“作为使他人承担义务的(道德的)能力,亦即作为对他人的一个法律根据的法权,其上位的划分就是生而具有的法权和获得的法权,前者是不依赖于一切法权行为而自然归于每个人的法权;后者是需要这样一种法权行为的法权。”(6:237)“生而具有的法权”和“自然法权”,“获得的法权”和“实证法权”分别有一种对应关系。“生而具有的法权”也就是内在的“我的”和“你的”的法权,这种法权只有一种,即自由①。自由(法权)就是所有具体的、实证的法权的最终标准,“一旦对获得的法权发生了争执,出现了问题,谁有责任作出证明……可以在方法上像依据不同的法权条文那样援引生而具有的自由法权”(6:238)。“生而具有的法权”是更为内在的、出于本心的,它意味着一种主体的能动性,而“获得的法权”,也就是实证法权,是更为外在的,它意味着一种被动的“束缚”。因此,可以认为,康德试图通过法权的形式与内容的划分来追溯法权的道德根基,自由是法权成立的最高标准。
简而言之,法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它仅限于规范范围上的行为合法性[3]。康德从先验的角度,将法权之为法权的先天条件,以及它的规范力来源,都建立在其道德理论之上,法权法则最终指向的是道德法则。那么,康德对于人的先天实践能力(实践的自由)的定义是适用于法权领域的,对《法权论》的阐释自然应当以准确把握实践的自由的内涵为前提。
(二)意志(Wille)与任意(Willkür)
自由概念是贯穿康德三大批判的核心概念,它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与自由感[4]。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对先验的自由的设定,并进一步过渡到了实践的自由。《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三个二律背反的正题指出:“自然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推出的唯一因果性。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来解释这些现象。”(A444=B472)自然因果律需要追溯更早的原因,而这种追溯是无止境的,为了满足充分理由律,进而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现实存在,我们必须假设一个纯粹自发的自由因。为此,我们同样可以为人的因果序列设定一个先验的自由理念,给人的经验性行为提供可归责性(自由选择的能力,即任意)的真正根据,这对于实践的自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先验的自由理念在另一种意义上(实践意义)具有了实在性,康德将关注点从人的认识能力转向了人的实践能力。
康德首先定义了人的任意,并将其与动物的任意进行比较:“在实践理解中的自由就是任意性对于由感性冲动而来的强迫的独立性。因为一种任意就其(通过感性的动因)被病理学地刺激起来而言,是感性的;如果它能够成为在病理学上被迫的,它就叫动物性的。”(A534=B562)人和动物的活动都是一种任意并且是带有感性的。动物的任意完全受到病理学因素的强迫,是被动的,而人的任意是一种自由的任意,代表着自由选择的能力,能够独立于“由感性冲动而来的强迫”。动物的任意对应着本能,自由的任意对应着一般的实践理性,在康德看来,两者都有着专属于自身的使命。本能的使命就在于追求幸福,这是大自然的本来目的,“因为比起每次都通过理性才能做到,这种被造物必须在这一意图中实施出来的所有的行动,以及他的行为的全部规则,若有本能来给他拟定将会更为准确得多”(4:395)。康德在此处接受了由卢梭开启的浪漫主义的观念,即对幸福的追求不需要理性的干涉。但不同的是,康德并没有因此贬低理性,而是进一步挖掘理性自身的价值。在康德看来,“理性必定具有其真正的使命,这绝不是产生一个作为其它目的的手段的意志,而是产生一种自在的本身就善良的意志”(4:396)。对理性的使用也有层次之分,如果仅仅将理性作为手段而追求其它目的,那么我们能够掌握的只是“技术上实践的规则”,尽管属于一般的实践理性,但它不属于实践哲学。然而,一般的实践理性已经暗含着纯粹实践理性的种子,我们只要把任意完全置于理性规则之上,不是为了其他感性的目的,而是使得一切感性都服从于纯粹实践理性自身的要求,那么,就能直接反映出人的意志(自由意志)的存在。
康德进一步区分了意志与任意。贝克认为:“康德并未挑出这两个概念,然后形式性地展开它们的彼此关系。他对它们加以一并处理,而从未清晰地表明哪一个才是他正在讨论的对象。”[5]但通常来看,康德在“意志”概念的使用上有着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意志与任意分别承担着立法的机能与执行的机能。意志为任意提供规定根据,它本身是绝对的,不再有任何其他的规定根据。任意直接与行动相关,它既能够因感性刺激而产生行为,也能够以纯粹意志作为行为的规定根据。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康德为什么宣称:“只与法则相关的意志,既不能被称为自由的也不能被称为不自由的,……只有任意才能被称作自由的。”(6:226)意志不关注行为本身,注重为行为的准则立法。任意之所以是自由的,就在于它是一种自由选择行为的能力。广义上,意志代表着一种统合立法与执行的整体能力,只有广义的意志才具有“自律”的特性,这种意义上的意志才能说为自己立法①。
在康德看来,尽管意志与任意同为实践的自由,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并不是能够自由选择行为的、任意的自由,而只能是具有超越一切感性欲求之上的,能够自我立法的意志的自由。因此,法权与德行同属自由的实践领域,真正探寻《法权论》之阐释路向,需要回到康德所设立的人的实践行为的先天标准,从实践的自由,尤其是意志着手,方可得出结论。
二、契约论阐释路向:任意(Willkür)作为道德之本质
讨论实践的自由概念的目的是厘清康德对于作为自由主体的人的道德本质的理解,这直接关系到《法权论》阐释路向的选择。不同阐释路向的差异取决于对实践的自由概念的取舍,究竟是意志还是任意决定了人的道德本质。因此,要判断哪一种阐释路向符合康德文本的论证逻辑,并且能够内在地一以贯之,首先必须清楚阐释的逻辑起点是什么,进而分析其阐释依据。
(一)基于理性选择的社会契约
契约论阐释路向认为,应当将康德解读为一个社会契约论者,顾名思义,康德关于公民状态建立的形式基础在于社会契约的签订,而社会契约是体现人的理性选择的理想模式[6]。契约论阐释路向的代表人物是墨菲与凯尔斯汀,之所以如此理解康德的《法权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强调康德语境下的道德之本质应当是人的自由选择行为的能力,即任意,而非具有立法能力的意志。实际上,两位学者都缺乏对康德关于实践的自由概念的整体关注,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本选择以及关注点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墨菲的《康德:权利哲学》一书是英美世界中具有代表性的阐释康德法哲学的著作,他在康德文本的选择上主要集中于《实践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而《道德形而上学》则处于次要位置。墨菲的论证始于对两个问题的关注,其一,康德在讨论自由与道德法则关系时的“循环论证”;其二,自黑格尔开始的对绝对命令的批判,他们认为康德的最高道德法则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第三章中“承认”了他的循环论证:“人们必须坦率地承认,这样一种循环看起来是无法摆脱的。我们假定自己在起作用的原因的秩序中是自由的,是为了在道德法则之下的目的秩序中设想自己,接着,我们把自己设想为服从这些法则的,是因为我们把意志自由赋予了自己。”(4:450)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定自由是为了道德,但我们服从道德法则又是为了自由,自由与道德法则互为根据,在逻辑上这显然就是一种循环论证。墨菲在解决这一困境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康德的“综合”方法,而是提出了一种实质性而非形式性的自由概念。墨菲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是任意,而非意志赋予人以尊严,那么我们将使康德对于道德的刻画免于循环论证的指责。因而人的尊严将不再源于他能够成为道德存在者的能力,而是源于他选择任何行为过程的自我立法的能力。”[7]墨菲以康德描述意志的话语来定义任意,赋予人以尊严的是自由的任意,道德之本质就在于“个人自由选择行为的能力”,而非立法的能力。此外,墨菲指出,个人自由选择的目的是“人性的本质性目的”,即幸福和完善,其来源于绝对命令的第二项变形公式①,而正是这一目的构成了绝对命令的实质内容,因此,针对康德最高道德法则的形式主义批判并不成立。可以看出,在墨菲那里,并不是具有普遍性的法则限制着个人的选择,而是个人的选择及其本质性目的决定了哪些法则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政府、法权是理性同意的产物,社会契约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设立。
同样采取契约论阐释路向的凯尔斯汀关注的主要文本是《道德形而上学》,他的《良好的自由秩序》是全面研究康德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著作。凯尔斯汀较为注重《道德形而上学》自身的论证逻辑,但他在处理文本中某些含混之处时,转而诉诸了大量康德为澄清其思想而准备的预备性笔记。实际上,这些预备性笔记的时间跨度长达30年之久,以至于并不能完全保证康德思想的连贯性[1]56。预备性笔记着重提到了关于外在对象占有的正反命题,正命题支持一种理智性占有的观念,反命题支持一种经验性占有的观念①,而在这些笔记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凯尔斯汀的方法是支持正命题,即理智性占有,并进而形成了一种规定主体—客体关系的财产权观念。凯尔斯汀认为,康德正是基于这种财产权观念展开了政治合法性之形式的论述,主体间的政治义务就是通过达成一致的同意来约束选择自由,“一个契约的必要性源自这样一种要求,即使得对于外在对象的单方面的占有能够与所有人的立法意志相一致”[8]。顯然,凯尔斯汀将公民状态的形成建立在人们的理性同意的基础之上,同意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选择,而这也是所有人的联合意志的立法对象。
墨菲与凯尔斯汀尽管在文本的选择以及阐释的起点上有所差别,但两者关于政治合法性之形式的阐释都是建立在基于有限选择的契约观念之上的。他们的解读都倾向于将体现人的自由选择能力的任意作为康德语境下法权状态的核心观念,法权概念在这并不具有无条件的有效性,也不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种先天主张,其论证逻辑是通过诉诸基于人的理性选择的社会契约来回答政治合法性之形式的问题。
(二)一种经验主义的自我消解
对经典文本的阐释,应当首先回到文本自身,尽量遵循作者本人的论证逻辑。契约论阐释路向的问题就在于它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处理并没有关注康德本人的解释,而是试图以完全悖于康德哲学基本特征的方式来探寻一条全新的解释路径,因而,所得出结论的合理性是不无疑问的。
墨菲在处理康德的循环论证时所采取的办法是将重心转向任意,从人的自由选择能力及其本质性目的来论证政治合法性之形式的问题。然而,康德只是表面上承认了自己的循环论证,经过“综合”办法的解读,其论证显然是成立的,并且意志仍旧是人之道德行为的本质。康德认为,“自由和意志的自我立法都是自律,因而是可互换的概念,但正因如此,一个不能用来解释另一个,且提供论证上的根据,而最多只能为了逻辑的意图,把同一对象的那些显得不同的表象归结为一个唯一的概念”(4:450)。在这里,自由指的是自我立法的能力,而自律就是道德律,那么自由和道德律就等同了,因而涉及自由与道德律的关系也是循环论证。但康德强调这种等同只是“为了逻辑的意图”,这就是说循环论证只是对于形式逻辑而言的,只关系到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并没有考虑到本体论的关系。形式逻辑的自相矛盾或循环论证,在其他方面(例如本体论)上是有意义的,这在康德那里并不少见,《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二律背反采取的就是这一解决思路,即“同一性命题在形式逻辑上是分析的,但在先验逻辑中却是综合的,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9]。就此而言,自由和道德律虽然在形式逻辑上可以互换,但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仍有不同。我们为了道德律而假定自由,此时的自由作为一种消极的自由,它停留在智性世界(intellektuellen Welt)①中,而我们服从道德律是为了自由,这说明此时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它是要影响感性世界(Sinnenwelt)的。因此,康德采取了物自体与现象界的不同立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假定一种先验的自由,在实践论的意义上,我们的道德行为需要以实践的自由为基础,进而“综合”智性世界与感性世界,这基本上就是康德在第三个二律背反上所采取的思路。墨菲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康德在讨论自由与道德法则关系时循环论证的“错误”,在他看来,如果康德不采取一种经验主义的论证方向,那么这一“错误”就是无法避免的。物自体与现象界的划分在墨菲那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无需考虑的,唯有完全根植于经验世界的任意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但是,物自体与现象界的划分正是康德哲学的根本,人的道德行为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就在于物自体的超越性,墨菲站在经验的视角上的阐释是与康德哲学难以相容的,因而不得不说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凯尔斯汀将康德视为一位严肃的政治哲学家,但他本人对康德文本的处理可能是不严肃的。凯尔斯汀注意到了财产权观念之于康德《法权论》的重要意义,进而重点讨论了理智性占有的命题,但问题仍在于他对外在对象占有的二律背反的解决上是非康德式的。康德认为,“理智性占有的正命题与经验性占有的反命题都为真”(6:255),这一判断的根据依然是物自体与现象界的划分。经验性占有仅在现象界成立,并且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理智性占有“必须从实践理性的公设中得出……实践理性不需要直观,乃至先天直观,仅通过自由法则所授权的对经验的排除来扩展自身,这样就能提出先天综合的法权命题”(6:255)。理智性占有表面上与财产权相关,毋宁说是对法权何以成立的先验演绎,本质上,法权成立的先天条件考虑的是排除一切经验性条件的意志与意志的关系,也就是作为自由主体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实践理性的公设。凯尔斯汀笼统地否定了经验性占有,并将理智性占有乃至财产权观念解释为人对物的关系,与墨菲类似,“限缩”了康德的论证逻辑,以“经验”去理解康德的“形而上学”。
目前来看,康德法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径路并不少见,而这也是对康德产生怀疑的重要来源。部分学者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写作是“不纯粹的”(impure),与康德早期的批判性作品的形而上学特征大相径庭[10]。然而,康德始终都强调意志与任意的划分,真正的自由就是自我立法,就是自律。如果不是自我立法,那么自由就不再是自由,任意只是行为选择上的自由,它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由的,若不以意志作为规定根据,仅仅只是为了更大的、长远的利益,那么这种自由马上就会自我取消,终究是被外在的其他目的所决定的。康德主张:“法权的普遍法则……尽管是一条赋予我责任的法则,但却根本没有指望、更没有要求我为了这种责任而把我的自由限制在那些条件上,而是理性仅说,我的自由在其理念上被限制在上面,而且事实上它也可能受到他人的限制;而且理性把这说成是一个无法得到进一步证明的公设。”(6:231)尽管法权仅考虑外在的合法性问题,并不要求主观上的动机,但就其要求的限制而言,是来自于纯粹的实践理性,即意志的理念自身的[11]。如果法权的成立是建立在有条件的契约观念之上,那么法权就不是自在地就存在的,因而也不是一个“无法得到进一步证明的公设”。契约论阐释路向以任意作为道德的本质,进而也作为法权的本质,显然难以符合康德自己的主张,经验主义阐释的最终结果将是不可避免地自我消解于某一外在的有限目的之中。
三、先验阐释路向:基于意志(Wille)的法权演绎
据前文所述,康德哲学的关注点始终是“形而上学”,它在理论与实践维度一以贯之的是其批判与先验的“方法论”,这一标准在如此“实践”的法哲学中也完全适用。法权本质上是一种先验的实践知识。先验阐释路向之于康德《法权论》的意义就在于其“先验性”:一方面,它对法权的演绎是基于排除一切经验的意志的,得出的是关于法权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另一方面,先于经验的知识并没有脱离人的认识范围,也就是说,“先验”仍然是与经验相关的,人的(自由)意志是能够被“反思”到的。概言之,先验阐释路向是完全康德式的阐释路向,通过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康德的法权学说是在与何者的“对话”中形成的,以及在哪些方面作出了改进。
(一)先验维度的社会契约
先验阐释路向的“先验性”首先在于对人的先天实践能力,即实践的自由的关注。康德的法权以人的意志而非任意为最终根据,整个法权体系的论证是在“先验”的维度上进行的,這主要反映在财产权的演绎中。尽管较少提及康德关于人的实践的自由的预设,与契约论阐释路向相对立的自然法阐释路向在理智性占有的论证中着重提到了意志,在这一点上遵从了康德原本的论证逻辑。自然法阐释路向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在其修订的1986年版《法权论》中指出,由于一些印刷上的错误,需要重构该文本的体系结构[12]5。路德维希将《法权论》第2节的内容移到了第6节“纯然的合法占有(本体性占有)的概念的演绎”中,并且指出正是第6节关于理智性占有(本体性占有)的演绎揭示出《法权论》并不是一本实用的法律手册。不同于凯尔斯汀,路德维希保留了理智性占有的主体——主体向度,理智性占有之所以必然是可能的,不是因为主体对外在对象的一种支配权主张,而是如果没有理智性占有的观念,就不能对主体与主体间的外在自由进行规制。在路德维希看来,理智性占有或者法权关系源自纯粹实践理性,“如果它们(法权原则)是从纯粹实践理性推演出来的话,那么法权原则必定是形式的。”[12]113法权关系就是依据纯粹实践理性原则本身的形式约束所展开的本体论关系,它所反映的是主体间的意志的关系。依照这种阐释路向,理智性占有反映的是整体的意志的演绎,意志为自身提供行为根据,而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状态的转变所依据的应当是纯粹的意志,因而这种转变是先天必然的,所谓契约只是预设的政治合法性的形式的理念[13]。
自然法阐释路向将关注点转向了法权原则的形式性,也就是自由主体之间的关系,仅就这一点上来说,它也可以被称为先验阐释路向,任何经验性的内容并不是其考虑的重点。先验阐释路向的独特意义不仅在于如何理解财产权的成立,还能看出经验在康德法权学说中的地位。经验主义始终是康德哲学的批判对象,在法哲学中,这种批判反映在康德对于近代自然法学或者说意志论的超越上。康德首先接受了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指出“自然状态其实是一种战争状态,也就是说,尽管并非一直有敌对行为之爆发,却不断有敌对行为之威胁”(4:349)但康德认为人们签订契约并进入公民状态,并不应当以自身的利益为动机,后者的社会契约思想是经验主义的。近代的经验主义来自从神学形态向世俗形态转化的意志论传统,意志论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具体指每一个公民本人的意志,但问题在于,它没有区分、排除经验的理性与情感,使得人们对意志的理解陷入经验主义。先验阐释路向在公民状态的论证上选择了排除一切经验的意志,公民状态的建立不以其他经验内容为目的,因而不是偶然的,它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演绎结果,其本身就是目的。在这里,“先验”的意义就在于对经验主义的超越,人作为自由主体必然进入公民状态,法权关系的形成并不来源于我们“选择”签订的社会契约。
(二)认知主义的自由概念
先验阐释路向强调从先于经验的纯粹理性的实践自由出发,排除一切经验内容构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权,进而运用于现实经验中,这是基本符合康德本人的论证逻辑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实践的自由对康德的法权,以及公民状态的阐释并不是单向性的,在这之中,人自身能够通过反思来“认识”到纯粹的自由意志,这种阐释应当是双向互动的。
我们把建立在人的反思的基础上的意志归为认知主义的自由概念。有学者认为,康德实际上是一名道德实在论者,在康德看来,“道德的基础存在于一种已经被确立起来的结构——理性存在者基于本性就拥有的结构——之中”[14]。根据道德实在论,道德或者自由之存在,独立于任何一个有可能受制于他们的人。如果我们接受了道德实在论的观点,道德—自由—行为(选择)的关系就会是单向的,既然道德本身就已经存在了,自由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确定了的指令,我们也必然会这样去行动。然而,这种观点尽管可以满足先验阐释路向的必然性要求,但却忽视了“先验”的认识论特征,即人的自我批判的认知活动。如果接受道德实在论的论证逻辑,自由就不再是实践的,它只是悬挂于人的理性范围之外的超验理念,人的行动只能是被动地服从指令。
认知主义的自由概念并不是说康德试图获得任何有关自由的理论知识,只意味着人能够通过自我反思“认识”到超出经验的自由的存在,并且使其在实践领域证明人这一主体的道德性。康德主要在三个方面提到了主体的反思。其一,康德认为,我们能够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来反思自由,“认识”到自由存在的理性“事实”。当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意识到道德行为的可能性时,他就可以“认识”到自由在实践中的实在性,“他能够做某事是因为他意识到他应当做某事, 他在自身中认识到了平时没有道德法则就不会知道的自由”[15]。其二,个人在行使权利时,同样能够反思到自由的存在,权利的有效性依托于自由,唯有自由概念的普遍性才使得权利的自由行使得以可能。布朗特就指出,康德引入许可法的目的除了为满足法权原则的普遍性要求外,还在于反映人的反思性承认①。个人通过主张权利,能够意识到具有普遍性的意志本身,从而承认自身对其他每个主体所负有的责任。公民状态的联合意志正是通过人的自我反思得以形成,每一个人都将意识到建立法权关系的先天义务。其三,理性不仅具有通过概念进行认识的功能,它还有通过意志而行动,并且形成实践法则的功能。现代社会都是建立在法则之上的,如果没有这些法则,我们的生活就会立即瓦解,社会不再是人的社会,生活也不再是人的生活。理性之所以能够形成法则,正是因为理性是自由的,在意志自由的基础上,才会有法则,如果人不是自由的,法则就将失去规范的效力,是毫无意义的。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客观有效性,使得自由具有了客观实在性,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在法则社会的人可以透过法则反思到意志的自由,认识到一切法则其实都是建立在意志之上的。可以看到,上述三种“反思”都指向纯粹的实践的自由,某种意义上是对康德法权理论的一种“反向”阐释,即从法则、自由权利的主张返回到自由的任意与意志。因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公民社会中的法权法则既是人们行动的信任标准,也是认识主体的自由本质的媒介,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法则是基于普遍联合的一般意志,是以人的具有普遍的、无条件性的意志为根据的。
先验阐释路向忠实反映了康德法权学说的“先验”特征,任何经验性的内容在这都是偶然的、有限目的。然而,对经验的排除并不代表理性就是万能的,可以论证一切的。在康德的时代,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哲学在德国各个大学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这种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打破人的理性有限性,进而形成了理性的独断论。对于康德而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依照理性主义所设立的“自然法”标准是超出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外的。认知主义的自由概念表明意志是可以被实践、认识的,并且依据其所建立的法权、公民状态并不是一种“已经确定了的结构”,而是诉诸人类之认知能力与反思能力的实践理性标准,尽管它在知识的认识论上与我们无关,但在实践的意义上是我们能够反思到的。因此,可以说康德实现了对以往的理性主义传统的超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紧张关系。
四、先验、法权与永久和平
康德《法权论》的阐释路向不仅涉及政治合法性之形式,还指向政治合法性之范围,后者即“永久和平”,也就是康德的世界公民主义。尽管《法权论》中没有深入讨论与“永久和平”相关的国际法权以及世界公民法权的问题,但康德在前言中作出评论:“在本书结尾处,有几章我处理得不够详细,不及人们与前面几章相比所可能期待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前面几章推论出来。”(6:209)康德在论证法权时依据的是已经确立的先天自由理念,它是贯穿私人法权、国家法权、国际法权以及世界公民法权的一条红线。康德之所以将“永久和平”称为一项哲学性规划,因为它是康德法哲学所面对的终极问题,相应地,《法权论》的阐释路向也应当与“永久和平”的问题导向相契合。
赫费对于康德《法权论》的政治合法性之范围的阐释具有代表性。赫费反对将“永久和平”视为一种“政治乌托邦”,并明确指出:“和平的概念并不局限于《论永久和平》,而是系统贯穿于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16]12某种程度上,“永久和平”确实可以说是贯穿三大批判的核心规划,赫费的判断仅在这一点上是符合康德哲学的基本要旨的。和平就在于消除战争,后者的必要前提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具有普遍性的法权关系,而法权仅涉及主体间的外在关系,“永久和平”也就是康德所构想的一种旨在处理外在冲突问题的特定方式。赫费对于“永久和平”的动机的解读是霍布斯式的,他认为现代国家乃至“永久和平”的形成都是基于人对战争的厌倦[16]16。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言,康德接受了霍布斯关于人类自然状态的战争的描述,但在公民状态的论证中并没有采取霍布斯式的经验主义视角,自利在康德那是不被考虑的。赫费正确地指出了“永久和平”之于康德哲学的重要意義,但却将康德解释为一名政治现实主义者,这不得不说是与“永久和平”的先验特征相悖的。基于“厌战”或自利的考虑,休战协议的达成只是临时性的,战争任何时候都可能再次发生,“永久和平”将不会达成。尽管赫费的解读是基于对康德文本的全面考察,从结果来看他并没有充分理解何为“一项哲学性规划”,而这也是契约路阐释路向的问题所在,以至于对康德法权学说的把握在整体性上略有不足。
如何理解康德的法权与“永久和平”的关系,存在正向演绎与人的“反思”的双重视角,这也是先验阐释路向的基本要旨。从正向演绎来看,康德指出:“公共法权这一普遍概念使人不仅想到国家法权,而且还想到国际法权;由于大地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表面,公共法权必然把二者引向一种多民族的国际法权或者世界公民法权的观念。”(6:311)一国之内的国家法权的建立是以实践的自由意志为根据,法权普遍化的结果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如果仅从自由的理念来看,避免冲突的最好办法是尽量减少来往。但康德在这里还考虑到了自然目的的阐释,有限的地球表面以及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冲突无法避免,因此,社会需要一种更大范围的法权关系来调和冲突,正是先天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目的结合使得全球性的法权关系得以必然。依照这一逻辑,国家法权、国际法权以及世界公民法权缺一不可,三者具有统一的理念前提,“只要有一种缺乏由法律限制外在自由的原则,其余两种形式的大厦就必定会被削弱,最终坍塌”(6:311)。从人的“反思”来看,康德认为,人的理性与知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判断力,它在认识领域里是规范性的,在实践领域里是反思性的。规范性的判断力能够将特殊归摄到已被给予的普遍中,反思性的判断力则从特殊中寻求普遍,人们可借此在客体对象上设定一个目的,从而达成一种统一性[17]。从公民状态的建立到社会的逐渐文明化,人们通过一种道德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权利,可以反思到自身的自由本质,以及最终的共同道德理想——人类的永久和平。人在不断反思、认识主体的自由本质与道德目的的过程中,转而将其贯彻到现实的社会生活,这使得“永久和平”的达成成为可能。
“永久和平”是康德在先验视角下提出的人类政治制度的构建方案,其论证逻辑始于康德的法权学说[18],更确切地说,是始于康德对于实践的自由的意志与任意的划分。《法权论》的先验阐释路向既抓住了具有立法机能的并且以自身为目的的意志,将任何经验的内容排除在外,同时强调了人的“反思”,即自由并不是超然于人之外的存在,它是能够被我们所“认识”的,通过对自身道德目的的“认识”,现实的法权关系才是可能达成的。因此,先验阐释路向契合于“永久和平”的政治道德理想,而唯有以先验的视角审视康德的《法权论》,才能明晰“永久和平”何以必然的终极问题。
五、余论
康德法哲学以《法权论》为依托,对后者的理解决定了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康德《法权论》之阐述路向的判定,需要从康德哲学的批判本质来整体把握,其批判对象是人的诸先天能力,在实践领域中,则是对人的自由的实践能力,也就是对欲求能力的批判。法权本质上是先验的,对它的解读应当以实践的自由为前提,实践的自由意味着先天的自由能力,它在逻辑上是先于经验的,并最终要运用于经验之上。康德将人的欲求能力划分为意志与任意,意志具有立法机能,它自在的就是目的,任意具有执行机能,仅与行动相关,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是意志的自由。《法权论》的先验阐释路向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将意志作为法权演绎的出发点,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状态的转变不以任何经验内容为目的,是人为实现其自由本质的必然阶段;另一方面,将实践的自由视为一种认知主义的自由,先于经验并不代表脱离人的认识结构,尽管不同于知识意义上的认识,但人类可通过对现实的法权的“反思”来认识到自由的存在,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自由属性。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把握,先验阐释路向对国家法权的解读,可进一步推论出国际法权以及世界公民法权,三者在体系上缺一不可,这也是康德论证“永久和平”的先验逻辑。本文将康德《法权论》的阐释置于“先验”的层面上,并不代表要破除康德关于法权与伦理(德行)的区分,法权依然只关注外在行为而非主观动机的合法性。先验阐释路向仅意味着使对法权何以成立、法权的规范效力等问题的解答尽量符合康德哲学的批判本质,并且契合康德对于“永久和平”的“哲学性规划”的定位。
参考文献
[1] FLIKSCHUH K. On Kant's Rechtlehre[J].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0: 5(1).
[2] Mark Timmons.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terpretative Essay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汤沛丰.康德法哲学中的人权、所有权与国家[J].中国人权评论,2018(1):15-33+178-179.
[4] 鄧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24-30.
[5] Lewis White Beck. 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98.
[6] 邵华.论康德的社会契约论[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7-24.
[7] Jeffrie Murphy. Kant: The Philosophy of Right[M].Berlin: Mcmillan, 1970.
[8] Wolfgang 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Immanuel Kant's Rechts-und Staatsphilosophie[M]. Berlin: De Gruyter, 1984: 356.
[9]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50.
[10] 方博.自由、公意與社会契约——关于卢梭和康德的一个政治哲学的比较[J].哲学研究,2017(10):102-110.
[11] 卞绍斌.走出自然状态:康德与公共法权的证成[J].学术月刊,2019(6):13-31.
[12] IMMANUEL KANT. Die Metaphysischen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M]. 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86:5,113.
[13] IMMANUEL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x.
[14] LESLIE A, MULHOLLAND. Kant's System of Rights[M].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111.
[15]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M]. Hambur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1974:35.
[16] OTFRIED H?魻FFE. Einleitung: Der Friede - ein vernachl?ssigtes Ideal[M]. Berlin, Boston: Akademie Verlag,2015:12,16.
[17]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nteilskraft[M]. Hamburg:FelixMeiner Verlag, 1924: 15-17.
[18] 洪涛.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33-149.
On The Approach of The Account of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A Review of Contractarianism and Natural Law Accounts
He Ziheng
(Administrative Law Schoo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Scholarly researches of Kant's legal philosophy have focused on the Doctrine of Right as the core text, but there is considerable debate among scholars as to the approach in which the Doctrine of Right should be interpreted. Kant's right is a kind of transcendental right. The a priori condition for right to be right is man's practical freedom. The account of Doctrine of Right should take the practical freedom as the premise.Kant divides the practical freedom, that is, people's faculty of desire, into will and choice. The will itself is the purpose and bears the function of legislation. The choice is only related to action and bears the function of execution. When the latter is completely based on the former, people's behavior is moral behavior, and the real freedom in the strict sense is the freedom of will that can self-legislate.The contractarian approach takes the choice as the essence of morality, and establishes the formation of citizen state on the social contract based on rational choice, which is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The transcendental approach grasps the transcendental essence of Kant's philosophy, establishes the deduction of right on the base of man's a priori freedom, that is, will, realizes the transcendence of voluntarism and rationalism, and opens up the argumentation logic of the right of a state, the right of nations and cosmopolitan right,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why "perpetual peace" is possible.
Key Words: Kant; doctrine of right; practical freedom; transcendental; perpetual 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