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的幻覺(十):系統史觀
2022-04-11王五一
王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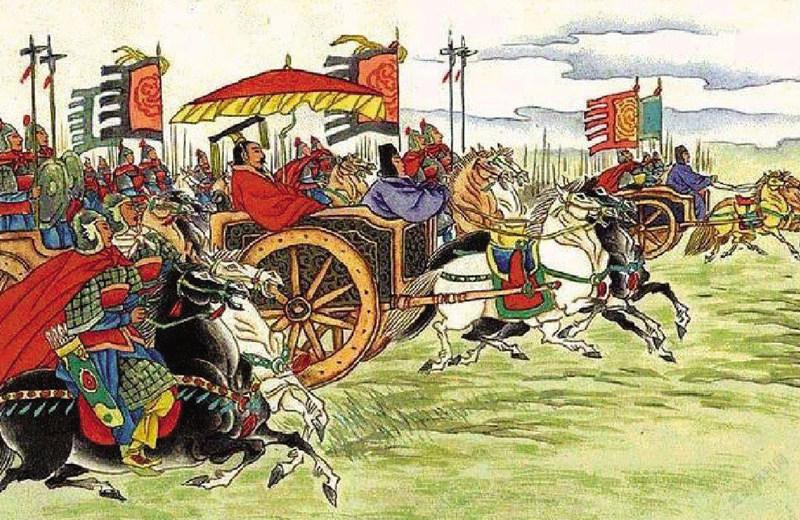



這是《進步的幻覺》系列的最後一篇了。十評歷史進步主義。十評,前九評都是批評,這最後一評,來點正面的、建設性的、結論性的——系統史觀。
說進步,就一定是說全人類的進步,羊國狼國一起進步,只是有快有慢,有“先進”有“落後”而已。至於狼國是不是吃羊吃進步的,羊國是不是被狼吃落後的,羊國最終會不會被吃死,最後只剩下狼國在進步,歷史進步主義哲學不糾纏這類問題。如此,這進步史觀對於羊國就是精神毒藥,因為它會忽悠著羊國把狼國看作是歷史進步路上的同路人,同志,甚至老師。
其實從邏輯上打倒進步主義並不難——生老病死,成住壞滅,萬物皆然,豈人類社會獨反其理而行之?僅此常識的力量,就足以將其打倒。之所以下這大功夫搞個系列,又是“掀地毯”,又是“掏髒貨”,又是“破假定”,目的是要通過批評這個學術靶子,批出另外一片正面道理來。
一旦理解到了歷史不是在進步而是在墮落,一旦理解到了人類與世間的萬世萬物一樣,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也是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則我們對人類社會的理解,真假、善惡、美醜、高低、貴賤,差不多都會顛倒過來,好事會變成壞事,壞事會變成好事,好人會變成壞人,壞人會變成好人,人類進步的火車頭——西洋文明,會變成人類墮落的火車頭,人類進步的領導階級——知識份子,會變成人類墮落的領導階級,現有的人文社會科學乃至哲學,會發生體系性大崩塌。看著挺過癮。然而,如此再製造另一場思想抽風、精神雪崩,卻也未必是善舉。幾百年歷史進步主義製造的思想混亂,不應該再用另一場思想混亂來代替它。如果說,編造出歷史進步的神話是讀書人對歷史犯下的罪過,那麼,換上另一個極端的理論,並不是在贖罪,而是在雙重犯罪。
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命運而言,真正有害的,真正應當打倒破除的,是這兩種歷史觀的那個共同的思想根源——縱向思維,普世思維,全球思維,這種把全人類看作一個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思維方式。進步主義也罷退步主義也罷,只要是普世思維,都有害,因為,它都會誘使我們誤解自己的利害所在,背離自己的責任焦點,並且,會給各種意識形態陰謀提供一個學術容器。須知,這世上所有超民族的理論都是用來糊弄弱國的,所有超階級的理論都是用來糊弄窮人的。
筆者前幾年寫了一篇寓言,題目是《智叟船長》:“風暴起。為大船免于傾覆計,船長愚公,將居上等倉者俱驅至下等倉。眾皆嗔。智叟趁勢居間鼓噪,煽動群起攻之,將愚公打倒。智叟奪得船長位,遂使人人官歸原倉。‘還倉團’歡聲雷動,艨艟船頃刻顛覆。至怪至奇者,眾落水者在水中掙扎將死之際,仍在感念智叟青天,仍在詛咒愚公專制。”
船客之愚癡,源自其立志之褊狹。一個人若自幼立的是“倉志”,則其一生的偏狹愚暗、不知好歹亦便由此鑄定。一個民族,若自幼便對孩子們進行“倉志”教育,個人主義教育,鼓勵其起跑戰,排位賽,這個民族的偏狹愚暗、不知好歹便鑄定了。近四十年來,中國的教育哲學是二元的。幼、小、中,對孩子們進行的是“倉志”教育;到了大學,則轉跳了另一個極端,“海志”教育——普世價值教育,歷史進步教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教育。唯獨把船志教育——國家責任教育,空白了出來。
為“倉志”披上一層“海志”的外衣,辦法夠高明的——直接用個人主義仰攻愛國主義,道德力道不夠,轉而站上普世主義的道德高地,居高臨下地攻擊“狹隘民族主義”,就厲害了。聯想到四十年來西方與中國在思想上密切的師生關係,再聯想到師生之間在教育取向上的這種奇怪的“國際分工”“多元格局”——“先生國”是單一的“船志”教育,而“學生國”卻是與其師南轅北轍的“倉——海”教育,容易使人產生出陰謀論聯想。
區區個人,如何對“大海”的命運負起擔當,如何為使“大海”更美好而貢獻力量?歷史進步主義可以幫忙克服海志論的這個邏輯弱點。它可以為這不著邊際的“海志”提供一個道德支點——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為實現全人類美好的終極目標而奮鬥——這理想美麗無比啊,誰敢說它不對?至於怎麼奮鬥,奮鬥什麼,再說,先用這美麗的高姿態把“狹隘民族主義”踩在腳下,從而把國家責任的枷鎖甩掉,然後,各位就可以放心去謀自己的“倉利”了。——“倉志”與“海志”之間的邏輯暗道,是在這裡。
西洋人船駕得好,因其哲學是船哲學,文化是船文化,從船長到船員人人立的是船志。而中國的船之所以玩成今天這樣,因為船員們不但胸懷倉志——五等倉的琢磨著爬四等倉,四等倉的琢磨著爬三等倉,而且,更可怕的是,人人嘴裡還喊著美麗的“海志”情操,普世價值。在中國學界,“倉志”不丟人,“海志”不丟人,唯獨這“狹隘船主義”丟人。這個意識形態設計可太科學了。“倉志”教育,至少在理論上還可以批駁,畢竟,我們有五千年道德文明,有公善私惡的大理。而“海志”教育,披著美麗的最高道德的外衣,並且可以和中國文化的大同精神以及共產主義的普世理想融和起來,所腐蝕的,不是中國的受教育者而是教育者,不是中國的學生而中國的教師,不是中國人的道德而是中國人的哲學,從而在意識形態的最上游就把中國的文化生機堵死了。
搞這“十評”,目的之一,就是要拆穿當今中國主流思想界的這“形海實倉”的哲學把戲。打倒了“進步”,打倒了“普世”,撕去了“海志”的假面具,每個人面前就只剩下了“倉志”與“船志”兩個選項了。手裡沒有了“普世價值”的攪屎棍,赤裸裸地站在這個雙項選擇面前,看你怎麼選?
正確的選擇當然是“船志”。“船”者,國家也。“船”是一個系統,國家是一個系統,本文標題“系統史觀”,就是“船”史觀,國家史觀。批倒了歷史進步主義,把歷史觀從普世的視野收縮到國家層面上,史學就找到了正確的哲學基點,民族就找到了正確的立世目標,個人就找到了正確的人生責任閾。列位看官可以大致從這三個“找到”來體悟這“十評”的立論。
什麼是系統?簡單說就是四個字:有機整體。整體由部分組成,系統由多個“子系統”構成。子系統與子系統是勾著的,連著的,相互依賴的,相互作用的,相互影響的。
世間最典型、最複雜的系統便是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一個生命之所以能活,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子系統間的“功能耦合”——消化、循環、筋骨、神經等各個子系統間分工協作,相互配合,共同撐起一個生命,其中有一個子系統壞掉,人就完了;二是系統要能與外界進行能量變換,吐故納新——人身上長著許多對外開放的眼兒,喘氣、吃喝、排泄等等,維持著生命的運轉,把其中任一眼兒堵上,人就完了。
系統為什麼能生存,為什麼能運轉,用生命做例子,最好理解,但要講系統的演化嬗變,生命的例子就不好用,因為,生命這玩藝兒,要麼活,要麼死,一個子系統完了,大系統跟著完,一點妥協餘地沒有。然而在無機世界,在大自然中,在人類生活中,卻有這樣的系統,當它的某個子系統發生變化乃至壞死的時候,大系統不一定跟著死掉,而是有可能通過其他子系統的調整來適應這個變化,最終大系統演變為另一個系統後繼續生存。
例如,由村民、農田、牲畜三個子系統構成的一個村莊,村民役使牲畜耕種土地,種出農作物來養活村民和牲畜,村民和牲畜的糞便作為肥料施到土地裡,保持土地肥力。三個子系統功能耦合,構成村莊“活”的機理。再來看它“變”的機理。村民中開始有人闖外謀生計。這些本事人出去發了財,買了好東西回來,蓋上小樓,過上好日子,進而勾引著更多的人棄農外出闖天下,更多的農民變成了工人、商人、資本家。系統的嬗變先從村民這個子系統開始,然後延及其他兩個子系統,逐漸地,農田變成了道路廠房樓房,牲畜變成了汽車,最後,大系統的嬗變完成——村莊變成了市鎮。
顯然,與生命的情況不同,村莊並沒有因為其中某一個子系統的改變而死掉,而是先變促後變,後變適先變,小變帶大變,最後使得整個大系統變成了另一個系統。這恰恰就是人類歷史演變的原理,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系統史觀的原理——歷史的演變,不是縱向直線的,而是橫向互動的;不是由低級向高級的,而是由系統代系統的。前系統與後系統之間,原則上並無優劣之分,如果硬要分,則更大的可能是一個不如一個。
現在,我們從假定回到現實,把從這“村莊”的例子中歸結出來的系統演變的道理,“代入”真實的歷史。代入就是驗證,我們就選三個史例來驗證一下系統史觀。東周列國,近代歐洲,近代中國。
先說東周列國。我們都知道《三字經》裡有“八百載,最長久”一句,史家把這八百載分為前三百年後五百年兩段,兩段歷史的美醜形象大不一樣。前段,文武周公,制禮作樂,孔子“吾從周”,好世道;後五百年,即東周列國,有了亂臣賊子,孔子謂其“禮崩樂壞”。
從系統史觀看,周朝立國所建立的是這樣一種社會構造:井田制的經濟子系統,諸侯分封制的政治子系統,等級倫常觀念的文化子系統,等等。天子分封諸侯,諸侯應召勤王——這是政治子系統;農民“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孟子》),老老實實地耕種國家的井田——這是經濟子系統;維持著政治子系統和經濟子系統運轉的是文化子系統,即,君君臣臣、尊卑貴賤的倫常觀念,講禮、要臉、溫情脈脈的人情關係。政治上,諸侯為什麼聽話,因為講禮,要臉;經濟上,農民為什麼老實耕種,因為講禮,要臉。三個子系統如此功能耦合。
生活在今天“法制時代”的我們,可能會對這種社會構造感到不可思議——如果碰上那不講禮的、不要臉的怎麼辦?而周公時代的人對於今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可能也會感到不可思議——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人呢?那還是人嗎?
周朝社會大系統的“和平演變”正是從這個“疑點”開始的,從文化子系統開始的,從“禮崩樂壞”開始的,從“這樣的人”越來越多開始的,從人開始不是人了開始的。
僭越、逾禮、犯上作亂、家臣奪大夫的權、大夫奪國君的權、國君悖逆天子等等,成常事了,人開始不要臉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越來越多了,社會沒法繼續靠“天子——諸侯——大夫——家臣”一套倫常秩序來維持運轉了,霸道取代了王道,文化子系統出問題了。隨著文化子系統的壞死,政治子系統和經濟子系統的運轉自然也成問題了,不聽天子招呼的諸侯越來越多,不好好種井田的農民越來越多——大系統就玩不下去了。
於是,歷史面臨選擇,形成了兩派,儒家和法家。儒家主張“克己復禮”,把人心教育回去,把壞掉的文化子系統修復回去。法家則認為,人心已不能收拾,文化子系統已不可挽回,修復不了了,只有一個辦法:改革其他子系統,以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文化子系統。怎麼改?經濟上,廢除井田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同時,獎勵耕戰;政治上,對上,淡化周天子的權威,對下,鎮壓國內大夫、家臣作亂,從上下兩個方向把政治中心往諸侯國君層面收縮。
結果歷史選擇了法家。各諸侯國紛紛變法。“村莊”變成了“市鎮”,“周天下”變成了“戰國”。社會結構嬗變了。
文化子系統先變,先變促後變,後變適先變,小變帶大變,最後大系統變質——一個典型的社會系統演變的史例。
再來說第二個史例,近代歐洲。從十五世紀末地理大發現開始,歐洲發生了一系列巨大變化:大航海、大貿易、大掠奪、工業革命、民族國家、民族主義、頻繁戰爭、立憲政治、私人企業、自由市場、僱傭勞動、科學技術、啟蒙運動、宗教改革等等等等,巨變延宕了幾百年。顯然,這是一場系統性變遷,其經典學術稱呼是:封建社會變為資本主義社會。今天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和民間主流學界,都把這場巨變說成是個歷史大進步。
大變遷之前,西歐封建社會的構造,可以大略歸納為這樣幾個子系統:貴族等級制的政治子系統,土地采邑制的經濟子系統,基督教騎士精神的文化子系統,以及無休止打仗的國際環境子系統,等等。要探討此一構造是如何演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按照前面我們已經開闢出的思路,應當先找出啟動了這場大變的那個“先變”的子系統。如何找?從前面“村莊”和“東周列國”一假一真兩個例子中,我們已知道了竅門:它必須是一旦變了就再也回不去的那種子系統,只有這種無法修復、不可逆轉的“先變”,才能迫使其他子系統“後變適先變”,而最終引發整個大系統的嬗變。
歐洲思想史上,早就有人在找。浪漫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找到的是文化子系統。他們認為,是田園情調、騎士精神的喪失以及新興資產階級貪婪私欲的氾濫,導致了歐洲滑向了邪惡的資本主義社會。這些思想戰士持的是退步史觀,他們認為歷史是不斷墮落的,因此,負責任的歷史態度應當是把歷史往回堵,往回推,往回抗。他們是其時歐洲的“儒家”。
持進步史觀的馬克思,就是其時歐洲的“法家”了。馬克思找到的“先變”子系統是經濟,是工業革命——生產力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是它的發展,催著其他社會子系統相應地發生變化。馬克思的觀點是在對空想社會主義、浪漫主義的批判中產生的,是辯出來的,“真理越辯越明”,所以聽著挺有說服力——你即使有辦法把物欲橫流批倒批臭,即使人人都願意回到中世紀騎士時代,你也沒有辦法把生產力的發展堵回去,沒有辦法讓工業革命縮回去,而你只要承認了工業革命是不可逆轉的,則其他整個社會大變遷就都是不可逆轉的,必然的。馬克思的推論已經很具系統論的思維了。
筆者挑戰馬權威,找到的是“國際環境”——是歐洲日益加劇的國際生存競爭,導致了的歐洲社會結構的全面的歷史大變遷。
我之所以不同意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理由是:經濟子系統,在所有的子系統中,並不是最硬、最不可逆、最具決定性的。一紙法令就可以改變的經濟生活,怎麼能用來解釋大歷史之大必然性呢?
而我的國際爭鬥論,外部環境論,則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思維實驗來證明:假如當時的歐洲是一個統一的單一國家,也就是說,假如歐洲沒有國際爭鬥,沒有國際戰爭,歐洲近代史上所有這些歷史變遷都不會發生。歐洲近代史是鬥出來的!
在所有的社會子系統中,外部環境無疑是最具剛性、最不可修復、最不可逆的,單獨一個國家,誰都不能改變國際大勢,而只能面對它,接受它,並調整著自己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各個子系統去適應它。外部環境是“腳”,自己國家內部的各個社會子系統都是“鞋”;腳變了,鞋都得跟著變;單獨一個國家,你管不著腳的事,只能管好你自己的鞋。在巨大的國際競爭的壓力下,你必須搞工業革命,必須搞海外開發,必須到海外掠奪,必須搞民族國家,必須搞民族主義,必須搞科學技術,你必須團結起來,必須武裝起來,必須……,——正是國際競爭的日益加劇,催生了近代歐洲的一切。
國際環境決定論,不但能夠解釋歐洲近代史,也能解釋中國近代史。
從漢武帝到鴉片戰爭,兩千年,中國社會有著一個大致穩定的系統構造:儒學倫理為核心的文化子系統,自耕農業為主體的經濟子系統,中央集權的政治子系統。除了這三個軟性子系統,還有一些硬性子系統,例如,西高東低、大江大河的地勢特徵構成的地理子系統,再如,以長城為標誌的外部環境子系統。
鴉片戰爭,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一變而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還是那個問題:哪個是“先變”的那個啟動性子系統?與歐洲巨變時的複雜情況不同,中國的事,很清晰,這個子系統不難找,就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外部環境子系統,最具剛性,最不可逆,最無可奈何,中國近代史亦然。狼要來,當羊的沒法不讓它來,也就是說,這個子系統修復不了,我們再也不能回到以前的國際環境了。
說到外部環境,中國其實一直有外患,漠北有胡虜,東海有倭寇等等,但那都是以賤犯貴、以愚侵智的騷擾性力量,即使它騷擾進了北京城,騷擾進了紫禁城,那也只是騷擾,它不能改變“華夷之辨”的文化大倫理,更不能對我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構成根本威脅。而這次則不同,那是要從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全面地要我們命的。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
外部環境的惡化與中國本有的系統構造相結合、“狼來了”與“羊文化”相結合,推動著中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結構演變。政治子系統——朝廷還在,但已變成了“洋人的朝廷”;經濟子系統——主體上仍然是農耕經濟,但具有鮮明的買辦色彩的工商經濟也得到迅速發展;文化子系統——儒家傳統道德觀念還有殘餘,但懼洋、崇洋、媚外、民族自卑的意識也在迅速膨脹。
西狼東來,羊沒有選擇,然而,會不會被狼吃掉,卻不是絕對沒有選擇的。如果繼續保持羊性不變,就一定會被吃掉;如果把自己也變成狼,就不會被吃掉。結果,中國選擇了前者,日本選擇了後者。
“選擇”一詞可能會引起誤解,好像是說一個國家具有選擇自己歷史的自由意志,一國之歷史結局只是一念之差的結果。這裡的“選擇”不是這個意思。不是人在選擇,而是文化在選擇。中日歷史選擇的差異來自于其文化差異。日本人尚武,中國人尚文;日本哲學是民族主義,中國哲學是天下主義。這種文化差異是幾百年上千年歷史鑄成的。換句話說,日本選擇了做狼,是因為它有相應的文化資本;中國選擇了做羊,是因為中國沒有選擇做狼的文化資本。
所謂“狼”,簡單說其實就是四個字:民族國家。歷史已經千百次地證明,民族國家是團結性最強、最具國際競爭力的國家組織形式。就像國際爭鬥必然催生出坦克飛機一樣,國際爭鬥也必然催生出民族國家。民族國家之所以從近代歐洲興起,原因很簡單:歐洲是地球上的虎狼窩,這裡爭鬥最激烈。
這其實是歐洲的幸運。當建立民族國家的客觀要求擺到歷史的桌面上時,低頭一看,祖先已經把文化資源給準備好了;當國家呼喚狼性的時候,閉目返觀,先輩們用自己的鐵血歷史已經為子孫後代積聚了足夠的狼性基因。於是,歐洲狼群開始向世界進軍,地球上一個又一個的“羊圈”被開發了。
歐洲歷史上“民族主義開悟”的先驅是法國宰相黎塞留。三十年戰爭中,當其他參戰國都還在玩宗教的時候,他偷著玩起了民族,率領法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或者至少,作為一個帶著民族覺醒精神的國家,參與到了這場宗教戰爭中。結果,由此所顯現出來的競爭優勢,使法國把整個歐洲玩弄於了股掌之中。這次戰爭,啟動了歐洲的民族覺醒運動,嗣後的歐洲歷史上再也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國際間所有的戰爭都是民族戰爭了。
一個國家怎樣才算是一個民族國家?只有一個標誌:具有民族主義文化。
何謂民族主義文化?浸淫于每個國民骨子裡的尚武與愛國精神。
鑒定民族國家,“靈魂”特徵比“肉體”特徵重要得多。一個在“肉體”上看著很不像民族國家的國家,可能會因其有著精誠的民族主義靈魂而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國家,如今天的美國;一個在“肉體”上看著很像民族國家的國家,會因其沒有民族主義靈魂,而只是一個假民族國家,如今天的中國。
一個國家一旦具有了民族主義文化,一個國家一旦成為了民族國家,那麼,它內部一切子系統都會發生相應的演變。例如,人民的愛國精神必然推著國家政體向民選化演變——民既愛國,何不托之以國?“君主之箍”就是多餘的了。有了政治自由市場,經濟自由市場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進而,工業革命,私人企業,僱傭勞動,海上擴張,立憲政治,科學技術,……,等等,所有這些有利於提高國際爭鬥力的結構性要素,這些戰鬥性子系統,都會被歷史催生出來的。於是,那個被歷史進步主義者別有用心地冠以“現代性”的那種歷史構造,那個被稱作“資本主義”的大系統就產生了。資本主義,是列強們相互間鬥出來的,不是在生產力推動下自然發展出來的——馬克思是錯的。
明白了歐洲近代史的這些道理,近代中國的事情也就看明白了:面對狼來了,中國需要變成狼,即需要建立民族國家;建立民族國家需要民族主義文化,而中國沒有;中國沒有,是因為我們的祖先沒給我們留下相應的文化遺產——尚武精神與愛國精神。是幾千年尚文精神和天下主義,使中國成為了羊。我們天然是羊。
歷史走到了今天,中國實際上仍然生活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仍然背負著同樣的歷史矛盾——“狼來了”與“羊文化”的矛盾,仍然面對著同樣的歷史課題——民族主義文化補課。
阻止中國的民族覺醒,阻止中國的民族主義補課,把中國的命運在文化環節上一劍封喉——歷史進步主義就是這樣一把利劍——既然全人類有一個共同的光明前途,何必去“狹隘地”在乎一族一國之暫時的高下得失?
中國若突不破這文化阻擊戰的陣地,則在其他領域裡一切現代化的努力,都是白忙活。“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一個國家是狼還是羊,由它的文化決定,而文化是歷史鑄成的,一個國家不能靈機一動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文化,民族覺醒不是一念之間的事情,然而,“學術明白”卻可以是一念間的事情。我們不能在一念間把我們由羊文化變成狼文化,但我們卻可以在一念間就明白:二百年來我們倒霉是因為文化。
文化雖然不是靈機一動就可以改變的,卻也不是永遠不能改變的。世間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一個民族做出這樣的選擇:搞清自己的歷史病根,從而下定決心,從現在做起,一點一滴地、代複一代地為自身的文化改造、文化變革做持續的努力,從而逐漸地累積出建立民族國家所需要的文化資本。在這層意義上,我們永遠是有選擇的,何況,我們有著舉世無比的五千年文化資源。話說到這裡,這個《進步的幻覺》系列的結論,也就抖落出來了——用系統史觀替代進步史觀,用民族主義替代普世主義。
學術性替代,需多長時間才能變成文化性替代;學界的覺醒,需多長時間才能溶入國民的骨子裡而變成民族的真實性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一個國家民族覺醒道路上,如果其學界是最糊塗的一群,這個民族就死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