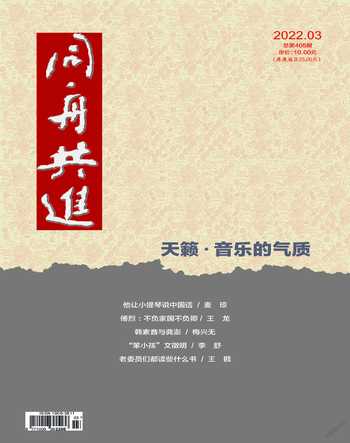老委员们都读些什么书
2022-04-04王戡
王戡
爱国将领是老一代全国政协委员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半生戎马、出生入死,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各有贡献。在外界看来,这些爱国将领委员作为赳赳武夫,自然追求赫赫战功,“上马击贼,下马露布”者并不常见。但若通过日记、回忆录深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发现他们对文学、对知识的渴求热烈而平和。
寒窗苦读、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这条看似简单的道路,自科举考试建立以来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政协老委员中的爱国将领们,普遍出生于清朝末年,成长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环境中,四书五经曾是他们最初的启蒙读物。
李济深和蔡廷锴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也同样是民国时代的粤军将领。前者曾任粤军第1师师长、北伐战争时的总参谋长兼第4军军长,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后者北伐时任第10师师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担任第19路军军长,后担任民革副主席。
两人家庭环境迥异,却有着类似的启蒙经历。李济深出身耕读世家,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廪生,他6岁前就随父亲、叔父读书,“日间所读之书,夜必令熟习背诵而后已”,十二三岁随塾师学习四书五经,16岁开始学作八股文,直到18岁时考入广州黄埔陆军中学。
蔡廷锴比李济深年少7岁,家道贫穷,他的父亲29岁时才娶到他的母亲,当时已经算是非常晚婚了。7岁时,父亲曾“很颓丧很苦楚似地”对蔡廷锴说,“人家有钱的,早就送去读书了,我家穷到如此,未能送你读书,或者过两年家中稍好的时候,送你读几年认识几个字”。直到9岁时,父亲才准备了“几支香烛、一本《三字经》、一管笔、一条小墨、一个墨砚、几张白纸”,把蔡廷锴送到了书馆。但只读了3年,刚读完四书,诗经学到一半,就因家境不济而再度失学,几经曲折当了兵。
有同样经历的爱国将领政协委员不在少数。张治中是国民党军上将,多年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抗战胜利后参加过多次国共谈判,1949年后担任过民革副主席、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对自己少年时的读书生涯评价不高,“我在私塾读书时受的是旧式的教育,至于学问是怎样,怎样应用到实际的人生,怎样与国家民族有关系,可以说根本谈不到……当时的私塾学生,不过是装满一肚子线装书的字句罢了”。
年少失学的蔡廷锴大概不会同意张治中的看法,他曾对海外华侨演讲,劝他们好好学习中文典籍,“中国现在虽是衰弱,但以往四五千年之文化歷史,何等灿烂,焉能数典忘祖,自毁家珍”。而张治中对读书的兴趣也是从线装书开始的,离开家到商号做学徒时,他在做工之余对各种书籍“到手就看,手不释卷”,最喜欢的是清代学者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
出身湘军,北伐战争后期曾任第6军军长,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李明灏总结,“我少年时,读了一些老书……继而读高小和中学时期爱看英雄侠义小说,崇拜个人英雄”。
这也是很多爱国将领委员的心路历程。蔡廷锴说,自己失学之后喜欢读《三国志》,看起来似乎是指《三国演义》,这本书对他带兵打仗和个人做派影响不小。桂系领袖之一、后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绍竑同样如此。20世纪20年代,他看到一支云南部队每名士兵都带着步枪和烟枪,还带着一盏烟灯,“在黑夜行军的时候,活像一个提灯队,行列漫长”,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少年时所看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不想,书中手持双枪的清代绿营,在现实中仍然存在。
私塾的课程千篇一律,新式学校则海纳百川,军事院校也不例外。特别是军校招考来自各地的学生,也让各种思潮得以传播发扬。很多爱国将领委员便是在军校时第一次阅读到了催生革命意识的书籍。
老一辈的爱国将领委员多是在晚清时代入读军校的,最初触动他们心弦的,多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一类宣扬清初满军暴行的小册子,继而深入到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反而多来自《民报》上的零散篇章和口耳相传的精神教育。湘军领袖、辛亥革命元老,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的程潜,以及粤军将领,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陈铭枢,都有这样的阅读经历。
与他们相比,后一辈的爱国将领委员们有更系统化的革命思想阅读体验。对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期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侯镜如、宋希濂等而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令他们记忆犹新。对杜聿明、郑洞国等政协委员而言,这些书籍的内容也并不陌生,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已经将《共产主义ABC》的内容编入了军校的政治讲义当中。
相比之下,夹在辛亥革命一代与国民革命一代之间的保定军校生们,在校阅读经历要单调得多。北洋政府禁止保定军校生阅读“小说闲书”,只有《三国演义》因为可以激励忠义而特许豁免,至于革命书报更在严查之列。同样,从陆军小学到保定军校,整套教学体系中,仍然以传统文学教育为主。黄绍竑回忆,他在陆军小学读书时,国文第一篇是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陆军中学时则是庄子的《秋水》。
这对同样就读于保定军校的张治中来说并不算什么。他早就已经深深沉浸于阅读经典的快乐当中,“我尤其喜欢读古人或名人的关于修养方面的书,如《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群学肄言》《菜根谭》《自助论》等书,都喜欢看;此外如发明家、思想家的传记,《宋儒学案》《中国历代名臣言行录》《饮冰室文集》等,也都涉猎过”。
对于读书成痴的张治中而言,军校的标准读物“典范令”——各科(步兵、骑兵、炮兵……)操典、各种(射击、筑城、交通……)教范以及阵中要务令,同样要精熟。“肄业期间,两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利用暑假,遍阅军事参考图籍。譬如,一部《阵中要务令详解》十厚本,以及《作战纲要详解》七本,都读完了。”
黄绍竑也是如此,他“不但对学校所定课程,精心研究,即当时出版之此类书籍,我都浏览殆遍。我对战术战略课程,不是分数主义,而是问难主义。有时教官被我弄得很为难”。未来雄踞广西的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此时已经有枭雄的姿态了。
“成年人没时间读书”是社会的焦虑话题,但回溯爱国将领委员们的日记、回忆录,会发现这是穿越时代的通病。他们对少年时摇头晃脑背诵的古文经典、青年时的一接触便心潮澎湃的革命著作记录得颇为详细,但当走进军营、迈上沙场,提到读书的人便微乎其微。即便仍在读书的人,口味和兴趣也指向了不同分野。
进入中年后,黄绍竑回忆中只提到过一次读书。1933年,他奉命去宣慰蒙古王公,在归绥遇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后者给他送了两本自己的著作《我的探险生涯》和《万里长征记》。黄绍竑翻阅《我的探险生涯》后,盛赞“虽然内容大多数是记述在雪山或是沙漠中极干枯寂寞的生活,却写得十分有趣,处处引人入胜,使读者不忍释手,好像自己亲历其境一般”,读完兩本书后,甚至激发了前往新疆的念头。这份狂热的反应,与今天多年不深度阅读,突然遇到一本好书的人无二。
也有人保持了传统的读书习惯。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高树勋,每天都把阅读《左传》《史记》等历史典籍作为功课。《鲁迅全集》出版后,他还专门买了一套。高树勋的女儿回忆,“他每读书都把他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的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对照理解”。
还有人通过读书找到了自己在军事生涯之外的寄托。陈铭枢在青年时读过谭嗣同的《仁学》,对其中关于佛教的阐述印象颇深,并从中选取了“真如”二字作为他的别号。1922年,已经担任团长的陈铭枢对广东局势失望,到南京追随欧阳竟无学习佛学,同时广泛接触各种学术思潮、阅读各类书籍杂志,如张君励的新儒学论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多年后,他总结自己“我从小是读线装书长大的,深受儒家封建思想陶冶,继又学佛习禅宗,把大乘教奉为圭臬,因它同我的政治生活并无矛盾,且为我不受任何约束的习尚找到了理论基础”。
话虽如此,1930年,陈铭枢接办出版社“神州国光社”后,大量出版了各类政治学、哲学著作,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以及河上肇的《通俗剩余价值论》等,并没有以自己的阅读兴趣限制出版社的运作。
张治中的读书经历则是另外一个样板。五四运动前后,他的思想受到《新青年》《新潮》《向导》等杂志很大影响,他甚至去找陈独秀谈了一次话,听过瞿秋白的演讲。在广州黄埔军校当教官期间,他更是与学生一起追求进步。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随后出版成书。当年夏天,李济深读到了《论联合政府》,立即提笔写信介绍给陈铭枢等人阅读。1945年底,起义后的高树勋读到《论联合政府》与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感叹“其中人民战争之一章,于今日始深切领会其涵义”。
毛泽东著作的忠实读者中,有不少爱国将领政协委员的身影。李明灏之子回忆,其父年届八旬时,仍以病弱之躯坚持学习《毛泽东选集》,留下来的学习笔记“蝇头小楷,字迹工整,一丝不苟”。
1949年后,张治中同样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同时对其它著作保持极高的阅读兴趣。1958年,郭沫若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在《人民文学》杂志进行连载,很快进入了张治中的阅读视野。《洪波曲》第十五章涉及长沙大火的内容,对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颇不客气。张治中看到后,在1959年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指出“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在叙述完自己的看法后,又说,“至于您是不是应该在《人民文学》上作一个更正,又如印单行本时是不是应该删改,这就听您的善意斟酌了”。双方几番书信往来,郭沫若不愿意删改文字,张治中也坚持己见,直到惊动了周恩来,做通了双方的工作,才让《洪波曲》在略作修改后以单行本问世。这样因为读书引发的争论,在爱国将领老委员身上也不多见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