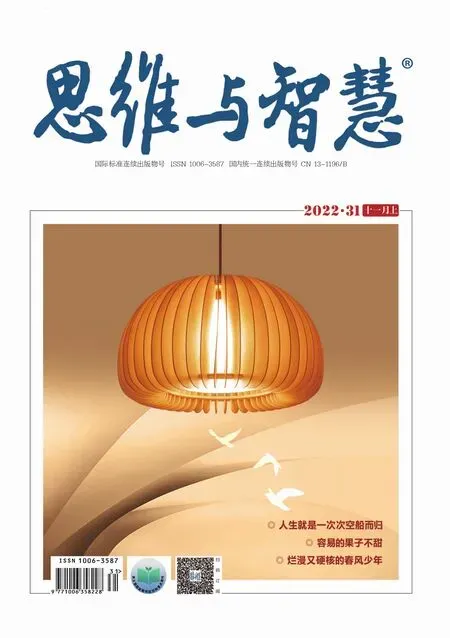烂漫又硬核的春风少年
2022-04-02张云广
◎ 张云广
不管岁月远逝多少年,我都会把那段童年的多彩时光称之为少年。
少年的双手拉开加了石子的弹弓。
村南村北,村东村西,村庄的鸟雀都对我们印象深刻,人不用走近,鸟就已经惊得展翅而逃。那时候,我们自称为游侠,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绰号。我们知道鸟雀的每一处集聚地,也知道它们在哪里度过整个夜晚。有时候,我们也会“不务正业”一次,把在巷子里流浪的鸡鸭当作练习枪法的移动靶位,于是鸭飞入院,于是“一地鸡毛”。
少年的双脚踩在青砖瓦房的房顶后檐上。
前空翻或者后空翻,动作要领不尽相同,秀的却都是勇敢。后墙根是新堆成垛的连绵麦秸,厚实而松软。并肩成排,号令响,人起跳。不跳的是懦夫,稍有迟疑者也会被扣上“胆小鬼”的帽子。这顶帽子,没人愿戴。
少年的目光锁定在高挂于老槐枝上的蜂巢。
蜂巢大如葵花盘,外有强悍的黄蜂张牙舞爪地在担当警卫,但这绝不会让英雄的少年望而却步。一根长长的竹竿,一头扎好了破布,浇上从家中偷来的用于夜间点灯的煤油。一根火柴划过,火势一下子旺起来,把竹竿握住,与蜂巢准确无误地进行空中对接。愤怒的黄蜂倾巢出动,在我们的头顶和四周盘旋。穿着自制防护服的我们迅速作战术性后退,等待与之进行下一个回合大战的时机。
少年的耳朵在草间搜集蝈蝈藏身处的情报。
脚步向高而密的草丛深处挪移,像猫科动物那样小心地接近目标。蝈蝈的鸣叫声突然间消失,少年蹲在一片扎人的尖草里,小虫爬上了额头也绝不动身分毫。放松警惕、再次鸣唱的蝈蝈暴露了自己潜伏的位置,少年瞅准机会闪电出击,起身看时,一位绿色小歌唱家已经赫然在手。
少年的脑袋露在小河沟的水面上。
狗刨,仰泳,潜泳,自由泳,花样不断在翻新中。盛夏酷热难耐,自有清凉透顶,惹得河岸高柳上的蝉羡慕得嘶叫不停。河水清且涟猗,阿中逮住了一条小虾,阿祥捉住了一只小蟹。阿超一个猛子扎下去,嘴中满是水草和泥沙。
少年的嘴巴吹着没有节奏感的柳笛。
春风送暖枝条新,我们抓住了杨柳发芽时这全年唯一的一段树皮松动的时光。折下一段杨枝或者柳枝,转动使其离皮,咬住粗的一头用力一抽,笛管已经做成。再用小刀切成恰到好处的一段,择其一头,削去一小截的外皮,一个春笛便有了抒情的魂魄。但我们只用来抒豪情和快意,袅袅笛声里没有青春的感伤,更没有历经沧桑的凄凉。柳笛吹在上学的路上,吹在回家的路上,也躺在教室里的铅笔盒中。自习课上,阿亮忍不住拿出来试了一下调调,瞬间便吸引来全班的目光,幸亏没有老师在场。
少年的臂膀甩在黄昏回家的路上。
从校门口到家门口的路线,用一个个四角包的移动曲线来串联。凝神,用力,只为把对方的四角包掀翻。这是力量的比拼,更是技巧的展现。口袋里的四角包变薄又变厚,变厚又变薄,人生战场的胜负提前以这样的方式上演。唯有好男儿,才能打得赢又输得起。
简单的快乐,清纯的诗意。当我正在为回忆竟然如此快乐且诗意而感到困惑之际,我从孙犁先生的一篇散文中找到了答案。他说:“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成年以后的欢乐,则常带有种种限制。例如说:寻欢取乐,强作欢笑,甚至以苦为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