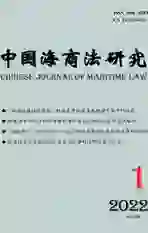《民法典》下合同对第三人效力规则在船舶优先权制度中的优化适用
2022-04-02李志文柴芳玲
李志文 柴芳玲
摘要:船舶优先权作为《海商法》特有的一种担保物权类型,其转让与代位规则的行使存在着理论争议。《民法典》下合同对第三人效力规则的完善,尤其是第三人代为清偿法律地位的明确,为船舶优先权的行使开拓了新路径,松动了某些特定的船舶优先权绝对禁止转让模式。然而,当前第三人代为清偿规则在船舶优先权制度中的相关规则运用及法律适用还存在不协调之处,人身属性海事请求权的转让与代位直接牵动着船舶优先权的行使。鉴于此,有必要从规则识别转向制度关联,在遵循《民法典》基本价值理念的同时,注重《海商法》规则的内生动力,从制度、理论及实践层面协调《民法典》和《海商法》之间的适用冲突,以在制度框架内实现二者的优化适用。
关键词:第三人代为清偿;船舶优先权转让与代位;规则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2)01-0060-08
Abstract:Maritime liens, as a unique type of security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have persistent theoretical disputes over the exercise of the rules on its transfer and subrog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ule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tracts to the third party in the Civil Code, especially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third party paying off on behalf of others,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the exercise of maritime liens and loosened the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the transfer of some specific maritime lien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inconsistencies when the rules of the third party paying off on behalf of others are applied in the system of maritime liens, and the transfer and subrogation of personal maritime claims directly affect the exercise of maritime liens.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from rule identification to system association, while following the basic values of the Civil Code, pay attention to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and coordinate the application conflicts between the Civil Code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from the institution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optimal application of the two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Key words:the third party paying off on behalf of others;transfer and subrogation of maritime liens;application of rules
一、问题的提出
船舶优先权在中国立法和理论上被定位为船舶担保物权,它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簡称《海商法》)所规定的特定海事请求权。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五类海事请求都具有或部分具有财产属性,属于债权请求权范畴。在发生第三人垫付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相关费用的情况下,第三人因此介入海事请求权人与债务人(包括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人)之间的海事债权债务关系,由此涉及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出台之前,理论界曾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4条、第65条视为合同对第三人效力规则的原型,并就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形成了利他契约说、交付说、利益第三人合同说等诸多学说,其中最鲜明的争议在于第三人代为清偿能否成为合同对第三人效力规则的应然范畴。[1]而《民法典》赋予了第三人代为清偿以正式法律地位,并在第524条规定了具体行使规则和法律效果,回应了学理上的这一分歧,并为该规则在《海商法》船舶优先权制度中的适用提供了思路。鉴于第三人代为清偿规则与船舶优先权制度在体系上存在着一般与特殊规则的适用差别,故而需要准确厘清两种规则之间适用的衔接关系及在衔接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寻求优化途径予以协调。
二、合同对第三人效力规则在船舶优先权制度中适用的规范关联
合同对第三人效力规则属于《民法典》合同编的调整范畴,而船舶优先权则专属于《海商法》船舶物权的规范范畴,二者看似呈现物债两种不同的状态,实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债权外部化之合同对第三人效力
《民法典》下合同对第三人效力规则主要集中于对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和第三人代为清偿,而在对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与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并未受到实质影响,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合同效力不及于外部第三人。相反,《民法典》第524条所规定的第三人代为清偿规则存在行为和结果上的债权外部化效力,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第三人产生了法律约束力。从行为效力角度来看,第三人代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行为是基于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的合法利益关系,或因第三人自愿清偿,[2]或因债务加入或其他合法事由,此时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与合同履行利益之间产生了实质关联性,第三人对自己的履行瑕疵需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从法律效果来看,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后产生的是外部债权让与的法律效果,即第三人代替原债权人的地位而成為新的债权人,原债权债务关系开始对新债权人产生合同约束效力。因此,债权外部化特征贯穿于第三人代为清偿规则行使的整个过程,对第三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也成为它区别于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之所在。
(二)物权债权化之船舶优先权
物权债权化是指某些物权本身的特征有所弱化,转而呈现出债权的属性,常见的物权债权化包括登记对抗主义下未登记的物权、具有债权属性的担保物权等。[3]《海商法》第22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是一种发挥担保功能的优先受偿权,从体系上看,其与船舶所有权、船舶抵押权共处一章,共同形成特殊动产船舶的物权体系,因此船舶优先权的上位概念仍是物权。但不可否认的是,船舶优先权不可离开海事请求权而单独存在,其为船舶优先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的担保,因此,船舶优先权本身的物权属性有所弱化。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五类海事请求中,工资、劳动报酬等给付请求及人身伤亡赔偿请求本身带有一定的人身属性,但对该类海事请求的救济措施都指向了债权请求权。除此之外的其他三类(包括港口规费、海难救助款项及侵权财产损害赔偿)均属于财产性的债权请求权,自不待言。通过分析不难发现,附随于海事请求而存在的船舶优先权具有物权债权化的共通之处。
(三)第三人代为清偿规则与船舶优先权的内在同一与外在差异
第三人代为清偿与船舶优先权虽属不同领域的制度,但因《民法典》与《海商法》之间的关系而使二者在具体运用中产生了联系,这一关联性主要体现为功能、目的和行使规则具有同一性。
第一,二者功能相同。第三人代为清偿看似属于债务履行的分支,实则发挥着担保功能,第三人本不属于合同之债的当事人,但当其代替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后,便具有了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海事请求权与船舶优先权为主从关系,船舶优先权的从属性及优先受偿性决定了其所发挥的是担保物权的功能。
第二,二者目的相同。第三人代为清偿是基于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法利益关系,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以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如期实现;船舶优先权的目的是在债务人未按照约定或法律规定履行债务时,凭借该担保性权利实现特定海事请求权。因此,二者的目的均为保障债权的实现。
第三,二者行使规则相同。第三人代为清偿债务会发生债权让与的法律效果,受让债权的第三人享有代位权。同样,第三人代为垫付由船舶优先权担保的特定海事请求相关费用后,即发生海事请求权转移的效果,作为从权利的船舶优先权也随之转移,受让海事债权及船舶优先权的第三人即可依此向债务人行使代位权。
当然,第三人代为清偿与船舶优先权制度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如在行为主体上,第三人代为清偿的主体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船舶优先权的行使主体包括海事请求权人;在权利属性上,第三人代为清偿属于债权范畴,而船舶优先权本身属于担保物权范畴,但在其发挥担保功能时,也显示出一定的物权债权化特征等。可见,二者之间的差异仅为形式意义上的区分,不足以影响第三人代为清偿规则与船舶优先权制度的内在联系。
三、第三人代为清偿规则与船舶优先权制度之间适用的衔接关系
《民法典》对第三人代为清偿规则的确认,为《海商法》船舶优先权的行使奠定了理论根基,二者从清偿债务行为到债权转让及代位规则的衔接与融合,破除了担保人身属性债权的船舶优先权绝对禁止转让的限制。
(一)识别依据:船舶优先权制度中第三人垫付费用的行为属于第三人代为清偿
第三人垫付费用的情形不仅存在于民事领域,在航运领域中也较为常见。在《海商法》第22条所设定的五类海事请求中,海事请求权人主张由债务人或侵权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而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此时第三人的介入恰巧能够打破僵局。由此,需要对该第三人垫付费用行为的性质加以准确认定,并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则予以规制。
中国海事理论界对于第三人垫付费用行为的性质认定莫衷一是,存在着债权转让、债务承担、债的概括承受等不同观点。[4]4-6笔者认为,在识别第三人垫付费用行为的性质时,不应仅以行为本身作为单一判断标准,还应该从第三人与原债权债务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债权债务对第三人的效力角度出发,寻求第三人垫付费用行为的合法依据。而《民法典》所确认的第三人代为清偿能够在前提基础、规则效力上与第三人垫付费用的行为保持高度一致性,第三人垫付费用行为由此成为第三人代为清偿在海事领域的具体应用。
第一,合法利益关系是第三人垫付费用行为的成因。第三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往往是出于对二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合法原因的考量,以使债务人摆脱债务缠身的困扰。而海事领域中第三人代为垫付费用时也存在着此种考虑,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允许第三人垫付费用的实质性前提是第三人与海事债务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利益关系,第三人对债务的履行,也是为了促使其与债务人另一关联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履行,从而为了避免共同利益受损而为的垫付行为。例如在航运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船方因经营不景气无力向船员支付工资,而由承租人代替船方向船员支付工资的情形。[5]据此,第三人垫付费用行为涉及船舶优先权人权益转让时,第三人与海事债务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合法与否成为影响海事债权人权益实现的核心因素。
第二,原海事请求权的基础关系对垫付费用的第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此处所指的海事请求权基础关系是指在船舶优先权担保之下存在于海事请求人与债务人或侵权人之间的违约或侵权法律关系,这是海事请求权发生的基础原因。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及侵权责任规则的限制,原海事请求权基础关系原则上对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但是在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受该请求权基础关系影响时,可对其产生相应的约束力。同样,第三人本不是《海商法》第22条所确定的海事请求的直接当事人,其代替海事债务人或侵权人偿还债务或支付赔偿的行为也非加入债务人的行列,而是作为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承担债务的履行。第三人代为清偿债务的行为直接影响债权的实现,此时原债权债务关系当然对其产生约束力,这也是第三人代为清偿原有样态在海事请求中的具体展现。
(二)规则承接: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依附于第三人代为清偿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权分为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具有财产属性之债与具有人身属性之债。根据《民法典》物权编及《海商法》第21条的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是主债权债务关系,这里的债权债务能否包含具有人身属性之债在内,还有待商榷。但是,按照《海商法》第22条所确定的标准,船舶优先权担保的五类特定之债并未作前述债权性质上的具体区分,由此,在第三人代为垫付费用之后,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也应遵循主债权的可流通性,同时需要明确的是此种债的转让是海事请求权的转让而非债务承担。
第一,第三人代为清偿债务后发生债权让与后果。债权让与是在不改变债的内容的前提下,债权人将其债权转移给第三人享有的一种债的变更类型。第三人代为清偿的后果可以从债权让与的定义中抽练出两方面的内涵。其一,第三人代为清偿因债权让与而实现了原债权人的债权。债权让与仅改变债的主体,因此海事请求权人受领第三人的清偿仅实现的是自己在海事债权债务中所应取得的债权。反之,若以第三人清偿债务为由直接确定原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无疑是容忍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行为,容易滋生不诚信行为,同时第三人的权益保护也会陷入困境。其二,第三人因受让海事请求权而取代了原债权人的地位。原海事请求人的债权实现后,清偿债务的第三人即可依照《民法典》第524条第2款之规定受让原海事请求权,包括权利之上存在的瑕疵、从权利等,自此第三人当然取代了原海事请求人的地位,并成为新的债权人。可见,第三人代为清偿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海事请求吸收了《民法典》第524条第2款关于债权让与的特定规则,同时在让与目的上更加突出海事权益保护的特色。
第二,船舶优先权随债权的转让而发生相应的转移效果。担保财产属性债权的船舶优先权具有当然的流通性,而担保人身属性债权的船舶优先权因受到主海事债权请求权性质的影响,在理论规则运用上屡受重创,由此担保人身属性债权的船舶优先权能否转让成为理论争议的焦点所在,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垫付费用与优先权分离说”认为垫付费用并不能发生船舶优先权的转让,[6]这看似为海事请求权人的利益实现确立了双重保障,但对第三人而言,却缺乏了垫付费用的动力,实际上并不利于对海事债权人的保护。第二阶段的“有偿转让说”将船舶优先权担保的具有人身属性的债权转让作为特殊情形予以认定,代垫费用的第三人只有附加有偿条件才能受让海事请求权。[4]7如此一来,原债权人的债权即会出现二次受偿问题,增加了第三人的负担,对第三人极度不公平。第三阶段的“新债权债务产生说”另辟蹊径,[7]巧妙地化解了具有人身属性债权在《民法典》与《海商法》之间的适用冲突,但也直接回避了这一难题的解决,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略显薄弱。
由此可以看出,学界多将船舶优先权的转让放在某个单独的规则中予以分析,忽略了债权转让一般规则与船舶优先权转让目的的联系及海事审判实践对船舶优先权转让理论的导向作用。如“海隆公司诉荣耀公司船舶优先权纠纷案”“利比里亚籍‘奥维乐蒙’轮船员劳务合同糾纷系列案”“梁某某等诉钻石国际邮轮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等典型案例中,裁判结果均认可垫付费用的第三人可以基于债权转让就债务人的船舶享有船舶优先权。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规定》)第9条专门规定了船员工资、劳动报酬等人身债权的可转让规则。出于司法解释及海事审判实践的回应,人身伤亡赔偿的海事请求权转让也应当与工资、劳动报酬等人身债权及其他三类财产债权的转让保持规则适用上的一致性。
(三)效果转换:第三人行使代位的效力及于船舶优先权
在船舶优先权发挥担保物权功能的情况下,因主海事请求权的转让,从权利也附带转让,故而垫付费用的第三人取得代位是船舶优先权转让的应然结果。
第一,第三人垫付费用后取得的是债权代位。债权代位的行使规则有别于求偿权:在权利性质上,债权代位是在债权转移的情况下,第三人承受原海事债权的效果,而求偿权是基于原债权的实现而产生的存在于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新债权;在法律效果上,第三人垫付费用后代位行使的船舶优先权因海事请求权的转让而一并转让,此时当事人之间存在主债和担保双重法律关系,而求偿权则通常只存在于主债权债务关系之中,无担保可言。《海商法》中第三人垫付费用后取得的应该是债权代位权,而非求偿权,此时债权代位权是基于第三人垫付费用的清偿行为而发生。在比较法上,就清偿有正当利益者,因其清偿而当然代位债权人的债权,此为法定清偿代位;对债的履行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代为清偿者,在其清偿之限度内承受债权人的权利,但不得有害于债权人之利益,此为约定清偿代位。《民法典》第524条将第三人代为清偿的情形规定为法定清偿代位,并将第三人对债务履行具有合法利益和债权让与作为衡量法定清偿代位的条件。《海商法》中为海事请求权人垫付费用的第三人代位行使原海事请求权人的权利,属于行使代位权的情形。虽然《海商法》未对清偿之后的代位问题加以明确,但是从《民法典》第524条的一般规定中可以解释出,海事债权人与垫付费用第三人之间债权让与关系发生之时,也伴随着代位的发生,债权让与的效力经向债务人通知而发生约束债务人的效果。
第二,船舶优先权的代位是海事请求权效力扩张的结果。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债权人代位权是债权效力之一种,以债权存在为前提,[8]此种解释不无道理。无论是清偿代位还是债权人代位权,均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将债权的效力扩大及于第三人。而在存在债权担保时,基于主债权与从权利之间的依附关系,第三人行使从权利是主债权效力扩大的表现。英国和美国的判例都承认船舶优先权的代位,但是在英国,第三人自愿垫付款项后就船舶优先权的享有存在着限制,即垫付行为须获得法院的认可。[9]《涉船员纠紛案件若干规定》规定了垫付船员工资、劳动报酬等费用的第三人可以请求确认受让的海事请求权或行使船舶优先权,此种确认和行使的合法依据来自于海事请求权或船舶优先权背后所隐藏的清偿代位。当垫付费用的第三人以受让债权为由向债务人主张债的履行时,海事债权的效力直接扩及船舶优先权的代位范畴之列,即垫付费用的第三人代位行使主债权时,也伴以船舶优先权的随之代位。
在海事债权难以实现时,第三人可因代位取得船舶优先权而优先受偿,由此提高第三人垫付相关海事费用的积极性。
四、第三人代为清偿与船舶优先权制度之间的规则适用之冲突 船舶优先权是《海商法》专有规则,因船员工资、劳动报酬等债权,人身损害赔偿及港口规费海事请求权在性质上不同于海难救助及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故而出现第三人垫付费用情形时,此三类海事债权与民事规则衔接过程中难免出现不协调之处。
(一)第三人代为清偿后与其代位行使船舶优先权的范围上存在着不协调之处
垫付相关海事费用的第三人代位行使船舶优先权的范围应当以其实际垫付的数额为准,在此范围内才具有合理性。由于《民法典》第524条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造成实务中有的第三人以要求海事请求权人放弃一定范围的海事请求为前提进行垫付和代为清偿,其后通过债权和船舶优先权的转让和代位,主张全部海事债权。而在船员外派中也存在着不规范的认知和操作。通常船员劳务外派的情形下,由船员雇佣单位向船员外派机构支付佣金和船员工资,再由外派机构将工资支付给船员。[10]但某些外派公司在先行支付船员工资后,采取鱼目混珠的手段,将自身应得的佣金混同于船员工资,以一揽子请求的方式主张船舶优先权,从而谋取法定权利之外的特殊利益。[11]由于《海商法》未对该类行为予以明确的效力规则,在实践中存在着海事法院默许船员外派企业请求工资支付及行使船舶优先权的情形,导致第三人将不属于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普通债权纳入了船舶优先权的适用范围,并通过代位行使船舶优先权而优先实现了债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船舶优先权人的利益。可见,第三人代为清偿后,对代位行使债权及船舶优先权范围的模糊认识助长了第三人对船舶优先权的肆意使用,也为其在法律灰色地带寻求了可乘之机。
(二)人身债权转让规则发生适用上的冲突
对于船舶优先权担保的具有人身属性的海事债权能否转让,此前海商法学界多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2条,直接否定了人身损害赔偿、工资、劳动报酬等债权的可转让性。而《民法典》对可转让债权的范畴作了概括性规定,既未明确列举也未完全限定,由此工资、劳动报酬等费用及人身损害赔偿的海事请求能否转让无法找到直接对应的法律条文。在长期的交易活动中,人们默认了此等海事请求权的人身属性,依据不可转让的债权性质予以处理。然而在一些第三人代为清偿相关费用的情况下,船舶优先权的转让和代位日趋缓和,不再绝对地被否认。这种认识和处理的方式,除考虑海事请求权本身的性质外,还侧重利用船舶优先权平衡海事请求权人、债务人及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对同一性质的债权转让采取不同处理方式的问题,导致了债权转让规则适用上的混乱。
(三)港口规费海事请求及附随的船舶优先权代位规则尚不明晰
关于港口规费请求之下的船舶优先权代位困境集中在其行政行为的属性上,理论上认为港口规费的收取主体为行政机关,即使第三人垫付缴纳费用也不能代位行使行政机关的职权。《海商法》就代位问题只字未提,对此完全遵循《民法典》中的代位权规则予以处理恐有不妥。如果第三人垫付费用后无法就清偿的债权予以追偿,也无法获得船舶优先权的担保,那么第三人规则的运用效果会大打折扣,不仅会影响第三人积极性,而且也会使海事请求权人再次陷入债权无法实现的困境。在司法案件审判过程中对此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江门市中新拆船钢铁有限公司诉庆达海运有限公司海事债权确权纠纷案”与“华亚海运公司与五星福建船务有限公司船舶租用合同纠纷案”针对垫付费用的第三人代位行使港口规费的船舶优先权问题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认定。由此可见,港口规费所附带的船舶优先权究竟能否代位行使的问题暂时只停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探讨,无法寻求到直接相关的法律依据。
五、第三人代为清偿对船舶优先权制度优化适用的协调进路
第三人代为清偿与船舶优先权在债的转让及代位规则上有其融合之处,但是在规则衔接运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困境,因此应当在正确处理好《民法典》与《海商法》关系的基础上,作好具体规则之间的协调,尤其是关于垫付费用第三人在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与代位问题上的优化配置。
(一)制度层面:以《海商法》规则为核心,以相关司法解释及《民法典》规则为补充
《海商法》自1993年实施至今未曾修改,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诸多规则已然无法解决理论层面的争议及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故而转向适用《民法典》中的具体规定,但海商法领域的特殊性,又反衬出《民法典》中某些规定无法全盘适用的问题。因此需要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以相应的司法解释作为具体规则的补充加以适用。
1.厘清《民法典》与《海商法》之间的关系
《海商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中,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案)〉的说明》中也明确指出该法属于特别的民事法律。[12]因而,现行《民法典》与《海商法》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二者在体系地位与价值理念上具有共通性。[13]但是这种认识仅是站在整体层面的概括认定,细化到具体规则适用中可以发现,诸如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与代位若全然适用《民法典》中的一般规则,会与自愿、公平理念相悖。因此,理应保持《海商法》规则的特殊之处。
处理船舶优先权这类特殊问题时,应当加强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的双重协调。其一,在价值理念上,与《民法典》基本价值理念保持一致,但是在此之外还应允许《海商法》扩充利益保护的范围,例如对垫付费用的第三人及其他相關人的利益均应加以考虑。其二,在具体规范上,应当先适用《海商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范,无法律规定时,还应当考虑适当参照海事惯例,而后再适用《民法典》中的一般规定。201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简称《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2.19条、第2.23条对船舶优先权原有的制度设计作了些许调整,涉及了船舶优先权的转让和代位问题,如将第27条所规定的海事请求权“转移”修改为“发生转让或代位”,明确了船舶优先权的适用范围,增加了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方式,这意味着船舶优先权的转让及代位规则应当优先遵循《海商法》的特别规定,对于不明确之处可以结合《民法典》中的一般规定予以解决。
2.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填补船舶优先权转让与代位规则空缺
船舶优先权虽作为海商法中的船舶物权制度,但却被视为《民法典》物权制度中的另类。因《海商法》的模糊规定招致了船舶优先权性质认定之争,还引发了转让与代位不确定的连贯效应。即便《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承认了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与代位,但未对其具体规则予以明确界定,由此人身属性海事请求之下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与代位又再次陷入《民法典》一般规则的迷局之中,为此实有必要为船舶优先权的适用建立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鉴于《海商法》的修订需协调《民法典》及相关法的体系模式,保持二者之间的互塑性,[14]避免条文及具体规定之间的重复,因此,关于船舶优先权的细化规则可以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补充。《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规定》已对第三人垫付船员工资、劳动报酬等费用后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与代位问题进行了相应规定,后续应当重点结合船舶优先权的设立目的及基本规则,对人身损害赔偿、港口规费等海事请求及船舶优先权的转让和代位担保内容加以明确,尤其要将该规则与《民法典》债权人代位权相区别,以避免其与债权人代位权之间的混用,引发不必要的法律适用纠纷。
(二)理论层面:以可转让与代位为原则,不可转让与代位为例外
《民法典》在确定债权让与及代位规则时设定了一般与特殊规定,即债权可以转让或代位,但存在除外情形。而在《海商法》中从未出现类似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海商规则中可以在条文基础之上采用意思自治的方式确立同等规则,以实现《海商法》与《民法典》在船舶优先权适用上的协调。
1.回归《海商法》第27条寻找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依据
《海商法》第27条规定船舶优先权从属于海事请求权,并随海事请求权的转移而转移。可见,债权与债权请求权是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所作的分类,具体而言债权是请求权的类型之一,[15]而海事请求权与债权本身存在些许差异,债权注重债本身的性质、存在与否,为静态意义上的概念;而海事请求权侧重于债的变更、消灭等过程,为动态意义上的概念。第三人未介入海事请求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海事债权债务关系时,海事请求权人享有的是债权及债权请求权;而第三人垫付费用之后,原本由海事请求权人享有的债权消灭,但债权请求权依然存在。此外,《民法典》债权让与中所禁止转让的是债权而非债权请求权,因此不宜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及船员工资、劳动报酬等费用给付的海事请求权及船舶优先权具有当然的不可转让性。从《海商法》第27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海事请求权的转移是不区分人身属性或财产属性的,《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也继续坚持《海商法》的现有规定,故而理论界关于不可转让的人身专属性债权争论在船舶优先权制度之下并不存在特例,而人身损害赔偿、船员工资、劳动报酬等海事请求不具有《民法典》意义上的人身属性,属于《海商法》的一般规则,应当适用第27条的规定,认可五类船舶优先权的可转让性。
2.以约定代位或任意代位的方式化解船舶优先权代位困境
为保护垫付人对其所垫付的费用的追偿权,约定代位或任意代位的合法存在可以弥补《海商法》在船舶优先权代位制度上的空缺。以约定代位或任意代位的方式破解船舶优先权代位之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优化《民法典》第三人清偿代位规则与《海商法》空白条文之间的适用。《民法典》第524条所确定的代位权属于法定清偿代位,约定代位可作为法定清偿代位权的特殊情形加以适用。而船舶优先权制度中,第三人代为履行后所取得的代位权难以在《海商法》中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故而应沿用《民法典》第524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同时,从对垫付费用的第三人权利救济角度考虑,既然《海商法》未曾对第三人垫付行为作出强制性规定,第三人垫付与否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那么海事请求权人债权实现之时,理应允许第三人与海事请求权人之间以约定代位的方式实现其代偿债权。其二,有助于解除人身属性船舶优先权代位之禁止。船员工资、劳动报酬及人身损害赔偿等海事请求的人身属性之认定不是《海商法》规范的结果,而是基于《民法典》第三人代为清偿代位规则的特殊规定。既然约定代位并不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则,自然不能产生无效的效果,由此,通过约定代位,船舶优先权禁止代位的争议不攻自破。此外,任意代位是德国、日本立法的产物,成立任意代位必须征得债权人的许可,第三人垫付费用后债权人已然获得应得利益,此时征得债权人许可的条件对于第三人来说难度较小,其与债权让与的时间可保持同步,也可后于债权让与而发生。总体来讲,任意代位可以解决船舶优先权代位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难题。
(三)实践层面:发挥指导案例及典型案件的指引作用
船舶优先权转让与代位规则在实践层面的应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法官运用概括的法律规定进行价值评价时难以把握裁判的尺度,可能导致裁判结果偏离船舶优先权转移规则的基本设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及典型案例能够把握同类案件的裁判方向,可帮助各级法院准确适用法律规定。一方面,吸收指导性及典型案例中对船舶优先权转让与代位规则的准确理解。前文提及的船员劳务合同及港口规费等案件中涉及的船舶优先权问题多是因第三人垫付费用而产生了纠纷,不同法院针对类似案件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裁判说理中虽然各有陈词,但是在法律规则的准确适用上还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而指导性案件的裁判要旨能够综合法律规定、立法目的及利益平衡等多方因素作出较为公正的审判。另一方面,准确选用符合案件事实的法律依据进行裁判。针对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与代位一类案件,因《海商法》仅对海事请求“转移”作出简要规定,那么“转让与代位”能否被评价为“转移”,较难认定。因此个别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直接采用民事规则予以裁判,导致了部分海事请求权及附随的船舶优先权禁止转让和代位的结果,故而参照指导性案例及典型案件的说理部分来指引案件裁判,能够有效避免法官陷入适用《海商法》与《民法典》二选一的难题中。
六、结语
船舶优先权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人身损害赔偿及船员工资、劳动报酬等海事请求权的转让与代位问题上,由此引发了《民法典》第三人代为清偿与《海商法》船舶优先权规范之间的适用冲突。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海商法》第22条所列举五类海事请求权的转让与代位在遵循《民法典》基本價值理念的基础上,均应回归《海商法》概括规则中找寻相应的法律依据。人身属性债权与海事请求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第三人垫付费用的情形下,《海商法》一般规定认可了海事请求权及船舶优先权的转让,理应按照该规定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冉克平.民法典编纂视野中的第三人清偿制度[J].法商研究,2015,32(2):36.
[2]王利明.债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75.
[3]温世扬,武亦文.物权债权区分理论的再证成[J].法学家,2010(6):44.
[4]韩立新,宋海华.人身专属性视域下的船舶优先权的转让与代位[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24(1).
[5]王炜.垫款人取得船舶优先权的相关问题分析[J].水运管理,2004,26(6):21.
[6]尹伟民,刘云龙.关于外派船员人身伤亡赔偿问题的探讨[J].当代法学,2002,16(8):159.
[7]司玉琢.海商法专论[M].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7.
[8]奧田昌道.新版注釈民法(10)II[M].東京:有斐閣,2011:685.
[9]徐新铭.船舶优先权[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5:99-100.
[10]徐俊.从船员劳务合同角度思考《海商法》有关船员规定的修改[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24(3):34-36.
[11]傅廷中.论船舶优先权制度建构下的船员权益保护[J].环球法律评论,2010,32(3):43.
[12]杨景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案)》的说明[EB/OL].[2021-05-06].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92-06/23/content_1479244.htm.
[13]孙思琪,胡正良.《民法典》对于《海商法》修改影响论要[J].国际法研究,2021(1):49.
[14]马得懿.作为补充型特别民法之海商法的丰富性与体系性[J].社会科学战线,2016(8):211.
[15]王利明.论债权请求权的若干问题[J].法律适用,2008(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