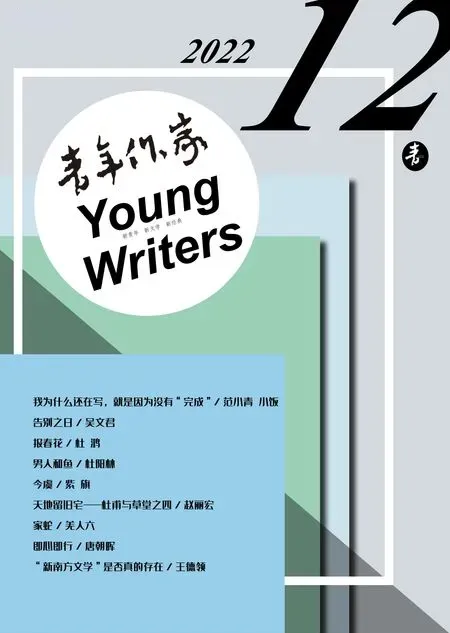小园
2022-03-26紫旗
紫旗
弟弟死的那天早上,天气出奇地冷,风从喉咙滑进腹部,吹得空荡荡的肚子都鼓起来。我把春天的褂子全部裹上,还是不觉得暖和。太阳照到房顶上了,我叫弟弟起床。他醒了,穿上衣服,套进两条裤腿,盖上被子继续睡。太阳照进木窗框时,我第二次叫他,我把他身上的被褥扯翻,他喊冷,手脚一起发抖。
我说,快起来,再晚蛋就凉了。
弟弟不知道,我其实是怕被人发现,尤其是妹妹。那样母亲就会知道,然后父亲就会知道,知道我违背他的意愿,胆大妄为地私吞了本该属于奶奶的鸡蛋。
前几天,奶奶吃蛋的时候,弟弟扒在桌沿上偷看。他面前的碗里装着红苕稀饭,黄色的红苕,白色的稀饭,和鸡蛋是一样的颜色,但弟弟不看。我跟着他的目光,在春天的风中飞来飞去,看到奶奶把蛋清咬开,露出黄澄澄的蛋心,他的目光停在那里,像人游了一会儿泳又趴在池塘边上,我就知道了,弟弟想吃。
不只我,奶奶也看出来了。奶奶说:“牛儿想吃得很,把蛋拿给他吃算了。”
父亲勃然大怒,一下子从凳子上弹起来,他吼:“你惯得他,小娃娃看到啥子都想吃,给他吃再多都吃不够。”
父亲是说给奶奶的,吼声却朝着弟弟,他使足了劲地说话,脊背拱得像座小山。弟弟的嘴巴哆嗦起来,他捏紧了胸口的衣服,用两只手捏着,像是怕寒风灌进自己的脖子。
我看到父亲生气,我也生气了,因为我知道父亲在乱讲。弟弟没有多吃,我们姊妹三个谁都没有多吃,因为家里没有更多的钱和食物,连每个学期的学费,都要从一个学期的开始,交到一个学期的结束才能交完。奶奶没来之前,我们不觉得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吃红苕稀饭,但是奶奶来了,父亲说,奶奶没享过福,现在他和母亲调到城里工作,就要每天给奶奶吃好的。所以奶奶早上吃两个鸡蛋,中午喝一碗丸子汤,隔一天晚上,还能再喝一碗肉片汤。从那以后,弟弟总是悄悄和我说,他闻不了肉的味道,闻到就会眼睛发花。
我低声对弟弟说:“等明天,明天早上,大姐给你蛋吃。”
隔天是周六,周六我们不用去学校,可以继续睡觉,只有父亲和母亲还是起得很早,因为他们都是老师,以往的很多个周六他们都要去学校。我也起来了,我每天都在太阳升起前起床,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说过,大姐是不能偷懒的,必须每天帮着母亲做饭。
我醒来的时候,两只脚冰凉,等到我把鸡蛋煮熟,四肢都变得暖和起来,变暖和的手指出奇灵活,所以他们没有发现,我悄悄把煮好的鸡蛋藏进了袖子里。
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家里,太阳也在同时升了起来,红彤彤的天空越来越多,我摇醒了弟弟。
弟弟把身体挪到桌子边,弯下来一半,把鸡蛋在昨天趴过的桌沿上敲了几下,接着剥开蛋壳,把鸡蛋放进了嘴里。他吃得很慢,圆圆的眼睛看着我,嘴里慢慢地咀嚼。
“好吃吗?”我问。
“好吃,”弟弟说,“我好喜欢吃蛋。”
弟弟的嘴里黏着蛋黄,说两句话,口水就从嘴角流了出来,他撮起嘴巴吸两下,把蛋黄和口水都吸回去一些。太阳照到他的脸上,把弟弟的脸照得河水一样,金灿灿的鱼儿在他眼睛里跳跃,一下一下的,我闻到弟弟嘴里呼出来的鸡蛋的香,我的肚子更饿了,饿得抽搐。我也好想吃蛋,想让弟弟给我两口,但弟弟吃得那么认真,他小口小口地啄,我忍住了。
“大姐对你好不好?”我问。
“大姐对我最好了,比二姐还好。”弟弟说。
我笑了,空空的肚子仿佛被另一种分量填满。
弟弟埋着脑袋,露出一个游鱼形状的发旋,我按上去,把手按进他乱糟糟的头顶,揉了揉,感觉扎手,想起父亲前天带弟弟去剪了头发。我知道弟弟讨厌理发,他喜欢长得盖住耳朵,那样柔顺、滑腻,我用手指就能帮他梳理。但父亲不能忍受弟弟的眼睛躲在刘海后面,那会让他觉得难以捉摸。所以每隔两个多月,父亲就会带走弟弟,让他的脖子被摁进一个凹槽,弟弟于是不能动弹,然后滚水从半空降落,从弟弟的后脑开始,漫过他的眼睛,直到他痛苦地号叫起来。回到家,弟弟就告诉我,理发和砍头是一样的感觉。
我一听就知道弟弟在胡说,他哪里知道砍头是什么感觉。他怕水,一定是因为属兔,兔子都很怕水。但弟弟听了,说不对,他说他不怕水,只是不会水。我默认了,想到小时候,父亲带弟弟下河,回来他告诉我们,弟弟是一只不能下水的旱鸭子。
现在没有河了,只有堰塘。在乡下的时候,门前就是河流,河水从西向东流过,在晚上,偶尔会听到水珠落在荷叶上的声音,鱼儿始终在游。如果是清晨,就不是鱼儿游泳,是有人在岸边淘米的声响,打破了水面的宁静。我爱听淘米的声音,像大雨倾盆直下,可是真到下雨的时候,我又不喜欢了。五月快要入夏的这个时候,乐阳总会连下一个星期的大雨,阴沟里的泥巴被大雨冲上平地,起先它还拥有形状,是一摊一摊的,越来越多的人从它身上碾过,到最后,灰黑的脚印犹如树根爬满所有的土地,那时,我们不但会失去嗅觉,还会失去行走的能力。
姚瑶就是这么摔倒的。不是摔在别的地方,她摔在我们屋子外面,不是摔在路上,她摔进了阴沟里面。我是在做午饭的时候听到了一声巨响,放下洗到一半的莴笋,走到门口,远远地,看见阴沟边上露出半截短短的手,我继续走到沟边,看见粉红色的衣服染成了酱色,我喊,姚瑶。
我的声音很大,我想把姚瑶喊醒,我怕她永远醒不过来。
幸好她应了,用响亮的哭声回应我虚弱的呼唤。我和奶奶、弟弟,我们三个一起把她拖了出来。阴沟很窄,还不够吞进姚瑶,但她很怕,一直在哭,哭到姚老师过来了,哭到父亲和母亲都从学校回来了,她依然在哭。
姚老师说:“硬是怪得很,昨天晚上来向老师屋头,瑶瑶也是摔得莫名其妙。”
前一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当时,我们正在吃饭,我炒了清炒莴笋和红苕稀饭。我们吃饭不把饭锅放在桌子面上,因为桌面太小,勉强摆了六副碗筷,再也容不下一口锅了,虽然它其实不大。锅被我们放在脚边,桌子的下面,谁要添饭,就自己弓身去捞。
姚老师不是第一次带着姚瑶过来串门,他们经常来看父亲,每次姚瑶都跟在他的身边,我们叫她,她也不理,好像比起和我们玩耍,她更爱听两个大人说话,于是我们三个也不理她了,让她像个扎实的墩子摆在那里。
他们聊了五分钟,也可能是三分钟,总之是很短的时间,短得谁也没有看清楚怎么回事,姚瑶一屁股坐进了饭锅里。紧接着,弟弟发出一声尖叫,像吹响了一串号角,姚瑶醒了,她环顾把她团团围住的大家,开始哇哇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暗黄的两颊涨得通红。
父亲的脸也变得通红,他涨满血丝的眼睛鼓起来,像一只受惊的金鱼,我知道,父亲又要扯起嗓子吼叫了。
“搞啥子,你们一个个的,不晓得注意到妹妹啊。”他喊。
父亲把筷子摔在桌上,其中一根掉下桌沿,在地板上滚了又滚,在稀薄的空气中撞出很清脆的声响。弟弟和妹妹都没有说话,他们吓呆了,徒劳地抱紧面前的饭碗,像抓住了一根稻草。我低着头,没有回答父亲,用泛白的骨节把筷子握住。
“都起来,给姚老师和瑶瑶道歉。”他又说。
我是大姐,所以我第一个站了起来,几乎和父亲平视。母亲说,再过两年,我估计能长得比他们都高。但我没有那么高兴,我的个子很高,不是竹竿那样的高,是柳条那样的高,说弯,就弯下去了。
我弯着腰,先向姚老师道歉,然后和母亲一人抓住姚瑶的一只胳膊,用力地把她拖出来,从饭锅里面拖到安全的平地上站着。等到这次,我发现她又摔倒了,摔进了阴沟的时候,母亲不在家里。我找到奶奶,弟弟也窜了出来,他伸出两根黑黄的手臂,火柴棒一样,任姚瑶死死地抓住,把她拖出吸附住她的水面。
父亲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前,我就已经预感到,这次我一定会挨打,因为我又没有看好妹妹。危险只是换了一种样子,我就任由它降临,这和我做错了数学题没有区别。父亲会用他强劲的胳膊教会我,应该怎样记住答案,必须是刻骨铭心的,才能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会重复再犯。所以我没有抵抗,我盯着父亲爬满掌纹的大手,认真地想,我要长到多高,才能不用挨打。
弟弟冲了上来,他用力地抱住父亲的手臂,仰起脑袋,用很小的声音哀求。
“不是大姐的错,爸爸莫打大姐。”
父亲的巴掌没有落在我的脸上,他反手一巴掌,打在了弟弟的脸上。
弟弟立刻把身体蜷成一团,他不住地颤抖,两行眼泪刷刷地流下来,在脏兮兮的脸上冲出两道印迹,我又想起大雨过后的阴沟,再看父亲,他的手掌就像踩进泥里的脚印,在我和弟弟的脸上,踩一下,又踩一下。
父亲又一次证明了他的力量和存在。
月亮又升起了,从越来越浓的夜色里。透亮的月从天空一角慢吞吞地移动,云也在动,我认真盯着圆盘一样的月亮,想像嫦娥那样飞得高、飞得远,谁也捉不住我。等到月亮从我的脸上挪开,我就不想它了,我掉进梦里,听见门外响起一道陌生的声音。
“打蛇。”他说。
另一道声音跟在后面,几乎听不清楚,我跑到窗边,把耳朵贴在窗户的缝上,才听到他说:不要打。
“打不得,打了要死人。”他说。
第二天早上,姚老师过来了,他问父亲借菜刀用。临走之前,他说,晓不晓得,昨天晚上有人打死一条菜花蛇,好大的一条。
姚老师的声音不大,是从关了一半的门外漏进来的,但我清晰地听见了。
我把长在作业本上的眼睛转向他,他正用手圈住一条无形的大蛇,又圆又粗,要两只手才能抓住,不像蛇,很像一条巨蟒。
我想,原来我不是在做梦吗?
“姚老师,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喊打不得。”我说。
在自动对焦系统上,E-M1 II的纸面数据更优秀,它使用了集成121个十字型焦平面相位对焦点的混合对焦系统。而G9仍在使用225区的反差对焦系统,尽管如此,基于松下独有的DFD技术的自动对焦系统,表现异常迅速。
“没有哦,小园怕是听错了。”他冲着我的方向说。
姚老师说话很慢,这次也是,他慢条斯理的,但很笃定地回答我。我立刻就沉默了,我分不清楚,到底是我在做梦,还是像姚老师说的那样,是我听错了。
到了晚上,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马上睡着,我的眼睛看着屋里的黑暗,听着妹妹呼噜呼噜的鼾声在耳边滚来滚来,最后,我把妹妹戳醒,我坐起来,问她,昨天晚上有没有听见谁在喊打蛇,或者有人在喊别打。面对妹妹,我有更多的勇气,所以白天在父亲和姚老师那里不敢说的猜测,我现在愿意说了。我说,打蛇好像要死人的。
外面没有灯了,只有月亮,妹妹的眼睛一会儿眯起、一会儿睁开,像天上闪烁的星星,黑夜里发出湿漉漉的亮光。
“没听见。”她说。
虽然我猜到会是这个答案,但真听到妹妹也这么说,我突然非常失望,把眼睛转向窗户的方向,胡乱地点了点头,然后想起来,黑暗中她看不见我的动作。
我转回去,把妹妹脖颈两边的被子掖进去,掖得严严实实,确保一点风都跑不进来,妹妹像一只小羊,软软地团在那里。
我轻声说:“快睡吧,明天还要上学。”
我明明说得很轻,可是妹妹好像被惊醒了。她麻溜地钻出被窝,支起身体叫我。
“上个月妈带我和弟弟回金顺看爷爷,我们遇到玉芳表姐了,她带了玉溪表弟来,你没看到,玉溪表弟拜了三个保保。”妹妹说。
“那也正常的,他上头三个姐姐,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儿娃子,屋头肯定金贵得很。”我说。
“那我们家也是啊,大姐和我下头就是弟弟一个男娃,妈咋个不给他拜保保呢?”
妹妹的声音好轻,几乎是用气音在说话,她那么小心谨慎,像是生怕被人发现了秘密。我本来随便地坐在床上,但听见妹妹这么问我,我就猜到她还有话说,于是我把屁股往妹妹窝的地方挪了挪,紧紧地挨着她。这样,我们微弱的说话声就不会被父亲发现。
“妈不想拜。”我小声说。
“我有点害怕。”妹妹说,“当时他们看见弟弟,有个保保说弟弟是鱼大塘小,养不大的,大姐,鱼大塘小是啥子意思?”
突如其来的寒冷席卷了我,我不得不扎进被窝,让被子完全地裹住身体,长长的一段沉默,温暖终于驱散了后背的凉意。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就是我们还在金顺乡下的时候。”我说。
妹妹摇了摇头,我知道她不记得,她那时候太小了。
我说,那时是奶奶在带弟弟,有一次,奶奶回她中江老家,弟弟也一起回去,有个仙娘婆,到祖母家里耍的时候遇见弟弟,弟弟当时才几个月大,仙娘婆说,弟弟的命特别好,我们这种地方出一个不得了。
“这是‘鱼大’。”妹妹说。
“我们家太穷了,所以人家说我们塘子小。”我说。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妹妹问,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不知道,”我说,“但仙娘婆当时让弟弟拜她当保保,还说一定要拜,不拜,弟弟就养不大。”
“可是弟弟没有拜保保。”妹妹说。
“妈妈不想拜。”我又说了这句话。
我没有告诉妹妹,母亲一开始是想的。杨舅舅是中江人,他接媳妇的时候,母亲带弟弟也去了,因为何孃孃劝她,为了弟弟,到中江把仙娘婆拜了。但是这一次仙娘婆没有同意,接媳妇的场面太大了,仙娘婆说,拜保保不能搞得人尽皆知,还有很多礼数,是要私下进行的,反正,绝对不能在接媳妇这种乱哄哄的场合,所以她让母亲带着弟弟上她家里。
母亲最后没去,她说时间不够,又说,太麻烦了。
我当时也是妹妹这样,我说我有点害怕,不拜保保,弟弟会不会有事。母亲坐在饭桌前,批作业的时候它是书桌,她干瘦的手臂摇晃在黄纸上空,等我说完,朝我露出一个轻微的笑容,不是那种从眼角弯到嘴角的笑,是那种轻飘飘的、从鼻腔里飘出的笑。
母亲说:“我一辈子不整人、不害人,我就不相信了,我一个儿子都带不大。”
于是我知道了,这些都不是母亲真正的理由,她不愿意上门,一定是嫌那样的自己显得太殷勤、太迫切了。母亲和父亲是不同的,她和时刻紧绷着的父亲完全相反,我从孃孃们频繁摆起的龙门阵里拼凑出了他们的过去,虽然他们都很贫穷,习惯了肚子空空,但父亲和我一样,是家里的老大,老大是不能偷懒的,我们要为弟弟妹妹的生活负责,但母亲不是,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她不用负责。她有食物就自己吃,她有衣服就自己穿,她在我这么大的时候,上面的哥哥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所以母亲从来就是这样,这样平静、稳定,对一切东西表现得云淡风轻,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样子,哪怕我们都知道不是那样。
后面没有人再提拜保保的事情,孃孃没有,我没有,母亲更没有,于是它在我的记忆中渐渐地沉入池底了,直到妹妹把它打捞上来,问我。我告诉她,过段时间,中考一结束,我就去问母亲。
弟弟吃完鸡蛋就出去了,他说,去找徐二娃玩。回来的时候,裤管卷到了膝盖上面,弟弟赤着脚,两只脚上都是泥。
“你是不是去堰塘边耍了?”我说。
我有些生气,大雨连续下了一周,到处飘着水洼和烂泥,父亲不准我们任何人乱跑,要我们老实待在学校和家里,我那么听话,还要为姚瑶的事情挨打,弟弟为什么要触怒父亲?他明明不会游泳,却老往水边跑,游泳有什么好的呢,河水那么脏,人有什么垃圾都往里面扔。母亲以前说弟弟,说他上辈子肯定是条鱼,所以才老想回到水里。在当时,我知道母亲只是开玩笑,但到后来,我越想越觉得是那么回事,因为弟弟那么弱小,只在游泳这件事上有着让我惊讶的活力。有时候,我甚至羡慕弟弟,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一条鱼,鱼没有脚,没有拘束,可以不为任何事物停留,可以随心所欲去到任何它想去的地方。
“绝对没有。”弟弟说。
弟弟说得很坚决、很干脆,我就不生气了。我想,池塘深不见底,弟弟也是知道的,所以我说:“赶快进厕所弄干净,慢点中午爸回来看到了,你要挨打。”
但就在这时,门开了,我听见了吱嘎一声。
其实我没有害怕,但身体自然的反应,让我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我挡住弟弟跑过的剪影,死死地盯住门。
幸好是母亲,她先回家了,黑瘦的胳膊搂住一捆蓝布裹着的书。两片灰色的衣领在风里抖动着,像是一双小鸟的翅膀在拍打。
“奶奶在做啥子?”她问,声音慢吞吞、轻飘飘的。
“在煮饭。”我说。
“那你还耍起,赶快去帮奶奶。”母亲的声音变沉了。
“弟弟进屋我才出来的,这就回去了。”
我往厨房走,然后愣住了,我被地上的泥巴印拦住了脚步。它们尚未干涸,深浅不一,弯弯扭扭地接在一串,从门口开始,指向一个显而易见的出口。
我转过身,在母亲发现更多蛛丝马迹前走回门边,挡住了母亲的眼线。我知道我必须说点什么,于是我问母亲,中江的事情为啥子不告诉我?想了想,我又问她,之后准备咋办?
母亲晃了晃脑袋,说:“屋头穷,没得钱。”“那就借钱。”我说。
“啥子仙娘婆,都是假的。”母亲又说。
“你怎么知道真假,就算是半真半假,也有一半是真的。”我说。
母亲不说话了,她定定地看着我,她肯定没有想到,我会在拜保保的事情上纠缠不休,两个理由都没能把我说服,所以她陷入沉默。母亲用了几个呼吸的时间思考第三个理由,最后她说:“没那么快。”
母亲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没那么快,但我一下子明白了母亲没有说出口的话,我又马上明白了,为什么她没有把它说出口。正午的太阳大放光彩,照在母亲脸上,是我熟悉的那副样子,但我竟然觉得非常陌生,几乎认不出来,火从我的胃里蹿到喉咙,我的呼吸由于它的缘故变得急促和沉重起来,并且渐渐地上气接不住下气,于是我猛吸了一口冷气,然后才能说话。
我说:“妈,你晓不晓得你在说啥子话,啥子叫没那么快?”
我一直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母亲更令人害怕,我说不出为什么,只是每每听母亲用那种漠不关心的口气说话,会觉得心口发冷。现在我发现了,父亲的拳脚虽然有力,像火焰一样伤害我们的身体,但母亲压根儿不需要拳脚,她用冰凉的目光和言语。像我前年吃到的一根冰棍,冻了很久,比砖头还硬,第一口下去,我没有咬动,我看它嘶嘶地吐着白气,像一条吐舌的银蛇,于是我也伸出舌头,舔了舔它,然后我就知道了,冰是凉的,也是烫的,不是火烧起来的那种看在眼里的烫,它是不易察觉的,因为毫无防备,所以出奇地烫人。
吃完午饭,母亲没有多待,去了学校,父亲一直没有回来,我们因此可以安心地午睡。梦中,那个男人的声音又回来了,这次不是在晚上,是在早上,亮堂堂的天空上面回荡着他的哭声,含混的、模糊的,像是把许许多多的话含在了嘴里,一开口就会掉落。我站在很高的楼顶上,向下看,波光四起,火光在水中晃晃荡荡,我纵身一跳的时候,终于听清楚他的声音,他喊,别动。
我醒来时,先闻到了青草地的腥气,然后听见雨滴在屋檐上溅开,我平躺在床上,想了好久,才打捞起一些没头没尾的碎片,有白纸黑字,黄色的纸钱,成群结队的人抬着花圈,还有一口宽大的黑色棺木。他们无声地流泪,从红星桥开始前进,走过城西小学,走过元帅公园,走过我们每天上学都会穿行的好吃街,都走出乐阳县城了,他们还在向前,一直走到金顺乡下,我们大院对面的田坎,他们站住了脚,轻轻地放下了黑棺。
这实在是很离奇的梦,所以我继续回想,努力地想要捕捉到更多更连贯的画面,直到听见有人拼命地拍打我们家的大门。
我看见姚老师的时候,差点没有认出来。他的眼睛又小又红,黑色的头发和胡子沾满了面粉,像一只刚刚被雨淋湿的大狗。我还在想,天这么冷,姚老师怎么满头大汗呢,就听见他发出一声小狗似的呜咽。是他在喊我,小园。
“快去幸福面厂,小旭下午淹进堰塘了,到这会儿还没捞起来。”姚老师说。
我浑身上下的血一起涌进了脑袋里。
他说,小旭和徐二娃一起去幸福面厂旁边的堰塘游泳。他又说,徐二娃会游泳,所以他爬上岸了,小旭不会。他还说,徐二娃说他们以前下过堰塘,当时就差点被淹,好在当时有人捞起来了,小园,这个事情你晓不晓得?他说,小园,你晓不晓得?
我不晓得,我明明想告诉姚老师的,可是我说不出。
我跟在他的后面飞快地跑,感觉我干瘦的身子几乎要被风撕成两半,我突然想起我隐秘的愿望,想成为一条没有拘束的鱼,现在,我觉得我的速度比鱼还快了,我跑得感觉不到腿的存在。
风呼呼地打在我的脸上,从我的喉咙滑进我的胸口,起先它是冰凉的,等它掉进胃里,我感到火烧似地疼痛,疼得我喘不上气,我只能用力地张大我的嘴巴和鼻子,让泪水沿着两侧的脸颊下流,流进我的鼻孔、我的嘴巴,像雨水爬过玻璃窗,泪水在我的脸上织出了一张密密的网。
终于,我看到父亲和母亲了。
母亲跪坐在地上,低着头,她用枯瘦的手掌捂住脸,父亲站在她的旁边,小山一样的身体缩在人群当中,我只能看见他垂下的脑袋。远远地,我听见哭声就像号叫那样响亮,眼泪在他们的脸上交错纵横地流,可是谁也没有伸手去抹。
我拔足狂奔,用最快的速度。就在我快要跑到母亲跟前的时候,一股突如其来的恐惧截住了我的脚步,我怔住了,脑袋里嗡嗡地乱叫起来。
“快去安慰你爸妈。”姚老师说。
我就又开始挪动步子,这次我走得很慢,步子迈得很小很小,我听见自己微弱、嘶哑的呼唤,像被击中心脏时的一声闷哼。
“妈。”我说。
母亲听见我的声音,她停下了哭声,用她从来都像水一样沉静的眼睛,把我盯死在原地,它现在像两束探照灯了。
“牛儿咋会跑出来游泳?”她问。
“我不晓得。”我说。
现在我可以正常说话了,每个字都从滚烫的喉咙里挤出来。
“他上午在干啥子?”
“我不晓得。”我说。
“牛儿之前就被淹过,你为啥子不跟父母说?你以为你帮弟弟瞒到父母就是为他好?”
“不,我不晓得。”我仍说。
五月是春天了,每一杈树枝都显出春日的盎然生机,就是前些天,弟弟跟在我身后,徒手折断了一根油菜花茎,真漂亮啊,绿意浓郁,盛放在他手心,令人想不起半点山雨欲来的征兆。我说,不要扯花花,弟弟就点头,乖乖地说,以后不扯了。那是又一个美好的晴天,山上的薄雾正在散去,太阳光温柔地照上弟弟侧着的脑袋,他的眼睛朝我望过来,暖水拍溅。现在四周幽暗极了,没有油菜花田,没有绿意,也再不会有弟弟,只有肮脏的烟雾从很多人的嘴里喷出,缭绕在我的头顶,记忆因此膨成一个鼓胀的气球,突然迸裂了。
“妈,你为啥子不带弟弟拜保保?”我说。
母亲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抬起手去抹,冰凉的巴掌把滚烫的泪水往两只耳朵的上面抹,却越抹越多,眼泪从她的脸上流到了我的手掌里,一点点地,填满我沟壑纵横的掌心。
“你是不是觉得,牛儿都是因为我?”母亲说。
她鹰爪一样的手指抠着我的肩膀,带动我的身体一起发抖。我很痛,但我不敢喊,我慌乱地摇头,躲着母亲的眼睛说不是,母亲的脸在我眼前闪来闪去,我摇得停不下来,这时父亲的脸也出现了,还有他高举的手,一巴掌甩在我的脸上,非常用力,我的头歪向右边,终于停在了这个瞬间。
父亲说:“你晓不晓得你在说啥子话,你还想把责任推给你妈?”
我看见大颗大颗的水珠从父亲血红的眼眶里滚出,滚落下颌,又滚到他泛黄的衣领上,也是在这时,我感到颈后好像挨了重重一击,千万条小虫从心底爬向我的全身,父亲咧着嘴,面朝我的表情那么狰狞,我们互相盯着,好像彼此的仇人。我在哭吗?可是我没有声也没有泪,只有粗重的喘气呼出来,我一动不动,心想,原来是我杀了弟弟吗?
风从人群间顽强地挤了进来,吹得我浑身发冷,连同母亲一声声的哭泣吹进我的耳里,我两腿一软,瘫坐在地。
弟弟的尸体被打捞上来,是在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
我不敢走近,退后几步,躲在人群背面,竟然认不出来这是弟弟。我记忆中的弟弟又瘦又小,肤色发黄,每次我梳理他柔软茂密的头发,都像在抚摸一只小兽,可是现在,一晚上的浸泡后,弟弟整个人变成了一块泡开的发糕。我从没见过这种样子的弟弟,看了一眼,我就不敢看了。
不敢看的不只是我,母亲离他最近,也只看了弟弟一眼,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我从没见过母亲那么可怖的样子,她捂住眼睛,两条细瘦的腿在风中簌簌发抖,像是承受不住她的重量,马上就要崩塌。还好,父亲伸出了一只手臂,握住她的胳膊,只是他鼓鼓的眼睛更肿了。
弟弟必须马上下葬,父亲说,入土为安,得把弟弟带回老家。三叔不同意。他说弟弟是化生子,死在外地,这是霉上加霉,绝对不能葬回家里。父亲和三叔吵了起来,他们在屋里,我站在门口,看父亲抄起大堂的独凳,砸向三叔脚边,凳子越过方桌,摔落地面,一直滑到墙角的木桶旁边,大雾四起。三叔不肯让步,骂骂咧咧,手把桌子拍出了打鼓的韵律。巨大的声响灌入我的耳中,起先我还能分辨,但很快,我失去了辨别声音的能力,然后连行走的能力也没有了,站在那里只是一个摆设。最后三孃出来了,她一点也不着急,不紧不慢地走,走到父亲和三叔的中间。她说,莫打了,牛儿不能拉进院坝里头,拉到对门可以。
现在,弟弟可以下葬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棺材店的老板拿不准尺寸,因为弟弟是小孩,是在水里泡了一天的小孩,我们都不知道,小孩在水里泡了一天会变得多大。最后他和父亲说定,不如就把棺材做大做长,总而言之,宁大不小。
于是弟弟躺进了一口大大的棺材,这么看,他几乎是个成年人了。这一天的中午,弟弟的老师也来找父亲,老师说,同学们都很伤心,为表心意,大家捐款凑了些钱,为向小旭同学买了一个花圈。
弟弟死后的第五天,父亲把棺材装上了一辆小货车,弟弟和几个粗布麻袋堆在一起,不和我们一起,我们四个坐姚老师的车子,跑在前面,领弟弟回家。
这一天傍晚的时候,车子停在了大路边,父亲领着金顺的叔叔伯伯,抬起了花圈和棺材。棺材很黑,但是花圈很艳丽,一层绿色,一层粉色,一层蓝色,又一层绿色,像水波一样层层荡开,牢牢地圈住中间的白色,和浮在上面一个大大的“奠”。老师送过来时,母亲感动极了,眼球上下左右地动,像是不受控制。
“谢谢张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对小旭太好了。”母亲说。
我跟着父亲他们,走过了坎坎坡坡、一大片油菜花地,走到我们大院对面的田坎时,他们站住了脚,轻轻地放下弟弟。从弟弟死的那天早上开始,到现在,天气都冷得不像五月,我把毛衣都穿上了,还冷,今天也是,太阳好像再也没有升起,寒冷彻底笼罩了大地,我不得不浑身发颤地爬上后山。
理发店的杨师傅也来了,下葬的时候,杨师傅放了两块陈皮糖在弟弟的旁边,我知道他很喜欢弟弟,他说弟弟聪明、机灵,未来肯定是个大学生。但我也知道,很可能是因为每次理发父亲都去杨师傅那里,他认为有必要多多地夸赞弟弟。他蹲下去,又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两块陈皮糖托在他的手里。我说,都给弟弟吧,他那么好吃,以后都吃不到了。杨师傅唉唉唉了几声,说可惜啊,把脑袋晃得拨浪鼓一样。
“之前我就觉得哪里要出事,还跟你爸讲过,”他说,“往前一周多,就是幸福苑旁边的面厂和砖厂,天天晚上都有人在喊,我口渴,我想喝水,喊得好大声哦。”
我没有什么反应,他也不管我,自顾自地往下说:“但是你说怪不怪,等工人打电筒出来看,声音又没了,就这么个情况持续了一周多。”
杨师傅激动了,把他浑浊的眼睛睁得很大。我看着那对眉毛忽上忽下,越挑越高,几乎要挣脱额头,觉得实在没什么意思,只有父亲和杨师傅说话,我在心里回忆,这是听说的第几个预言。弟弟死后,我平淡的生活里突然冒出了很多预言,比如昨天,父亲跟母亲谈他的高中同学,他说一周多前窜出了一只黑猫,每天什么也不干,只是和家里的橘猫窝在一起,面对面地哭泣,弟弟一死,黑猫也不见踪影。
开始的时候我和母亲一样,深信不疑,它们每个都那么神乎其神,是死水一样的生活中唯一慰藉。但有一天,我经过中学坡下,装冰棍的泡沫撞进我的眼里,我忽然就浮出了水面。许多东西看起来和实际的并不一样,好像冰棍,它应该是凉凉的,却可以火烧似的烫人。后来再听他们讲述,我就不回应了,我知道他们安慰的是活着的人,用一种把灾难归咎给命运的方式,他们想说,弟弟逃不掉死亡的命运。
“所以说啊,其实小林出事的那个堰塘当时围了好多人,就是没人去救,大家看到小林淹死的。因为早就猜到了啊,肯定是要死人的。我一个妹儿在耍朋友,男方弟弟和他爸爸就在幸福苑面厂上班,当时就在场,亲眼看到的,前两天过来他说起我才晓得,我当时就跟他说,那是向老师的儿啊,他也说可惜得很,要是他晓得的话一定会去救的。”
“杨叔叔刚刚说什么?”我问。
两块陈皮糖被我捏在手心,跟着我的呼吸微微颤动。我突然对他的预言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又问了一遍,杨叔叔刚刚说什么?
他愣住了,好像没想到我会搭腔,连带着他的记忆也卡住了,他沉默了两秒。
“哦,就是我妹儿他男朋友,说可惜得很,要是他晓得的话一定会去救的。”杨师傅说。
“不对,上一句。”我摇了摇头说。
“大家早就猜到,幸福苑这边肯定是要死人的。”杨师傅说。
“不对,上一句。”我说。
“堰塘当时围了好多人,就是没人去救,大家看到小林淹死的。”杨师傅说。
我说,对,就是这一句。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弟弟。就是在梦里,乐阳也连续下了很长时间的雨,直到太阳再次出来的时候,我起床,发现窗外的操场变成了一片泽国,原本是水泥地的地方生满了密密的芦苇。
弟弟就是在这个时候划着船来找我的。
他把船停在一棵小树的旁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对着我的窗口大声喊我。我就站在窗边,听到弟弟的声音,探出头来,见他赤脚叉腰站在船头,样子傻气得好笑。我问弟弟,你为什么没有穿鞋子?他说,早上上山抓鱼的时候弄湿了。他说话时,身体微微后倾,我好怕他会掉下去,就说,别动。他却冲我笑了笑,把两只手伸得老远,眼睛亮晶晶的,像一轮崭新的旭日。
“大姐你没看到,好大的一张渔网,捞了好多的鱼。”弟弟说。
弟弟下葬后的第三天中午,我们返回了乐阳县城。下午,父亲和母亲都去了学校,我没去上课,去了幸福苑。
沿着那个淹死了弟弟的堰塘走过去,我看到面厂的房屋从堰塘的四周伸出来,一直伸到池水里,太阳的光彩把水面染得如火如血,真是奇怪,有阳光还感觉冷。我把毛衣的袖子撸到胳膊的最上面,让没有温度的阳光晒在我的手臂上,顿时我原本暖和的手臂,被阳光晒得瑟瑟发抖。我看到一处石阶,走了下去,在堰塘边坐下,堰塘的两边种满了青菜,只有我坐着的地方没有绿色,好像春天把它遗忘了。前几天开始雨不下了,只有仅剩几片水洼,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波光。从水面的倒影中,我看到两个男生在玩陀螺,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挥舞鞭子,使它一刻不停地旋转。
我摸了摸口袋,掏出一颗陈皮糖,走到他们面前。我说:“你们都住在幸福苑吗?”
他们停了下来,陀螺也停了下来。个子矮一点的男生抬头看我,他没吭声,我想他是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出现感到很疑惑。
我迅疾把糖塞进他的手上,露出了一个友好的笑容。我说,知道向小旭吗?一个男孩,很小,上周在这里。他突然接过我的话:“我知道,我们是同学。”
我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你当时见到他了?”
他摇了摇头,却是旁边高个子男生说话:“我爸爸在,他见到了。”
我立马摸出了第二颗糖,这次它刚刚走到半空,就被突然伸出的手夺了过去。他一边嚼,我一边说,那叔叔当时肯定帮到救人了嘛。男生说没有,说得干脆极了,满脸写着毫无问题。
“那是为啥子呢?”我说。
他嘿嘿地笑了笑,五官扯得扁扁的,太阳的金光洒进他的眼睛,莹莹有光,像鱼儿跳进了池塘。他说:“那个男娃娃之前就在这里被淹过一次,我爸说,当时就该死的。”
我看了他很久才说:“哦,当时就该死的。”
“所以说,这回本来有人也要去救,周围的人把要救的人拦到了。”
“周围的人把要救的人拦到了。”
“都说他早就该淹死了,多活了这么久,这回不能再救了。”
“这回不能再救了。”
我觉得自己好像听不清他们的话,必须用嘴巴重复一遍,才不会让自己忘记。可是到后来,我连自己的声音也听不见了,耳朵里始终有嗡嗡的声音惊天动地地响。于是我说,我知道了,转身往回走,迈出去的两条腿宛如灌了铅,每迈出一步都要费尽全身的力气。所以很短的路,我走了很久,经过刚才的堰塘,我没停,继续走,往前,跨过马路,穿过一条巷道,再往前,我想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么沉重的路,当视线里终于出现了一间灰扑扑的小卖部,我停下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太婆埋在里面,她问:“买啥子?”
“有打火机吗?”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