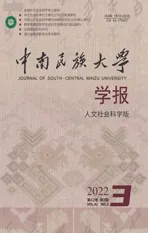日藏写本《天地瑞祥志》编纂诸问题考论
2022-03-25宋小芹曹建国
宋小芹 曹建国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天地瑞祥志》是一部藏于日本的唐初汉文典籍。据卷首所载《启》文及目录,可知该书系唐高宗麟德三年(666年)太史萨守真奉旨编撰,原本共二十卷。此书在日本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现残存九卷。抄本年代最早的是东京都尊经阁文库所藏江户年间(1686年)抄本;其次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昭和七年(1932年)据尊经阁本的誊抄本;又有石川县加越能文库藏1810年据尊经阁本所抄本,并将其与《天文要录》《六关记》合为一册藏存。该书在唐以来的中国古代书目中未见著录,故中国学者此前一直未曾言及此书。1990年薄树人根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抄本加以影印,收入所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1]中,《天地瑞祥志》才得以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中。
《天地瑞祥志》内容丰富,价值巨大,故颇受学界重视。但因为是残卷,文献著录不清,所以其编纂者身份、文本性质以及版本流传等问题,学界存在很大的分歧。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该书中存有数量可观的诗赋表赞类,对此学术界甚少关注。而比较发现,《天地瑞祥志》所存诗赋大多和《艺文类聚》相重复,这对于我们研讨该书的编纂方式、编纂者身份等问题有益。缘此,本文将不揣谫陋,拟对《天地瑞祥志》所引诗赋作品作一初步考述。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其编纂方式、编纂者身份、编纂目的以及文本类属等问题提出一点粗浅看法。
一、从《天地瑞祥志》 注文论其编纂者身份
《天地瑞祥志》编纂者萨守真的国别,是目前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今存《天地瑞祥志》卷首启文末署“麟德三年四月,大史臣萨守真上启”,而没有明确“萨守真”的国别身份。关于萨守真的国别,概括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说法。
其一,以萨守真为唐人。这大概是最直观的看法,因为文献本身是用汉文书写。所以一直以来学者都把萨守真看作是唐高祖时当过太史令的薛颐家族中人, 卷首启文提到的“大王殿下”被认为是高宗太子李弘,如太田晶二郎即持此说[2]。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纂《纬书集成》从《天地瑞祥志》中辑佚资料,并称之为“中佚”,视其为中国资料[3],想必也是将萨守真看作是中国人。中国学者游自勇对水口干记之说逐一作了辨析,这一点详见下文,暂不赘述。游氏并不支持萨守真新罗人说,认为“本书是唐人撰述的可能性仍然是最大的”[4]11-12。
其二,以萨守真为新罗人。这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主流意见,率先由韩国学者权惪永[5]提出。随后,日本学者水口干记[6],中国学者赵益、金程宇[7],韩国学者朴胜鸿[8]等皆撰文,力证萨守真为大唐邻国“新罗国”人。朴胜鸿总结梳理诸家证据,大抵包括“麟德”年号、启文格式、避讳问题,又提出吏读标记的新证据,以及《高丽史》关于932年高丽太祖引用《天地瑞祥志》的记载等,皆可证明萨守真为新罗人,并推定《天地瑞祥志》于657年传入日本,以及编者萨守真即《三国史记》中的薛秀真。
除此以外,《天地瑞祥志》卷二十“祭物载”下所收录《就利山会盟文》是麟德二年百济和新罗在熊津就利山的盟约。权惪永最先利用了这一证据,之后赵益、朴胜鸿等都将此当作萨守真为新罗国人的重要证据。朴胜鸿认为编纂者不录唐代其他会盟之文,而独选此条与新罗有关的盟约入例,且注文对“就利山”有详细解释,若萨守真不是新罗人,则不会对会盟地点如此知悉。赵益还解读了启文中的“物阻山海”,认为这显然是海东人语。
应该说,诸家的论证对于辨别编纂者萨守真国别都有重要价值,但正如上文所引游自勇意见,有些证据还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如“麟德”年号问题、避讳问题、“大王殿下”称呼问题、“萨守真”为“薛秀真”误书问题,游氏都提出了反对性意见,也应该引起注意。但朴胜鸿提出的“吏读标记”值得学界重视。同时,正如游氏所说,若为唐人奉命编纂,编者在已知乾封改元的情况下,不可能还是用旧年号。相对于“大王殿下”那种两可的证据,这些证据更具说服力。缘此,笔者倾向于认为萨守真为新罗人,至少不是唐人。《天地瑞祥志》中存有许多萨守真的注文,仔细分析这些冠以“守曰”的注文,对于我们了解编纂者的身份国别也有裨益,而上述诸家甚少关注。兹举几例:
(1)小学类。注音,赵益注意到《天地瑞祥志》中的注音,认为“兼注四声”, 中土作者既不必为,更不必专门强调。确实如此,中土著述虽以反切注音,但绝少注四声者。释字,《天地瑞祥志》常解析字形,尤其是遇到异体字,常标注正体。如《明载字》引《左传》“天反时为灾”,注曰:“烖、災,必皆同灾字。”[1]316“地反物为妖”,注曰:“祅、訞同妖字也。”[1]316训诂,《明载字》“徘徊不去其度为守”,注曰:“徘徊犹彷徨,若来若去,犹似有遗而久居也。”[1]316其实“徘徊”一词很常见,根本不需要解释,甚至古籍常用“徘徊”去解释其他词,如《大人赋》“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颜师古注:“低徊犹徘徊也。”[9]
(2)典籍类。卷十六注《汉书·五行志》所引“《传》曰”,注:“守曰:《洪范五行传》是也。”[1]372对于一般人来说,《洪范五行传》并不是特别生疏的知识,也无需出注。但如果是一个外国人,又缺少上下文语境,“传”的理解或许会有难度,所以便需要注释。卷二十载《就利山盟约》“《春秋》二百四十年中诸侯盟誓多矣”,注云:“周平王即位卌七年者,鲁隐公元年,《左传》自此始。来到鲁哀公十四年,二百卌二年,《传》终也。”[1]447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去解释“二百四十年”这样的简单年数,实在匪夷所思。若为唐人所作,确实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其中“者”“来到”等表述也不似中国人语。
(3)名物类。《明载字》“一曰五行”,注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也。”[1]316卷二十“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注:“守曰:地名,越也,音于侯反也。”[1]437这些都是常识,若阅读对象为唐人,便没有解释的必要。尤其是一些叠床架屋的解释,本来原注解释得已经很清楚了,但编纂者似乎还担心理解问题,于是又追加了一些解释。如《卷二十》“《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编纂者引了郑司农的注释,曰“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又引了郑玄的解释,曰“玄谓天皇大帝也”。按道理说,这已经非常清晰了。但编纂者接着解释:“昊天上帝是天总号,非别之也。”[1]439他似乎担心读者误解了郑众、郑玄的注释,所以特别加了说明。若阅读对象为唐人,相信不会把昊天上帝理解为两个不同的对象。类似这种叠加性解释比较多,似乎编纂者对阅读者的知识背景很没有信心。
总之,现有的证据似乎更有利于证明萨守真非唐人这一结论,而“守曰”注文也可以为此提供比较有利的佐证。不仅如此,“守曰”还彰显了《天地瑞祥志》文本编纂的层次性,这提醒我们该书可能不是一次编成。如果萨守真是新罗人的话,似乎回到新罗以后他又对文本进行二次编辑,并且补充了一些注文。如果这种推测有合理性,也可以帮助我们换一种思路去理解上述诸家理解有歧异的地方。例如为什么书中既有麟德年号,又有乾封年号,或是因为麟德代表初次编纂,而乾封则是二次编纂的结果。
二、从《天地瑞祥志》所引诗赋看其资料来源
《天地瑞祥志》引用了丰富的汉文典籍,这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游自勇统计了《天地瑞祥志》残本征引的文献,说有250种以上[4]。但实际可能没有这么多,许多书应该是重复的篇目,如《京房别对灾异》《京房灾异》《灾异》应该是同一本书,《异物志》与《临海异物志》也当是同一种书。有的则是因错而导致重复统计,如《部老目旧传》应该就是《陈留耆旧传》。如果去掉重复,目前所见残本《天地瑞祥志》征引文献可能有200种左右。这其中《禽物载》《兽物载》所引诗、赋、表、赞等艺文类作品都是以单篇形式记数的,有四十多篇。如果这些单篇艺文也计入,那么残本《天地瑞祥志》引书或达到250种。当然,更大可能是,这些单篇艺文出自某一种书或某几种书,所以残本《天地瑞祥志》引书约有200种。如果考虑到完本《天地瑞祥志》有二十卷,而残本只有九卷,若以完本计算,它实际引书数目肯定会远远超出这个数目。但即便是200种,这个数目也已经非常可观了。人们不禁要问,萨守真是如何获得这么多文献资料的?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萨守真是在新罗还是在大唐完成《天地瑞祥志》编纂的?
权悳永认为“如此大量的资料,在当时的新罗国内是搜集不到的”,推测“薛守真在唐朝留学的时候,出于个人兴趣而开始编纂天文地理书,基本完成之时回国,到新罗之后最终完成定稿。新罗的留唐学生往往将自己在唐朝撰写的东西,回国后修改补充,呈献给国王,新罗晚期的崔致远即有此经历”[5]。对此,赵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根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列传》记载高句丽“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的内容,认为“高句丽一地的文献已经涵盖了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同时又据《东夷列传》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赐新罗“《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而《晋书》正是萨守真编纂《天地瑞祥志》重要文献来源,认为“新罗接受汉文典籍的程度已经很高”,“《天地瑞祥志》的编纂完全具备充分的文献基础”,因而“不必非是留唐时所为”[7]。
两说皆有依据,也都有成立之可能。但两说又都有可商榷之处,因为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萨守真或许不需要这么多文献便可以编纂《天地瑞祥志》。我们以纬书为例,《天地瑞祥志》引纬书达27种,如果依照《隋书·经籍志》将郗萌的《春秋灾异》和无名氏《孔子王明镜》也纳入统计范围,其征引纬书达29种。其中《春秋》类纬书则包括《春秋纬》《春秋演孔图》《春秋合诚图》《春秋保乾图》《春秋考异邮》《春秋说题词》《春秋感精符》《春秋潜潭巴》《春秋元命苞》《春秋运斗枢》,几乎含括所有的《春秋》类纬书。中土纬书类文献屡遭禁毁,《隋志》记载梁时尚存《春秋》类纬书,隋唐之际大多已经亡佚。如果说偏远的新罗还有如此丰富完备的纬书文献,却也很难让人相信。这就不能不让我们猜测,萨守真应该是借助他此前的星占类文献才获得如此多的纬书材料。
如果说关于《天地瑞祥志》中纬书材料来源还只是推测的话,那么该书中诗赋等艺文材料的获得则可以肯定是借助了类书,尤其是《艺文类聚》。
《天地瑞祥志》征引了较多的诗文作品,根据统计可知共42条,涉及诗、赋、颂、赞、表、文、论等多种文体,其中以诗赋最多。除了涉及《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外,就作者论,这些作品还涉及李陵、班固、曹操、曹植、王粲、刘祯、薛综、王肃、嵇康、成公绥、枣据、傅玄、刘琬、郭璞、孙绰、曹毗、湛方生、桓温、孝武帝刘骏、简文帝萧纲、萧统、刘孝绰、刘孝仪、庾肩吾、朱超、萧琳、虞世基等诸多作家。这些作品大多为单篇节选,鲜有完整篇章。这引起了笔者的好奇,萨守真是如何获得这些材料的?通过比较发现,《天地瑞祥志》所引诗赋作品和《艺文类聚》[10]的重合率很高。仔细排比这些艺文材料发现,42条材料只有3条不见于《艺文类聚》,其余皆在。不仅如此,还有几个引文的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天地瑞祥志》和《艺文类聚》之间的关系。第一,和《艺文类聚》一样,《天地瑞祥志》引诗赋也是节选。而39条材料只有《楚辞·招魂》和曹植《恶鸟论》引文有差别,其余引文的起止及句数皆相同。个别文字有差别,大多是因为抄写所致。第二,一般说来,《艺文类聚》在同一条目下常引好几首作品,而《天地瑞祥志》大多情况下引1条。但不管是诗赋还是赞表,这些艺文绝大多数为《艺文类聚》中所引艺文的第一篇,少许为最后一篇。这种位置特征有助于我们判定《天地瑞祥志》和《艺文类聚》的关系,因为这反映了编纂者在摘录材料时的某种便宜心理。第三,《天地瑞祥志》引诗赋等材料,常在前面标注文体,如“诗梁朱超《城上乌诗》”“赋晋傅玄《鹰赋》”之类,这很显然是继承了《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原有的体例。第四,卷十九引刘琬《神龙赋》,谓“晋刘琬”[1]434。而《艺文类聚》卷十六引《神龙赋》亦谓“晋刘琬”,二者相同。因为文献不见晋朝有刘琬的记载,所以一般认为《艺文类聚》的“晋刘琬”当是“汉刘琬”之误[11]。而《天地瑞祥志》亦谓“晋刘琬”,极大可能也是误书,而且是承《艺文类聚》之误。第五,卷十八引晋成公绥《鸿雁赋》曰:“轩翥鼓翼,杭志万里。过云梦以娱游,投淮湘而中憩。”[1]400据《初学记》,知“过云梦”句前至少还有“奔巫山之阳隅兮,趋彭泽之遐裔”[12]735。《艺文类聚》常节录文献,因而省去两句,而《天地瑞祥志》也如出一辙,便让我们不禁认为二者间的因循关系。第六,卷十八《鱼》引晋王肃《贺瑞应表》,较之《艺文类聚》多出“又曰:鼎,元吉亨。其彖曰:鼎,象也,圣人以亨上帝”[1]412。比对发现,“又曰”以下文字在《艺文类聚》中属于紧挨着的《鼎》条内容[10]1719,可以断定,编纂者误抄了《艺文类聚》的内容。除了这些诗文间的继承关系,其他的证据也可以证明两者有关系。比如卷十八《鹣》引了《尔雅》《山海经》《瑞应图》和郭璞的《比翼鸟赞》[1]399,与《艺文类聚》祥瑞部“比翼”类所引完全一致[10]1710。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也不局限于艺文,因此几乎可以认定《艺文类聚》是《天地瑞祥志》重要的资料来源。甚至可以具体说,《天地瑞祥志》从卷十三到卷二十的材料都主要取自《艺文类聚》。
除了《艺文类聚》外,萨守真应该也参照了其他类书,比如《修文殿御览》《初学记》之类。就诗文等艺文作品而言,其他几条不见《艺文类聚》的材料则和《初学记》有关,如薛综《赤乌颂》[12]733。卷十八引曹植《恶鸟论》[1]407和《艺文类聚》鸟部“鸠”条[10]1600、人部“讽”条[10]432引文差距较大,但和《太平御览》[13]引文很相近。考虑到《太平御览》和《修文殿御览》等前代类书间的关系,推测萨守真或是利用了《修文殿御览》等材料。以此类推,《天地瑞祥志》前几卷有关星占的内容也当是采自其他的星占书。这一点上文已作讨论,于此不赘述。
总之,萨守真编纂《天地瑞祥志》应该主要是参考《艺文类聚》等类书,以及相关的星占书进行编纂。尽管统计《天地瑞祥志》的残卷已涉及200种左右的书,但实际上萨守真也许不需要太多的书便可以进行编纂工作。这样看来,权悳永以《天地瑞祥志》引书多而担心其不能在新罗编纂实际上是多余的,而赵益考证新罗地区已拥有较多的中土文献从而认为萨守真有可能在新罗编纂也意义不大。但问题是,是不是用到的书少就一定能在新罗编纂呢?答案恰恰相反。通过考证《天地瑞祥志》和《艺文类聚》的关系,笔者认为该书不可能在新罗编成,理由如下。
第一,尽管文献记载《艺文类聚》的编纂始于武德年间,纂成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武德七年。但有学者研究认为,《艺文类聚》虽纂成于武德七年,但编成之后并没有及时颁布,“其颁下时期可能在太宗即位以后,千秋功业,太宗攘以为己有”。所以欧阳询《艺文类聚序》避李世民讳,改“皇帝世代膺期”为“皇帝命代膺期”,而序中欧阳询的职官为“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也是其贞观初任职。过去以为是好事者所改,学者认为可能是颁布时所改[14]。但不管《艺文类聚》颁布时间是在武德七年还是在贞观年间,距离《天地瑞祥志》编纂之麟德年间都不算久远。因此,考虑到抄本时代书籍传播的实际情况,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百卷《艺文类聚》不可能在编成不久就传到新罗,并能为萨守真所用。
第二,《艺文类聚》是一部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的官修类书,若传入域外便具有了颁赐功能,能彰显华夏天朝的文化声威,所以一般情况下文献或有记载。正如上文所说,唐太宗赐新罗《晋书》,史书便有记载,但是文献中并没有关于唐朝颁赐《艺文类聚》给新罗的记载。
第三,根据文献记载,中国类书最早进入韩国地区是在高丽宣宗十年(1093年)也即宋哲宗元祐八年[15]。当时高丽黄宗悫入宋献上《黄帝针经》并提出购求书籍,但遭到了苏轼的反对,最后所采只是《册府元龟》。高丽肃宗六年(1101年),文献记载宋徽宗赐给韩国人《太平御览》。因此,《艺文类聚》可能并未更早传入新罗。尽管萨守真编纂《天地瑞祥志》所需要的书并不多,但仅仅依据该书与《艺文类聚》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应该就可以推断该书首先是在中土大唐完成的。
综上,通过对《天地瑞祥志》所涉及材料的勘察,我们认为该书的编纂主要利用《艺文类聚》之类的类书工具书,而其编成地点应主要是在大唐。其编纂方式主要通过这些类书中摘录一些相关资料,“以类相从,成为廿卷”。其中二至卷十二为天之祥瑞,卷十三至卷二十为地之祥瑞,合称“天地瑞祥志”。
三、由所引诗赋看《天地瑞祥志》的编纂缺失
萨守真为什么要编纂《天地瑞祥志》?这一点在其书前启文中有明确的交代。其曰:
伏奉令旨,使祗承谴诫,预避灾孽,一人有庆,百姓右安,是以臣广集诸家天文,披览图谶灾异。虽有类聚而相分,事目虽多而不为条贯也。……然则,政教兆于人理,瑞祥应乎天文。……观图諜于前载,言涉于阴阳,义开于瑞祥。纤分之恶无隐,秋毫之善必陈……所谓“瑞祥”者,吉凶之先见,祸福之后应,犹响之起空谷,镜之写质形也。[1]315-319
据此,萨守真分类纂集祥瑞,其目的是为了彰显“政教”与“人理”,“瑞祥”与“天文”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瑞祥”之“吉凶之先见、祸福之后应”警示作用,以期为执政者的“修政”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治理范本,“祗承谴诫,预避灾孽”,从而达到“灾消而福至”的政治功用。而这种通过“瑞祥”警示吉凶祸福,希望执政者“祗承谴诫”的编纂思想贯穿全书,这一点从他文献征引以及注解中不难发现。在此,笔者特以其《招魂》注解为例加以论说。
作为楚辞类作品,《招魂》一般被认为是宋玉哀悼屈原,或以为是屈原哀悼楚怀王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没人将之与灾异祥瑞关联在一起,即便是汉代灾异说的大家刘向也未曾这样处理。但在《天地瑞祥志》卷十四《魂魄》中,萨守真重点从灾异的视角对《招魂》作了解读。试举几例:
(1)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讬。长人千刃,唯魂是索。十日代出,流金烁石。守曰:其国君闇,群臣争起,故《京房易传》曰:无道之臣与君争起,其日七八并出之也。(1)按照朴胜鸿的研究,文中的“之也”属于新罗人吏读用语,无意义。
“十日代出”涉及扶桑神话,王逸《章句》以及洪兴祖《补注》皆从十日神话角度注解这一句,和灾异无关[16]。萨守真遵照传统星占理论和比附模式,以日为君道,将“十日代出”解释为君臣相争。
(2)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得人以祀,以其完骨为醢。蝮虵蓁蓁,封狐千里。守曰:蝮首大如臂,身广三寸,毒蛇煞人也。蓁蓁,众盛貌也。封狐,[大]狐也,言有大狐也。言南方之国君失国家之礼,故《洪范》曰:人君不得其中,不能立万事。龙,虵之蘗号也,弃,妖狐自远方来,告其君恶之也。
蝮蛇、封狐,就训诂而言,萨守真所注与王逸、洪兴祖差别不大,皆是从形貌特征的角度作的一种描述性解释。但“言”之义理则大有不同,王逸《章句》认为南方皆是啮人的兽物,说明了身处环境之恶劣、不可久留;而萨守真则从政治灾异论的角度解释,认为蝮蛇、大狐的出现代表了君主失礼、国家失政。
(3)魂兮归来,西方之国,五谷不生,菆葌是食,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守曰:菆,小叶草名也。葌,香兰之类也。言西方之国,有常旱灾。《洪范》曰: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常旱,伤百,但食草木,其完不能,热燋犹如烂之也。
这里王逸《章句》的注解仅仅涉及西极之地自然环境恶劣的层面,而萨守真则另发挥,引《洪范五行传》的说法,将之比附为国家政治失序、刑罚妄加,以致阴阳失调、天降旱灾。
(4)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守曰:北方之国,有常寒灾。《汉五行志》:听不明是谓不谋,厥罚恒寒也。秦始皇其政忽暴则夏寒,有冻死者,此类也。[1]364-365
此条“守曰”注文,也是附会政治灾异说,认为北方常寒的自然环境是上天对君主无道、施行暴政的惩罚,并举秦始皇之例加以说明,而王逸《章句》则完全不涉及此说。
可以发现,《楚辞·招魂》的这几条注文,全不用王逸注,而以萨守真自撰的“守曰”形式出现,并引用《京房易传》《洪范五行传》和《汉书·五行志》等作政治灾异论的解释,主旨是将《招魂》所谓“四方之恶”归结为国家政治失败所致。在这里,萨守真皆从“祥瑞”与“治道”相关联的角度进行解释,充满“以诗言政”的政治功用色彩。他认为《招魂》文本中描绘的东方十日并出、南方得人以祀、西方五谷不生、北方冰雪千里的四方恶劣世界,是君臣失礼、国道沦丧所致的灾孽之变,是天意对君主和王政的谴诫[1]368。
从另一个角度看,王逸所建立的楚辞阐释系统,在楚辞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萧统编次《文选》时采录《楚辞》,李善注《文选》,《楚辞》类作品的注悉采自王逸《章句》。《隋书·经籍志》云:“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以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17]由此可见,王逸所注《楚辞》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也有相对较大的稳定性。但《天地瑞祥志》的编者萨守真自行对《楚辞·招魂》所作的这些注解,则基本舍弃了王逸的注释,尤其是义理言说的内容全凭一己之见,为符合其编纂主题,完全从政治灾异的角度解说。这种做法在传统《楚辞》学语境中很难被接受,也全然不符合传统中国学人的注释风格。

尽管萨守真在其启文中明确地表达要以“祥瑞”观治道的思想观念,而且通过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萨守真的初衷是想编纂一部内容上关于“祥瑞”的书,但这一思想,并没有完全贯彻到他对于诗文的征引选录中。细究《天地瑞祥志》所引艺文,发现实际情况更加复杂。除了前文所述的赋、颂、赞这三类文体与祥瑞之物有着比较明显的关联外,《天地瑞祥志》所引诗类,从内容上看,大多并非是吟咏祥瑞的,也极少有表达祥瑞思想的诗篇。编纂者在“禽”目之下“越鸟”类引《古诗十九首》“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1]394,“凤凰”类引枣据诗“有凤适南国”[1]395, “鸾”类引嵇叔夜《赠秀才诗》“双鸾匿景耀”[1]397、王粲诗“翩翩飞鸾鸟”[1]397,“鹄”类引曹植诗“双鹄俱遨游”[1]399,“凫”类引梁简文帝《咏寒凫诗》“回水浮清浪,沙场弄羽衣”[1]400,“乌”类引梁朱超《城上乌诗》[1]404、虞世基《晚飞乌诗》[1]404-405,“鹊”类引魏太祖曹操歌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1]405, “燕”类引虞肩吾《咏櫩燕诗》[1]406等,这些诗赋在内容上与灾异祥瑞等数术理念毫不相关,而且主要表达的是一种个人的感性情绪,多与祥瑞之征无涉。由此看来,萨守真对诗赋赞等文艺作品的选录十分混乱,并没有严格遵循自己所设的以“祥瑞”为中心的标准。
我们再将之与《艺文类聚》相比较来看,《艺文类聚》在鸟部的“乌”“凤”“鸾”“雀”“燕”“鸠”“雉”,在兽部的 “马”“狐”“鹿”“兔”“驺虞”,在麟介部的“龙”“鬼”“鱼”, 卷九十九祥瑞部也同时设有这些属类,但仔细辨别两处的引文可以看出,《艺文类聚》在分类征引的时候是比较严格地区分了它们作为一般鸟兽之物和祥瑞之物的不同。以“凤”为例,鸟部凤类中引的是《说文》《毛诗》《礼记》《论语》《庄子》等经学文献和子部文献,主要是将凤鸟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加以描述说明,而祥瑞部下凤凰类中引《瑞应图》《孝经援神契》《礼斗威仪》《尚书中侯》《春秋合诚图》等谶纬文献,突出的是凤凰的祥瑞意义。但是《天地瑞祥志》从中引录的时候,却并没有严格遵循祥瑞的标准,如在禽物“凤” 类中前面所引文献基本是与《艺文类聚》祥瑞部凤类相一致,但引录的艺文却又是《艺文类聚》鸟部凤类中汉李陵和晋枣据的两首诗,与祥瑞之义关系不大,而《艺文类聚》祥瑞部凤凰类中是明显将凤凰作为祥瑞物加以书写颂赞的晋顾凯之《凤赋》、吴薛综《凤颂》以及晋郭璞《凤鸟赞》,萨守真却一条未引。既然是以祥瑞为中心进行编纂,就应该集中引录《艺文类聚》祥瑞部的文献,但萨守真却将《艺文类聚》在鸟部“凤”类、祥瑞部“凤”类文献杂糅其中,显得自相矛盾、不伦不类。《天地瑞祥志》中除了郭璞的《比翼鸟赞》《驺虞赞》《白狼赞》,薛综的《白虎颂》,王肃的《贺瑞应表》,刘孝仪《为始兴王上毛龟表》是引自《艺文类聚》祥瑞部,其他类中的艺文绝大多数皆是出自《艺文类聚》鸟部、兽部以及麟介部,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艺文类聚》相同类在对应的祥瑞部中没有引诗文,但这也是《艺文类聚》相较《天地瑞祥志》在体例上更为严谨的地方,毕竟很多诗文虽然内容上有所涉及,但严格说来并不是抒写祥瑞的作品。
笔者认为,正因为《天地瑞祥志》整部书的编排体例有模糊之处,导致其归类的困难。《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将《天地瑞祥志》归入天文类,朴胜鸿也认为这是一本天文书,水口干记认为这是一部以天文为中心的类书。其实从内容上严格区分的话,《天地瑞祥志》具有天文占书和艺文类书的双重属性。除第一卷为该书“条例目录、明灾异例、明分野”等总论之外,卷二至卷十二可以视作“天”的内容,其中“广集诸家天文”,辑录了大量与天文星占相关的资料,这可以归为天文占书一类。而下半部分卷十三至卷二十则可视作“地”的内容,包括各类梦物、鬼神精怪、农业植物、服用器物、飞禽走兽、祭祀等多个方面,在内容上呈现出杂录汇编的特点,特别是辑录有不少诗、赋、表、赞等文学作品,这在《开元占经》等占书中是从未见引用的。因此,这部分似乎更倾向于是综合性的类书,与《艺文类聚》等类书有些相似,而且体例上“地”的部分也很大程度承袭了《艺文类聚》的“以类相从”“事文并举”的编排格式,采取经史子文献在前,诗文作品在后的模式,所引文献皆注明出处,尤其所引诗文作品按“诗”“赋”“赞”“箴”等字标明文体类别。同时,详细注明作品的时代、作者和篇名等,完全是效仿类书的体例。
从表面上看,以上看似混乱的引录编排是编者萨守真对材料筛选甄别的标准不一,从而导致了体例不谨的情况,但从深层次来看,这暴露出了编者萨守真对传统中国的祥瑞灾异学的理解困惑,甚至存在诸多误解和不通达之处。同时,那些在我们看来完全与祥瑞意义无关的诗文作品,在他的思想观念中皆可从祥瑞的角度加以征引,而且萨守真对整部书的编排也可以说是在一种不太专业的灾异学说和祥瑞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点除了导致《天地瑞祥志》编纂的一些缺失,也可进一步佐证编纂者萨守真并不是中土唐人这一推断。所以,朴胜鸿推断这本书是萨守真留学唐朝时所编是有道理的。不惟如此,启文“率愚管轻为撰著”云云透露萨守真编纂起始是一种个人行为,回国后进承大王殿下时应该又作了一些调整,比如增加注文。
综上,《天地瑞祥志》的注文、所引诗文等对我们研判该书的编纂有较大的价值。然而,今天所见《天地瑞祥志》为日人转钞本,已非该书原貌,因而文字讹误以及语句舛乱之处较多,这也对我们判断该书编纂相关问题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做出有关《天地瑞祥志》的研判时,需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