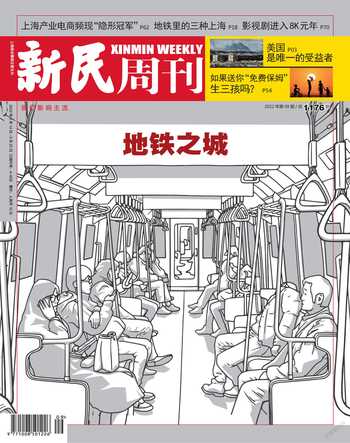地铁站里,看见新式浪漫
2022-03-25吴雪
吴雪

上海地铁14号线,五彩缤纷的彩灯艺术造型。
在上海地铁博物馆,有一张老照片,上下班高峰的时候,上海55路公交车上的一平方米可以挤下11个人。据上海地铁博物馆副馆长梁伟杰介绍,当年这辆车到站时,有人好不容易挤上车,下车的时候又是困难重重。一些市民挤车门、推车门的情形至今令人难忘。
那时,北京、天津都已有地铁,上海造地铁曾被专家认为在“豆腐里打洞”,难度可想而知。1993年5月28日,上海1号线南段投入观光试运营,当时人们乘车难、过江难、行路难,而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正是从根本上解决市民出行难的必然选择。
地铁发展初期,交通属性显然是地铁的主要属性,乘客们乘坐地铁的目的只有一个:便捷出行。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中国大城市的地铁也开始从功能地铁向人文地铁转变,许多城市开始尝试让公共艺术介入地铁空间。
在上海,每天,有超1000万人次在上海地铁中穿行。人们在这个空间,聚集,停留,又涌向楼宇街巷。
陆家嘴的“今朝踏浪”大屏;吴中路站的圆顶拱形设计;汉中路的“地下蝴蝶魔法森林”,都让地铁站蒙上了一层科技艺术的质感与浪漫,引来无数市民打卡停留。而当你将目光放眼世界各国的地铁线路,在艺术这个议题上,它们又总能藏着惊喜的彩蛋。
艺术家薛峰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一列地铁多了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其肌理延展出的视觉设计、布局交错,所产生的新的城市景观,将会是公共空间里一种全新的开拓。
不可否认,3D 巨幕、灯带、超大屏,几何结构,与当代艺术的结合,成为了地下空间的新式景观。
在看似不起眼的地下空间,历史、现代、魔幻不断穿插碰撞,像一部纪录片,又像一支变奏曲。上海地铁14号线开通后的三个月,“一站一景”的站厅不像刚开通时那么喧闹,但来打卡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旅行达人kimi在社交平台上,剪辑1分钟视频推荐豫园站。画面中,蜿蜒的灯带变换着颜色,其曲线的造型,似黄浦江的江水,有韵律地流动着。浪尖的几何造型还借意城隍庙飞檐的轮廓倒影,打造成极具科技未来感的创新站点。
这一出圈的设计《上海脉搏》,出自ToMASTER明日大师团队之手,作为上海地铁最深车站(3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基于对在地文化的深度思考,设计师希望用纯粹形式来诠释多个层面的丰富性,融汇东西方建筑风貌,连接历史、当代与未来。
在展厅中间醒目位置,还悬挂着一个名为《魔都律动》的艺术装置,是一个橙色球体的分层片状构造,结合优美的律动,反映都市快速发展与慢生活的平衡关系。薛峰告诉《新民周刊》,地铁属于半封闭式空间,易于做一些主题视觉设计,其公共艺术形式又有别于商场、地面空间,没有东西南北的延伸,但各个站点会有个性化的思考在里面,是当代艺术的缩影。
15号线吴中路站的无柱拱形结构,也一直在旅行大片中频繁露出。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站点在上海地铁车站设计中属于突破性的建筑尺度上的创新。为充分利用无柱拱顶结构的纯粹感,站厅内隐藏了肉眼难辨的细节,比如逃生线、摄像头等,还取消了广告位。
不可否认,3D巨幕、灯带、超大屏,几何结构,与当代艺术的结合,成为了地下空间的新式景观。上海14号地铁线总设计师郑鸣表示:“我们既有建筑本体的审美特征,同时又能有一些隐喻的含义在里面,真正达到了用空间艺术打造艺术空间的效果。”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地铁建设时并不考虑艺术风格,艺术与站点的结合也不紧密。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设计系副系主任孔繁强说,在节约成本的标准化设计下,车站建筑空间通常是单一的“方盒子”,乘客不看站名,就分辨不出站点。
比如,上海第一条通车的地铁1号线,略显艺术的呈现往往在于廊道两边的灯箱喷绘和风景壁画。后来,地铁2号线、3号线陆续建成通车,站内艺术氛围渐渐浓起来。2013年初,上海地铁启动公共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把浮雕壁画、陶瓷、玻璃等装饰艺术引进地铁车站。

上海K11 公共空间地铁口可看到可愛的涂鸦作品。摄影/ 王凯

2019 年,在上海地铁1 号线徐家汇站举办的“三毛之父”张乐平作品展。
以上海地铁13号线为例,淮海中路站的设计,与过去点状公共艺术方式不同,采用了红砖墙、鹅卵石墙面、铜制站牌等艺术语言呈空间化穿插;自然博物馆站更用了大量陶土板和石头材质作为内部装饰,在站厅内打造“溶洞”。
最近十五年里,伦敦也一直致力于把艺术作品变成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并引入当代艺术,这个已有154岁的地铁系统甚至还有一个自己的地铁艺术项目组。他们常常把博物馆里的元素,巧妙嵌入地下空间,试图开发这个空间与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
薛峰谈及2019年,他曾专门参观过由法国艺术家丹尼尔·布伦用波普艺术新翻修的伦敦托特纳姆宫街地铁站。简洁的黑白色条纹几何图形墙,因加入橙色、红色、绿色、蓝色的几何图形,而显得更加跳跃活泼。
“改造之前,这里充斥的是爱德华多·包洛奇的马赛克壁画。当2015年传出消息,大约有5%的壁画将作为车站翻新的一部分而被拆除时,还引起过不小的争议。”薛峰说,事实证明,改造后的站点更迷人了,每天有15万人,在这里近距离欣赏丹尼尔·布伦的作品。
要知道,在此之前,这些作品还只能在蓬皮杜中心、LV 基金会、古根海姆美术馆等地方看到。
如果说,地下空间的当代艺术馆、博物馆是通过视觉冲击吸引大众喜爱,那么,有文化气息的展览或橱窗设计,则是通过有故事的内容留住人们的视线。
“有些站有传统色彩,也有新的科技介入,各种流派围绕一个肖像、一个地标,用特有的表达重组,产生新的风格。游客来乘坐地铁,不再是为了到达某一个目的地,这就体现了地下空间的文化意义。”薛峰告诉《新民周刊》。
乘上海地铁10/11号线,经过交通大学站的乘客,通常会为地铁走廊上一面艺术墙停下脚步。艺术墙中心是一块较为周正的三维空间,通过立体的设计将钱学森手稿中的文字符号化,再在中間区域利用这些符号重构钱老的头像。
当乘客从艺术墙前经过,随着步伐远近与视线变换,不同层次的钱学森视觉肖像,缓慢变换呈现。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的杰出校友,橱窗里,被妥善装裱展出的藏品,包括钱学森的成绩大表、本科毕业证书、发表在《空军》杂志上的论文等,让人们对钱学森有了更深了解。
而同济大学站一直被称为上海最有文化气息的地铁站。
矗立在站厅,抬头望去,设计者通过天窗设计巧妙地把阳光从同济校园直接引入车站,向上挑高的一角藏有国画大师汪观清的作品《梦里徽州》。站内工业风的站台、水墨画的立柱,以及大量土木搭建的结构,似乎呼应了同济招牌土木工程专业。
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金江波看来,不同站点分布在城市不同区域,而每个区域又有独特的人文地理特征。艺术的介入若是与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市民生活方式相勾连,其“在地性”不仅能够启迪心灵,还体现城市品格与精神。
比方说,上海4号线海伦路地铁站虽开通较早,但其站内墙上满是鲁迅先生的画像、名句、作品,道出了鲁迅先生和虹口的渊源;18号线丹阳路站,黑白电影感的设计,黑的一面墙上介绍着杨浦百年工业历史,白色的墙面上则有电子屏展示新杨浦的发展景象。
除了地铁站点与空间的联系,城市特色与空间设计的呼应也越发紧密。
南京作为一座藏着 40 多处《红楼梦》遗迹的城市, 夫子庙站艺术墙的主题为“除夕夜宴”,表现了群芳夜宴寿怡红和除夕夜宴猜灯谜的场景,墙上以贾母为中心,贾宝玉等人分立左右,侍女们端着食盒随在其后,秦淮名小吃跃然墙上。
千年古城雅典因丰富而珍贵的考古文物而闻名,在修建地铁之初,就设计打造“地铁里的博物馆”。在站厅,乘客可以观摩当地发掘的古代生活用品,如双耳瓶、陶瓶、黄金首饰等,还能阅读古代希腊的经济、政治、宗教及日常生活的内容。
当然,现实问题是,地铁在修建之初,很难将人文价值考虑周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章莉莉的一项工作目的就是为地下空间条件较好的地铁站点里的公共艺术留白,汉中路站的设计就应运而生。在增添地铁文化韵味上,许多城市也并非从大规模的空间设计着手,而是从优化车站装饰细节开始。
近日,在杭州东站,站台层扶梯三角区上的“火车东站”四个字,换上了新的“苏东坡”字体。新字体的左下角还有一枚刻有站名的印章,一句唐诗。这个颇具江南韵味的“字+印”的组合,正是杭州市地铁集团联合西泠印社进行的视觉优化设计。
作为杭州地铁的指示标志,让人以字识站,以字共情,成为市民和游客认识杭州的“第一站”。地铁站名印还采用了浑厚古朴的汉官印,一些重点车站的印章将由西泠印社知名篆刻家进行篆刻,未来还将制作一套站名章复制品,放在各个站点供市民乘客“打卡”集章。在上海,14号线用紫砂制成的站名墙,设计理念也取自于传统书画艺术。在香港,港岛线地铁站,全线最有特色的是除了杏花邨站及柴湾站外,站牌都是书法字体。它们都出自前议员区杰棠笔下,区杰棠写的第一个站名是“金钟”,“看着就像一幅画,仿佛还能听到钟声。”据说是因为港岛线的月台大多都是比较窄的,为了让月台的乘客舒缓紧张情绪专门进行了这样的设计。


上海新天地太平湖秀场,一场以都市地铁车厢为背景的秀。摄影/庄毅
随着地铁空间的发展,地铁衍生品及文创,也逐步成为地铁艺术的一种形式。
李龙是收藏地铁卡的行家。从1996年开始关注并收藏地铁卡到1999年自己创建中国地铁卡网,一直与地铁卡有着不解之缘。之前收藏的地铁卡相对单一,比如,生肖卡、拜年卡。近年来,上海地铁开始跨界创新,与大耳狗、胖虎、天文馆等各类IP联名,在建党百年、冬奥会等重大节日推出纪念卡等。
在梁伟杰看来,除了地铁票卡,“可阅读”的地铁站以及车厢,也是重要的地铁文创载体。
特别是在人民广场站建成“上海地铁音乐角”“地铁文化长廊”“中央展台”核心文化圈,形成了以人民广场站为核心,4号线环线则为文化环线,文化列车、车站建筑艺术、地铁票卡、虚拟空间等为展陈形式的地铁公共文化体系。
网络一片赞扬声中,同样有质疑的声音。“地铁站就是运人用的,如此搞地铁艺术,值得吗?”地铁中人流量大,步履匆匆,能停下来仔细观摩艺术品的人少之又少,“地铁公共艺术”对公众审美能否产生有效作用?”
对此,有专家回应:公共场合的色彩、设计对社会的影响是潜意识层面的,无意中看到的东西会慢慢影响大众的审美趣味与人文情怀。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柳立子认为,一个城市在地铁网线达到500公里之后,地铁对于城市的功能和意义就会开始变化,转而承载产业方面的诸多功能。
当今中国,地铁在承担市民出行和城市文化形象的同时,同样创造着产业价值,甚至可以改变城市格局。这反过来要求城市管理者,在地铁建设的过程中,不仅仅考虑到通行性、安全性和经济性,还要通盘考虑,站在整个地区综合经济体的高度上,全面考量和提升其价值。
薛峰认为,地铁艺术作为稳定场域的公共艺术,要根据不同的地方、环境去构思,规划。媒介出来以后,需要表达公共艺术的集群介入。比如,豫园路站由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做新媒体的艺术家等组成,不同专业的人共同打造这样的空间,跨界合作也让地铁艺术更精彩。
目前,中国地铁公共艺术发展需要有稳定的资金投入和保障机制,也需要有运营负责地铁公共艺术展览和活动,以及文创产品开发的主体单位,才能得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繁荣。地铁是“十年建设、百年运营”,地铁公共艺术更是“百年运营”中重要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