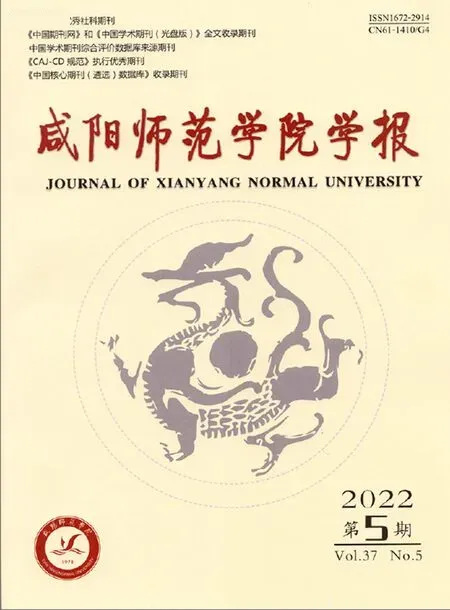班固《汉书》的“英雄观”
2022-03-24王长顺
王长顺
(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作为一部文史典籍,《汉书》记录了西汉一朝的历史人物,展现了西汉的历史风云,也反映了儒家正统的封建思想。这些思想中包含着的“英雄观”也值得人们关注。
一 班固“英雄观”的思想基础——封建正统思想
作为史学家,班固及其父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可见当时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体现儒学正统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合法性。班固认为,文章典籍应当褒颂盛世王朝,因而像赞颂前代帝王那样赞颂汉代诸帝。他在《汉书·叙传》中说:“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1]4235对此,王充也予以了肯定,《论衡·须颂》:“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2]198班固在《典引序》中还说:“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盖咏云门者难为音,观隋和者难为珍。不胜区区,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戆,顿首顿首。”[3]2158-2159可见,“光扬大汉”是班固宣汉思想的表达。因此,其“英雄观”也应具有封建正统性质,符合封建道德伦理,为君权统治服务。下面,以班彪的《王命论》、班固有关论说见正统观念对其“英雄观”的影响。
首先,帝王的统治地位是“天命所授”,其能称为“英雄”是“天命”“神意”。班固《汉书·叙传》中录其父班彪《王命论》:“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济四海,奕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民,其揆一也。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暗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1]4208-4209在班彪看来,历史上唐尧虞舜的帝位继承都是天命,后稷、契受天命辅佐唐尧虞舜,其荣光泽于四海,美德被于后世。尽管商汤、周武改朝换代的方式不同,但也都应天命,顺民意。汉高祖刘邦续接火德,彰显赤帝符应,加之明圣显懿的德行、世代累积的基业、精诚通达的智慧等,最终能为鬼神所佑护,天下百姓归附。
班彪认为,无论是达官富贵,还是贫贱平民,都应当知命以顺应天子。他说“夫饿馑流隶,饥寒道路,思有短褐之亵,儋石之畜,所愿不过一金,然终于转死沟壑。何则?贫穷亦有命也。”[1]4209一时得势的权贵也不能违背天意去夺取王权,“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幺么,尚不及数子,而欲暗奸天位者乎!”[1]4209帝王天命之分决定了一切,“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审此四者,帝王之分决矣。”其《王命论》曰:“当秦之末,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之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而刘氏之将兴也。是时陵为汉将,而母获于楚,有汉使来,陵母见之,谓曰:‘愿告吾子,汉王长者,必得天下,子谨事之,无有二心。’遂对汉使伏剑而死,以固勉陵。其后果定于汉,陵为宰相封侯。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1]4210-4211说明帝王乃是天命安排,这样的道理连匹妇都明白,从而能够“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明白如“大丈夫”者,更应该明晓。
其次,文臣武将“英雄”的辅佐只是对帝王成就帝业这一“天命”的顺应。班彪陈说汉兴的原因:“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1]4211汉高祖刘邦之所以兴汉的五个原因中,三个都有“神”的特征,“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则是高祖自身的修为。而这种修为的具体表现是:“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响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悟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收陈平于亡命。”[1]4211正因为如此,才能使得“英雄陈力,群策毕举”,而这些都是“高祖之大略”。更何况有灵瑞符应为证:“初,刘温妊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1]4211-4212因此,淮阴侯韩信、留侯张良都说高祖刘邦承接帝位,乃“天授,非人力也。”
再次,“英雄”也应当“知天命”“畏天命”。班彪《王命论》:“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1]4212就是说,考察古今得失、成败、兴衰之理,都应当“取舍与地位相称,灵验的征兆符合天命之意”,如果“不安本分”“不自量力”“不知天命”,就会遭遇凶险,受到诛杀。哪怕是“英雄”,也应当暗自醒悟,弃非分之想,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不信征伐,相信帝王的权柄自有天授,只有这样,才能使福分延及子孙后代,永世享受天赐之福。
班固亦有相似论说,《汉书·刑法志》:“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1]1090这与其父班彪所论如出一辙。刘汉乃是正统统治,是“英雄”施展才能的舞台。正如有的学者所论:“东汉时期,史学开始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光武帝时期,对史学尚重视不够。明章之世,随着机构化和组织化的官方史学的建立,以及历史著作审查制度的形成,这一时期的历史编撰特别是《汉书》受到皇权的格外眷顾,深深打上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烙印。权力不仅关心史家写作的内容,更关心史家写作的目的,其中既有皇权的监管、审查,又有宗室外戚的监督、指导,这些方面正体现了‘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的‘汉家之制’。权力的介入和审查制度,对历史写作进行了一种区分:什么是可以记录的,什么是不可以记录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是呈现也是遮蔽,是暴露也是压制,两方面都显示了历史写作背后绝对权力的存在。”[4]《汉书》实乃正统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史书显现,这也是班固“英雄观”的前提和基础。
二 班固《汉书》载录“英雄”的标准
尽管班固《汉书》没有明确提出“英雄”的标准、条件和载录原则,但我们仍可通过各人物记述看出班固正统观念下的“英雄”标准。
(一)帝王“英雄”的卓越功勋
班固在《汉书》中,对诸位帝王取得的卓越成就予以记载并弘扬,甚至认为汉高祖堪比周文王、周武王,其他诸帝也胜过周成王、康王、宣王。对于高帝,《汉书》论曰:“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1]80-81对于惠帝,记载其减民租、城长安等史实,评价惠帝“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可谓宽仁之主”[1]92。称颂景帝说:“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1]153称赞元帝能善用人,“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1]298-299。就记载和评价帝王功绩而言,既体现了班固宣汉的思想,也体现了实录精神。
班固《汉书》对帝王治世之功进行赞颂,以表“帝王英雄”之功德的诸记述中,尤以文、景、武、昭帝的论赞最能体现班固“帝王英雄”的载录标准。如《文帝纪》:“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1]134-135汉文帝注重节俭,施行仁政,减轻刑罚,“以德化民”,乃“仁德”之君。《宣帝纪》:“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1]275赞扬宣帝善于治理,吏治清明,“功光祖宗”,乃“中兴之君”。《武帝纪》:“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襢,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1]212颂赞汉武帝文治武功,雄才大略。《昭帝纪》:“赞曰: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1]233赞颂昭帝与民休息之策,体恤民间疾苦之举。
(二)人臣“英雄”的忠心、节义
帝王“英雄”业绩的取得,要靠忠诚人臣的辅佐,因此,班固在对帝王功绩予以肯定的同时,对忠臣良将也予以了称颂。在《汉书》中,班固采用了两种方式阐发其对人臣“英雄”标准的定义。
一是以记述人物言行反映出其“英雄”标准。如在《苏武传》突出了人臣的忠贞爱国。“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王死后,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1]2463苏武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牧羊,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他手握汉节,在九死一生中坚守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而“李陵劝降”一节则更加凸显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后李陵与苏武饮酒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苏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李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呼!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襟,与武决去。”[1]2464-2465详细记述了李陵苦口婆心的劝说以及苏武坚决的态度,升华了苏武忠君的形象特质。
再如于《霍光金日磾传》体现人臣“英雄”的忠君勤恳。霍光初以门荫,选为郎官,历任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所为公正,勤劳国家。汉武帝临终时,拜大将军、大司马,受命托孤辅政,封为博陆侯。辅佐汉昭帝,解除上官桀拥立刘旦阴谋,昭帝死后废立昌邑王刘贺,拥立汉宣帝即位。苏轼曾评价说:“霍光又有忘身一心,以辅幼主。处于废立之际,其举措甚闲而不乱。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于其成。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天下固有能办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则有侥幸之心,以一时之功,而易万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节’。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马仲达是也。天下亦有忠义之士,可托以死生之间,而不忍负者矣。然狷介廉洁,不为不义,则轻死而无谋,能杀其身,而不能全其国,故曰‘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古之人有失之者,晋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节气有余,此武帝之所为取也。”[5]63金日磾作为降汉的匈奴人,被封为御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平定马何罗叛乱。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病重时,随霍光、上官桀等人接受顾命,辅佐太子刘弗陵,班固《汉书》:“金日磾夷狄亡国,羁虏汉庭,而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姓金氏云。”[1]2967王夫之《读通鉴论》:“金日磾,降夷也,而可为大臣,德威胜也。武帝遗诏封日磾及霍光、上官桀为列侯,日磾不受封,光亦不敢受。日磾病垂死,而后强以印绶加其身。”[6]86
又如于《何武王嘉师丹传》体现人臣“英雄”的直言极谏。《何武王嘉师丹传》乃是何武、王嘉、师丹等忠臣合传。何武,两任刺史,能了解下情。为大司空,与丞相孔光议限民名田及奴婢,因外戚丁、傅用事,遂寝不行。后因反对王莽免官。因昌宽之狱见诬,自杀。王嘉,刚直严毅,官至丞相,见哀帝欲封宠臣董贤,上封事切谏,封还诏书。被哀帝借故下狱,乃绝食呕血而死。师丹,哀帝时为大司马,徙大司空,因贫富悬殊,乃建议限民名田及奴婢。以反对傅太后尊号忤旨,为外戚丁、傅诬陷,被罢官。该传以此三人皆忠鲠切谏终致祸患,合为一传。班固赞曰:“何武之举,王嘉之争,师丹之议,考其祸福,乃效于后。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贤之爱,疑于亲戚,武、嘉区区,以一蒉障江河,用没其身。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故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者也。”[1]3510西汉末叶,王莽专政,董贤用事,武、嘉所为,实是“以一蒉障江河”,必然失败。所谓“违俗则危殆”,意思是个人难以挽回大势。言之成理。
二是通过论赞直接表达“英雄”标准,称颂贤能良臣。《李广苏建传》赞曰:“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1]2469李广为天下人所悼念,已见其为人影响。苏武作为忠君之士,其“不辱君命”的行为得到颂扬。
《张陈王周传》赞曰:“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至登辅佐,匡国家难,诛诸吕,立孝文,为汉伊、周,何其盛也!始吕后问宰相,高祖曰:‘陈平智有余,王陵少憨,可以佐之;安刘氏者必勃也。’又问其次,云‘过此以后,非乃所及’。终皆如言,圣矣夫!”[1]2063称赞周勃以智勇辅佐高祖平定诸吕之乱。
《盖宽饶传》赞曰:“盖宽饶为司臣,正色立于朝,虽《诗》所谓‘国之司直’无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终其身,斯近古之贤臣矣。诸葛、刘、郑虽云狂瞽,有异志焉。孔子曰:‘吾未见刚者。’以数子之名迹,然毌将污于冀州,孙宝桡于定陵,况俗人乎!何并之节,亚尹翁归云。”[1]3269赞扬盖宽饶的直言谏诤,近于“古之贤臣”。
《王商史丹傅喜传》赞曰:“自宜、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史丹父子相继,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辅道副主,掩恶扬美,傅会善意,虽宿儒达士无以加焉。及其历房闼,入卧内,推至诚,犯颜色,动寤万乘,转移大谋,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无言不雠’,终获忠贞之报。”[1]3510史丹直言不讳进行谏诤,获“忠贞之报”。
《霍光金日磾传》赞曰:“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闼之间,确然秉志,谊形于主。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昔霍叔封于晋,晋即河东,光岂其苗裔乎!”[1]2967霍光忠于朝廷,其匡扶汉室的辅佐之才得到了充分肯定。
三 《古今人表》与班固“英雄观”
《古今人表》以古代人物为经,以品第人物为纬,按九品分了九栏。根据表序“上智”“下愚”的层次及表所分品第标准具体情况来看,表以人的品行为主,参之以事功的大小和学术的高低。表名“古今人物”,实际上列古人而无今人(汉代人)。尽管如此,也可从中推断班固对“英雄”标准的界定。
第一,重视“人”的存在。《古今人表》收录了历史上各个类别、各个阶层的历史人物,包括帝王、诸侯、文臣、武将、逸民、人师、诸子、商人、医者、工匠等等。“把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统统当作‘人’来审察评价,反映出班固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重人事的人文主义思想。”[7]班固《古今人表》把人物分为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三科九品,“上上”居首,上三品分别是“圣人”“仁人”“智人”,“下下”居末,为愚人。《古今人表》所收录人数众多,社会阶层广泛,既有远古先民氏族部落代表,又有帝王诸侯、文臣武将;既有游士刺客,又有先秦诸子;既有史官,又有商人、门吏、舟人、渔父。可以说,表中所列乃是历史上活动着的“人”的全记录。从这点可以看出,班固注重“人”的历史存在。
此外,《古今人表》评价人物,不以尊卑贵贱确定等级。君主被列在臣下的不在少数。如管仲被列为仁人,鲍叔牙被列为智人,而齐桓公却仅仅被列为中中。再如狐偃、赵衰和介之推被列为上下智人,而晋文公却被列为中上。诸如诸侯列在帝王之上,大夫列于诸侯之上,士人、平民列于大夫之上等品评结果比比皆是。
再看,《古今人表》从上古传说的伏羲氏到秦末,选取1 931人,上自三皇五帝、诸侯王臣,下至平民百姓,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职业汇辑于表,范畴广,体现了重视人,以“人”为中心的观念。
第二,不以尊卑、而以人物品格道德高低确定人物品评等级。班固在《古今人表》序中说:
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而诸子颇言之,虽不考乎孔氏,然犹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诫后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又曰:“中人之上,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传曰:如尧舜,禹、稷、契与之为善则行,鲧、讙兜欲与为恶则诛。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1]861
引孔子的话,如“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未知,焉得仁?”将“仁”作为评价的依据。再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把学的智慧作为评价的根据。同时,把“善恶”作为评价人物等级的标准之一,体现了以“道德修养”评判人物的“人格平等观”。如同样是帝王,《古今人表》将圣明与昏聩相区别,如周文王、周武王为圣明者,周穆王、周敬王为平庸者,周幽王、周赦王则为愚者,也是以道德评价人物的体现。
班固《古今人表》不以位高者就评为上等,如孟曾、蔡中胡、卫康伯、陈申公皆被列为中下等,在“愚人”一等中,如卫共伯、宋场公、鲁魏公、齐胡公、楚熊挚、齐献公、宋厉公等就在其中,君王和贵族并不少。相反,普通的平民并没有因为地位低下等位就低下。被列为“上下”等的就有子贡、弦高、范蠡,“中下”的有白圭、秦武阳,“中上”的有豫让、计然,鲁仲连被列“上中”,荆轲被列为“中中”,聂政被列“中上”,专诸被列“下上”。可见,班固并不以地位尊卑评价人物。
第三,以事功作为评定人物等级的重要依据。班固在《古今人表》序言中说:“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这也就是以“霸”“乱”的事功评价人物。《古今人表》把五帝列为“上上圣人”,乃是以他们为社会创造发明的贡献而论。还有勇于变革的政治家,如魏国的李悝、齐国的邹忌、秦国的商鞅,分别被列为上下、中上、中上。对于班固《古今人表》以事功评价人,有学者论道:“譬如‘五伯’中的齐桓公、晋文公,根据德、才,班固把他们列为‘中人’。孔子曾替评论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已对二人有所抑扬。‘孟坚最尊信《论语》’,但他却把晋文公排在中上,齐桓公排在中中。杨慎认为‘首霸者齐桓’排在晋文以及秦穆公、楚庄王之次,殊为不当。其实,仔细体会,班固这样安排的‘予夺之意’,主要是以事功论人。诚然,齐桓公是春秋首霸,事功多可称道,但他晚年用人不当,怠于政事,及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卒,‘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能‘令终’。故班固置齐桓于晋文等人之下,亦不无道理。”[8]分析得极为透彻。
总的来说,从《古今人表》看,“班固对于不同社会阶级、等级、阶层的人们,都尽量用智愚、善恶、事功的标准衡量,使历史人物得到比较合理的抑扬”[8]。一定程度上,《古今人表》所分层次及品第标准,也可看作是班固《汉书》“英雄观”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