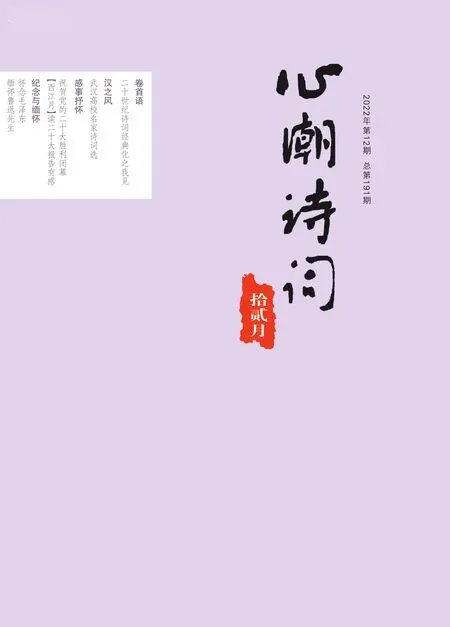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管窥当下旧体诗词创作中化新俗入古雅的“君子诗”法
2022-03-22郎晓梅
郎晓梅
“白话文运动”以降,破旧立新,一贯文以求白。百年后,再一场破旧立新,古典复兴。今人欲文而犹白者众,良有以也。
孔子《论语·雍也》载:“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说质胜于文易流于粗俗鄙野,文胜于质易流于华丽造作,君子养成需在文与质的均衡协调的状态下。倘若将之比夫我国当下旧体诗词,严格说来,质胜者众,文胜者寡,而能文质彬彬,堪称“君子”者,其实微乎其微。诗风文弱质盛,蔚然久矣,尽管诗人的向文之心从未彻底崩缺,2019年所谓“老皇皇”引发的旧体诗国哗然现象足以证明。
至于新俗之物可否入诗的问题其实不必赘言。早在1075 年苏轼在《题柳子厚诗二首》中就曾提到,“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我们将其调转过来,谈“化俗为雅”,“新而能古”,尊严羽所谓“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严羽《沧浪诗话》)者为上。如是则近“君子”。
当下语境,“口水诗”“打油诗”等概念甚嚣尘上。毫无疑问,彼类质胜于文,而相较于质,文更近于君子。笔者视域之内,确有数位擅揽撷或新或俗之事物、语词入诗,而能除鄙野之气,呈古雅华丽之章,令其作品近乎文质彬彬者。因此不妨秉持由“质”向“文”之一端,试窥当下旧体诗词创作中化新俗入古雅之“君子诗”法。
我们且从传统作文所倚重的“情”“境”二字入手,谈托境、融情二法。
先谈托境。所谓托境,即指依托语境。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将语境分为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我们这里谈旧体诗的“文”须得依托文言语境,即其所谓上下文语境。托境须先造境,所以文言语境营造是诗作古雅之气的根底,俗语新事倘能适当依托于文言语境,自然浸润古雅意味。
李海彪有《小黑》道:“汝目乌溜溜,汝毛黝且滑。汝跃喜见我,相迎明且黠。痴玩不知性,皮球小欲掇。偶尔撕我衣,偶尔窃我袜。我怒汝愈欢,蹦跶难自拔……”诗写所收流浪犬,俗常题材。行文中不乏诸如“乌溜溜”“皮球”“蹦跶”等现代汉语口语词,然而这些新俗之词不但未损诗之古雅,反而令作品在古雅之上闪烁着活泼灵动的光。其现代汉语口语词托于古雅基调之上,独得锦上添花之功。此诗基调氛围古雅,盖在于其所造文言语境。窥探其文言语境的营造,其一得益于适当调用“汝”“掇”“窃”等古语词。试将所列三字易为“你”“拿”“偷”,则味道迥然不同。其二则在于拈取古语连词“且”,构成“黝且滑”“明且黠”等单语素词联合结构。此种结构较早可见于《诗经》,如“终温且惠”(《燕燕》),“洵美且异”(《静女》),“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令》),“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园有桃》),读之古风浩荡,今人善用略无两样。
韦树定有《山塘流浪猫歌》,诗中用语极俗白,罕有僻字,却古今捭阖,文雅天成。取其结句管窥,“生不得馆娃之奇福,死又不得真娘之奇速。同与山塘流浪猫,坐看人五复人六”。“人五人六”现代汉语口语中常用以嘲贬装模作样假正经之徒,用于此处全无“口水”之感,反而文气十足。何也?一在文言句式铺垫,二在熟语改造。之前连续两次使用古助词“之”造成文言句式,兼用典,同时借助复沓修辞重复使用“不得”,生成酣畅的文言语用之流势,如湍濑落石,激跃而来。如此语境铺垫之后,出“人五人六”之俗语。然而诗忌用熟语成语,倘若直接挪用“人五人六”,或恐不佳,作者增字改造,于“人五”“人六”之间增一“复”字,解其定构,增其文质,遂乃一字真通灵,入俗而出俗。
邢涛涛有《长沙登机有怀》:“黄花机翼逆风倾,旅抱凄凄复北行。三夜阳台遗楚梦,一筠珠泪是湘情。井非太傅多偏浅,路去南山尽不平。万尺乱流更回首,合天霞色火焚城。”中间两联虽是不着痕迹,但连化四典,滋养了不断侧溢的文气。诗中虽无一古奥僻字,然而浑然圆融,古意盎然,读之令人不觉慨叹“真古人矣”。反观其诗题,《长沙登机有怀》,飞机,旧体新意象。将其入诗者他不是第一人,但一般尚古者信奉“以故为新”不纳新象,为力避其新仅用于标题。他将其用于正文,且不惮提及黄花机场名,还用到新词语,飞机飞行中的气流干扰——乱流。然而取于新而用若古,这些新意象、新词语妥帖于诗中,自在不违,究其缘由,盖由作者善用典故、善用常字构建文言气场的旧体创作功力所决定。
诗要古雅务求文言语境,新俗者欲求古雅,必须依托文言语境。而文言语境的创造,通常我们说你要多读古书,获得语感。但眼时捉急之下,我们仍需得有个抓手,那么通过对如上作品的分析,我们可执古语字眼、古语结构两柄,同时借典实及各种修辞手法助力。当然,根本仍然还在于多读古书,获得语感。白俗字眼可用为文气,而古语词、典故过度亦可为害文气,文言能力全在诗人积淀修养,不着力于古书终究不成,不着力于锤炼终究不成。
再说融情。这里“情”单指诗人的真性情。诗出性情,自然高格。性情不俗,则用字虽白俗平常,出语可不俗,其性情已先雅于语词。即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谁谓粗疏?“敲门试问野人家”,谁说鄙野?即若存魏晋风骨者,情志所在,骋笔即傲然超绝,何赖雕琢。
口语入诗者如李海彪《官山下洞野居》:“山村花草春风弄,我自幽居在下洞。君来便来同一醉,君去便去不相送。”似乎就是信手写给朋友的便条,告诉他你来就来,你走就走,尽可随意。粗糙四句,一如口语,尤其后二句直接取于口语,然而任谁也断难将其归为口水诗、白话诗。作品拂面而来浓郁的古雅幽芬,有言语组织改造不显山水之奇力,更因潜于字底的性情有如沉麝在袖。诗中“同一醉”实为写其多情相思,“不送”出其不拘俗礼之真率,练达融情,出尘若古。
污物入诗者如邢涛涛《周末》:“双休何事惬,戴雪住山房。白石谁贪煮,清樽自解藏。书多唯做枕,日暖好黏床。无客惊门雀,胞中便转长。”写周末赖床,事本忒俗,且用寻常字,更有甚者竟将“胞便”引入。然而正由于此,令诗人慵懒之状毕现,张扬着散淡不羁的文人性情,闲逸疏狂的主体感觉出来了。诗人个性旷放先于诗句,于是“胞便”虽属污物,于此反倒愈显雅气,别趣横生,一似古人扪虱而谈之事,物因人情俗雅而俗雅。当然此处诗人化典无痕地用了嵇康转胞事,即便不用也不伤其雅。
新事入诗者如苏俊《泰兴席上》:“尊前敢惜醉颜酡,宣堡黄桥至味多。我亦平生忙为口,基因大半自东坡。”平生忙着生计哪有时间打磨,文章事不过是有老苏家的文豪天赋罢了。何等狂傲!虽借酒话,却也可爱,文人气足,所以“基因”虽新而用旧,言语用乎平常而不平常。再如萧雨涵《重阳翌日卧病四首》其二:“反侧孤衾半暖寒,远人旅次可加餐?如今或有相思句,却按微屏逐字删。”痛写相思之苦情难解,用手机“微屏”新事而能新诗如旧。
事件入诗者如安全东《三月杨花白》,其诗写2021 年4 月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106 岁老妈妈李东连奔波400 公里,时隔41年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看望她长眠于此的儿子——李加友。倘一般作者或写壮伟之豪情,而安诗能融入忠烈之歌,却更多地从母子之人情写开去,从小我之人情入,又从小我之人情出,其诗云:“正月杨花无,天地尚模糊。二月杨花秀,正值春雨后。三月杨花白,风吹满头雪。满头雪,说不得,嵩明老妪年逾百,逾百何堪吊儿魂,眼如空亡泪如血……”贯通一股悲怆之气,宣泄而来,揉肠摧心,极富感染力。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本发乎天然性情。原初的文人性情,率性、散淡、旷放者有之,雄豪、狂傲、沉郁者有之,天真之处,平白语亦自典雅。但是后来很多人一端坐起来准备写诗,就想要载道,想要迎合,于是性情丢了,于是诗就不好看了。所以本真天然的性情是诗之根,情于笔先已定俗雅,人于诗先已定俗雅,字词乃为情所驱,所以写古雅的诗必得先有古雅的性情。
那么问题来了,或曰俗人俗情难得雅句可解,雅人雅情常得俗句何故?
我们来看韦树定《十一月初九夜北京西站送老母返桂六首》其六:“白日独闲暇,公园销寂寞。众人有擅场,老母在角落。人歌神已扬,母心卑且弱。忽有陌生婆,前母与言乐。谈笑喧寒暖,渐解母心缚。忽劝齐投资,理财以为约。还家告子女,惊知陷阱幕。叹此美园林,人心隔丘壑。”
诗写母亲公园遇理财骗子,其意不可谓不新,而其风趋古。诗中“公园”“投资”“理财”皆典型新熟词语,尤其后两者常为注重古雅风气的诗人所力避,用不好直接败坏诗气。而其诗信手拈来,自然妥帖,且丝毫不伤诗之古雅,是所谓用字俗而得句雅者。何也?盖其新意、俗字已然浸渍于诗整体之古雅风气之中。而其整体古雅从何而来?文言语境尔。文言语境从何而来?一可借文言字眼,譬若“销”“缚”之类;二可借文言句法,譬若“卑且弱”“以为约”之类。
所以可知遣词造句之法不可废,而后诗能情境相协。这里注意,“情”指诗人性情,“境”指文言语境。情是动态的,情在境先,从一首诗来看,情由外而内注入,复由内而外逸出。境是静态的,境是情的根底,境由内而内,自我圆融。境造好了,情可以托境升华,好诗脱手如丸。情若不谐,则境若沼泽,诗则涩而缠粘,令人生厌。所以就如同农人春种,境是土壤,农人需要翻土施肥,土沃土贫是收成的决定因素之一;而情如同种子,播进去、长出来,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决定于它自己是什么,也决定于土的品质。雅人雅情有了优良的种子,遭遇贫土,则出俗句。所以还需修炼造境之功、锤语之法。我们文中所选诗例作者无不是可以自由行走于文言语境的性情中的“君子诗”者,身畔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