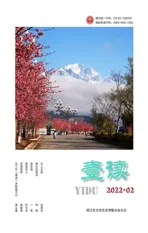西部荒野(组诗)
2022-03-22韩敬源
◆韩敬源
联系人
在手机通讯录里
看到一个已经辞世的朋友
我顺势把整个通讯录
翻了一遍
已经有好多个
辞世的人
在我的通讯录里
我不敢再拨打他们的电话
我知道打也打不通
有的注销过的号码
可能能打通
但已经换了人
包括我的母亲
爱穿亚制服的老人
那个我记忆中的人
在今年春节再见时
老了
唯一没变的是
他身上的亚制服
从撕掉领章的军服
到警式衬衣
没有标识的运政服
没有标识的保安服
他都穿过
不知道他从什么途径
搞到这些旧服装
在孩子们零零星星的爆竹声中
他穿着一件警式羽绒袄
靠着乡村的墙根
睡着了
奔跑的牦牛
一头牦牛在滇西高原上奔驰
视觉里真实的印象
是这样的
一头牦牛的四条腿
被绳子穿过脚骨
牢牢固定在门店的柱子上
全身的肉已被剔除
填充它身体的是塑料
老板希望买它肉的客人
清楚地看到
是一头牦牛
在滇西北高原上奔驰
爆竹瀑布
响了一晚上的爆竹
让早睡的孩子们
紊乱
更远处的爆竹
像一阵急雨
打芭蕉
这多少有点像我走过的路
在早春二月里
才能听到
逝去人们的骨头
崩裂爆炸
延绵成河
西部荒野
我们喝了那么多酒
接了那么多吻
做了那么多爱
地球毁灭
也一起看过了
孩子尚未长大
没有自然远去
忍不住打喷嚏时
该麻木的也麻木了
狮王酒店的老板
换了三茬
我的鱼人小姐
燃烧平原上的孤独女孩
毫不回头
那么倔强
芭蕉黄了又绿
去老年公寓探望父亲
对面床上的老人
已经不见了
护工悄悄跟我说
那老人走了
2019年我从新世纪诗典江油诗会
受诗人赵克强邀请参观北川地震遗址
返回昆明探望父亲的时候
这个老人像从废墟中
向我伸出过手
我缓缓走过去
坐在那张空空的床上
看着我爸
我爸看着我
中间什么都没有
我爸已经认不出我
而我认不出这个世界
卖菜的人多数都有个阳光的网名
经常到菜市场买菜
刷微信付款时
我都会留意一下
对方的网名
今天刷到的六个网名分别是
会飞的鱼腥草
不辣人的小辣椒
开花洋芋
我的萝卜不花心
煮熟的鸭子
最后一个网名叫伤心伤肝
我留意了一下
是个手腕处
纹着蝴蝶的中年妇人
像一条鱼一样丰满
让早晨的菜市场
不停地在地板上跳跃
清明节的蜜蜂
清明节这天
一只蜜蜂
闯入我家
我熟悉这个世界里的蜜蜂
在父亲没有痴呆
母亲也还健在的那些日子
与蜜蜂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母
指挥蜜蜂
酿出花蜜
供我和胞弟念完大学
清明节这天
一只蜜蜂
母亲的精灵
从时间的缝隙中
冒了出来
围着我家客厅的灯泡
翩翩起舞
南京
看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时
有个老人的口述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入侵的日本兽兵
糟蹋过当时的国都
一年之后
一个年轻的女人
幸存下来的
我的女同胞
亲手掐死了
刚出生的婴儿
我必须信任理发师
我到丽江工作十六年来
都没有换过理发师
电话号码也没有换过
学校搬迁过一次
他也追到附近
继续开店理发
后来房子也买在
同一个小区
他知道我老婆
知道我孩子
知道我父母
知道我同事
除了不知道我有没有存款
最近风声比较紧
十六年的熟人了
每次理发到最后
他按着我的头
手起刀落
剔除我鬓角的绒毛时
我越来越紧张
生日
他是荷花开的时候出生的
他是包谷花开的时候出生的
她是谷子熟的时候出生的
她是挖土豆的时候出生的
她是太阳出的时候出生的
他是鸡叫的时候出生的
她是麦子黄的时候出生的
他是米线只卖三毛钱一碗的时候出生的
我诞生于这个世界的准确日期
至今是个谜
我从一张木框镶嵌的
父母结婚时
南京长江大桥落成
通车纪念的画框上
一行纪念的小字中判断出
从父母结婚那天算起
我的出生日期怎么都对不上
在那个严打一切的时代
我的出生
非常幸运
非常清晰
我是母亲
在12年前她辞世的那天
顺着她出嫁的路回去的那天
重生的
我特别能感受一滴水的恩情
诗人左右(真名)
替我在微信微店
卖诗集和诗论
销售廖廖
今晚他发信给我
留了一个地址
附加留言
“他是你的铁杆粉丝”
我喝了点酒
我会规规矩矩
签下自己的姓名
亲自寄出
我儿时在昆明石林
一个边疆民族地区
还在使用战国时候
就使用过的
食不果腹的
牛耕铁犁的现代生活
几乎泪下
我特别能感受一滴水的恩情
哪怕你嘲笑我如此幼稚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