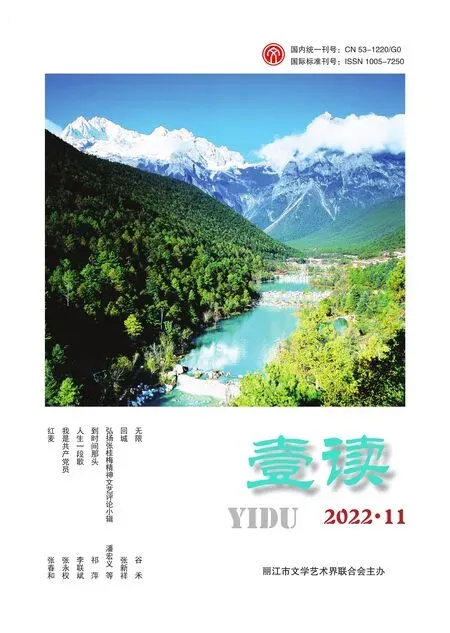人生一段歌
2022-03-22李联斌
◆李联斌
恢复高考的第3年,也就是1979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不到6%,大多数考生未能如愿挤上“独木桥”,而在麻栗坡县八布中学高中毕业的我,不幸也在其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待业、复读、当兵等选择。当时我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低落,心里茫然,不知未来的人生与命运将会如何。
时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改革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制度已经停止,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亟需人才与人力,而各条战线的干部职工队伍又青黄不接。在这样的背景下,9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去县里参加分工的通知,犹如白日好梦来袭,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我们那批分工的达90人之多,县人事局长在会上讲完话之后宣布了分工名单。有的分到党政部门,有的分到金融系统,有的分到商业系统,有的分到公路系统,有的分到乡村学校,我等6人则分到县广播站。分到工作的每个人,脸上笑容都发自内心,庆幸赶上了好时代,党的阳光暖到了心里。
分工会结束后,我依然带着喜悦,跟着带路人来到了县广播站。不曾想到,这一来,就在广播站工作了整整5年。5年时间,在人生历程中虽不算长,而我这5年时光,却如人生一段歌。
这一年,我刚好16岁,一时难以适应工作身份的转变。天真无知的我,就像一个匆忙上车的旅客,手忙脚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单位里,不时向“大人们”问这问那,都是些不着边际、无关痛痒的话题,偶尔会因自己的幼稚轻浮引来大家的发笑。我不时在单位旁边的小广场上跑去跑来、玩耍打跳,一点不像工作人员的样子。一次,我跳上用于架设广播线的绞线机上剧烈摇玩,不小心踩滑跌倒,机柄戳到我的大腿,疼痛难忍,滚在地上,半天没能爬起来,当时我就骂自己,都是“少年黑发不知愁”惹来的祸。从那以后,我慢慢学会收敛,规矩了许多,不再乱跑乱跳。
我一直在中越边境农村长大,从未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工作了来到县城,顿觉陌生而又新鲜。出于好奇,有空我就东游西逛、找人闲聊,并借助于县志,对麻栗坡县及这座县城的自然和历史人文有了些了解。
麻栗坡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位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东西长100公里、南北长40公里,东西北部与州内其他5个县相连,南部与越南河江省的“五县一市”接壤,国境线长227公里。当时全县有12个公社,大约14万人,壮、苗、瑶、傣、仡佬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8%。
县份虽小,位置却很重要,历史也算久远。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西汉时期纳入祖国版图,之后历朝历代都为边境要塞。光绪年间,设麻栗坡为副督办,直隶于省。1914年(民国3年),改副督办为对汛正督办,第二年又改设为省辖特别区,又过了两年即1917年,改称为特别行政区对汛督办。1949年3月,全县解放,废除对汛督办特别行政区建制,成立县人民政府。
县城因地势山高坡陡、环山多有麻栗树而得名。县城不大,也就两万来人。房屋依山而建,称得上街道的就两条,一条是老街,建在一条狭长的斜坡上,早先的对汛督办设置于街头,算是县城的制高点,街道两侧主要是民居,街尾右侧是县电影院和篮球场,左侧为县一中;另一条为沿河街,因前些年县城人口增多而新设,两旁主要是县级相关部门办公楼。“麻栗坡,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是其最大的特点。幸好上苍给这个“夹皮沟”式的县城赏赐了两条河,一条叫畴阳河,在城中蜿蜒穿流,还有一条叫小河,从城边山脚洞中流出,汇入畴阳河跨境流向越南。碧波荡漾、清澈见底的大小两条河流,给这座边城增添了不少灵气、带来生机。
小河出水口名叫小河洞,高2米、宽8米、长千米以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省有关部门的专家在洞内清理发掘,出土有石斧、石刀、石锛、石印模和印纹陶片等物,这是滇东南地区首次发现的距今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繁衍生息的遗址。我曾多次出入,探寻、感悟祖先们生活的踪迹,敬仰祖先们的生存智慧与能力。听好多人都说,县城东郊的大王岩岩画很古老,于是,在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沿着崎岖山路,蹒跚而行,爬到岩脚,慕名探访。岩画在一座叫羊角脑山的石壁上,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又受岩浆侵蚀、自然风化,看上去已不清晰,只能看到由红、黑、白等色彩绘制的图形。过后我查看专家考证结果得知,岩画可辩图像25个,其中人物11个、牛3头、小动物2只,还有其他图案。画面完整,为新石器时代岩画作品,迄今大约4千余年。后来我又多次去观仰岩画,赞叹不已,反复猜想,也许这就是当时居于小河洞内祖先们留下的珍迹。再后来,它被国际岩画学界誉为“代表着一种巨大的原始创造力”的岩画,为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七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县委会坐落在畴阳河东岸,而县广播站则在县委围墙内的东北角,准确点说,房子是盖在一个旮旯里。我清楚地记得,县广播站也就十四、五个人,加上我们新来的,也就20多人。全站就一幢长型小楼房,白墙青瓦人字木顶两层楼,横面有门、中有通道,两层总共20间,每间不过20平方。这幢房子,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其中一楼有2间连通为广播室、另有2间为办公室,楼上2间为仓库堆放广播器材,其余就是宿舍。
当时我就在想,这是什么单位啊,房子又小、职工又少,我们几个刚来的人,吃在哪住在哪恐怕都成问题。好在站里早就把吃的问题协调解决好了,就在县委食堂搭伙。住的嘛,安排在县中波发射台筹建处的简易房。筹建处离县城不远,在一座名叫弯担坡的山顶上。男的自带行李住二楼,女的住一楼。白天到站里学习工作,晚饭后各自回来住宿,一天上下要跑两三趟。住下不几天,我观察了周边环境,工地左边有片冬瓜林,下有沟壑,壑中有溪,潺潺流淌;右边有个大山凹,旁边有个小山包,上面长着棵大榕树。
住在山上的感觉真好,朝看东升旭日,暮看西边霞姿,夜听鸟啼虫鸣,空气清新、带着甜味。还可进入树林中,静听音乐般的流水声,或坐在榕树下,鸟瞰县城全貌,尽赏四周山水,给人一种身在尘世外、心若闲云飘的感觉。只是冬天难在一些,天气阴冷、山风呼号、雨打树林,夜里时而会被刺骨寒风吹醒。至今我还忘不了,住在简易房的那些日子。
开初,站里并没安排具体工作,主要组织我们学习,既学时事政治、又学业务知识和技术。站长多次给我们讲解广播室机房全套设备的功能和使用,包括调频机、功放机以及话筒、电唱机、磁带录音机等设备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术、简单故障排除方法。副站长主要讲无线电的基本原理和收音机的修理技术。有一个分来不久的大学生,主要讲收录机的原理及其集成电路、检修方法。还有一些工作老道的同志,主讲有线广播线路的架设和维护、各种喇叭的连接安装和修理等实用技术。为了让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掌握基本知识,站里买来相关书籍和检测仪表、修理工具发到各人手上,要求我们抓紧自学。
这些技术设备和书籍,以前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还真来了兴趣。在家时常听老人们讲,“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当时我就一直在想,分来广播站,算是来对了,要倍加珍惜,学会这些技术,即便没了工作,也可在社会上混碗饭吃。所以,师傅讲解,我专心听、认真记、主动学,有事无事也跟在师傅后面转,目的就是想多学点技术,以防日后不测。
那段时间,免不了要我们做些临时性工作。比如,哪段广播线路出问题、信号送不出去了,就去突击抢修、排除故障。因为才来不久,我只能给师傅们拉拉铁丝、递递工具。有一次,要将城郊广播线路的木电杆换成水泥电杆,站里职工全动员、齐上阵,有的拉线、有的挖洞、有的抬杆。水泥电杆又粗又长又重,要从公路边顺着小路抬到山坡上栽起来,一次抬杆需要8人,其中前后端各2人、中端4人。我参加抬杆,在后端,横杠放在肩上刚迈出几步,因年少体力不支,突感眼冒金星支撑不住,站长立即叫停,我被换下,由于用力过猛,脸上发青半天缓不过气来。过了2个多小时,抬到了目的地,大家七手八脚把事先装有瓷瓶的横档安在电杆顶端,再把杆子栽入洞中。一个师傅动作娴熟,腰系安全带、脚踏铁扣、肩杠铁线,爬到杆顶,把铁线安置在瓷瓶上,另外的同志用绞线机把线绞紧,最后测试广播信号,确认能够传输,才算完工。
县广播站为县委宣传部直管(当时未设县广电局),下属12个公社广播站,主要任务是放广播、架设维护有线广播线路,筹建县中波发射台和电视差转台,管理全县广播工作人员队伍。与此同时,县委宣传部还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要县广播站开办自办节目。面对新老任务,站领导研究后给我们作了岗位分工,有的到中波发射台,有的筹备县电视差转台,有的安排到外线组。而我,则安排在广播室,做新闻采编、开办自办节目。
面对岗位分工,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新闻咋写、采访咋搞、节目咋编,我连一点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当时心里很矛盾、顾虑重重。一来搞技术是手艺,何时何地都需要,而且越老越吃香,开初学技术、做技术工作的想法泡了汤;二来编自办节目、搞文字工作,政治性强、责任重大,一不小心还容易犯错误;再则还得离开已经适应的山顶环境,有些不舍。后经领导点拨,我忽然醒悟,这是在单位不是在家里,还得服从组织的安排。没有谁生下来就会做事,不会就要学,人的潜能都是通过学习释放出来的。于是,我再没多想,搬宿舍、学业务、编节目,一切从零开始,当起了“小编辑”、“土记者”。
当时不曾想过,那样的分工,赋予了我生命不同的意义,影响了我人生的走向。后来,我被调到县、州、省的一些部门工作,都与在广播站的这段工作经历紧密关联。更想不到的是,25年后,峰回路转,我调到省委宣传部门工作,直到今天。
那个年代,全党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号角,催人奋进,各行各业你追我赶,都在争着把“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为祖国“四化”多作贡献。那时的年轻人,充满朝气、充满活力,以“80年代新雷锋”张海迪为榜样,进取奉献是青春最美的状态,“创造奇迹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是那一代青年的标识。可像我这样的人,在学校又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在单位又没工作基础,面对时代召唤,我反复追问自己,拿什么来为“四化”作贡献呢?总不能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吧!受时代精神的熏陶,我不断告诫自己,唯有加紧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做好工作,不负青春好年华。
边工作、边学习成了平常,书籍成了好朋友。已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我守住孤独、忍耐寂寞,卯足劲头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时事政策成为必学内容,它能帮助我在工作中不偏航、不走调。我曾仔细研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云南日报》一、二版头条新闻,分析其内容、结构和语言表述方式,力图快速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同时,自学《新闻记者入门》(孙世恺著)、《采访与写作》(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主编)、《新闻采访方法论》(艾丰著)及《新闻报道与写作》(美国麦尔文·曼切尔著,广播出版社出版)等书籍,对新闻特点、要素、写作基本要求和采访基本方法、以及如何增强新闻敏感、识别新闻价值、提炼新闻主题等有了大致了解。还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韩树英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主编)等书籍,逐步扩展知识。只要有机会,站领导也支持我参加相关培训。记得在1980年参加县里举办为期3个月的写作培训班时,我将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起因、经过、结果)与新闻五个“W”(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人)作了对比,发现二者写作虽有不同,但基本要求大体相似,慢慢消除了采写新闻心理障碍。之后也参加过省、州举办的一些业务培训。
心里有了点底气,我就大着胆子外出采访。值得庆幸的是,采写的第一条新闻《豆豉店大队购销店承包给个人经营成效明显》被上级主要媒体采用,给我增添了工作信心与激情。随后几年,我在完成自办节目编辑的同时,不断到基层和群众中采写新闻,除在自办节目中播出外,省州主要新闻媒体也采用刊播了不少。
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战役打响前3天,县委安排我陪同一名副县长到老山脚下的猛硐至磨刀石一带,看望配属部队作战的民工民马连。当时,县委和县武装部组织了3个民工连、4个民马连,安扎在不同的指定位置。我同副县长一个连一个连地走访慰问,再次进行战前动员,并及时协调解决生活、担架、马料等实际困难。这批民工民马连在参战中运送弹药到位、抢救伤员神速、表现英勇顽强,出色完成配属作战任务,为胜利立下汗马功劳。随后我写的新闻报道被刊发在省报刊上。
那几年,我采访了不少当地群众支前参战、军民共建的典型事迹,参战军民共同培育的“老山精神”,深深教育了我,切身感到,国家若不安宁,哪来家庭的安宁。以爱国奉献为核心、以不怕苦、不怕死、不怕亏为主要内容的“老山精神”,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如今,“老山精神万岁”的主题雕塑,依然耸立在老山主峰。
当时广播室就3人,每天按规定广播3次,早晨6:20开播,8点结束;中午11:50开播,13点结束;晚上17:50开播,20点结束。开头都是用电唱机播放歌曲《歌唱祖国》,随后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少年儿童节目》和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云南新闻》《对农村广播》等节目,晚上18:30插播《自办节目》,中间用电唱机插播群众喜爱的歌曲, 19:50播送县气象站提供的《天气预报》。另外,还按要求录播有关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农业科技等知识,播出涉及人民群众工作、生产、生活的内容。每天每次播出的节目内容,都要进行规范登记、归档。
我们办自办节目要求严格、态度认真,但有时也会出现疏漏。有天晚上,我们的《自办节目》还没播完,县委宣传部分管副部长急匆匆跑来广播室,指出刚才播出的一则消息,广播员把我边防侦察小分队“边打边撤”的“撤”读成“散”,意思完全变了,严厉地批评我们。我快速核对边防守军通讯员采写的稿子,确定是读错了。那一瞬间,我们无地自容。问题严重、教训深刻,我们作了检讨。从那以后,播音员在录制节目时,对拿不准读音的字,都会先查字典,我在审听时,增加了次数,严防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那个年代的有线广播,是党委宣传、发动、组织、教育群众的主要工具,在促进农村改革、包产到户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丰富群众文娱生活、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干部群众听广播也成为一种习惯,偶尔停电、听不到广播声,一些听众会打电话寻问,我们得耐心解释、说明。有的觉得哪首歌曲好听,也会打电话来要求安排再次播放。《自办节目》受到欢迎,有的听众还积极争当业余通讯员,踊跃采写广播稿、提供相关宣传材料。我们顺势而为,发展、培训了上百人的通讯员队伍,新闻稿件源源不断。我们的自办节目,越办越红火。
我在学习工作中的点点进步,得到相关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与支持,县里开展专项性工作,也常“点”我参加,让我从中得到不少锻炼和提高。1981年,我参加县委小分队到基层宣传党的农村政策,我按分工要求,搜集整理资料、编成宣传节目送审后,让广播员录制好节目,带着广播器材,跟随小分队到各个公社,利用街子天巡回宣传。广播器材就摆放在露天,不少赶街群众围坐静听广播的声音。1982年,大坪公社广播员休产假,派我去顶岗。在半年多时间里,除了放广播、维护线路外,还要完成公社党委交办的临时性任务。秋收后,有个生产队迟迟未交公粮。一天中午广播结束刚关机,党委书记要我跟他去这个村催公粮。我陪他坐在队长家火塘边,边吃刨花生、边喝包谷酒、边拉家常,书记只是偶尔提及公粮一事。第二天我去公社粮管所察看,结果有8张小马车在排队交公粮,一问都是那个队的,我暗自佩服书记的工作方法,跟他学得了做群众工作的一招。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后,县委组织相关人员到农村开展宣讲,我被抽去与县委宣传部和党校的同志一个组,到地处中越边境的董干公社马崩大队村寨宣讲。当时农村已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白天群众下地干活,晚上才便于集中,我们每天都要到夜里十一、二点才宣讲结束。到苗族村寨,由党校的老师用苗语宣讲,到了汉族村寨,则由宣传部的同志或我宣讲。在宣讲时,我都会留心观察,现场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忙活一天的村民们,身上还带着田地里的气息,可每个人的精神都很饱满、听讲的神情十分专注,我仿佛感受到,群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急需得到致富政策的迫切心情。
在工作与生活的交往中,站里新、老同志从不认识到熟悉,从同事到朋友,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学习上相互帮助、工作上相互支持、接人待物上相互理解,人际间没有虚情假意,也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关系融洽、相处和谐,全站就像个大家庭。
有个同事,大我一岁,在山顶简易房二楼居住时,3个男生打的是通铺,我在左边,他在中间,另一个在右边。他的理科知识比我好,听不懂、看不会的无线电知识,我常常请教于他,他则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他家就在县委,不时带我到家里做客。他还备有一套理发工具,头发长了帮我理。有时工资接不上趟,他也会解囊相助。我们的关系日益密切,亲如兄弟。我从山头上搬到广播站时,曾与一同事同室住了一段时间。他当过回乡知青、在过县委农村工作队,3年前到了县广播站,主要搞外线。他大我10岁,起初我叫他叔叔,没过几天,让我叫他大哥,就一直叫到了今天。他虽只是初中生,但看上去文质彬彬,待人接物都很得体。从他身上,我学会了一些做人的社会知识。只可惜,他因家在农村,一直没谈上对象,好在不久前天保农场职工因战撤进县城,有一年轻漂亮的女职工看上了他,一年后组建了家庭。
站里的领导都是搞技术的,他们对同志很和善,大家也愿意接近他们。站长个子不高、40来岁,性格不温也不火。他的办公室桌上摆满各式各样的破旧收音机和修理工具,我常去看他修理。一个没有任何声响的收音机,经他用起子左敲敲、右敲敲,再焊一烙铁,然后打开开关,就有了声音。我觉得他技术高超,对他尊重敬佩有加。我们几个年轻人,不时受邀到他家蹭饭、小酌。
年轻人爱热闹、爱交流。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单身汉学会了“打拼东”(类似于AA制)。到了周末,为凑热闹、解嘴馋、过酒瘾,我们商议,你打酒、他打饭、我买菜,聚在一间宿舍,饭菜摆在地板上,喝开水的玻璃杯当酒杯,有的坐着、有的蹲着,边吃边聊,工作上的事、生活上的事,愉快的事、烦心的事,天大的事、鸡毛蒜皮的事,无可不说。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头年试用期就29块半,还加上了2块粮价补贴,一年转正后也就39块半,可到“打拼东”时,似乎都忘了节约,只想多打点菜饭和酒水,好让大家交流个痛快。后来,“打拼东”改为“轮流坐庄”,这个周末我负责,下个周末你安排,再往后是他准备,大家争先恐后,不亦乐乎。
多年以后,虽然有的同志调到不同地方、不同单位工作生活,但心里都有着那份惦记。
最初的爱恋如此美妙而又青涩无果,就像一篇有了激情而又没有动手写成的文章。我来到广播室,与两个女广播员成为同事,其中一个工作了3年,我们都叫她“大姐”,另一个与我同批分配进来,因她音质较好、普通话说得相对标准,之前就安排做了广播员。编、录、审、播自办节目,以及值守广播室等工作,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与我同时分进的广播员,在县城长大、毕业于县一中,那时正值花季年龄,不仅声音甜美、做事灵巧,而且身姿婀娜,面色桃红,脸上常露微笑,还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自办节目的编排,需要一起商量确定,录音节目的审听修改,需要相互协作,边听边改。县里召开大会,站里也常安排我们俩去搞广播服务。商量工作所见略同,遇到问题见解一致,工作中的配合默契而顺畅。如此一来,工作也就常常在轻松、愉快、和谐的气氛中完成。
忙完工作,我们也常在广播室一起欣赏音乐。比如李谷一演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中的玫瑰》,王洁实和谢莉斯演唱的《九九艳阳天》《外婆的澎湖湾》等等,优美的旋律、形象的歌词,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每每听到我国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演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的眼前都会呈现湛蓝的天空、无边的草原、洁白的羊群、美丽的姑娘、还有她的帐房……我仿佛觉得,身边的这位同事,就是歌中的那个姑娘,让我心驰神迷。
我在那个年龄段,并未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而在工作与交流中,我朦胧的内心,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喜欢上这个参加工作遇见的第一个女人。工作时趁她不注意,我则会多看几眼。从她工作专注的神情里,我能够感觉到她呼吸的气息,仿佛看到了她心灵带着的那份清纯,我的心田好似吹过春风荡起涟漪。那段时间,我初感青春的美妙工作的美好,生活里有了更多的阳光。自然而然,她的身影、她的音容,会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印入脑海。时而外出,也会心有所思,想着尽快返回,能够早点看见她。虽然羞于告白、又从未牵手,可这份情感,在我内心驿动。
人世间的一些美好,或许就只一瞬间。随着时光流转,我慢慢学会了一点点观察、一分分思考。再往后的一些时间里,我便意识到,她的内心有我无法预知的世界,与她之间,就像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人挨得很近,心却离得很远。正因如此,我心中飘过一丝淡淡伤感,往日的快乐难以重现,活泼的个性里多了一份老成。我找来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力图从中找到安慰。曾有不少夜晚,我独自来到畴阳河边,借助如洗的月光,平我心中的忧伤。还曾主动“坐庄”,邀友豪饮,把酒泼到心里,浇灭春愁,任凭窗前雨滴到天明。
一觉醒来,我忽然明白,不属于自己的就不要勉强,青春的绽放不只是爱情,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自己的心魔“反侧自消”,心胸豁然开朗。悠悠岁月,会带走曾经美好的季节,多年后与她偶然相遇,交流如昨,只是那份情感早已随风而去。
43年如电抹,往事回首已云烟。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天翻地覆,而那时曾经辉煌的农村有线广播,早在80年代后期,随着收录机、电视的普及,已离人们渐行渐远、淡出了视线,当年广播站的功能,如今也被县融媒体中心所取代,而我在广播站工作的那些时光,则变成永不消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