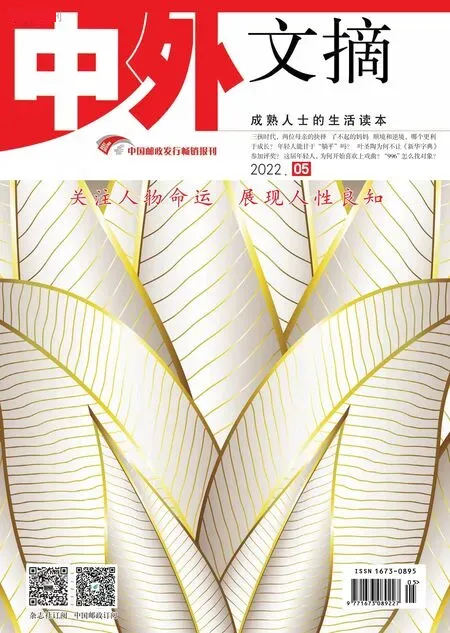故宫的书法风流
2022-03-21□祝勇
□ 祝 勇

小篆:大秦的线条之美
在文字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的字体是大篆。这种古韵十足的字体,被大量保存在西周时期的青铜、石鼓、龟甲、兽骨上,文字也因刻写材料的不同,分为金文、石鼓文和甲骨文。大篆的写法,各国不同,笔画烦琐华丽,巧饰斑斓。
秦灭六国,重塑汉字就成为政府第一号文化工程,丞相李斯亲力亲为,为帝国制作标准字样,在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于是一种名为小篆的字体,就这样出现在书法史中。
这种小篆字体(见右图),不仅对文字的笔画进行了精简、抽象,使它更加简朴、实用,薄衣少带、骨骼精练,更重要的是,在美学上,它注意到笔画的圆匀一律、结构的对称均等,字形基本上为长方形,几乎字字合乎二比三的比例,符合视觉中的几何之美。这使文字整体上显得规整端庄,给人一种稳定感和力量感。透过小篆,秦始皇那种正襟危坐、睥睨天下的威严形象,隐隐浮现。
一个书写者,无论在关中,还是在岭南,也无论在江湖,还是在庙堂,自此都可以用一种相互认识的文字书写和交谈,秦代小篆成为所有交谈者共同遵循的“普通话”。它跨越了山川旷野的间隔,缩短了人和人的距离,直至把所有人黏合在一起。文化是最强有力的黏合剂,小篆则让帝国实现了无缝衔接。以至于今天,大秦帝国早已化作灰烟,但那共同体留了下来,比秦始皇修建的长城还要坚固,成为那个时代留给今天的最大遗产。
《兰亭序》: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的第一天,郑欣淼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说,午门上正办“兰亭特展”,相约一起去看。尽管我知道,王羲之的那份真迹,并没有出席这场盛大的展览,但这样的展览,得益于两岸故宫的合作,依旧不失为一场文化盛宴。
那份真迹消失了,被1600 多年的岁月隐匿起来,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块病。我在展厅里看见的是后人的摹本,它们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这些后人包括: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米芾、陆继善、陈献章、赵孟、董其昌、八大山人、陈邦彦,甚至宋高宗赵构、清高宗乾隆……几乎书法史上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暮春三月初三,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同谢安、孙绰、支遁等朋友及子弟42 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行“修褉”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酒酣耳热之际,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一气呵成,写下一篇《兰亭序》,作为他们宴乐诗集的序言。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以后成为被代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更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王羲之酒醒,看见这卷《兰亭序》,有几分惊艳、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寂寞,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这卷《兰亭序》反复重写了数十乃至百遍,都达不到最初版本的水准,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成为家族的第一传家宝。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张纸究竟能走出多远?一种说法是,《兰亭序》的真本传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孙智永的手上,由于智永无子,于是传给弟子辩才,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策骗到手;还有一种说法,《兰亭序》的真本,以一种更加离奇的方式流传。唐太宗死后,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
《祭侄文稿》:最沉痛最深情的血色文稿
若说起“安史之乱”期间所经历的个人伤痛,恐怕难有一人敌得过颜真卿。颜真卿的侄子颜季明是在常山城破后被杀的,那个如玉石般珍贵、如庭院中的兰花(《祭侄文稿》形容为“宗庙瑚琏,阶庭兰玉”)的美少年,在一片血泊里,含笑九泉。
颜杲卿(颜季明的父亲)被押到洛阳,安禄山要劝他归顺,得到的只是一顿臭骂。安禄山一生气,就命人把他绑在桥柱上,用利刃将他活活肢解,还觉得不过瘾,又把他的肉生吞下去,才算解心头之恨。面对刀刃,颜杲卿骂声不绝,叛贼用铁钩子钩断了他的舌头,说:“看你还能骂吗?”颜杲卿仍然张着他的血盆大口痛骂不已,直到气绝身亡。那一年,颜杲卿65 岁。除了颜杲卿,他的幼子颜诞、侄子颜诩以及袁履谦,都被先截去了手脚,再被慢慢割掉皮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颜氏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口。
颜杲卿被杀的这天晚上,登基不久的唐肃宗梦见了颜杲卿,醒后为之设祭。那时,首级正被悬挂在洛阳的大街上示众。没有人敢为他收葬,只有一个叫张凑的人,得到了颜杲卿的头发,后来将头发归还给了颜杲卿的妻子崔氏。
颜真卿让颜泉明去河北寻找颜氏一族的遗骨,已经是两年以后,公元758 年,即《祭侄文稿》开头所说的“乾元元年”。那时,大唐军队早已于几个月前收复了都城长安,新任皇帝唐肃宗也已祭告宗庙,把首都光复的好消息报告给祖先,功勋卓著的颜真卿也接到朝廷的新任命,就是《祭侄文稿》里所说的“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御史”。
颜泉明找到了当年行刑的刽子手,得知颜杲卿死时一脚先被砍断,与袁履谦埋在一起。终于,颜泉明找到了颜季明的头颅和颜杲卿的一只脚,那就是他们父子二人的全部遗骸了。这是名副其实的“粉身碎骨”了。颜真卿和颜泉明在长安凤栖原为他下葬,颜季明与卢逖的遗骸,也安葬在同一墓穴里。
因此,《祭侄文稿》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血浸的,用泪泡的,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沉痛,也最深情的文字。支撑它的,不只是颜真卿近50 年的书法训练,更来自颜真卿的人生选择,也是整个家族的选择。
我恍然看见颜真卿写完《祭侄文稿》,站直了身子,风满襟袖,须发皆动,有如风中的一棵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