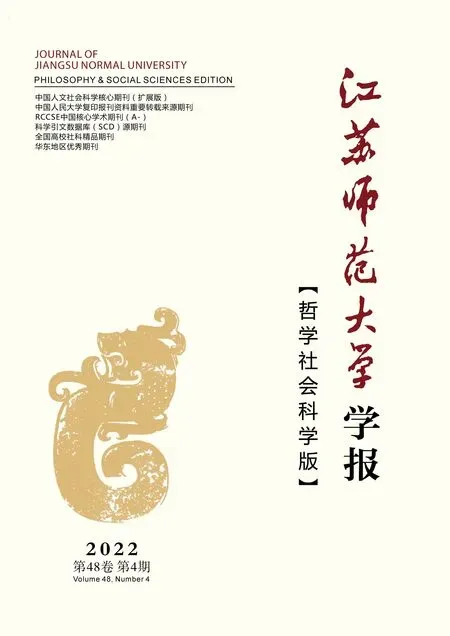湛若水“以测解经”的经学模式及其历史命运
2022-03-18程潮
程 潮
(广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湛若水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心学家和经学家,他不仅开创了以“随处体认天理”为核心的心学派别,还开创了“以测解经”的经学模式。由于他的测类经学著作除《二礼经传测》外均已失传,不经一番考证,就无法了解他的“以测解经”的经学模式曾经受的磨难与辉煌。本文拟对湛氏的测类著作及其所反映的“测”与“经”“传”“训”的关系以及湛氏“以测解经”经学模式的历史影响、悲剧命运及其原因作一探索。
一、湛若水的“测”类经学著作
清初张云章说:“(湛若水)所著有发挥经传者,皆以‘测’名其书。”〔1〕朱彝尊:《经义考》卷五十一,四库全书本,第16页(卷页)。至于湛氏到底有哪些测类经学著作,弟子郭棐则列出“四书测、五经测”(1)郭棐:《粤大记(上)》,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不过,根据湛氏作过“自序”的带有“测”字的经学著作来看,除了保存至今的《二礼经传测》外,还有已经失传的《仪礼补逸经传测》《古大学测》《中庸测》《修复四书古本测》和《修复古易经传训测》。
《二礼经传测》又名《二礼经传》《二礼测》《二礼经传训测》,今存有六十八卷本。湛氏已于1525年作《二礼经传测序》,表明该书已完成的初稿。他于1536年上奏《进二礼书疏》,称该书“仿朱子之意,而推之始于丁丑,迄于乙酉,详定于丙申”(2)蔡淑、陈辉璧:《增城县志》卷十,1686年刻本,第34-35页(卷页)。,意即该书在该年已终稿,宗旨符合“朱子之意”,望刊行时获朝廷支持。
《仪礼补逸经传测》在朱彝尊的《经义考》中是与《二礼经传测》分别介绍的,并将后者目录中《仪礼补逸经篇名》的“测”文直接作为本书的“自序”,为一卷本(3)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三十四,四库全书本,第10-11页(卷页)。。元代吴澄著有《仪礼逸经传》,分《仪礼逸经》和《仪礼逸传》二卷。湛氏可能受此影响而将本书分为《仪礼补逸经测》和《仪礼补逸传测》两部分,这可以从《二礼经传测·目录》的《仪礼补逸经篇名》和《仪礼逸经传》(卷六十至卷六十八)(4)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2-23、26-27页。中反映出来。
《修复古易经传训测》又名《古易训测》《古易经传》《古易经传测》《周易训测》。湛氏任礼部尚书时,于1535年为该书作“自序”;任吏部尚书(1536-1539)时,弟子黄省曾也为该书作“序”。该书的体系结构似乎一是参照了朱熹的《原本周易本义》(四库全书本),首为“上经第一、下经第二”,其后篇次为“彖上传第一”至“杂卦传第十”,卷末有《五赞》;二是参照了吴澄的《易纂言》(四库全书本),依次为“卷一上经”“卷二下经”“卷三彖上传”……“卷十二杂卦传”。根据湛氏的“出羲、文、周公之《易》,复为上、下经,而取孔子之翼为后人所分附者,复合而为《十传》”(5)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81页。和黄省曾的“二十三赞以毕”(6)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二十六,明嘉靖间刻本,第14页(卷页)。之描述,则该书的体系结构及篇次大致为:《黄省曾序》《湛若水自序》《上经》《下经》《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二十三赞》。湛氏的《文言传》因受吴澄以《系辞传》中说上、下经的“十六卦十八爻”之文为“错简”而移入《文言传》(7)纪昀、永瑢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页。的影响,也将原《系辞》中“亢龙有悔”以下十九条移入其中(8)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81页。。
《古大学测》又称《大学古本训测》《古本大学测》《大学测》《古大学章句测》;《中庸测》又称《中庸训测》《古中庸测》,二书各有一卷。湛氏居西樵山时,于1518年孟秋(农历七月)作《古大学测序》,九月作《中庸测序》(9)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五十四、卷一百五十九,四库全书本,第10(卷页)、9-10页。。他曾收到同住西樵山的方献夫寄来的《大学原》和《中庸原》书稿,回信时也寄去了《中庸测序》,并谈到《中庸测》已于月朔(约为九月初一)写成,等二日有了手抄本就寄去指正(10)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25页。。方氏回信说:“承示《中庸测序》,已领其大旨。”(11)方献夫:《方献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因此,《中庸测》在1518年已有稿本和手抄本。《古大学测序》又比《中庸测序》早出,则应在该年有《古大学测》的稿本和手抄本问世。而湛氏在给陈惟浚的信中也提到:“山居曾整理《古本大学》及《中庸》二测,因令人录奉一阅。”(12)湛若水:《湛若水全集(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48页。后来,二书被收入《修复四书古本测》中。
《修复四书古本测》又名《四书测》《古本四书训测》《古本四书测》《四书训测》。湛氏于1537年10月作“序”(13)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98页。,意味该书已完稿。该书可能参照了朱熹“十九卷”本的《四书章句集注》,也分为十九卷,即《古大学测》一卷,《中庸测》一卷,《论语测》十卷,《孟子测》七卷。
二、“测”与“经”“传”的关系
湛氏之前,明初学者蒋悌生在《五经蠡测》中“以先儒训释经传有未洽于心之处,因推究本旨,旁通诸说,以证明之”(14)四库馆臣编撰:《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校证》第1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版,第249页。,有“测”的特点,但未将《五经》及其各篇都纳入“测”的范围,特别是没有将“测”作为一种与“传”并列的解经模式。湛氏已自觉将“测”作为一种新的解经模式。湛氏的测类经学著作都涉及“经”“传”“训”“测”四者的关系。
“经”是指儒家经典,被儒家奉为“不刊之书”(15)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宋刊本,第2页(序页)。“恒久之至道”(16)刘勰著,杨明照校注:《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页。。《五经》在汉武帝时就被确立为“国家的经典”(17)陈来:《陈来讲谈录》,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四书》在宋代被魏了翁作为“经”而列入《九经要义》中,有《论语要义》《孟子要义》和《礼记要义》(18)冯桂芬总纂:《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九,1883年刊本,第22页(卷页)。;在元代被吴澄奉为“圣经”,并称“读圣经者先《四书》”(19)吴澄:《吴文正集》卷九,《何自明仲徳字说》,四库全书本,第19页(卷页)。。在湛氏那里,《周易训测》以伏羲的卦画、周文王的彖辞和周公的爻辞为“经”;《二礼测》以《仪礼》《曲礼》为“经”;《四书测》以《四书》为“圣人之训”,意即《四书》为“经”。
“传”是相对于“经”而言的,是对儒家经义的阐发。杜预云:“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20)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宋刊本,第2页(序页)。;孔颖达云:“传者,传也。博释经义,传示后人。”(21)杜预注,孔颖达疏:《左传注疏》卷二,阮刻本,第1页(卷页)。合而言之,“传”不仅对经义有所阐发,也对经文有所补充。例如,《易》有孔子作的《易传》;《礼》(《仪礼》)有《礼记》,熊禾称大、小戴《记》为“传”(22)熊禾:《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四,《刊仪礼经传通解疏》,清正谊堂全书本,第18页(卷页)。。汉代以来,这些“传”类著作逐渐升格为“经”,如:《易传》(《十翼》)在西汉成为“《易经》十二篇”(23)班固著,颜师古注:《前汉书》卷三十,武英殿本,第1页(卷页)。的一部分;《周礼》《礼记》在唐代成为《九经》(2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60页。的组成部分。在湛氏那里,《周易训测》以孔子的《易传》(《十翼》)为“传”,《二礼测》以《戴记》及《逸传》为“传”,这些“传”的地位与“经”相近,是“明经”的直接通道。但何休说:“传谓训诂。”(25)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页。这里的“传”只具有一般性训诂意义,包含“注”“疏”“正义”“音义”“笺”“章句”“集注”等解经形式,如程颐的《伊川易传》、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朱熹的《诗经集传》(《诗传》)。不过,湛氏不点名地批评程颐“分传附经”(26)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81页。的解《易》模式,黄省曾也指出:“后之儒复于经而有传,是与仲尼争衡也。”(27)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二十六,《吏部尚书湛公古易经传训测序一首》,明嘉靖间刻本,第12页(卷页)。湛氏的测类著作中也有大量训诂内容,如《修复古易经传训测》的书名有“训”字,《修复四书古本测》又名《四书训测》,《二礼测》中各卷开头有“甘泉湛若水集训并测”之说,但这些“训”并非都是“集”他人之“训”,也有自己独到之“训”。不过,最能体现湛氏的独特解经方式和独到见解的是他的“测”。
何谓“测”?湛氏在《二礼经传测》中定义说:“测也者,测也,近取诸心,远取诸文,会而测之,知圣人之精意如此乎,如彼乎。故测之抑变化不测乎!故曰测。”(28)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测”即是推测、测度。“测”的特征表现为:第一,从测的方式说,就是通过近发自本心、远参以经文以作出综合推断;第二,从测的目标说,就是要推断出“圣人”的精深意旨;第三,从测的精度说,因事物变化多端而存在测不准的可能性。
后来,湛氏在《修复四书古本测序》中对“测”作了新的阐释:“测也者,测也,不敢知之谓也。是故其词谦,其指严,其忧患深,其析义也微。夫圣贤之弘训奥义,其普矣,畸矣,如天之无不覆矣,如地之无不载矣,如天地阴阳之变化而不可以典要索矣。知在此乎?在彼乎?而生乎百世之下,神会乎百世之上,以意逆志,研精覃思,钓深致远,犹徐徐正以待其自来,而不敢强探力索焉,以自得夫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曰测。……夫天之理,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如天地阴阳之变化而不可测。不可测斯,矧可言斯!知不可言,而吾测之,以心测心,言之不得已也。”(29)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97-298页。在这段话中,“测”具有新的特点:第一,“测”是一种谦辞,有“不敢知”之谓;第二,“测”是一种“自得”,不可以“典要”(绝对的准则)来衡量,而应“以意逆志”,务求“自得”;第三,“测”是一种“以心测心”,使测者与古圣贤之心在“天理”上相契合。
在湛氏那里,对于不同的《经》与《传》,则有不同的“测”的对象。在《二礼经传测》中,《仪礼》和《曲礼》的“经”与“传”都是“测”的对象。在《修复古易经传训测》中,“训测”是指“训说仲尼之翼言而彰测其蕴,不敢以训测夫经”(30)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二十六,明嘉靖间刻本,第11页(卷页)。,意即“训测”的对象是“传”而不是“经”。作“测”的目的在于“俾学者因‘测’以明‘传’,因‘传’以明‘经’”(31)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81页。。他在《修复四书古本测》中指出:“夫《四书》者,子朱子已‘传’之矣,而子复有‘测’焉。”(32)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98页。意即《四书》为“经”,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传”,而他对《古本四书》深义的揭示为“测”。“测”与“经”“传”三者的关系是:“传解其词,测明其义,以翼乎传,以发挥夫圣人之训。”(33)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98页。而他的“测”则是对经传之“义”的推断,亦即对“圣人之训”的发挥,属于对经传的深层意蕴的把握。故他自信其“测”比朱子的“传”在解经上更深入,更高一筹。这也是他创立“测”这一新的解经模式的目标之所在。
三、湛氏“以测解经”经学模式的历史影响
湛氏开启了中国经学史上“以测解经”的经学模式,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
(一)测类经学著作在明末频繁出现
湛氏“以测解经”的经学模式在明末学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涌现了一批与之相似或同名的测类经学著作。一是廖暹(1528年举人),邹守益弟子,著有《四书测》《春秋测》(34)张文旦修,陈九畴纂:《康熙高安县志》卷八,1671年刻本,第6页(“文苑”页)。。二是曾朝节(1534-1604),曾从程天津讲王艮的“格致之学”,著有《易测》(35)张奇勋修,周士仪纂:《衡州府志》卷十六,1671年刻本,第41-43页(卷页)。,该书的段文结构是由《易经》原文和另起一段、不写“测曰”的测文组成。三是管志道(1536-1608),耿定向弟子(36)王昶:《直隶太仓州志》卷六十五,1802年刻本,第4-5页(卷页)。,著有《大学测义》、《中庸订释》后附《中庸测义》、《论语订释》后附《论语测义》、《孟义订测》(37)管志道:《孟义订测》,1608年刻本,第1页(“自叙”页)。。现存《孟义订测》段文的完整结构主要是由《孟子》原文(内有音注)、“订释”和“测义”构成,与湛氏《二礼经传测》的体例结构相似。四是万尚烈(1546-1640?),章潢弟子,究心姚江致良知之旨,著有《四书测》(于《大学》、《中庸》独尊古本)、《诗述传测》(一称《诗测》)(38)承霈修,杜友棠纂:《新建县志》卷九十四,1871年刻本,第45页(卷页)。、《易赞测》(测孔子之赞《周易》)、《易大象测》(测六十四大象)(39)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四库全书本,第13-14页(卷页)。。五是吴三极,可能为王阳明弟子陈明水的弟子(1569年岁贡),著有《心法大要》(40)李士棻修,胡业恒纂:《东乡县志》卷十三,1869年刻本,第9页(卷页)。《大学测》《中庸测》(41)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五、卷一百六十一,四库全书本,第4、12页(卷页)。。六是李颎(1606年举人),邹守益的弟子李材(1529-1607)之子,著《论语测》(42)何士锦修,陆履敬纂:《丰城县志》卷十一,1664年刻本,第26-27页(卷页)。。七是阮文(旻)锡(1627-1714?),师事东林党人曾樱(1581-1651)传“性理学”,著有《四书测》(43)周凯纂修:《厦门志》卷九、卷十三,1839年玉屏书院刻本,第2(卷页)、22页。。在这7位明末学者中,前6位都属王门后学,故他们的测类著作难免会打上王学的烙印,而王学与湛学又都属于心学阵营,所以他们很可能受到湛氏“以测解经”治经模式的影响。而在湛门后学中反而未见有测类著作,可能是他们以为湛师已经作测而无须再作测,但也反映出湛氏一派心学在明末的衰落状态。
(二)湛氏测类经学著作被明末学者广为引用
对于《修复古易经传训测》,明代熊过的《周易象旨决录》、潘士藻的《读易述》、黄正宪的《易象管窥》、程汝继的《周易宗义》、汪邦柱的《周易会通》、张次仲的《周易玩辞困学记》、方孔照的《周易时论合编》以及清代查慎行的《周易玩辞集解》、汪璲的《读易质疑》都有引用。对于《四书训测》,明代王肯堂的《论语义府》、王国瑚的《四书穷钞六补定本》、沈守正的《四书说丛》、寇慎的《四书酌言》、张自烈的《四书大全辩》、桑拱阳的《四书则》和清代孙奇逢的《四书近指》、刁包的《四书翊注》、吕留良的《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陆陇其的《四书讲义困勉录》及《续困勉录》、王步青的《四书本义汇参》、孙见龙的《五华纂订四书大全》、吴昌宗的《四书经注集证》都有引用。因《修复古易经传训测》《四书训测》没有像《二礼经传测》那样被统治者贴上“与孔子相戾”的标签,反而有利于明末清初学者在学术意义上无所顾忌地加以引用。在引用湛氏测类经学著作的学者中,寇慎之学“出于姚江”(44)纪昀、永瑢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八)》,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6页。,而王肯堂“历引宋元明诸家讲义”(45)纪昀、永瑢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八)》,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2页。,王国瑚“博采精择”(46)施凤来:《四书穷抄四补序》,载王国瑚:《四书穷钞六补定本》,1651年刻本,第4页(“序”页)。,沈守正“一致百虑,殊途同归”(47)沈守正:《四书说丛》,《四书说丛序》,1615年刻本,第4页(“序”页)。,桑拱阳“取诸家讲章立说不同者,删定归一”(48)纪昀、永瑢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八)》,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7页。,孙奇逢视姚江为“接周子之统”“紫阳之贞”(49)孙奇逢:《理学宗传》,1667年张沐程启朱刻本,第6-7页(“叙”页)。,王步青主张“使殊途百虑胥统汇于同归一致之中”(50)王步青:《四书本义汇参》,1745年敦复堂刻本,第15页(“发凡”页)。,孙见龙“兼收并录”(51)孙见龙:《五华纂订四书大全》,1748年五华书院刻本,第3页(“凡例”页)。,吴昌宗“一遵朱子,复闲采其异义者”(52)吴昌宗:《四书经注集证》,1798年刻本,第2页(“凡例”页)。。他们或尚阳明心学,或尚程朱理学,但对湛氏的“训测”还是持包容态度的,主要是将湛氏观点作为“一家之言”来看待。如刁包虽不认同王、湛的《大学古本》而认同朱子《大学今本》(53)刁包:《四书翊注》,《大学》卷三,《大学古本辨》,清道光同治间刻本,第39页(卷页)。,但还是引用湛氏的“穷,如巢穴之穷”及“此心做主不起”(此实为周冲语)之说作为一家之言。不过,也有少数学者对湛氏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如张自烈称湛氏“大学即国学”之说“谬甚”(54)张自烈:《四书大全辩》,《大学章句》卷一,1640年石啸居刻本,第10页(卷页)。;吕留良以由湛若水而陈献章、王守仁而陆九渊而达磨而吿子为一系,而以由朱子而程子而孟子而孔子为另一系,斥陈献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55)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答吴晴岩书》,1725年天盖楼刻本,第24页(卷页)。。无论明末清初学者引用湛氏测类经学著作时持何种态度,但都反映了湛氏测类经学著作在当时的学术影响力。
四、“以测解经”经学模式的悲剧命运及其原因
湛氏“以测解经”的经学模式虽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其学术贡献,然而历史并没有给它留下应有的地位,几乎可以用“悲剧”来形容它的历史命运,这与湛氏生前被嘉靖帝所打压及其“以测解经”的非正统性密切相关。
(一)湛氏测类经学著作的悲剧命运
湛氏测类经学著作虽然在明末清初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但一直被明清官方所打压,除《二礼经传测》外,其他测类著作在清代中后期失传殆尽,学术界也就无从引用了。湛氏测类著作的结局可以反映出湛氏“以测解经”经学模式的悲剧命运。
其一,湛氏测类著作均未获得朝廷刊刻许可。《古大学测》和《中庸测》自1518年终稿后,没有上呈朝廷审阅,只是赠给自己的心学阵营好友(如王阳明、方献夫等)及弟子传阅。《二礼经传测》本望获得朝廷在刊行上的支持,但嘉靖帝以礼部尚书夏言称“与孔言相戾”为由,裁定该书“不可传示后学”,置之不省(56)范守已:《皇明肃皇外史》卷十六,宣统津寄庐钞本,第6页(卷页)。。至于何以“与孔言相戾”,曾师从湛氏(57)张慎为修,金镜纂:《长兴县志》卷二十三(上),1649年驯雉堂刻本,第54-55页(卷页)。的顾应祥后批评说:“以曲礼、仪礼为二,又以曲礼置仪礼之前,而又以周礼由曲礼中出,曲礼为纲,周礼为目,是以曲礼为经礼矣,岂圣人所谓‘曲礼三千’之意乎?”(58)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又五,明刻本,第8页(卷页)。此次申请官方刊行失败后,湛氏再没有将其他测类著作申报朝廷了。结果,《二礼经传测》由弟子卞莱刊刻,《修复古易经传训测》《学庸训测》均由弟子葛涧刊刻,《修复四书古本测》由袁贤刊刻(59)盛仪:《惟扬志》卷十二,1542年刻本,第11页(卷页)。。这意味着湛氏的测类著作没有一部在刊行上获得朝廷的支持,都是由弟子私刻刊行的。而私刻又被他的政敌当作攻击的把柄。游酢的后代游居敬(1509-1571)说湛氏“自刻书册,而不顾有司之扰”,故向朝廷建言“将私刊刻若水之书,尽行黜远”(60)吴栻修,蔡建贤纂:《南平县志》卷十二,1921年铅印本,第35、39页(卷页)。。清朝基本上沿袭嘉靖朝的政策,对湛氏的测类著作仍然予以排斥,不仅《四库全书》未收入,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只收入《二礼经传测》,还以“所注亦皆空谈”(61)纪昀、永瑢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五)》,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79页。批评之,《修复古易经传训测》和《修复四书古本测》更是只字未提。
其二,湛氏测类著作除《二礼经传测》外都已失传。湛氏致仕回乡时,并未带回多少测类著作。去世后,他的测类著作在家乡丧失殆尽,故《康熙增城县志》称《四书测》《二礼经传测》《古易经传测》《古本大学测》已“缺”(62)蔡淑修、陈辉璧纂:《增城县志》卷十,1686年刻本,第1页(卷页)。。从全国来说,最先失传的是《仪礼补逸经传测》,朱彝尊在《经义考》中称“未见”(63)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三十四,四库全书本,第10-11页(卷页)。;《古本四书训测》在清初尚“存”(64)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五十六,四库全书本,第16页(卷页)。,而在道光年间已“未见”(65)阮元修、陈昌齐等纂:《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九,1822年刻本,第27页(卷页)。,故王肇晋引用时只能取自陆陇其的《四书困勉录》(66)王肇晋:《论语经正录·采录诸儒姓氏》,1894年刻本,第3页。;《修复古易经传训测》《古大学测》及《难语》、《中庸测》及《难语》在道光年间尚“存”(67)阮元修、陈昌齐等纂:《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九,1822年刻本,第3、27页(卷页)。,而在《光绪广州府志》中都只称“据《经义考》”(68)史澄:《广州府志》卷九十,1879年刊本,第1、13页(卷页)。。这些测类著作的失传,是令人惋惜的。
(二)“以测解经”经学模式悲剧命运的成因
第一,遭嘉靖帝不断打压。湛氏在嘉靖年间做过三任尚书,似乎得到皇上的重用,但嘉靖帝既没有赋予他与其职位相称的权力,也不认同他的学术思想,时常任由湛氏的政敌对其进行学术和人身攻击。湛氏得罪嘉靖帝,最初是因反对嘉靖帝追尊其父兴献王及在奉先殿侧建庙以祀兴献帝,后又因在“郊祭礼”等问题上与嘉靖皇帝意见相左(69)黎业明:《思想和政治:湛若水与“大礼议”之关系述略》,《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令嘉靖帝尤为不快的是:一为湛氏1524年上的《乞谨天戒急亲贤疏》,将正德朝发生的“科道囚、老臣弃”现象比附才运作三年的嘉靖朝,并援引《周易》屯、否二卦来说明嘉靖朝存在“阴阳隔而不通,内外离而不孚”的严重危机。故反湛学的徐学谟批评此疏“非惟忧治危明之过,且于经义殊不相蒙”,认为对年轻的皇上“不宜进此疑骇无当之论,以启其疏远儒臣之端”,并认为湛氏后来“虽荐至大僚,终不柄用,而累以伪学目之”的原因与此疏给嘉靖帝造成“先入”的不良印象有关(70)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二,1698年徐光稷活字印本,第7页(卷页)。。二为湛氏1531年所上的《劝收敛精神疏》,劝嘉靖帝求嗣必“收敛精神”。嘉靖帝听后生气地说:“尔既欲朕收敛精神,更不必烦扰”(71)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九,1681年黄楷刻本,第29-32页(卷页)。。故反湛学的谈迁认为,嘉靖帝“盖深窥其微(弊病)”(72)谈迁:《国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而发此言。皇上对湛氏学术的冷漠,使得那些对湛氏不满的官员开始发难。御史冯恩为王阳明弟子,1532年10月上疏,劾张孚敬为“根本之彗”、汪鋐为“腹心之彗”、方献夫为“门庭之彗”;斥湛氏素行“不合人心”,学术乃“无用道学”。嘉靖帝大怒,将其下诏狱(73)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二十七,明天启刻本,第55、58、61页(卷页)。。沈德符(1578-1642)评议说:“恩虽用他语得罪,而此言则不以为非。”(7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1869年补修本,第25页(卷页)。意即嘉靖帝喜欢任用“锐意功名之士”,其对冯恩治罪,是因其“乞斩三奸”而冒犯,而不以其视湛学为“无用道学”为非。不过,湛氏在1533年初作的《乞休疏》中对冯恩的攻击言论未作反驳,反称“有警于臣多矣”,并乞求皇上将他罢黜放归,以免遭“诛戮之祸”(75)湛若水:《湛若水全集(22)》,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51-52页。。
《二礼经传测》的刊行申请被嘉靖帝否决,是湛氏测类著作得不到官方支持的开端。我们不烦从支持者和反对者两种不同的心态来说明湛氏的测类著作所经历的风波。吴昂(字德翼)与魏校和湛氏是同年(1505)进士,他告诉魏校说:“甘泉《二礼测》成,请于朝梓行天下。”魏校随即给湛氏去信说:“甚盛甚盛,莫更须讨论否?”(76)魏校:《庄渠遗书》卷十三,《与湛玄明》,四库全书本,第8页(卷页)。魏校信中既对湛氏将该书上报朝廷审核批准刊行表示祝贺,又对该书能否通过朝廷的审核讨论表示担忧,说明朝廷阻力肯定不小。朝廷的阻力主要是皇上和礼部,尚书夏言以“与孔言相戾”为该书定性,给了素视湛学为“伪学”的嘉靖帝拒绝支持刊行的绝佳理由。游居敬对王、湛心学极为排斥,当他1536年11月“内睹邸报”时看到礼部给予“奉圣旨,既与孔子之言相戾,不可传示后学,罢,钦此”的批复后,自然兴奋不已。次年,年仅28岁的游氏就以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身份上奏《乞戒饬阳倡道学阴怀邪僻大臣以端士习以光圣化事》,希望皇上以湛氏“偏诐之学、滥鄙邪诈之行”而“赐罢归或致仕,以示惩创”,还要将湛氏所创书院“或令拆毁,或令改别馆,以灭其名”(77)吴栻修、蔡建贤纂:《南平县志》卷十二,1921年铅印本,第37、35、39页(卷页)。。嘉靖帝将此奏下到吏、礼二部议断,尚书许赞、严嵩会奏说:湛氏所著书论,“窥测古人章旨,容有意见不同,措词未当,但原非诋毁之说,况于经传亦有发明,无足过谪”,虽然生徒中有附和标榜者,但“以是而深咎若水之罪,似未免于责备之过”(78)严嵩:《南宫奏议》卷二十,《请禁私创书院》,1545年严氏钤山堂刻本,第15页(卷页)。。应该说,二尚书对湛氏经学还是以肯定为主,是比较公道的。但嘉靖帝对私创书院还是强令有司毁之,并在学术上完全站在游氏一边,对湛学不仅生前打压,死后也不放过。湛氏曾孙寿鲁1561年奏乞其祖赠官,吏部复言:“若水学行醇正,舆望所归,宜允其请。”但嘉靖帝发怒说:“若水伪学乱正,昔为礼部参劾,此奏为之浮词夸誉,其以状对。”(79)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二十二,1608年徐光稷活字印本,第5页(卷页)。结果包括尚书欧阳必进在内的吏部相关官员遭到重罚,足见嘉靖帝对湛氏“憎之如此”(8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1869年补修本,第25页(卷页)。。
第二,与官方经学相冲突。朱彝尊说:“宋元以来,言道学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学,源于二程子。……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面攻之。”(81)朱彝尊:《曝书亭集(上)》,国学整理社,1937年版,第434-435页。这就是说,程朱理学及经学自宋至清初都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明代永乐帝更以程朱理学及经学为导向来诏颁《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嘉靖帝又“厉行文化专制政策”(82)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凡有不合于朱学之言者尽遭申斥。他以程朱“主敬”说为依据,于1526年作《敬一箴并序》(83)赵廷瑞:《陕西通志》卷十七,1542年刊本,第7页(卷页)。,以树立自己的“圣学”;又以“心学”为“伪学”,于1528年制“卓尔之见,一贯之唯;学圣君子,勖哉勿伪”之“十六字箴”(84)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宸章召对》,1609年中曼山馆刻本,第3页(卷页)。以警示臣下。王阳明因生前崇尚《古本大学》而与朱熹的《大学章句》相悖,嘉靖八年(1529)二月(刚去世两个月),朝廷就“下诏禁伪学”(85)马昊宸:《王阳明全集(3)》,线装书局,2016年版,第1137页。。同年三月,嘉靖帝以“《大学》《中庸》经传先儒具有定论,我祖宗已表章颁示天下”根据,斥陈云章所进《大学疑》《中庸疑》等书“剽窃谬言,淆乱经传”,要予烧毁(8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世宗实录》卷九十九,1965年编,第2357页。。而湛氏1505年(一说1506年)与阳明“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87)钱德洪、王汝中:《王阳明年谱》,力行要览编辑社,1933年版,第15页。,1523年为云章作《钝斋记》(88)湛若水:《湛若水全集(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487页。并曾赠诗称“钝斋吾老友”(89)江璧修、胡景辰纂:《进贤县志》卷十九,1871年刻本,第19页(卷页)。,二友都曾获得嘉靖帝的重用,但他们的学术都被嘉靖帝所否定,湛氏的学术自然也难逃厄运。对于湛氏来说,《二礼经传测》将《曲礼》置于《仪礼》之先,这与朱子 “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曲礼》《少仪》又自作一项”(90)黎靖德:《朱子语类》第3卷,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964页。的作书构想及其《仪礼经传通解》对《仪礼》篇目的安排明显不同。《修复古易经传训测》虽在推崇《古易》上与朱子的《周易本义》相一致,但与永乐帝钦定的以《程氏易传》为正统而“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传》之后”(91)纪昀、永瑢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87页。的《周易大全》有异。《修复四书古本测》崇尚《古本四书》,而与朱子崇尚《今本四书》有异,且不赞同朱子将《大学》分为“三纲领、八条目”(92)湛若水:《杨子折衷》卷五,明嘉靖刻本,第10页(卷页)。。因此,湛氏的测类著作与明代官方提倡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相冲突。而清代也奉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因此,湛氏的测类著作自然也为清代官学所不容,自然进不了钦定《四库全书》甚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对湛氏学术的禁锢,到了宣统年间仍未冲破。1909年5月,给事中陈庆桂奏请将湛若水“从祀孔庙”(93)王思章修,赖际熙纂:《增城县志》卷十八,1921年刻本,第15页(卷页)。。而外务部主事章钰在《外务部覆明湛若水从祀文庙说帖》中将前人对湛氏著作的批评言论(如《二礼经传测》“标目殊伤烦碎,所注亦多空谈”)汇集在一起,由此评议说:“甘泉著述虽多,或入存目,或并不入存目,其为《四库》著录者,又皆瑕瑜互见。……若水品诣久经先朝论定。”(94)章珏:《四当斋集》,1937年铅印本,第5-6页。意即湛氏无论人品还是学术,都不符合从祀孔庙条件。
五、余论
湛氏的测类著作除《二礼经传测》外均已失传,反映出他的“以测解经”的新的经学模式经受了巨大挫折,也给我们系统研究湛氏的经学和心学思想带来缺憾。不过,通过他的测类著作的自序和他序、《约言》以及被人引用的原文等遗稿,我们仍可大体了解湛氏各测类著作的写作目的、体系结构和核心思想。
湛氏学术思想在历史上因不符合“正统”而被反对者斥为“伪学”“新说”。游居敬称其“舍旧传而立新说”,也就是用“内外合一”“体认天理”“存心”之“新说”取代由朝廷颁布天下的“五经、四书、传注、五伦”之“旧传”(95)吴栻修、蔡建贤纂:《南平县志》卷十二,1921年铅印本,第37、35、39页(卷页)。。正因为湛学为“新说”,它与同被视为“伪学”和“新说”的王学一起,打破了明代中后期由程朱理学和正统经学所主导的僵化沉闷的学术气氛,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兴起的前导。而在湛学与王学之间,黄宗羲偏向王学,称“先生(若水)以为心体万物而不遗,阳明但指腔子里以为心,……然天地万物之理,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若以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万物以为广大,则先生仍为旧说所拘”(96)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60页。。而熊赐履偏向于湛学,称阳明主“致良知”,而甘泉主“随处体认天理”,则“阳明之虚不若甘泉之实”(97)熊赐履:《闲道录》卷十八,清刻本,第22页(卷页)。。近代章太炎也说:“玄明(若水)所主,在随处体验天理,文成(阳明)以为求之于外;玄明言阳明以方寸为心,吾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故以吾为求外耳。……心体万物而不遗,所见远出文成之上。”(98)章炳麟:《章太炎全集(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页。不管前人如何评价,湛氏“以测解经”的经学模式及其整个心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是有独特历史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