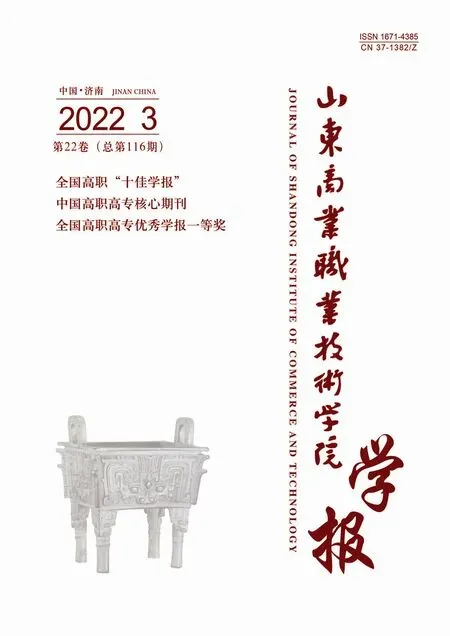劳伦斯小说中的孤独主题研究
2022-03-18胡春媛
胡春媛
(江苏省运河高等师范学校,江苏 邳州 221300)
一、引言
作为在20世纪英国文坛上放射出独特光芒的一颗巨星,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在44年短暂的一生里颠沛流离、浪迹天涯,尝尽人间冷暖,命运多舛。评论界偶尔会慷慨地赐给他一顶桂冠,但更多的时候是向他无情地投掷荆棘和石块。他被世人赋予多重身份:儿子和情人、“性爱牧师”“一个着了魔的人”“天才预言家”……,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叔本华说过:“人,要么庸俗,要么孤独。”卡森·麦卡勒斯也写道:“人越是明白,越是有追求,就越孤独。”作为一位拥有独特经历的天才作家和艺术家,孤独渗入了劳伦斯的血液,伴随其一生。劳伦斯曾经在散文《爱》中这样敞开心扉:“我仍要独立,成为宝石样孤独的人,与别人分离,像一头狮子般傲慢,像一颗星星般孤独。”[1]
劳伦斯的孤独首先来自他原生家庭的影响。劳伦斯于1885年9月11日出生于英国诺丁汉郡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其父母长期关系不和,母亲对儿子倾注了畸形的爱,束缚了劳伦斯与女性的正常交往,让他失去了追求美好爱情的勇气。由于劳动家庭出身,劳伦斯本性淳朴善良,但是性格复杂多变。浪漫、粗鲁、莽撞、乖戾、温柔、忧郁、傲慢等各种不同性格在他身上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畸形性格让他有时像天使有时像魔鬼——与人相处融洽时恨不得对人掏心挖肺,倾其所有;稍有龃龉便面目狰狞,拒人于千里之外。因而劳伦斯的住处时而高朋满座,时而门可罗雀。
劳伦斯的孤独还来自他标新立异的思想的影响。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自己对男女情爱的思索,用如椽巨笔来抒发自己对工业文明摧毁人性的痛恨,大胆挑战传统的社会习俗。其作品惊世骇俗,宛如平地惊雷,掀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比阴沟里的法国色情小说还要肮脏”,他的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历经几十年才被解禁。1920-1930年,他被迫告别祖国,颠沛流离,最后客死他乡。另外,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建造一个“拉纳尼姆”王国,并且在不断地向崇拜者鼓吹自己的乌托邦梦想,妄图拉拢信徒,但追随者却寥寥无几,最终只能成为一种痴人说梦。
劳伦斯曾悲叹:“生活是虚假的,艺术是真实的”,但是在《道德和小说》这篇著名散文里他又提出:“艺术的任务是展现人与其周围世界在活生生之时的关系。”[2]众所周知,艺术高于生活,但必然来源于生活,艺术的殿堂不可能建立在海市蜃楼之上。这位天才作家实际上把生活中的不少经历投射到他所创造的人物身上,他的许多作品都与他的情感体验息息相关,而孤独又常常是他沉浸其中的一种情怀。所以劳伦斯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孤独者,揭示了深刻的孤独主题。
二、孤独者群像图
劳伦斯在自己的小说中描绘了个性禀赋不同的众多孤独者,这些孤独者各有各的不幸。
有的孤独者紧闭心扉,离群索居,不与任何人交流,在自己的世界里顾影自怜、踽踽独行。例如,在《爱岛的男人》里,爱岛之人就像劳伦斯一样致力于寻找一座与世隔绝的、“孤立在时空之海”“融满自己人格”、神秘迷人的孤岛,这座岛其实就是他的精神庇护所和人间的“伊甸园”。这部小说充满了对人类孤独情感的细腻形象的描写,描绘出了一副自我封闭的孤独者画像,写尽了孤独者内心的恐惧、无奈和落寞。
有的孤独者逃离自己的家庭,四处漂泊流浪,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例如,在《阿伦的杖杆》这部长篇小说里,主人公阿伦·希森是一个有个性有追求的年轻人,“他从不随波逐流,总是我行我素。他妻子说他是倒行逆施。”[3]劳伦斯所描绘的经历了战争蹂躏的欧洲大陆仿佛成了一个患有炮弹休克症的士兵,失去了前进动力和思想力量。主人公阿伦在这种混乱的世界中,彷徨流浪,不知道何处是归途。他与世界好像隔着厚厚的一堵墙,只有长笛才能暂时抚慰他那颗孤独痛苦的心,但最后他的长笛也被弄断了。阿伦又该何去何从呢?小说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
有的孤独者与世俗妥协,得过且过,过着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耗尽自己平庸的一生。劳伦斯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写出了乔治这个被命运毁掉的孤独者的满腔辛酸。一个心地善良单纯的农家子弟最后却因为不如意的婚姻沦落成为一个别人眼中的怪物,每个人提到他时几乎都充满了鄙夷和不屑,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理解他的朋友,他只能慢慢走向毁灭。
有的孤独者无法忍受这个令人窒息的社会和不公平命运的压迫,奋起反抗。《牧师的女儿们》中教区穷牧师的二女儿露易莎不愿意像大姐玛丽那样嫁给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人,她爱上了退伍归来的矿工阿尔弗莱德。文中,亲人之间、恋人之间都像被一层钢板隔离着,每个人似乎都在带着假面具辛苦地演戏给别人看。露易莎鼓足勇气,抛弃了女人的矜持,最终赢得了幸福的爱情,但却被自私狭隘的家人逼得背井离乡。
有的孤独者无法忍受世人的鞭挞和冷眼,毅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侵入者》中的音乐教师辛格蒙德的悲剧是一部性格悲剧,也是一部命运悲剧。他孤独敏感脆弱,勤于思索而怯于行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能自拔,用孤独的外壳作茧自缚,无法与人交流。命运对他来说就是一股巨大的漩涡,他深陷其中,只能任其吞噬。
三、孤独的成因
(一)灵肉分离的痛苦
劳伦斯提倡“血性意识”,认为一个人应该永远服从自己的冲动。他曾对朋友说:“我的伟大宗教就是相信血和肉比智力更聪明。我说的头脑所想的可能有错,但我们的血所感觉的、所相信的、所说的永远是真实的。”[4]但是,令劳伦斯大失所望的是,当时的不少英国男子缺少阳刚之气,他曾经痛骂道:“这些臭不可闻的人,……,卑贱不堪,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给我道德败坏的感觉,几乎已至堕落的地步,这就使我梦见许多甲虫式的人物。”[5]在爱情生活中,当时的不少英国卫道士“谈性色变”,将之视为洪水猛兽。种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让真诚的劳伦斯怒火中烧,他在散文《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中指出:“我们过的是一种分裂的生活”“我们的性思想是落后的,它还处在冥冥中,在恐惧中偷偷摸摸爬行,这状况是我们那粗野如兽的祖先们的心态”“若想要生活变得可以令人忍受,就得让灵与肉和谐,就得让灵与肉自然平衡、相互自然尊重才行。”[6]在自己的作品中,劳伦斯对这种病态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塑造出了不少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爱情的灵肉分离带来的精神痛苦和人生困境以及人物内心无法排遣的孤独之感。
《儿子和情人》中的主人公保罗因“恋母情结”而饱受灵肉分离之苦。同米丽安的交往让保罗感到 “她没有付出热情。她从没有过活力,毫无生气。追寻她就像追寻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一样。”[7]米丽安的清心寡欲和控制欲让她不时地对心智尚未成熟的保罗进行无意识的控制,这让保罗的生命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保罗与第二位女友克莱拉交往时,起初两情缱绻,但是两人之间始终缺乏精神的交流,最后只能分道扬镳。在母亲死后,保罗成了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
劳伦斯对这种灵肉分离状况做出了精彩的比喻:“我们的根在流血,因为我们斩断了与大地、太阳和星星的联系;爱变成了一种嘲讽,因为这可怜的花儿让我们从生命之树上摘了下来,插进了桌上文明的花瓶中,我们还盼望它继续盛开呢。”[8]他提倡唤起男女双方的“血性意识”来促进英格兰的复活,重建男女之间被毁灭掉的伟大关系,让肉体从清规戒律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让热恋的男女再次拥有灵肉和谐的美好爱情和自由快乐的凡俗生活。
(二)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虽然给人们带来了科技的巨大进步、劳动效率的极大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巨大化,但却对如诗如画的大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毁掉了许多人间乐园。作为一个矿工之子,劳伦斯多次以矿工们的日常生活为素材来构思小说,也多次以矿区为写作背景来讲述动人的故事。在小说中,劳伦斯用细致的笔触生动地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幅被工业文明弄得丑陋不堪的英国农村风光图,也剖析了这种美好自然的陨灭所带来的恶果——矿工人格被异化,家庭生活开始变得不和谐,家人之间无法相互理解和相互扶持,每个人都寄生于孤独的泥淖中。
《菊花的清香》的第一段就对荒凉冷清的矿区环境有过精彩的描写:“在池沼的另一边,矿井井口隐隐约约地显现着,在下午呆滞的光线里,它的火焰像是红色的伤疤,舔着灰色的井壁。在过去便是布林斯利煤矿高耸的尖塔形烟囱和笨拙的黑色车头。”[9]矿工们住的房子破烂寒酸,被塌方闷死的矿工沃尔特的遗体被抬到家里时,怀孕的妻子伊丽莎白在擦拭丈夫遗体时深深感觉到,孤独感就像冰冷的死亡般的菊花的清香一样弥漫在寒碜的小屋里,连腹中的胎儿似乎也成了和她毫无任何关系的重负,躺在那儿的丈夫更成了一个陌生人。伊丽莎白好像突然明白自己和丈夫从未真正地走进过对方的内心,他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按照各自的运行轨迹运转。伊丽莎白甚至认为即使到了阴间,她和丈夫相见也只会平添一种羞愧感。这是一种多么寒彻肌骨的落寞和孤寂!
(三)社会规范的制约
劳伦斯生活的时代,充满了风云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劳伦斯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心灵阴影。在一战中他虽然没有入伍参战,但是由于妻子弗丽达的德国国籍以及他的反战言论,劳伦斯在英国受到了监视,还曾被强迫进行入伍体检。受尽屈辱的劳伦斯被迫背井离乡,亡命天涯。在与祖国告别时,他把英格兰比作一口缓缓地沉入地平线之下的灰色棺材。的确,一战结束后的欧洲大陆满目疮痍,巨大的外伤和内创让欧洲人意志消沉、颓废沮丧。而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决定了英国仍是一个被众多社会规范约束的国家,这些社会规范让内心有追求的人举步维艰,成为局外人,倍感孤独。劳伦斯对此不吝笔墨,在小说中多有呈现。
1920年出版的《误入歧途的女人》深刻地揭示了因社会规范和世俗偏见对人性的压抑而造成的种种孤独。主人公艾妮维娜·沃尔顿生活的时代,出现了一种社会怪现象——除了最底层的阶级以外,每个阶级都出现了大量的未婚小姐。艾妮维娜居住的沃德豪斯镇的商人和牧师这类有钱人家就有一大群未婚小姐,包括艾妮维娜家里聘用的家庭教师弗罗斯特小姐和女工管理人平纳希小姐,艾妮维娜也差点忝列其间。这种状况是当时的社会习俗和阶级偏见造成的。这些小姐们的家庭出身要求她们在与男人相处时要保持矜持,不能做出“出格的事情”,结婚更要讲究门当户对。在沃德豪斯镇这样的小地方她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而她们又固步自封,不愿意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更不乐意随爱人迁徙到异地他乡。因此,这些未婚小姐在面对热烈的追求者时,家庭淑女式教养和社会道德规范常常让他们面对婚姻踟蹰不前、错失良机。艾妮维娜曾经无限感慨:“为什么在自由的天空的名义下,却有人类的准则呢?为什么呢?纯粹是为了恃强凌弱的狭窄偏见。”[10]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男爵夫人康妮被迫每天和瘫痪的丈夫克里福德·查泰莱进行无聊的精神交流,如谈话、构思小说、招待朋友等,康妮的生命之花逐渐变得枯萎。后来,康妮和猎场看护人麦勒斯相爱,却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当地人的流言蜚语让查泰莱先生勃然大怒,辞退了麦勒斯;其次,康妮的父亲和姐姐也不赞成两人在一起,因为他们觉得康妮不该自降身份去找一名猎场看护人;最后,连康妮自己也觉得丢脸,甚至找了一个无聊浅薄的所谓艺术家来冒充自己的情人,这让麦勒斯感觉受到了很大的侮辱。由此可以看出,门第观念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十分盛行,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成为横亘在康妮和麦勒斯之间的巨大鸿沟,造成了两个有情人之间的隔膜和猜疑,也成为他们内心深处奔腾不息的孤独痛苦情感漩涡的源头。
四、结语
孤独是人类文学史上永恒的主题,也是西方现代文学关注的焦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道尽了百年家族在地球上灰飞烟灭的凄凉,卡森·麦卡勒斯写出了精神隔绝带来的巨大心灵创痛,威廉·福克纳描绘了思想枷锁控制下的人间悲剧,弗兰兹·卡夫卡抒发了被社会孤立的绝望个人的恐惧,欧内斯特·海明威表现了“硬汉”孤身作战的悲怆,赫尔曼·黑塞表达了人类与命运抗争的不屈……“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正因为胸中充满了对悲情男女的无限恻隐之情,劳伦斯才会悲天悯人、在肮脏虚伪的世界中挺身而出,宣扬有关爱情的真知灼见。在爱的荒原里,他甘愿做一名孤独的斗士和“传教士”,任由齐发的箭簇把自己射得遍体鳞伤。
21世纪的我们,也面临同样的精神困境,孤独感也时常侵蚀着我们的身心。世界依然长有冷漠的莠草,许多人脸上都写满了寂寞,在孤独的桎梏中有的人寸步难行。研究劳伦斯小说中的孤独主题,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去探索人性的幽暗之处、更透彻地去品味人生无法逃脱的孤独宿命,从而坦然面对并接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百年孤独,而不是万念俱灰、意志消沉。同时,我们还可以用爱和友谊来纾缓这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去用心感受别人和我们一样存在的孤独,我们就会对爱人、亲人、友人甚至陌生人多一份理解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