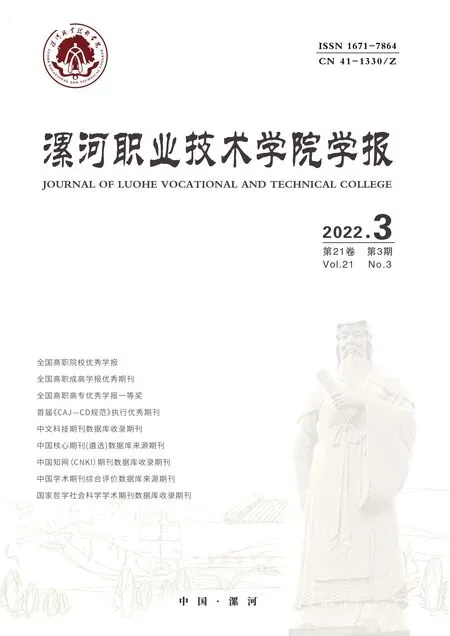试析内战后美国新移民对禁酒运动的影响
——基于纽约市禁酒研究
2022-03-18汪若冰
汪若冰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000)
19世纪中后期,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与美国先前的西北欧移民不同,这些新移民大多来自东南欧及亚洲等非新教国家,其中以罗马天主教徒居多,在宗教信仰、风俗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同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大量新移民的到来对美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对于美国内战后涌入的移民洪流及其对美国的重要作用,国内外无论是美国历史的通史类著作还是移民史专著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禁酒运动作为美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美国史学界对此研究颇深,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我国关于美国禁酒运动的专著、论文基本以围绕禁酒运动始末的历史叙事为主,但研究新移民对禁酒运动影响的专著、论文数量有限,多集中于宏观叙事,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微观探索有待加强。
自内战后新移民大量进入美国,禁酒运动的发展也一日千里。由于新移民的饮酒习俗,同老移民提倡的禁酒风尚产生冲突,加剧了新老移民间的矛盾。禁酒运动逐渐承载了美国社会原有居民维持新教社会权威,排斥非新教移民的社会情绪,从温和走向激烈,从地方发展至全国,成为新老移民文化冲突的发泄口。纽约市是美国当时移民结构最为多元化,新老移民文化冲突最为明显的典型代表,禁酒运动在纽约市的开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受到移民力量的深刻影响。本文基于纽约市禁酒运动的开展进程,从内战后美国新移民及其饮酒文化、移民冲突影响禁酒立法、移民影响禁令执行三个主要方面探讨禁酒运动中移民因素发挥的历史作用。
一、内战后的美国新移民及其饮酒文化
19世纪中后期,美国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型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由于工业化建设的需求,美国吸引了大量来自其他非新教国家与地区的移民涌入。美国内战以前,生活在美国本土的居民主要是来自西北欧的移民,即“老移民”,在内战以后,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数量不断上升,从1860年到1890年,一共有1000余万移民进入美国,其中85%来自西北欧和加拿大,但是从数量上看,来自东南欧和亚洲的移民,即“新移民”的数目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首次超过了老移民,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1]576。在1861年至1880年之间,德国移民占第一位,达150万之多,占第二位的是爱尔兰移民,有90万人。而从1860年到一战前来到美国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也有200多万人,其中90%是瑞典人和挪威人[2]23。1880年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只有12 000多人,但1907年却增加到285000多人[3]112。毋庸置疑,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为美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劳动力资源,为美国内战后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众多新移民的加入,给美国原有的新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与美国社会自殖民地时期就开始提倡节制饮酒的社会潮流不同的是,许多非新教国家的文化中,酒是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爱尔兰人就已酷爱饮酒,每逢婚丧嫁娶、朋友聚会、孩子洗礼等场合,他们都会开怀畅饮,还利用威士忌酒来应对阴湿的天气,治疗失眠、霍乱等疾病。爱尔兰工人常借助饮酒来强身健体,消除疲劳[4]。其他非新教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挪威等也有类似的饮酒习俗。
随着新移民在美国扎根落户,建立起移民社区,他们也继续保持了原有的饮酒习俗。据一位观察家称,纽约市的意大利移民对每天一杯葡萄酒没有(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或犯罪的看法,他们自己动手,自己酿酒[5]204。在纽约的意大利人居住区,酿酒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每年秋天,酿酒过程中产生的酒糟都会将公寓和店铺面前的水沟染成红色,在当地杂货店工作的妇女也会为自己沾满葡萄汁水的手而道歉[6]257。除了自己动手生产和制造酒类产品,这些新移民还习惯于聚集在酒馆共同饮酒,酒馆在显示新移民的身份认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爱尔兰酒馆展示了爱尔兰的场景、竖琴主题和其他民族主义象征。一位爱尔兰酒保在收银机上方放了一块莱特里姆郡30年前的干草皮,为他的顾客保留了一种民族认同感。德国的啤酒花园和酒廊非常准确地重现了德国的装饰、音乐和食物,布鲁克林汉密尔顿大街上的挪威酒吧橱窗里悬挂着挪威国旗[7]18。对于这些来自非新教国家的移民来说,酒馆是他们可以用母语和他人自在交流的地方。而对于美国本土的新教徒居民来说,新移民聚集的酒馆同美国本土文化格格不入,这些酒馆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提醒他们这里聚集的移民在族裔、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都与他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同时,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将一些新的饮酒方式、酿酒技术以及酒类品种带到了美国。内战之后大量涌入的墨西哥移民带来了先进的蒸馏酒技术,使得酒类产品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美国早期殖民地时期使用发酵技术生产酒精饮料,而蒸馏酒的酒精浓度更高,也更加易于保存和不易走味。蒸馏酒技术使得烈性酒能够大量生产,满足了许多饮酒爱好者的需求。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对此评论道:“这点大大改变了酒精饮料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因为若将发酵饮料比喻为弓箭,蒸馏烈酒有如枪炮,大多数传统社会都认为后者的劲道大得超乎想象。”[8]7与墨西哥移民类似的是,德国移民也将啤酒的酿造技术和消费习惯带到了美国。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啤酒异常流行,全美的啤酒消费大约是50万加仑,到了90年代初,增加到了100万加仑,到1913年,增加到200万加仑。啤酒已经代替了蒸馏酒,成为美国酒民的首选,所消费的各类酒当中,啤酒占60%[9]117。可以说20世纪初期美国饮用啤酒的流行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移民的推动作用,德国移民在19世纪中期将啤酒的储藏方法引入美国,啤酒很快超过了蒸馏酒在市场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美国社会原有的饮用威士忌的习惯逐渐被啤酒文化所取代。
二、移民冲突影响禁酒立法
19世纪初,美国各地已经成立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禁酒协会,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进入了改革年代,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主导,民众对社会和道德改革产生强烈且广泛的兴趣,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在移民潮、工业化、城市化的多重影响下,禁酒这一议题在美国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成为一场真正的大众运动。19世纪中期,德国和爱尔兰移民美国的人数激增,促成了禁酒运动的新尝试,即利用法律迫使美国人禁酒。
内战前,美国的禁酒运动主要局限于道德劝说领域,早在19世纪初期,美国各地已经成立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禁酒协会。以美国当时最大的全国性禁酒组织——美国禁酒协会为代表的禁酒团体一开始主要依靠道德劝说规劝人们远离酒精,说服酗酒的人群自愿戒酒。该协会出版了大量的禁酒宣传册,派遣志愿者和付费的讲师在全国各地宣传酗酒的害处。美国禁酒协会(ats)的成员、牧师贾斯汀·爱德华兹谴责酒馆与酒商:“每一家酒馆都应该用大写字母写上,通往地狱之路,通往死亡之屋,你们卖酒给健康的人们,然后毒害他们……那是可恨的,应当受到全世界的诅咒。”[10]10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美国掀起了社会福音运动。社会福音教派,如浸信会、长老派教会、卫理公会等,强调真善论,认为所有人的灵魂均可以得到拯救,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该教派关注社会问题,通过布道的方式向人们宣扬宗教和社会改良思想。对于饮酒问题,福音派新教徒宣称,圣灵不会拯救沉湎于酒精的魔鬼[9]4,男人们因为酗酒难以赡养家人,社会因为酒类的泛滥而丧失秩序,反对酗酒就是铲除邪恶,维护正义。
内战后,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如潮水般涌入美国,大多数爱尔兰移民定居在纽约和波士顿等东海岸城市,在工厂或铁路公司工作[11]。由于饮酒在他们的本土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将这一传统带进了美国,禁酒改革者对此深感不安。在内战后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中,爱尔兰移民的饮酒风气最为盛行。在爱尔兰,由于经济上的贫困,酒类产品被当作是食物的补充来源,因为酒不止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还能增加身体的热量。爱尔兰移民进入美国后,保持着本民族的酗酒传统。与之相应的,大批爱尔兰人从事酒类生意,在波士顿地区,爱尔兰人在该地区的1500家酒商中就占了800家[2]43。在爱尔兰人开设的酒馆中,往往从名称到陈设都带有鲜明的本族裔文化特征。他们在酒馆中讨论重大事务,庆祝本民族传统节日,如爱尔兰裔工人常在酒馆中庆祝他们的传统节日“圣帕特里克节”(St.Partrick’s Day)。这些新移民在酒馆内追求以族裔为基础的身份认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恰恰构成了一个令他们不容于美国社会的重要因素。“在美国人眼里,那些嗜酒如命的移民以及写着德、意文字的酒馆招牌无时无处不在昭示着一种‘非美国化’的趋势。”—位芝加哥牧师坚持认为,外来文化的“入侵”是从移民饮酒文化的蔓延幵始的[12]17。
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挤占了美国本地劳动力市场,一时之间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外来的新移民对城市风俗不熟悉,加之爱尔兰移民同美国新教徒格格不入的罗马天主教信仰,导致他们与美国原有居民的矛盾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饮酒风俗就变得尤为不可忍受。面对移民的文化入侵,本土美国人反击的方式就是首先号召禁酒。越来越多的禁酒改革者支持采取一种比道德劝说更加强硬的方法来解决日益加剧的全国酗酒问题,立法成为禁酒运动的新尝试。
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在美国禁酒协会和其他团体的游说压力下,禁酒运动取得了一些立法上的成功,十几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全州范围内的禁酒法。1851年,缅因州成为第一个禁止销售和生产除药用酒精以外的酒类产品的州。到1855年,美国其他13个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州和地区,包括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特拉华州、纽约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和明尼苏达州,都效仿缅因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10]18。
随着19世纪后半期妇女对禁酒议题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参与,禁酒运动进入了更为激烈的新阶段。众多妇女禁酒组织致力于推动禁酒运动走向全国,支持禁酒立法的民众数量持续增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禁酒组织得到了进步派人士的支持,这是一个由改革派人士组成的松散联盟,他们对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涌入城市的贫困移民十分担忧,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他们认为政府有必要解决城市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其中移民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酒精泛滥问题成为进步派人士关注的重点。进步派人士相信,过度饮酒虽然不是城市贫困和犯罪率上升的唯一原因,但它是造成这些社会弊病的重要成因之一。因此,进步派人士渐进式改革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向政府施压,通过立法手段取缔或至少严格限制白酒的生产和销售,迫使美国所有阶层都接受禁酒。
由于此时禁酒运动在纽约的积极推进,该市的禁酒立法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美国宣布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禁酒氛围空前高涨,在全国性的禁酒令出台之前,纽约市已经通过一系列战时对酒精消费的限制而逐步推进本州的禁酒立法议程。1918年,根据纽约市地方选择权法,该州59个城市中的39个在4月16日对酒类经营许可证问题进行投票,其中20个城市投票禁止给酒馆颁发经营许可证。1918年冬天,战时新增的禁止用谷物制造酒精的条例导致了该市和整个东北地区的啤酒供应大范围短缺。1919年2月,对酒类生产经营的限制变得相当严厉,这些限制是以保护国家资源和鼓励民众支援战争为理由制定的,以至于当地的啤酒厂被迫集中他们的粮食供应来维持经营。随后,该市禁酒立法的最大进展是通过了《战时禁酒法案》,这是1918年9月通过的一项临时联邦法律,1919年5月后禁止在美国生产啤酒和葡萄酒,1919年7月1日后禁止在美国任何地方销售含酒精量超过2.75%的饮料[13]141。许多当时的禁酒支持者相信,坚持推进纽约市的禁酒立法符合该地区大量移民聚集的现实情况需要。禁酒支持者希望将纽约树立成为实现禁酒的典型代表,进一步扩大禁酒事业的影响力,将每年成千上万往来此地的外国移民及游客转化成为禁酒事业中的一分子。正如反酒馆联盟的成员威廉·安德森(William·Anderson)所言:“禁酒令在世界范围内的成败在于它在纽约的成败。”他强调了这座城市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声望,他认为“欧洲人并不关心堪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或亚拉巴马州。”对他们来说,纽约就是美国”[13]41。
在成功确立地方、州一级的禁酒立法之后,禁酒支持者迎来了全国性的重要胜利。1919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并提交各州审议。它的主要内容是:“本条批准一年后,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等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所有领土。”[10]76
三、移民影响禁令执行
长期以来,禁酒倡导者将禁酒运动视为土著文化和移民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一部分。禁酒令的支持者认为,第十八修正案的通过是这场冲突中的一个关键胜利,因为他们相信,这将有助于迫使美国城市的少数族裔居民放弃他们的异族习惯,并保持美国人传统的文化优势。面对美国本土居民的禁酒要求,新移民群体并没有顺从地接受这一安排,由于移民和少数民族社区有着根深蒂固的有关酒精的习俗,但他们仍然坚持要求这些人遵守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以及由此延伸的禁酒游说团体所倡导的价值观,因而导致了移民群体对禁酒法令的公然违背,禁酒令的实施在这些地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以纽约市为例,早在1920年之前,纽约市就已成为美国文化最多元的城市。纽约市的人口略低于600万,有近200万外国出生的居民,另外还有200多万居民的父母是移民。纽约还有67万德国裔美国人、40万爱尔兰裔美国人、20万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和80多万东欧移民。此外,超过15万非裔美国人和数以万计的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包括波多黎各人、希腊人、中国人和西班牙人[14]128-130。纽约市的人口结构决定了禁酒法令在这座城市的实施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全国性的禁酒法令生效之后,往常作为斗争对象的酒馆、酒商不再合法存在,因此,当第十八条修正案没有像禁酒人士所希望的那样自动得到遵守时,反酒馆联盟以及其他禁酒组织和改革团体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移民及少数民族饮酒者身上。随着这一转变,在全国城市的移民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强制执行禁酒政策成了禁酒运动的首要任务。
禁酒支持者整顿外来移民饮酒习惯的行为在该市的移民居住区遭到强烈反对。尽管禁酒支持者将反对禁酒令等同于叛国罪,但在1919年战时禁酒令一生效,纽约的移民居住社区就公然反抗第十八条修正案。他们对禁酒的抵制并不仅仅是因为酒被列为非法。对纽约人来说,对禁酒令的抵制变成了一种对新教禁酒派文化权威的抗议,这些新教禁酒派标榜自己是所有真正美国事物的捍卫者。面对新教禁酒派对认可禁酒的美国人和反对禁酒的外国人的明确区分,纽约新移民两种都不接受。他们公然违抗禁酒支持者的命令,在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美国族裔身份。不管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还是犹太人,许多纽约人都对禁酒令视而不见,以此来抵制禁酒令。20世纪20年代初,在纽约市的各个社区,数百家种族酒吧照常营业。在哈莱姆区,烧烤架和咖啡馆依然营业,传统的胡桃木或红木屏风仍覆盖在平板玻璃窗上,以遮挡室内的动静[15]。几十年来,在这座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酒吧、咖啡馆和沙龙一直是移民社会的中心,尽管禁酒令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纽约市的非法酒馆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在20世纪20年代,纽约市民开始意识到,与禁酒派人士的斗争不是简单地要求废除一项不受欢迎的、不明智的宪法修正案能够做到的。随着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在纽约的全面施行,政府在禁酒执法方面的预算逐步上升,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激进和暴力的执法措施。政府对禁酒令的维护并未收获相应的回报,而是进一步激发了纽约市民对该项法律的不满。当纽约市民思考如何解决禁酒令带来的混乱时,政治途径成为他们实现目标的突破口。
1926年,《纽约时报》提出了一场反对禁酒令的严肃政治运动的可能性,指出禁酒派人士巧妙利用国家政治来为自己谋利,政治力量能够推动禁酒令出台,自然也能推动其倒台。19世纪20年代末,几个纽约人成为全国最直言不讳的禁酒令反对者,他们的努力最终迫使废除禁酒令的问题成为国家政治议程的头等大事。纽约两位最杰出的共和党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和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在禁酒令议题上成了主要的反对者。他们认为,该党顽固地坚持禁酒的事业,从长远来看将是灾难性的。他们推动该党放弃与禁酒运动的联盟,转而接受结束禁酒的议程,这很快变得比徒劳地继续一场失败的实验更具有政治可行性[13]234。纽约最终召集了许多美国最坚定的反对禁酒的领导人,包括该市市长詹姆斯·沃尔克(James J.Walker),竞选总统的州长艾尔·史密斯(Al Smith)这些领导人为结束禁酒令提供了第一个真正的希望[13]5。1928年,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艾尔·史密斯是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他在国外出生,信仰天主教,反对禁酒,是当时城市新移民理想的候选人。当然,艾尔·史密斯的提名引起支持禁酒的新教徒的强烈反对。“选举艾尔·史密斯当总统,就等于打开了外来移民潮水的闸门,我们的文明就将变成欧洲大陆那样的文明。”[16]18但是,史密斯在这次选举中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查尔斯顿和波士顿南部那些爱尔兰裔选区,他获得了多达90%的选票,在波士顿市的意大利裔选民聚居的北区也获得了几乎相同的票数。”[17]576移民族裔在这次大选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新教徒的传统政治地位遭到了巨大的挑战。随着这些新教禁酒派人士的主要政治反对派出现,美国其他地区对纽约移民政治主导下的禁酒斗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慢慢地开始被该市反对禁酒的论调说服。纽约人所提倡的废除禁酒法案,最终在激发全国人民对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州长的支持方面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推动性作用。罗斯福总统在1932年当选总统,这既结束了美国的禁酒时代,也带来了新政的出台。从这个意义上说,纽约人对禁酒令的政治反应,不仅为废除禁酒令铺平了道路,而且在塑造美国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的政治局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禁酒运动这项遍及全美的社会运动中,来自世界各地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促进了它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它的衰落。新移民的涌入引发了美国人关于禁酒议题文化上的冲突,这一冲突演变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进而推动了禁酒运动由道德劝说转向立法规制的进程,最终造成了美国政治格局的新变化。作为当时美国接纳移民的前沿城市,移民的进入对禁酒运动的开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纽约以移民为代表的公众群体对禁酒令的抵制来源于文化上的反叛,是新移民对自我身份和价值观的坚决捍卫,更是新移民寻求建设美国现代城市多元文化和世界主义的需求。同时,禁酒令问题的出现促成了这座城市多元化移民之间的政治合作,随着禁酒之争的展开,新移民开始发展组织和维护权力的机制,以此掌握政治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新移民在整个禁酒运动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不仅对禁酒运动的展开产生影响,同时也加速了自身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移民已从内战后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异类,成为政治上的重要力量,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