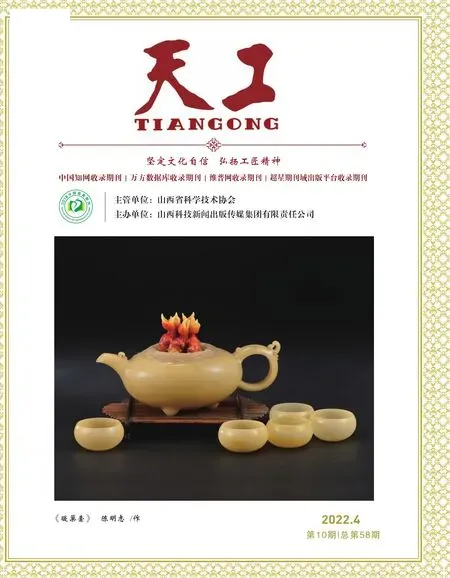明清徽州工匠群体的研究价值与画像素描
2022-03-17费利君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
费利君 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
徽州是明清文物之乡,遗存的地面文物极其丰富,据统计有二十多万件[1],它们造就了工艺的徽州、艺术的殿堂。徽州传统造物领域的成就,是徽州文化丰沃土壤滋养的结晶,更是徽州工匠群体创造的结果,但由于历史上工匠地位低下,再加上明清徽商光芒太过耀眼,至今这一群体的价值都未能得到彰显,湮没在历史尘埃中。
一、徽州传统造物研究的“热”与“冷”
目前,关于徽州传统造物研究呈现出一“热”与一“冷”并存的现状。
(一)物之“热”:徽州工艺研究成果丰硕
徽州自古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号称文物之海、文献之邦。徽州民间工艺极其丰富,具有独到的地方特色。近百年来,经过前辈学者的倡导和研究,徽州工艺已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徽州工艺在文房四宝、徽州诸雕、生活类工艺、科技类工艺、徽派图形符号等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很多著作,发表了很多论文。其中在专著方面,鲍义来所著《徽州工艺》是目前为止对徽州工艺阐述最为丰富、详细的著作,该书共五章,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既追根溯源阐述了徽州工艺的成因和特点,又分门别类有重点地总结归纳了徽州区域的各代表性工艺,可以让读者对徽州工艺有整体性的认知。在论文方面,方利山在《论徽州工艺的发展》一文中总结了徽州工艺的一些显著特征:丰厚的文化内涵;实用性与艺术性、技术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较强的精品意识和竞争意识等。[2]可以说,徽州工艺既有一般民间工艺的共同特点,又因徽州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明清徽商的关系和当时文人的参与,而具独特性。
(二)人之“冷”:徽州工艺的创造者——徽州工匠长期被忽略
这既与传统儒家观念视工匠之事为“奇技淫巧”有关,又与工匠群体社会地位低下有关。关于他们的资料散佚太甚,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记录,导致研究的困难。但徽州工匠作为明清时期徽州造物的主体,是徽州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必需品、消费品、奢侈品的提供者,正是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用自己的双手造就了工艺的徽州,所以他们的价值不言而喻。
二、明清徽州工匠群体的研究价值
(一)从“物”到“人”:发现人的主体作用
中国设计史对“物”的研究成果丰硕,从已出版的众多工艺美术史类著作中可以印证,这类著作从原始社会造物的起源到历朝历代的典型器物都有详细的描述。但设计史除了对“物”的研究外,同样要关注“物”背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基于什么样的动机,凭借什么样的技艺创造了“物”。因为历史上部分“物”还在当下,但“人”已经灰飞烟灭了,所以对“物”背后的“人”的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也是设计史对传统工匠研究长期缺席的原因所在,由此导致了设计史领域在“物”与“人”研究上出现了冷热分明的现象。
随着学界对徽州工艺研究的逐步深入,徽州区域不同工艺品类的造型、工艺、装饰、材料、功能和审美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成果积累,人们对徽州工艺在“物”的方面有了总体的认知。但是,在设计学的视野内,研究的视角从原先工艺史关注的“物”拓展到了“人”,是“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才造就了“物”。所以,我们不应当仅仅关注徽州工艺器物本身,对器物的创作者——徽州工匠群体及其生活也应予以研究,于此才能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和创造作用,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同时,缺乏工匠的徽州工艺也不利于通过设计的视角看出当时的社会面貌,以致妨碍我们对这个时期的工艺作品及工艺行业的深入理解。正如邱春林针对传统工艺美术史研究的问题指出:忽略器物背后的“人”的身份、行为、观念、技术能力以及社会环境对设计过程的制约等内容,如此见物不见人的研究,客观上造成了现当代设计史与传统手工业时代的设计史无法贯通。[3]所以,在设计学的视野下,我们要关注徽州工艺背后的工匠群体。
(二)徽州地域设计史研究的需要
设计史的写法决定着设计史的形状;设计史的形状建构着读者心目中设计史的地位。目前,国内设计史的写法主要以通史、断代史和门类史为主,设计通史以年代的先后发展为线索,在年代的更替中呈现物的变迁;设计断代史以某个朝代的设计物为专门研究范围;设计门类史以某个类别设计物的历史变迁为叙述线索。这三种模式都有其诸多叙述优点,但设计史还可以有更多的写法与可能性,比如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特色旅游需求的推动,对地域设计史的发掘与整理正在兴起。关于地域设计史,李立新认为“研究复杂、丰富、多样的中国设计历史,最好选择一个区域”[4],徽州作为我国三大地方显学之一的所在地,正是这样一个生动、具体、最具代表性的区域。
徽州地处江南一隅,山水掩映,自古就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明清时期随着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它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最具代表性的区域[1]。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徽商,称雄中国商界三百余年,在全国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辉煌局面,同时他们也将大量财富回馈故土,为明清时期徽州的鼎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自然资源的富饶、儒家文化的滋养和商业财富的投入,也造就了明清徽州造物的繁荣,使徽州成为民间艺术博物馆。自然、文化、商业与工艺的互动,对徽州造物生态系统的研究,可以发掘和总结中国江南地区传统造物运行的规律,为当代设计业乃至文化创意产业提供智慧的参照。因此,从徽州地域设计史这一局部,可以去认识设计的整体与一般。对徽州地域设计史的研究,除了对“物”的挖掘与整理外,更要去关注“物”背后的“人”,以及人与自然、文化、商业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冲突与互动,这是构成徽州地域设计史研究的关键一环。
三、明清徽州工匠群体画像素描
人群画像,是互联网环境下现代数字营销的重要术语,是借助互联网的“监视”功能,利用用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数字痕迹,来描绘用户特征的一门技术。画像的焦点工作就是为用户打“标签”。这里借用“画像”这一术语,以徽州工匠群体为对象,试图通过徽州区域的自然“痕迹”、人文“痕迹”和造物“痕迹”等,通过打“标签”的方式来粗略描绘明清徽州工匠群体的画像。
明清徽州工匠生活的时空以明中叶至清中叶为时间范围,以徽州地区历史上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6县为空间范围。群体画像素描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一)徽匠的生活
徽州工匠是一个多大的群体?据余同元整理的《中国历代名工匠统计总表》的数据,明清时期中国工艺名家及工匠共1530人,徽州府有154人[5],占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徽州工匠群体的庞大。徽州工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中?首先,徽州的自然环境。徽州自古山水掩映,山多水美,奇峭秀拔,自然资源丰富,有大量的木、竹、石、漆等物产资源,是世外桃源般所在。其次,徽州的生产环境。徽州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的俗语,宋代以来徽州地区由于山多田少人众,人地矛盾突出,徽州先民不能从土地中求生存,不得不从农耕之外寻找出路,于是形成了“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的生存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州工艺和徽商都是被徽州这一恶劣环境逼出来的”[6]。再次,徽州的文化环境。徽州自汉代以来,历史上经历了中原士族三次大规模的迁入。中原士族的迁入既传播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也带来了中原崇儒尚文的传统,使徽州文化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徽州“聚族而居”和“崇儒尚文”的文化环境,不仅衣冠之族重涵养,而且普通村民也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形成了“虽十户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浓厚氛围。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徽州工匠,既吃苦耐劳、勤恳务实,又超脱崇德、朴素亲切。
(二)徽匠的技艺
今人游玩徽州,除了对当地秀美的自然景观流连忘返外,更对当地的村落布局、民居建筑、文房四宝、雕刻艺术等叹为观止,这都离不开徽州工匠群体的努力和创造。徽州工匠是徽州工艺的创造者,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手艺,创造的是一个技与艺完美统一的世界,徽州工匠的技艺总体上表现出技术与艺术、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徽州的村落布局,随形就势,巧用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了“枕山、环水、面屏”[7]的特征,被誉为“东方文化的缩影”。徽州的民居建筑粉墙黛瓦、简洁淡雅,以马头墙为外观基本要素,既有防火之用又具视觉之美。徽州的雕刻中砖雕、木雕、石雕和竹雕闻名遐迩,它们材质虽有异,但都是融文化、绘画、书法、民俗于一体,呈现给了世人一个诗情画意的雅致空间。徽州文房四宝中的歙砚和徽墨既是文人书写必不可少的工具,又是江南文化的典范。从徽州工匠的造物“痕迹”来看,徽州工匠的技艺形成有多方面因素。首先,徽州地区重教兴文,府学县学社学发达,书院众多,讲学蔚然成风,使得普通百姓包括工匠群体有很多读书识字的机会,大多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新安理学成为当地的文化底色。其次,明清徽商的崛起,在商界称雄三百多年,在全国开辟了“无徽不成镇”的辉煌局面。因商致富的徽商见多识广,贾而好儒,他们将大量财富带回故土,用于光宗耀祖、兴办教育,这既为工匠群体提供了造物的物质基础和施展技艺的舞台,也创造了徽商与徽匠互动的契机,徽商的修养、喜好、见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徽匠造物的方向。再次,明代中晚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徽州工艺吸引了众多文人的参与,学者、画家参与设计构思的例子举不胜举,文人与匠人的互动与交流,使“文心匠意”成为可能,既有助于徽州工匠群体社会地位的改善,又提升了工匠群体的设计水平。徽州工匠群体凭借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吃苦耐劳,在与徽商、文人阶层的互动交流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达成了技艺双修,为世人创造了一个雅致精美的工艺徽州。
(三)徽匠的精神
“工匠精神”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下成为社会热词,它不仅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极致追求,也表征着一种艺术品格和文化追求。徽州工匠群体在待物的态度上,恰恰表现出这样一种精神境界。首先,徽匠精神表现出一种务实性。胡适先生称徽州人为“徽骆驼”,形容徽州人具有勤劳、坚韧、进取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在徽商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已广为人知;但这种精神同样是徽匠为人处世的准则:他们吃苦耐劳,依靠自己的手工技艺勤俭持家;他们坚韧不拔,对待技艺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正如郑振铎形容徽州版画刻工时所说:“他们绝不出之于轻心”“他们绝不苟简潦草”“一律的以全力赴之”[8]。他们开拓创新,将造物与文化、物质与精神融会贯通,造就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徽州,使徽州成为艺术的殿堂。其次,徽匠精神表现出一种超脱性。由于徽州地区崇文重教,文风昌盛,徽匠大多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基础,特别是作为业主的徽商贾而好儒,虽“身为商人,却显得儒雅高贵,富有书卷气”[9],所以,徽州工匠群体在待物的态度上,总要在形而下的工艺创造中表现出形而上的儒家理念来,这既满足了徽商好儒或附庸风雅之喜好,又可以使自己从物质世界中超脱出来,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从而使徽匠群体整体上表现出“儒匠”的气质。从徽州现存的实物看,如建筑的结构、“三雕”的图案、刻书上的插图、墨模上的图案、民间的年画等,可以说“徽州几乎所有的工艺形式都是围绕着儒家理念这个主旋律展开的”[2]。甚至有工匠将经验写成文字,著书立说,广为流传,如徽州漆工黄成的《髹饰录》。再次,徽匠精神表现出一种整体性,是技、艺、道三位一体的文化表征。徽匠精神不只是一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做事情的态度,它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表现出技艺双修、道技合一的特征,是一种融技术、艺术和哲理于一体的文化传承,这种整体性的特征正凸显出徽匠精神的可贵和价值。
四、结语
明清徽州的“物”还在,依然在装饰着徽州、美化着徽州,成就着诗情画意的徽州。但明清徽州的“人”已经灰飞烟灭,因为社会地位的低下徽州工匠昔日的光辉只能埋入记忆的地层中,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如何通过徽州自然的“痕迹”、文化的“痕迹”和造物的“痕迹”去寻找、琢磨、想象、再现徽州工匠的生活、教育、社交、技艺、传承和精神等,是徽州地域设计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艰难的工作才刚刚展开,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