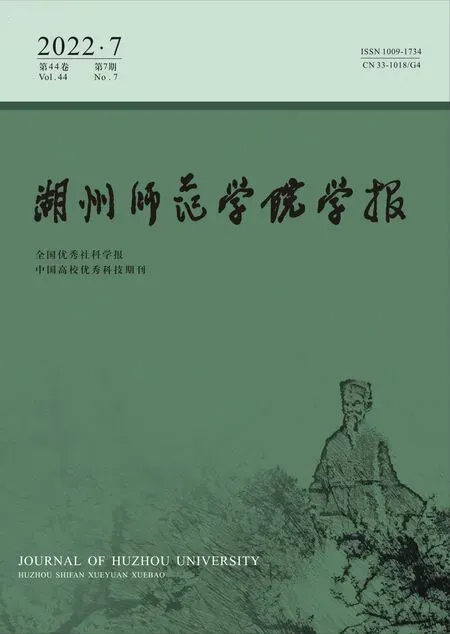论前国家阶段的文明与不文明*
2022-03-17叶文宪
叶文宪
(苏州科技大学 历史系,江苏 苏州 215009)
摩尔根把继野蛮时代之后、高于野蛮时代的社会阶段称为civilization,被译成“文明社会”。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22意思是说,国家建立之后,社会因为有了政府的管理,就有了正常的秩序,不像建立国家之前的野蛮时代,人与其他动物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还会人吃人。中国学者把恩格斯的这句话理解为一旦建立国家就进入了文明社会,把“国家”等同于“文明社会”,把“国家起源”等同于“文明起源”,甚至把“国家”等同于“文明”,可是刚刚摆脱野蛮状态而建立的国家是“文明社会”吗?
摩尔根所说的古代文明是指希腊罗马文明,他认为“希腊罗马文明的主要贡献在于帝国和王国的政治结构;民法;基督教;具有元老院和执政官的贵族式兼民主式混合政体;具有议会和人民大会的民主政体;组织了受过军事训练的骑兵、步兵部队;建立了熟悉海上作战的海军;形成了具有市政法的大城市;海上贸易;货币的铸造;建立在地域和财产基础上的国家;在发明方面则有火砖、起重机、水碾、桥梁、给水排水管道、带水龙头的引水铅管、拱门、天平;古典时代的艺术和科学及其成果,包括建筑上的各种柱型;阿拉伯数字;字母文字等。”[2]29他还认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2]30。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没有文字也没有文字记载,我们连有没有这段历史都不知道,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文明社会呢?考古发掘出土的精美玉器和宏大城堡确实堪称文明,可是怎么知道那时已经建立了国家呢?如果已经建立了国家,那么它是什么国家呢?
20世纪各国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许多物质遗存高度发达的考古文化,如印加文化、纳斯卡文化、玛雅文化和中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等,都是摩尔根没有见到过的。它们有的有文字,有的没有文字,如果再以文字作为判断“文明”的唯一标志显然不合适了,于是学者们纷纷提出各种修改摩尔根的“文明”标志的方案。1950年戈登·柴尔德首先提出以出现“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3]96-99。1958年克拉克洪提出以“城市、文字和礼仪性建筑”三项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志(1)转引自李学勤:《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3-6页。。1985年张光直先生提出以“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复杂礼仪中心”六项作为中国文明的标志[4]41-46,而夏鼐先生则强调其中的“国家、城市、文字和冶炼金属”四项[5]96-100。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中国近几十年来发现的考古资料提出了新的判断文明或国家的标准:“一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之上。良渚、陶寺、石峁等这些地方文明都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生产力。二是出现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比如有了专门为贵族服务的、由贵族专享的手工业生产,通过建筑规模大小、丧葬形式区别等而体现的等级制。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城市居民不再以血缘、氏族方式组成,而是按照行业、功能组织,当然还有最高等级的统治阶层等。这样就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化,城和乡之间又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这个社会在宏观结构上不再平等、平均。四是在这些城市,特别是中心性城市出现大型建筑。同时由战争、暴力来褫夺人的生命的现象不时出现。这些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个强制性的权威——王权。”[6]
古今中外学者提出的“文明”标志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是物质与技术的发明,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建树,第三层是社会组织形式的进步。物质与技术的发明即所谓的“物质文明”,这一点没有异议,实际上学者们就是因为折服于卓越的物质成就,才把某一个考古文化认定为“文明”的。出现祭坛之类的礼仪性建筑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建树,即所谓的“精神文明”,但它究竟是文明还是迷信呢?对此是存在异议的。至于把出现国家说成是“文明”就成问题了,因为按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的定义,“文明”的标志是贫富分化、阶级对立、暴力冲突、残酷杀戮、武力征服、王权独尊,这些确实是中国国家产生的途径,但是这样的国家能够叫“文明社会”吗?众所周知,最早建立的国家是奴隶制国家,其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难道能说奴隶社会是“文明社会”吗?摩尔根在论述希腊罗马文明时只列举了“国家结构”与“民主政体”而有意回避了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度,只列举了“骑兵、步兵”与“海军”而有意回避了用武力征服四邻,好像希腊罗马国家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文明社会”,可是如果没有暴力掠夺与征服,希腊罗马国家那么多的奴隶从哪里来的呢?希腊罗马的物质与精神的确是文明的,但是希腊罗马的国家是“文明社会”吗?摩尔根为了说明希腊罗马是“文明社会”而故意回避了国家的不文明,而我们的学者居然直接把国家的不文明说成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岂不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吗?即使在国家建立之后,从夏朝到清朝,社会上始终充斥着种种愚昧的习俗、野蛮的行为、残酷的杀戮、专横的制度、奸诈的权谋乃至邪恶的理论,所谓的“文明社会”其实并不那么文明,可见把“国家”等同于“文明社会”是不能成立的。
一、前国家阶段的创造发明
国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学者们都意识到从没有国家到建立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摩尔根把这个阶段称为“部落联盟”、塞维斯称之为“酋邦”、弗雷德称之为“阶层社会”、许倬云称之为“复杂社会”、苏秉琦与严文明称之为“古国”、田昌五称之为“万邦”、王震中称之为“邦国”、刘俊男称之为“神邦”,不管如何命名都可以统称为“前国家”。夏王朝被公认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国家,那么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和考古学家所揭示的龙山时代(距今4000—5000年)就处于前国家阶段。
因为在前国家阶段已经出现了许多创造发明,被称为“文明曙光”“文明萌芽”“文明迹象”“文明因素”,所以许多学者努力证明五千年前中国就进入了文明社会。摩尔根认为:“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2]28夏鼐先生也认为:“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5]96换言之,文明社会的各种因素并不是进入文明社会后才出现的,而是在野蛮社会中就出现了。前国家是躁动于野蛮社会母腹中的胎儿,还没有呱呱坠地,不能算真正的国家,而夏商周王朝是已经诞生的国家,虽然幼儿期的国家还不够完备,但是胎儿和幼儿是迥然不同的。虽然曙光初露天已经亮了,但是太阳还没有升起,而白天是从日出开始算起的。前国家阶段实际上处于野蛮时代的末期,不应该把它划入文明时代。前国家阶段是介于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因为历时很长,而且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所以可以单独划为一个“前国家阶段”。
据文献记载,五帝时代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创造与发明。
《逸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易·系辞下》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说神农“以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本草经》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汉书·食货志》曰:“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易·系辞下》:“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谯周《古史考》:“神农作市。”《世本·作篇》云:“神农作琴。”皇甫谧《帝王世纪》认为神农氏就是炎帝。
《世本·作篇》曰:“黄帝始穿井”,“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更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黄帝之臣仓颉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於则作扉履,雍父作舂杵臼,共鼓、货狄作舟,挥作弓,夷牟作矢,巫彭作医等。崔豹《古今注》曰:黄帝与蚩尤作战,造指南车,遂擒蚩尤。《淮南子》引《蚕经》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
《世本·作篇》曰:“蚩尤作兵。蚩尤以金作兵。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予。”《国语·楚语下》记载,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改变了“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原始状态。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敬授民时。”《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曰:“帝尧立,乃命质为乐。”《竹书纪年》曰:“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史记·夏本纪》记载帝尧之时,洪水滔天,四岳推荐鲧负责治水。鲧用“堵”的办法治水,结果“九年而水不息”,被舜殛于羽山。舜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终于用“导”的办法治平洪水,“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于是“九州攸同”。
五帝时代的发明创造都可以纳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是这些记载都不是当时人自己的记录,而是后人追记的,未必都是信史,所以疑古派认为这些不过是传说而已。虽然难以用考古资料直接印证五帝时代的成就,但是龙山时代的考古资料可以为五帝时代的成就做一些旁证与补充。
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小件铜器,但是由于冶金技术尚处于萌芽时期而水平不高,所以以冶铜术作为“五千年文明”标志的说法明显缺乏说服力而被摒弃了。然而,各地出土的玉器尤其是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石峁文化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让人叹为观止。其实早于龙山时代的红山文化和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已然令人震惊,以至有些学者提出应该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加入一个玉器时代的建议[7]31-37[8]41-45。
早在仰韶时代,聚落周围就开始出现垒筑或夯筑的城堡,各地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堡已有数十座之多,不过面积只有几万到几十万平方米,其实只是用土墙围绕的村落而已;但是,天门石家河文化城址达到120万平方米、襄汾陶寺文化城址达到280万平方米、余杭良渚文化城址达到290万平方米,而神木石峁文化石城遗址居然达425万平方米,这大大超出了人们对龙山时代的认识,于是很自然地就产生了把城堡作为“文明”标志的想法。
在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城址外围发现了11条堤坝遗址,组成了山前长堤、谷口高坝、平原低坝三个水利系统,在修筑水坝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了被称为“草裹泥”的工艺,即先用茅荻包裹土块,再用竹篾进行绑扎固定,最终以纵横交错的方式进行堆筑,其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超的治水技能[9]102-110。良渚文化的筑坝技术与打井技术都非常先进,容易使人想到鲧禹治水与黄帝始穿井的传说并非虚言,当然良渚文化绝不是他们的原型。
二、龙山时代的人殉人祭
由于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我们无法知道五帝时代的社会风貌究竟是怎样的,从“神农作琴”“黄帝垂衣裳”“嫘祖始蚕”“舜作韶乐”等传说来看,似乎真的是一个“文明社会”。但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时代就已经普遍出现了祭祀遗迹[10]50-61,最有名的就是红山文化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和喀左东山嘴石砌祭坛(2)相关考古信息详见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第1页;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家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第1-17页。。浙江嘉兴南河浜和苏州吴江同里都发现了崧泽文化祭坛(3)相关考古信息详见刘斌、蒋卫东:《浙江嘉兴南河浜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6期,第4-15页;张照根、朱颖浩:《江苏吴江区同里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1日,第1版。。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5300年前的祭坛(4)相关考古信息详见张敬国:《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第1-12页。。郑州荥阳青台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九个排列成北斗九星形状的陶罐,陶罐东部发现一座黄土圜丘(5)相关考古信息详见桂娟:《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发现疑似北斗九星祭祀区》,2018年3月29日新华网(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ha.xinhuanet.com/news/2018-03/30/c_1122612401.htm),《河南青台遗址重要发现:九个陶罐摆成了“北斗九星”》,2019年6月21日中宏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7002593349262698&wfr=spider&for=pc)。。对于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发现的110个埋有石磨盘、石棒、石铲、石斧、陶盂、陶支架的灰坑,学者认为可能是具有“瘗埋”性质的祭祀遗迹[11]149。
龙山时代的祭祀遗迹发现得更多,例如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城址附近的瑶山、汇观山等小山顶部都发现了人工修筑的方形祭坛[12]8-25。在平原地区如上海青浦的福泉山、江苏苏州的草鞋山、赵陵山、张陵山,常熟的罗墩,江阴的高城墩,常州武进寺墩等遗址都是人工堆筑的高土台,高土台上设置祭坛,还通常埋葬大墓[13]52。在天门石家河城址发现多处用大型厚胎红陶缸套接在一起组成的套缸遗迹,套缸遗迹附近出土成百上千的红陶杯、陶塑人偶与动物,这些遗存可能都与祭祀有关,城外的印信台则是专门的祭祀场所[14]213-294,406-407,417-418。祭祀遗迹除了在地上垒筑的祭坛以外,还有地面的墠、地下的坎和修建的庙(6)《说文》:“坛,祭场一也,从土。”《说文》:“墠,野土也。”“野,郊外也。”《礼记·祭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说文》:“庙,尊先祖貌也。”。墠和坎不容易辨认,用石块在地面摆放的石圆圈也常常被视为祭坛,而瘗埋祭品的坎则通常被视为祭祀坑,由于祠庙遗址与宫室遗址很难分辨,因此只有对于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的相关认定,大家都没有异议[15]6-15。
祭祀遗迹是信仰的物化表现,出现祭坛表明先民们已经有了某种信仰,其通常被视为“精神文明”,所以出现“礼仪性建筑”也被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志之一。但是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先民们信仰的内容与形式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考古学家发现在龙山时代遗址里普遍存在着文献里没有记载的人殉人祭习俗。
在陶寺文化中期大城的东北部发现一座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上有一座主体殿堂的柱网遗迹,柱网分布区内的夯土基础中发现5处比较明显的奠基人性遗存,肢体残缺或散乱的人骨均被夯在夯土版块里[16]3-6。陶寺文化中期小城内墓地的一座大墓IIM22的墓圹内东北角距墓口1.4米处填土中发现1具被腰斩的人牲骨架[17]3-6。在石峁外城东门瓮城的墙外侧和城门入口处各埋置了24颗人头,东门址北端石砌城墙的墙体基础之下还发现4处祭祀坑,埋葬1~16具多少不等的头骨,这些都是建城时奠基的人牲(7)相关考古信息详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第15-24页;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第39-62页。。在多处石峁类型墓葬中都发现了殉人现象(8)相关考古信息详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年;郭小宁,王炜林,康宁武,等:《陕西神木县神圪垯梁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第33-44页; 孙周勇,邵晶,邵安定,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第14-24页;邵晶:《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考古》2020年第5期,第65-77页。。良渚文化大墓中较少见到人殉现象,仅上海福泉山遗址发现过2座有殉人的墓[18]144-150。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内发现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型高土台,高土台上有一批大、中型墓,土台西北部的外围发现19座人骨架,大致分三排埋葬,没有墓坑,也没有葬具,5人有少量随葬品,14人没有任何随葬品,有的似呈捆缚状,骨架凌乱,12人或无头骨,或无下肢骨。在三排人骨架的东南有一片长4米、宽1.5米的黑色灰烬,灰烬上有一残鼎的碎片。发掘者推测这些人应为祭祀高土台上墓主的人牲(9)相关考古信息详见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昆山赵陵山第一、二次发掘简报》,出自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 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1936-1996》,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北区发现8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总共用20位妇女、少年与儿童陪葬(10)相关考古信息详见南京博物院:《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年第2期,第1-26页;王根富:《花厅墓地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第124-136页。,但是无法证明他们的身份是奴隶。
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王湾类型、后冈类型、王油坊类型都普遍流行着用人作为牺牲奠基的习俗。登封王城岗大城中部偏北处发现几处大面积夯土基址和一个埋有儿童的祭祀坑[19]3-5。王城岗大城东北的小城内发现13个祭祀坑,坑内埋人最多的7具、最少的1具,他们或呈挣扎状、或身首分离、或残缺不全[20]8-21。1979年发掘后岗龙山文化遗址,发现在15座房基下埋有26位儿童,其中最多的F23埋有四位儿童,他们有的埋在墙基下、有的埋在夯土中、有的埋在散水下、有的埋在柱础下[21]33。类似的现象在汤阴白营也有发现。在邯郸涧沟遗址的两座房址内各发现3具头骨,头骨上有斧砍刀切的痕迹,证明后冈类型先民有剥头皮和用人头骨制作头盖杯的习俗[22]38-42。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有一道7米长的残土墙,墙下呈一字排着3位儿童的骨架,应是筑墙时奠埋的牺牲。王油坊F20是一座方形硬土墙的地面建筑,面积仅10平方米,但是地面有6层白灰面和1层烧土面,房基下埋有3具砍去头顶骨的中年男子的骨骸,南墙的西南墙角外侧还埋有l位儿童(11)相关考古信息详见郑光:《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人殉人祭并不是龙山时代特有的现象,而是早在仰韶时代就已经存在的习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遗址的城墙与房基下就发现用于奠基的瓮棺[23]4-15。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仰韶文化中期墓葬M45,墓主身边用蚌壳摆出龙与虎的图案,东、西、北三面各殉一个青年,脚下还用两根人的胫骨与一堆蚌壳摆成一个斗形[24]1-6。郑州荥阳青台仰韶文化遗址圜丘形祭台和摆成北斗七星形状的七个陶罐南面有一个祭祀坑,坑内有一具无手无足的骨架(12)相关考古信息详见桂娟:《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发现疑似北斗九星祭祀区》,2018年3月29日新华网(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ha.xinhuanet.com/news/2018-03/30/c_1122612401.htm),《河南青台遗址重要发现:九个陶罐摆成了“北斗九星》,2019年6月21日中宏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7002593349262698&wfr=spider&for=pc)。。辽宁凌源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红山文化圆形祭坛(Z3)顶部积石中埋有三具人骨架,既无石棺、也无随葬品,似为牺牲。牛河梁第五地点有三座积石冢,中间方形的三号冢(Z3)石块下压着4具二次葬人骨,既无棺椁也无随葬品,似为祭坛上的人牲(13)相关考古信息详见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第1页;朱达、吕学明:《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1998—1999年度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8期,第15-30页。。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部石圈形台址的东北侧埋有一具人骨架,可能也是祭坛的人牲[25]1。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发现庙底沟类型的人祭遗存,在遗址窖藏区的西端发现一座大坑,周围环绕7座小坑,大坑呈椭圆形,最大径约2米,内有4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架,人骨架旁还有兽骨。这种有规律排列的小坑当与原始祭仪有关,大坑中的人骨应为祭祀时的牺牲[26]。临潼零口的一座距今7300年的大地湾文化墓葬中埋着一位16岁的少女,遗骨基本完整,但是左手骨完全失去,耻骨向右上方移位,左腿胫骨断裂外移、错位,全身上下在死前受了35处严重损伤,其中29处锐器伤、6处复合伤。在死者身上还残留着8件骨镖、8件骨簪和2件骨镞。有3件骨器由会阴部刺入小腹盆腔,滞留在骨盆内,还有1件骨器从会阴部刺入插在姑娘的坐骨上[27]3-12。究竟因为什么原因与目的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位花季少女?是惩罚、报复还是奉献给神灵的牺牲?不得而知,反正是暴力的证据。
人殉人祭习俗在商代遗址中普遍存在,郭沫若先生以此来证明商代是奴隶社会,但是人殉人祭从仰韶时代一直延续到明清,无法作为奴隶社会的证据。当先民们把人的生命作为祭品奉献给祖先神灵的时候,一定认为这是最神圣、最高尚的举动,人殉人祭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应当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然而杀人祭奠却是极其野蛮、极其残酷的行为,怎么能够说是“文明”呢?又怎么能够把这样的社会叫作“文明社会”呢?
三、前国家阶段的暴力杀戮
文献中的五帝时代和考古上的龙山时代所取得的物质成就与技术进步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学者们都在努力证明五帝时代与龙山时代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可是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考古资料都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充满了战争、暴力与杀戮。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神农氏之时)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因为战胜了炎帝、擒杀了蚩尤,所以“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实际上是一位凌驾于众部落之上的征服者,“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
五帝时代部落、部族之间战争不断,除了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和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外,还有颛顼“尝与共工争”(《淮南子·兵略训》),“孟翼之攻颛顼”(《山海经·大荒西经》),“战数盈六十而高阳(颛顼)未失”(《经法·十大经》)。共工又“与高辛(帝喾)争为帝”(《淮南子·原道训》),“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史记·楚世家》)。“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高辛氏内部也有纷争,“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伐”(《左传·昭公元年》)。
唐尧时战争更加激烈,尧使后羿“诛凿齿于畴华之泽,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杀锲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淮南子·本经训》)。有人解释这些动物名称当为部落图腾。“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尚书·尧典》)。
舜禹之际的战争主要是征三苗,“舜南征有苗……道死苍梧”(《淮南子·修务训》)。最后“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礼记·檀弓下》)。
因为缺乏直接的文字记载,所以五帝时代的历史显得扑朔迷离,但是考古发掘资料表明,龙山时代普遍出现的城堡与乱葬坑就是社会上暴力盛行的物证。当然,要直接从地下把龙山时代的暴力冲突发掘出来是极其困难的,一般只能依据各地出土的制作精良的武器和带箭镞、遭砍斫的尸骨(14)相关考古信息详见何德亮:《中国史前战争初论》,《史前研究》,2004年,第195-212页。来作间接的推测,但是在襄汾的陶寺文化遗址里却可以看到暴力留下的触目惊心的直接证据:(1)扒城墙,陶寺文化中期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2)夷宫殿,陶寺文化中期宫殿原地表以上部分的夯土在陶寺文化晚期均被夷平,彩绘墙皮和夯土被堆积在壕沟里。(3)毁宗庙,中期城址南边的祭祀区被压在陶寺晚期文化层之下。观象台也被彻底平毁。(4)掘祖坟,早中期的大墓都在晚期被捣毁,而墓中的财物并没有被盗空,还在墓道中填大石块厌胜。(5)杀壮丁,HG8里发现有5层散乱的骨殖,共有30余个人头骨和40~50具骨骸,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器劈啄痕,其中用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颊有6个之多。(6)淫妇女,HG8的最下层出土一具被折颈残害致死的中年女性骨架,在阴道部位还插着一只牛角(15)相关考古信息详见何驽、严志斌、宋建忠:《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13年1月31日第1版;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87-91页。。陶寺文化晚期发生了什么变故?邵晶先生认为这是石峁文化先民对陶寺文化先民造成的强烈冲击[28]65-77,戴向明先生也认为陶寺晚期的衰落可能与石峁文化先民的南下有关[29]46-60,而韩建业先生则直接指为是后稷放丹朱在考古上的表现[30]119-123。
在龙山时代的遗址中还普遍发现存在着文化断层现象,即上下叠压的地层虽然年代前后衔接,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文化遗物却没有从前者发展为后者的逻辑关系,这种文化断层现象意味着,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直接继承者,说明当前者演变为后者的时候,曾经遭遇了重大的变故。例如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之间、燕辽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河套地区的老虎山文化与朱开沟文化之间、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厂文化与四坝文化之间都存在着文化断层(16)对于此观点的详细阐释,详见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第67-77页;许宏:《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东方考古》,2012年第1期,第186-204页。。出现文化断层的原因有的可能是由先民遭到自然灾害被迫迁徙造成的(17)对于此观点的详细阐释,详见叶文宪:《距今4000年前后的文化断层现象和良渚文化的北迁及其归宿》,出自林华东主编、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编:《良渚文化探秘》.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145-162页;叶文宪:《文化断层现象与考古层位学——跨湖桥遗址的启示》,出自林华东、任关甫:《跨湖桥文化论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99页。,但是更多的可能是由战争造成的,不过要从考古发掘出来的遗存中复原出历史的真相实在是太难了。
人们曾经猜想原始社会是一种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社会,平等、民主、博爱、和谐,实际上五帝时代与龙山时代充满了战争、暴力、杀戮与征服,正是这种部族间的战争推动了国家的产生。但是韩建业先生却认为:“新石器时代的战争提高首领地位、促使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以粗暴的方式使得广大地区短时间内发生文化和血缘的深度交融,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进程;而文明的成长反过来促使大规模战争的发生,文明化进程每前进一步,战争的程度就升级一次。”[31]99-107那就令人费解了,明明是“粗暴”,明明是“大规模战争”,明明是“战争程度升级”,怎么可以称之为“文明”呢?粗暴地扩大战争的是“国家”,为什么要赖在“文明”的头上呢?怎么能把这样的“国家”叫作“文明社会”呢?
四、“文明社会”究竟文明不文明?
汉语“文明”是一个褒义词,本义是文采光明的意思。例如《周易·乾卦》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尚书·舜典》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下·格局》曰:“辟草昧而致文明”等。现在民众理解的“文明”也是褒义的,在人们的心目中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的人是文明人,文化昌盛、和谐理性的社会是文明社会。那么,实行奴隶制的希腊罗马国家是“文明社会”吗?实行人殉人祭的龙山时代是“文明社会”吗?充满战争、暴力与杀戮的五帝时代是“文明社会”吗?文明社会的人们虽然不再吃人,但是屠杀同类的残酷远远超过了野蛮时代的吃人生番。
把物质与技术的创造发明视为“文明”即物质文明,这毫无异议。出现祭坛之类礼仪性建筑说明先民们已经有了某种信仰,但是判断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不是“精神文明”,是由评判者的价值观决定的,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标准。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不仅在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充满了战争、暴力、杀戮与征服,并且在国家形成之后仍然存在着愚昧的习俗、野蛮的行为、残酷的杀戮、专横的制度、奸诈的权谋乃至邪恶的理论,国家并不都是文明的,绝不能把“国家”等同于“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