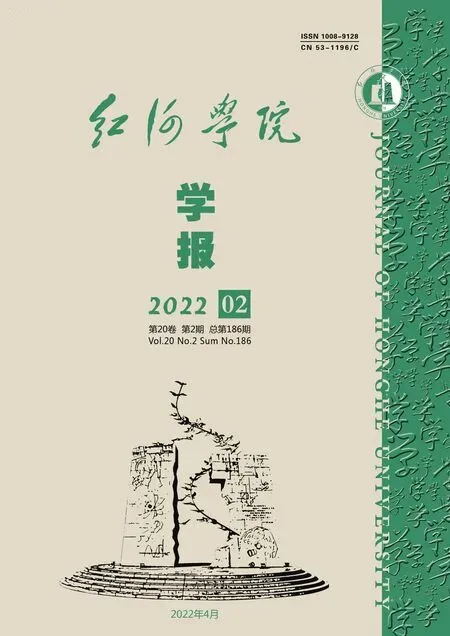峥嵘岁月下的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云南各少数民族百年红色歌谣的发展进程
2022-03-17张译匀
张译匀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00)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党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高度统一的步调,同呼吸、共命运,深入骨髓的红色基因,见证了百年峥嵘岁月的风雨和不屈。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在党百年历程中,各少数民族始终不忘初心,坚定决心跟党走,而云南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探究云南少数民族在党百年发展中的拥护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云南各少数民族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患难走过了十四年抗战的峥嵘岁月,又经历了三年的解放战争,最终迎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曙光。云南各少数民族红歌作为一把爱党爱国的利剑,总体呈现出利刃锋、流布广、主题多样的特点。
本文以前人学者搜集整理的云南各少数民族红歌为文本,从历史性角度爬梳共产党百年历史在云南各少数民族红歌中的体现和转变。纵向梳理云南各少数民族百年红色歌谣发展历程,将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11月至今[1],本文采用实例和实证的方式,运用实例验证不同时期的云南各少数民族红歌特色及民族叙事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南各少数民族红歌的创作历程中,有部分红歌是群众共同创作的,没有专属的创作者,只是简单注明该红歌属于哪个民族,共同创作的作品是少数;大部分红歌有专人作词作曲,他们拥有歌谣的著作权,清楚注明每一首红歌的作词作曲姓甚名谁,该类作品占多数。简单地说,红歌文学成分在很大比例上应属于作家文学中的一类,与当地口头集体创造的民间歌谣相差极大,应将两者区别看待。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中所列举的实例并不祥尽,相对而言,只是选取时代特征较为明显的红歌。
一 1921-1949: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下的建国大业
红歌有着自己的时代性与时效性,所谓时代性,是指红歌的产生与当下的社会现象息息相关,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而时效性则是由红歌的形式所决定的,所谓“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就是时效性的具体表述,基于红歌歌颂的为当下的热门事件或人物,在当下唱响才有意义,而过了当下这个时间段,其歌颂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虽然时效性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但并不意味着流传至今的经典红歌如《唱支山歌给党听》《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等就是“过气”的,这些红歌均属于革命文学的重要一部分,也是分析革命文学不能或缺的一部分。
(一)感恩毛主席与共产党之恩情
直接抒发情感是云南各少数民族红歌中最为常见的类型,其无须多余的修饰词或修饰手法,只需将真切的感情直白地表达出来。这类红歌通常用词简单,篇幅短小,流传广度和传唱完整度远远大于其他同属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歌谣。尽管如此,但丝毫不影响各民族对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情感抒发。如:“独龙族的《共产党领导就是好》:独龙江水向前流,高黎贡山高又高,高黎贡山高又高;我们走上幸福路,共产党领导就是好,共产党领导就是好”。[2]218“白族的《怀念大救星》:选上五彩大理石,选上最美山茶花,苍山洱海寄深情,献上白族心。毛主席呀红太阳,照得边疆亮堂堂,处处是春光。您的恩情胜父母,您的情意满边疆,白族人民怀念您,世代永不忘”。[2]177“壮族的《八宝水清清》:八宝(地名)水呀清清,水上起歌声。我们多么高兴呀,共产党领导,壮乡四季春。”[2]225
一首歌谣是否具有灵魂,最能打动人心的除了旋律之外,更重要的则是歌词,歌词是创作者的心情馈赠和思想表达。在红歌谣目众多和大力传唱的时代,如何能脱颖而出,深入人心,被历史所记忆。总的来说,拥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则是制胜的法宝。2011年正值建党90周年,人民网通过网络开展“爱国歌谣大家唱,亿万群众唱红歌”大型网络评选活动,历经四个月,共计评选出60首“最受人民喜爱的红歌”,如:《唱支山歌给党听》《南泥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十送红军》《红梅赞》等歌谣获选,回顾它们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旋律优美是不能否认的,更重要的则是歌词打动人心,在《南泥湾》一曲中,“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往年的南泥湾,处处呀是荒山……是陕北的好江南,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所描写的前后生活对比是真实可考的,直接将地区圈定陕北,让外地听众真实可感,而不会觉得是抒发一些空洞的情感。那么对于云南各少数民族红歌而言,这种直接圈定地名的红歌,比比皆是,如独龙江、苍山、洱海等大致的区域范围,再如“八宝”的地名,虽然这些红歌的流传广度不能同评选出的60首红歌相提并论,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样的创作方法的确能使这些依靠抒发情感为主的歌谣不会显得“假、大、空”,更多的是可感的真实。
(二)军民一家亲之融洽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口号常在我们耳边回荡。军队在抗战时期,面对侵略者勇敢地站在了第一线,耳熟能详的“南京保卫战、淞沪会战、上高会战”等都是军队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血证。在保家卫国期间,军队和人民的关系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利用放羊娃的身份,帮助八路军传递书信。”“11岁的王朴身为儿童团团长,常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八路军送信,甚至学会了布雷。”这样的感人故事还有许多,很多民众为了掩护军队或军人最终牺牲了,成为了无名英雄。在当今社会,我们国家日益强大,民众生活也稳步提升,过去腥风血雨的日子一去不返,但2020年6月,在中印边境,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线挑衅,边防战士为了保卫国家的神圣领土和人民的生命安全,与外军进行了抵抗。总的来说,无论在什么年代,军队是人民的保护伞,而人民则是军队的坚强后盾,在抗战时期一首首歌颂军民情感的歌谣唱响了云南大山。如:“彝族的《满三孃劳军》:游击队,打胜仗,打了胜仗转回营。众乡亲,喜得讯,今日就要来慰问,今日就要来劳军。勤打扫来快做饭,迎接亲人喜在心。唱起歌来跳起乐,单等乡亲早来临;满三孃,慢慢来,满篮子布鞋提着来。布鞋新,送战士,穿起布鞋好赶路,穿起布鞋好打仗。一双送给赵大哥,一双送给大老王。你们都是铁脚板,三孃时刻记心上……。”[2]66“藏族的《哈达哟》:哈达哟,我们藏族劳动人民,哈达哟,选出最好的哈达;哈达哟,多么洁白多么美丽,哈达哟,献给解放军哟!”[2]255
送军队的场面是最为宏大和热闹的,十里八乡的百姓都纷纷前来送行,拿着自己最珍贵的鸡蛋、布鞋等物品送军队,在彝族的《满三孃劳军》歌词中详细描写了为送军队前做的准备和欢送过程中的赠礼。一首首歌谣生动再现了军民关系,展现了军民一家亲,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欢送客人的最高礼仪,以藏族为例,献哈达便是藏族群众用献哈达这一礼仪送军队,可见军队在藏族心中的地位,深情表达了云南各少数民族拥护革命,拥戴军队的革命情绪。
(三)人民排除万难之翻身做主人
在旧社会,云南民族地区由本民族的土司头人管理,其余群众只能作为奴隶为其服务,一年耕作,大部分收入要交给头人,自己过着缺衣少食的困苦生活。在新社会,实施一系列举措改变了云南民族的生活状况,使大家彻底翻了身,做了自己生活的主人。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翻身诉苦的歌谣,兼有诉苦与感恩两方面,这类型歌谣在云南各少数民族大都是通过痛恨旧社会的劣势,凸显新社会的优势,表明民族地区的日新月异。如:“傈僳族的《木刮》(之二)又名(《我们生活幸福了》):在国民党统治,度日如年日子难过;在蒋介石压迫的年代,度日如年日子难过;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日子好过了;有个共产党的指引,我们生活幸福了”[3]105“普米族的《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想起过去层层石板头上压,毛主席来解放,层层石板掀掉了;毛主席领导好,普米翻身把家当,您的恩情比山高,千年万代忘不了。”[2]74
通过强烈的今昔对比,热情歌唱翻身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无论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与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对比,还是普米族的《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中用层层石板隐晦表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对比,无不强烈表达今天生活的美好,昔日生活的困窘,而一切新生活的改变,与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政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 1949-1978: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兴国大业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群众逐渐从过去的奴隶制、地主土司制中走了出来,成为当家做主的主人。在土地改革之后,人民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此举也为后来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策,为经济提升锦上添花,通过对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纪元。这些事例成为人民歌颂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题材,在这一时期,红歌的题材最为丰富,最为绚烂。在前期红歌的基础上,该时期的红歌无论在旋律歌词,还是思想表达上,都在茁壮成长。
(一)发展经济是建设的基石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云南各少数民族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新的生活,新的斗争,开拓了红歌新的局面。随着党所领导的各项革命运动和生产活动的开展,随着社会的变革,云南各少数民族红歌也发生了变化,不断注入新的元素。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事件,在新的红歌中,几乎都有反映。如:“傈僳族的《毛主席的领导好》:在毛主席领导下,兄弟可以相遇了;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姐妹可以相见了;如今有了毛主席领导,如今有了共产党指引;我们快马加鞭,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更美好的生活即将到来!更幸福的生活即将来到!”[3]121(改编于1965年3月)“彝族的《要开机器学文化》:要吃果子把树栽,要走大路把山开;要开机器学文化,文化没有咋个弄。”[2]75
世居深山的各少数民族在党中央的光辉照耀下,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为了对今天幸福生活的赞颂,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各少数民族创作了欢唱的歌谣。1977年,因文化大革命冲击而中断的十年高考得以恢复,全国各地工农纷纷加入高考大军,此制度的恢复为知识兴国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而远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各少数民族也纷纷响应号召,参加高考,改变命运,彝族的《要开机器学文化》这首红歌中,真切诉说文化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只有学习知识,才会开机器,开了机器,才能发家致富,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灌输到大众中。从另一方面看,该红歌得以流传,其也是对少数民族尊重知识,追寻知识的肯定。
(二)民族团结是稳定的前提
自古以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金朝女真族,辽朝契丹族,元朝蒙古族,清朝满族以及世居中原汉族,新中国成立后的56个民族,无时无刻都彰显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由于民族之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不同,民族问题是棘手的问题,但新中国成立后到1957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我国的民族问题。作为全国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而言,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尤为重要,在党中央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权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系列举措的实施后,云南各少数民族呈现一派祥和共存的景象。如:“佤族的《曼嘿兰》:佤汉人民是一家,同样一片祖国的山水把我们来养育,世上谁不爱祖国,人间谁不爱爹娘,祖国就像爹娘一样慈祥,把我们来关怀。各族人民是一家,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永远属于华夏,祖国开遍幸福花,幸福花开迎彩霞,彩霞伴着五星闪射光辉,照亮神州大地。”[4]“傈僳族的《傈僳汉族是一家》:一个根子两朵花,两呀嘛两朵花,傈僳汉族是一家,是呀嘛是一家,如今翻身做主人哟,团结互助好当家呀。”[3]121(改编于1965年3月)
诚如,前述民族团结红歌一般,各民族之间犹如“一根子上的两朵花”一样亲切,有着“血缘般的兄弟情”。随着时代的推进,民族问题面临新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此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5],可见民族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国家的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让不同信仰的人和平共处在同一屋檐之下,其道路可谓艰难险阻。尽管如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终将走向和谐。
(三)建设边疆是兴国的重要战略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并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等大批工业企业的投产,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远在边疆的云南虽然无法贡献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力量,但却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工业生产的成果。如:“苗族的《苗岭连北京》:山区修铁路,军民一条心……苗山飞彩虹,火车进山村……遇水架桥梁,逢山打岩洞。”[8]175“布依族的《毛主席派来访问团》:山里山外喜讯传,千重岭来万重山,毛主席派来访问团;访问团来了心理暖,山又高来水又深,带来毛主席一片心。”[8]200“哈尼族的《哈尼人民热爱毛主席》:毛主席号召我们学大寨,梯田层层云中起;毛主席号召我们学大庆,矿山处处飘红旗。”[8]208
建设边疆一直是党中央领导的关注重点,可追溯至1950年初,毛主席派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工作,此次决定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首创,同时也为后来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基石。俗话说“想致富,先通路”,可见道路的通畅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是多么重要,通畅的道路直接给当地带来经济的发展、人才的引进,间接则是改变了当地群众落后的思想。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山高谷深,这样的地理条件必然导致云南民族地区的道路通畅受阻,但共产党的关注、毛主席的重视,给云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大庆工人王进喜同志的铁人精神,也深深感动着地处边疆的云南各少数民族群体,当地民族群众选择用歌声回应着铁人精神的不畏艰难。
三 1978-2012: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下的富国大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并且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保持长期稳定,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要特征。
(一)科技走进家庭
“哈尼族的《哈尼姑娘赶街》:红茶绿茶卖了钱,贸易公司走一趟,丝线买回来绣荷包;大包小包装满筐,姑娘低头想一想,盐巴、锄头都买齐。”[8]203“彝族的《彝家山寨新事多》:一连串马车似长龙,一辆辆汽车跑的快,土特产品运进城,化肥百货送上来。”[2]157“傣族的《傣族人民怀念毛主席》:他给我们版纳谋幸福,宽广的荒山变成橡胶林,汽车开到我们家乡,工厂里机器欢乐地歌唱。”[2]239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商品经济不断深入,一时间大批五花八门的商品出现在了贸易公司的商品橱窗展柜里,色彩艳丽的冲击,形式夸张的款式,顿时打破了之前沉闷、单调、统一的形式,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在这样的改革开放之下,也出现了“下海”经商的时代潮流,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群众收入的提高,以往看似昂贵或高科技的产品,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之下,也变得不再“稀罕”,反而成为家家户户的必需品。
(二)传唱形式多样化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服务的对象,强调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形式,为后期的文艺指明了方向,随着《讲话》的出版发行,越来越多的文人投身到文艺工作的建设之中,脍炙人口的歌谣在战争年代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1991年,新文艺得到了重新的建构:第一阶段为新文艺的重构;第二阶段为新文艺的挫折;第三阶段为新文艺政策调整;第四阶段为新文艺的转型阶段。在新文艺的转型阶段中,其主要是将原来口传的内容、书本内容等改编重组,最终以图画、舞台剧、电影的视觉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从全国范围来说,文本改编成视觉影视的京剧《三座山》[6],川剧《柳荫记》[7]引起的反响最为强烈。从云南各少数民族来说,民间文学改编的电影《五朵金花》《阿诗玛》在民族电影中引起热烈讨论。民族电影的问世,一方面标志着边疆地区对于民族与文化问题的注重,另一方面成为推进民族工作、发展民族文化和落实国家文艺政策的有效策略。梳理这阶段的影视文学后发现,阶级斗争问题、社会发展问题仍是影片不变的主题,影片中的歌谣也是唱响共产党、毛主席。
电影主题曲《山间铃响马帮来》:“清清河水流不完,鲜花开满山。重重青山望不断啊,马帮行路难。毛主席的马帮为谁来?为我们边疆人民有吃又有穿呐!太阳升起,白云散开,山间铃响马帮来!”电影插曲《日出东方一片红》:“拨开乌云哎,万山丛中一片红哎,太阳出来哎,照在我们的心头。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恩情啊,这不是神鬼可怜我们的命苦哎。共产党哎毛主席啊,给我们做了主哎开了路哎。道路哎要给什么人哪,道路哎要跟共产党啊,要跟毛泽东啊,日出东方一片红哎。”电影主题曲《景颇山上太阳红》:“火红的太阳哎,射出了万道金光,照在欢乐的景颇山上哎。千万颗心哪,合成一颗心罗喂,雾再大也遮不住红太阳啊,哎罗哎,毛主席给景颇人架起了一道金桥,共产党给景颇人插上了高飞的翅膀哎。哎罗哎,景颇人的新生活哎,要像三月的椿树越发越旺罗哎,要像矫健的岩鹰展翅飞翔罗。”不难发现这些影片的主题曲或插曲只是将原先口头传唱的方式改变了,并将其搬上了荧幕,在人物色彩的展现中和故事情感的推动下,使得歌谣增添了几分生机,从意象化向形象化转变,但唯一不变的仍是歌颂的主题思想。
四 2012-至今:新时代强国大业下的红色歌谣“再创造”
如今,回望这百年历史,能让群众回忆或铭记的或许有书本上的历史文献,或许遗留至今的红色建筑物,再或许传唱至今的红色歌谣,都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姿。建党一百周年以来,红歌主题由原来的歌颂党中央、毛主席转变为歌颂政策战略,并转变为歌颂新生活的向往;红歌创作形式由原来的直接歌颂转变为隐晦歌颂;红歌传播媒介由原来的口耳相传转变为广播传播,并转变为影视传播,这些转变彰显红歌已进入了“新红歌”时代,开始向不同层面的“再创造”。回望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历史中,无论是精神层面或物质层面都有了质一般的飞跃,在“新红歌”时代,红歌“再创作”概括为:一是红歌“再创造”下的时效意义;二是红歌“再创造”下的人民性和群众性;三是红歌“再创造”下的新媒介。
红歌“再创造”下的时效意义。红歌具有时效性的重要特征,但并不指当今被称为“经典红歌”的歌谣过时了。我们这样来理解,那些“红歌经典”在其产生年代的时代意义是与社会紧密联系的,鼓舞群众的,给予群众感同身受的,其歌颂的对象是热门事实,其时效性不言而喻,而当今流传的那些“经典红歌”时效意义并没有消失,更多的是从歌颂转向教育,教育群众现今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需牢记前人的努力奋斗,不走前人“错误道路”的警示作用;从亲身经历转向展现经历,展现过去生活的艰苦和辛酸。所以说,红歌的时效性是跟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和发展,其变化和发展的歌颂意义也必然会在之前意义的基础上,衍生出更多的新的歌颂意义,无论新意义还是老意义都是红歌时效性的体现。
红歌“再创造”下的人民性和群众性。1921-1990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69周年,歌颂党中央、毛主席、社会主义、政策战略成为红歌的中枢力量,随手翻阅那个时代的红歌集册,就能发现这一时代精神。而当今流传的歌颂家乡美好、幸福家乡的歌谣是否属于红歌呢?回答是肯定的,因其仍是健康向上,传播着革命真理,寄托着革命信念的。这一主题形式的歌谣出现,与之前的红歌主题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再明确歌颂党中央、毛主席、政策战略了,而是将其融入歌词中隐晦地表达出对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感恩之情,对于政策战略坚定不移的实施,而这类歌谣,我们称之为“新红歌”。壮族的《红水河之歌》:“……红水河水波连波,两岸壮人歌连歌。歌唱祖国新面貌,歌唱我们的好生活。红水河水日夜流,壮人永远朝前走。向着美好的新时代,勇敢挺进不回头。”[4]彝族的《彝家山寨新事多》:“社员开山又劈岭,修成梯田一层层,当年刀耕火种地,如今黄谷香喷喷。一连串马车似长龙,一辆辆汽车跑得快,土特产品运进城,化肥百货送上来。”[2]布朗族的《深山淌来幸福泉》:“……村村寨寨电灯亮,好像是摘下蓝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村村寨寨亮堂堂,幸福和光明哪里来?是人民自己创造。拖拉机干起活来力气比象大,广阔的边疆,变成了富饶的田庄……。”[2]239“新红歌”是将红歌进行“再创造”而产生的,虽以之前的红歌为基础,但“新红歌”在情感的表达上显得更加隐晦,增添了一份朦胧的色彩。所谓的红歌“再创造”不是将之前的红歌形式全盘否定,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继承红歌的核心精神,加入一些新的创作手法,传播媒介,使其精神能够继续影响着当代人。
红歌“再创造”下的新媒介。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交软件微信、钉钉、Soul等,短视频软件抖音、快手、斗鱼等,视频软件腾讯、爱奇艺、芒果TV等,线下现场的红歌展播层出不穷,而“新红歌”利用新的平台开始专属的“再创造”。在抖音平台上一段“我爱我的祖国”快闪视频一夜走红,一首强烈表达爱国情怀的歌谣,配上人民群众日常的生活场景,完美地呈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人民的依靠。2021年初,讲述扶贫攻坚的两部热播剧《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娇》,分别讲述了祖国西北戈壁滩和中原大山村庄的不同脱贫故事,初看两部影视剧和红歌没有任何的联系,其实不然,两部剧作的主题思想与红歌定义中表达社会主义建设场景、传播革命精神、奋斗意志相一致。其中《江山如此多娇》的片尾曲《带着幸福来见你》实属于“新红歌”的范畴,两部剧作讲述的虽不是云南民族地区的脱贫故事,但透过这两部热播剧作,我们可以得知当下“新红歌”不仅在主题方面紧跟时代,而且在表达形式方面,不再是单一的歌词传唱,而是把歌词形象化与影视融为一体,更加立体性地彰显“新红歌”的“再创造”。云南首部聚焦脱贫攻坚电视剧《万物生》讲述昭通乌蒙山区群众脱贫故事,该剧作也将亮相第26届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成为此次展会上40部重点剧目之一,虽是未播剧,但云南各少数民族在脱贫攻坚的路上永远唱响“新红歌”。2011年5月24日,“不同的语言、共同的心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云南各少数民族歌谣展播活动”在云南昆明拉开了序幕,以特殊的方式、特殊的语言表达对党的热爱、感恩之情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本次展播的云南各少数民族歌谣以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伟大祖国、歌颂改革开放、赞美新生活为主要内容,有《阿佤人民唱新歌》《北京的金山上》《阿波毛主席》等经典红歌,又有《楚雄是个好地方》《麻栗花开幸福来》《太阳照亮独龙江》等近年来云南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红色歌谣。
总体来说,红歌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其转变是必然的,“新红歌”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红歌是“新红歌”的奠基石,“新红歌”是红歌的“再创造”,这是为了促进红歌走得长远。须注意的是,“新红歌”改变的只是主题的多样性及创作的形式和传播的方式,其红歌的核心精神力量不变。诚然,回望云南各少数民族红歌的百年建构,已呈现出其华丽的外衣,但内在仍是朴实无华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之所以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红歌进行建构,一方面由其独特的多民族社会环境决定;另一方面也想通过此次建构,对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红歌历程有个宏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