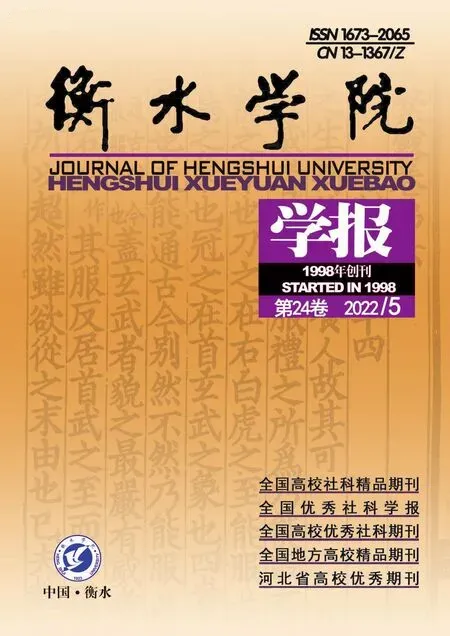新时代乡村儒学探析
2022-03-17段丽丽
段丽丽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中华文明是在长期的农耕生活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乡村是儒学发展的根基,儒学也是乡村建设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活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整体布局,不仅包含乡村经济和社会的振兴发展,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也包含其中。因而,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乡村儒学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美丽乡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乡村儒学的内涵
儒学是有关人的学说,落实于担柴挑水中人的日用常行。就其产生发展来看,无论农耕时代还是工业时代,儒学都是人所处的“自然”。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相对于经济发达的城市而言,乡村更能满足“自然”的条件,是更适合儒学生长、践行的土壤。颜炳罡教授称“乡村是儒家文化的根,儒学是乡村文化的魂。儒学自创始起,就没有离开过乡土,乡村广阔而深厚的文化沃土是儒学的原乡,是儒学持续生长的力量源泉”[1]。
乡村儒学作为儒学的一种新形态,并不是指乡村的儒学,如果从概念上来考量,它有多层内涵。首先,乡村儒学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广义上说,它是有关乡村的一切儒家文化现象,在此意义上的乡村儒学可以称为民间儒学更为贴切。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无论地域还是理念上,乡村与城市的界限都逐渐模糊。而儒学的传播、教化也不做主体的选择,且不受地域的限制,这就突破了时空和群体的边界。因而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地域等关涉乡村儒家文化现象的都可称之为广义的乡村儒学。而狭义的乡村儒学,指的是源于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的儒学现象。2013年以来,由颜炳罡、赵法生等先生针对乡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尼山圣源书院周边开展义务儒学讲习,通过宣讲孝悌仁爱等儒家思想初步探索乡村文明的构建。经过努力,开展乡村儒学活动的村子其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儒学的教化作用非常明显。这次成功的尝试极大地促进了乡村儒学的发展。其次,乡村儒学是一项儒学实践活动。传统的小农社会已不复存在,乡村儒学偏重于对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它所关注的不是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及严密性,而是一场以儒家立场为出发点的文化实践。不同于学术研究,乡村儒学不仅是知识体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儒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而乡土儒学则是由一批有担当、有情怀的知识分子走进乡村,以道德教育为出发点、以儒家学说为中介,旨在提高乡村文明素养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根植于乡土的儒学实践,它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把儒学进一步融入乡村生活,使儒家理念成为乡村生活的指引,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在新时代被发掘,以此来服务乡村、改善解决乡村的问题,再造乡土文明。作为民间儒学的重要形式,乡村儒学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被视为儒学复兴的重要路径之一。
乡村儒学有双向诉求,以儒家文化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文明发展的同时,也以乡村为源泉,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化。作为儒学的形态之一,乡村儒学兼具乡土个性和儒学共性于一体。它的特殊性在于乡村特性,虽然从儒学诞生起就没有割裂它的乡土性,但新时代乡村儒学不同于当代其他的政治儒学、精英儒学、生活儒学、民主仁学及自由儒学等形式,颜炳罡教授认为它是“民间儒学、大众儒学、草根儒学、生活儒学的具体形态”[2]。一定程度上乡村儒学是相对独立的,它扎根于乡村,通过乡村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儒学大众化、实践化,弘扬乡村人伦精神,重构儒家的教化体系,使之成为百姓的生活向导和生活方式,力图开出一条从家庭到社会的乡土文明建设之路。乡村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种形态,除了特殊性之外还有儒学的共性,它继承和发展儒家的核心理念,以道德为本位,从孝入手构建家庭秩序,秉承着爱有等差的仁爱理念将其推开去,探索适应当下乡村社会的伦理规范,培育民众的价值理念和人生信仰,丰富乡村治理方式,建立乡村的文化生态。可以说,乡村儒学既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又为自身发展寻求了新的形态和出路。
二、乡村儒学是儒学对时代的呼应
“乡村”一词并不是简单的居住场所的指称,它更多指内在的人文精神。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乡村社会转型期出现了一系列难以通过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构建乡村文化生态就成了乡村转型的前提。而儒家的思想资源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基础,因而乡村儒学正是社会转型期儒学对时代的呼应。
(一)城乡模式由二元对立向一体化转变
中国的文明是在农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注天人关系。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不断聚集,为了维持一定的秩序,就有了地域上的中心,自然形成了最初的城乡之别。“乡”最初并不是现在所指的乡村,而是指由啬夫管理的国中之乡。“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3]。
在现代语境中,乡村是相对于城市来讲的区域,无论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与城市有一定的区别。加上受西方二元分裂思想方式的影响,城乡之间就逐渐形成了二元的社会结构,忽略了人文精神的贯通,从地理因素上简单地把乡村和城市对立起来。这种片面的认识反过来又加剧了城乡的对立。随着现代化工业和信息化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乡村,离开土地,逐步脱离了农业生产。这就打破了传统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模式,传统的乡村组织方式被打破,也就是说城市化在解构着传统的由家到国到天下的序列。人伦缺少了家与乡情感上的滋养,人直接作为公民面对国家。家作为传统组织方式序列中的基础缺失,容易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失序状态。乡村振兴正是对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回应,在现代化进程中,从城乡二元驱动入手,寻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就需要站在城乡一体化的高度,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加剧城乡分离的同时,也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新时代现代化的工具、信息化的手段,便利了不同地缘不同时间的人们之间的沟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未有过的紧密。村民的关系向更广泛的范围扩展,社会秩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之内,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类构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在这一新的背景下,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得以消解,城乡一体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社会发展的新格局。虽然中西方都面临这一问题,但是中西文明类型,从根本上就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经验,而是要结合自身的特征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因而,在处理城乡问题时并不意味着以破坏乡村为代价发展城市或者简单粗暴地消灭乡村,而是要城乡一体化发展。儒学的根基在乡村,儒学的关注点在人,儒学的特征之一在实践性,乡村儒学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厚的实践经验。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乡村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形象、一种儒学实践,契合社会背景,将对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发挥巨大作用,这是对城乡关系由二元对立到一体化发展的时代回应。
(二)城乡文化由一体化向二元转变
对于农业文明来讲,城乡分化是为了安百姓、安天下,城市与乡村虽然有了地缘上的区分,但从文明的角度来讲,并非是单边的,乡村与城市作为文明载体,从根本上来说,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传统的城市与乡村的文化模式是一体的,二者具有同构性。农民居于农村进行农业生活生产,当政者居于城市虽然不参与具体的农业劳动,但他们却进行道德与政治实践,为农业提供治理服务。治理虽然出自城市,乡村却是着手处。一直到工业文明之前,中国的乡村和城市都沿袭这样一种模式。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西方思想的影响,价值理性不断弱化,工具理性逐渐抢占了人文世界,文化生态遭到冲击,出现了文化失衡。城市与乡村在文化模式上由传统的一体化逐渐出现了分化。在工业文明面前,城市更多地关注科学价值,而在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的农村,犹如戴着镣铐舞蹈,思想的交锋、文化的交流则更明显,一体化的城乡文化割裂开来。乡村作为传统文化之源式微了,乡村文明不断衰落,问题日益增多。传统的乡土文化活动正在消逝,诸如宗祠、庙会、社戏等文化载体也渐渐退出乡村生活。传统优良的礼乐教化也丧失了它应有的功能。传统的文化生态遭到破坏,新的文化形态又没有形成,思想出现混乱,导致宗教甚至邪教在乡村传播迅速。这些问题,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仅依靠经济、法律等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塑乡村价值观和教化体系、重建失衡的乡村文化生态是乡村现代化的前提。
对于文化而言,乡村与城市都是必不可少的载体,并不以地域上的城市或者农村而有所区分。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文化建设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文化价值。“被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特殊国情所决定,中国的工商文明仍然应该把‘根’扎在乡土文明中,如果这个‘根’枯萎了,那么中国的工商文明势必会出现种种病态”[4]。虽然市场化大潮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冲击,使农村和城市生活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都有了较大变化。但相较于城市而言,由于土地的亲近和几千年文化的积淀,使得农村在普及推广儒家文化方面更有天然的优势。尤其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乡村儒学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得如火如荼。他们开讲坛、读经典、办会所、评先进,经过几年的发展,乡村的道德风貌焕然一新,人文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乡村儒学真正走进了乡村生活,进而影响到了城市生活。
三、乡村儒学的现代价值
乡村是生活家园,更是精神家园。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弘扬乡土品质、延续历史文脉,还要统筹城乡发展,融入现代元素,使人有回得去的家乡、看得见的乡愁。乡村儒学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弘扬,唤醒民众道德自觉,重塑乡村文化生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由此,儒学在提升个人道德素养、重构乡村社会伦理以及自身发展等方面的现代价值已经显现出来。
(一)乡村儒学提升了个人道德素养
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但精神生活的发展却没有与物质生活同步,个人道德滑坡、行为不端等问题相继出现。乡村儒学作为儒学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内容上以孝为切入点,形式上采取乡村喜闻乐见的方式,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
乡村以农民为主要群体,针对农民整体文化水平有限这一现实,乡村儒学灵活多变,通过多种形式提升个人道德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在内容上,通过通俗易懂的案例培植家国情怀。乡村儒学围绕村民的生活,把天道人性的学理融于活泼泼的日用常行,弘扬村民自己的儒学,直指人心。它摒弃单纯儒学理论知识的讲授,通过关注身边的事弘扬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心之四端。孝作为人的原始本性,可推演出家国情怀,同时相较于其他诸德,也比较易于实践。人人都有父母,每个人都有对孝的追求,因此乡村儒学以孝德教育为出发点,以孝敬老人、友爱兄弟、守望相助为主要内容,加强完善自身道德,在乡村实现儒学的践履。在乡村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村民的道德素养明显提高,进而影响到家风和社会风貌。其次,形式上借助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阐发生活的智慧。在乡村儒学的践履过程中,专家和村民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知识的不对等。而如何引起村民的兴趣,将晦涩的学理转化成浅显易懂的语言是推行乡村儒学至关重要的一环。以老人、小孩、留守妇女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乡村群体对乡村儒学有热切的渴望,同时又担心自己的水平影响对乡村儒学的认知和理解。因此采取村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是推动乡村儒学的重要方面。通过考察,专家们根据村民的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采取生动的故事或曲艺等方式,讲授村民自己的儒学。同时,通过村民身边的人和事使之反观自身,产生共鸣,由此儒家理念深入浅出地传授给村民,使之入脑入心,完善道德人格。
(二)乡村儒学有助于乡村社会伦理的重构
传统乡村大多以家族聚居为主,这种聚落方式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符合家国天下的逻辑序列,村民之间相互熟悉,有出入相友的情感基础。而社会发展拓宽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人口流动逐渐打破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居住形式,行政村落或者社区的形成,虽没有割裂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系,但随着商业化因素的出现,情感皈依的因子开始淡化。乡村儒学致力于普及儒家文化,力图从人伦秩序与人伦精神两个维度重构乡村社会伦理。
就人伦秩序而言,乡村儒学通过重建礼治社会重构人伦秩序。儒家的伦理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5],以人伦生活为场域开展各项活动。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个体跳过家庭直面社会的现象,以家庭为出发点的伦常秩序发生了改变,传统的社会规范势必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做出反应。乡村儒学在社会失序现象屡有发生的情况下,从孝入手,大力倡导孝悌仁义,结合现代法治精神,发扬亲亲长长的儒家伦常,重建和谐有序的新型乡村秩序。在乡村儒学的熏陶下,个体村民行为上有了明显变化,村民之间重构起互动合作的关系,乡村风俗得到很大改善,乡村儒学参与到人伦秩序的重建,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维系着乡村的秩序。就人伦精神而言,乡村儒学通过人文教化重塑人伦精神。工业化和现代化作用下,农村的生存方式发生变化,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也发生相应改变。“乡村文化话语权缺失,失去了认同的基础”[6]。物质的诉求对乡村道德价值、家庭关系、社会伦常以及风俗习惯在无形中进行着解构。乡村儒学致力于村民内在修养的提升和社会外在礼仪的践行,重构长幼有序、和谐友爱的生活状态。经过数年发展,乡村儒学取得了初步成效,改善了家庭伦理和社会风气,重构乡村生活的意义世界,在乡村文明建设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乡村儒学是儒学发展的一种形态
儒学不是僵化的理论,它是活的有关生命的学问,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解决社会人生问题,有修己安人、经世致用的实用性。乡村儒学是新时期对乡村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思考。它是儒学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是儒学发展的一种形态,同时也是儒学的时代使命,是儒学生命力的体现。
第一,乡村儒学的发展是儒学的时代使命。
儒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程,同时又是超越历史的存在,本身就蕴含着现代性。其具体的表现形态也是随着不同的历史背景而有所变化: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等,都是对不同历史背景的回应。不同的形态是儒学一次次现代化的呈现,也是儒学的时代使命使然。
乡村儒学正是新时期儒学对新形势、新问题的回应,是当代儒学复兴的探索。它不守旧,不拉历史的倒车,在时代课题下,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历史、面对当下、面对未来。颜炳罡先生在推动乡村儒学的时候曾说是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他指出:“乡村儒学说到底是为儒学的世代传承发展探索新路径,为儒学的广泛传播创造一种新模式,一种新常态。”[1]通过推动乡村儒学,探索新时代儒学发展的新路径、新形态,实现儒学的大众化,使之真正成为人伦日用之常。乡村儒学结合了现代理念,以发展的眼光发掘它的现代价值,使之真正参与到生活当中。乡村儒学的双重诉求在重构乡村伦理重塑乡村生态文明的同时,也在乡村这一儒学原乡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所以说,乡村儒学不单单是返本,更是一种开新,紧扣时代脉搏,是儒学现代化的结果。
第二,乡村儒学是儒学生命力的体现。
在新时代语境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激发了儒学的活力。乡村是儒学发展的丰厚土壤,作为儒学的现代转型,乡村儒学根植大众,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焕发出生机。乡村儒学正是在担柴挑水之中体悟、践行儒家之道。从思想上、行为上实现儒学的大众化,使儒学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从思想上来看,儒学作为天人性命之学,不乏对万物本源以及生命价值的思考。儒学在乡村,有祠堂、讲堂等场地,有祭天地、拜祖先等仪式,有万物一体等理念。针对近年来外来宗教对乡村文化的冲击,乡村儒学通过多种方式将儒家理念渗透到村民生活,内化到村民的生命,以此重建村民的信仰体系。从行为上说,在生活中,乡村儒学从孝入手,通过彰显人性中的孝构建和谐的家庭伦理,进而推演到社会,将忠信礼义等儒家观念在社会中进一步推行开来,逐步形成乡村伦理规范,培植良好的民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乡村儒学在具体的实践中完成了修养身心、教化大众的教化功能。而儒学本身也具有普适性,它不是为某个人、某个阶层或某个国家所设计的,它是人学,不分上下、不分内外,所有的人都可学可用。乡村儒学的发展,使儒学由“百姓日用而不知”转化成了百姓既用又知,实现儒学的大众化,发掘出了儒学内在的生命力。
乡村儒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儒学发展的形态之一,更是村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儒学,而反过来乡村振兴也为乡村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诚然,乡村儒学不是万能的,无法解决乡村的所有问题,它自身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就更需要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中寻找乡村儒学的生长点,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发掘乡村儒学的更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