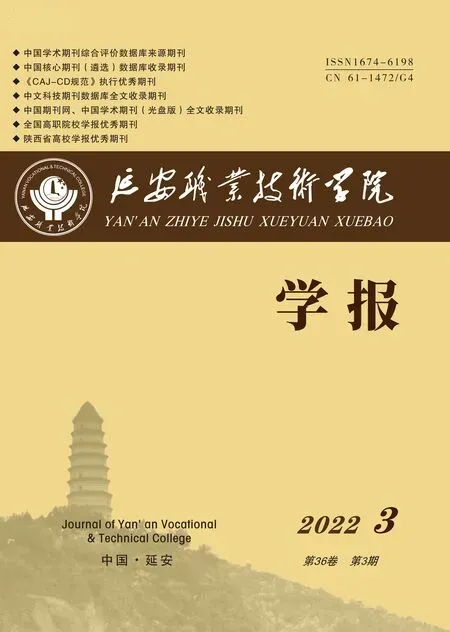子洲县面花习俗考察
2022-03-17高锦花郭咪咪骆梦男
高锦花,郭咪咪,骆梦男
(延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2018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振兴乡村战略的二十字方针,内容之一便是“乡风文明”。我们认为要想构建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孝悌友爱的文明乡村,必须立足于乡村本身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乡村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最可利用并能直接实现转化的就是民俗文化本身。以子洲面花习俗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可以让人们了解该地的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面花习俗进一步了解其在地方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所承担的构建功能。
子洲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腹地,榆林市南缘,1944年由绥德、米脂、横山和清涧四县划拨成立,因纪念烈士李子洲而命名。明弘治本《延安郡志序》中“幅员北控,穷荒绝境,酋虏跳梁,辄烽火连夜”[1]10的记载大体就是当时陕北人文地理环境的真实写照,同时书中这样描述绥德、清涧、米脂和葭州一带的风俗:“(绥德)地近边垂,俗尚强悍”[1]203;“(清涧)民务农桑,士崇学问”[1]218;“(米脂)务本业,畜牧,尚勇少文”[1]230;“(葭州)人性勇直,好尚武力”[1]239。又清康熙本《延安府志·舆地志·风俗篇》说:“清涧、绥德、葭州、神木、府谷、吴堡近晋,习俗颇俭,且近边,尚刚武”[2]18这些记载均说明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塑造了陕北人民注重实际、乐观豁达、淳朴善良、好直尚勇的民族性格。
子洲县南川一带(从何家集镇到淮宁湾乡)有一种从清代道光年间就已流行的特殊民俗文化现象——捏面花,每逢寒食清明前后,这里家家户户都要捏面花,随着社会发展,面花从清明节浸润至人生礼仪和其他节日庆典中,构建起一套具有区域特色的符号文化体系,使这里百姓的日常生活被各种人生礼仪和节日仪式文化所包围。由于在榆林十二县中具有极强的文化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2012年子洲面花被选入榆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年又被选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发展成为子洲的一张文化名片。具体在研究过程中,结合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口述史学等多个交叉学科理论,从文化视角去考察这一民俗事项所承载的内在文化价值与意义,在陕北乡村文化建设中作抛砖引玉之论。
一、子洲面花习俗的历史渊源
面花主要流行于我国长江以北以面食为主食的地区,其中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宁夏、甘肃等地最为流行。因各地风俗不同,就形成了“面花”、“花馍”、“面塑”、“礼馍”、“花饽饽”等不同叫法,陕北还有些县域(如米脂)称之为“燕燕”。至于其来源,在子洲县有一则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之子重耳因骊姬之乱逃往白狄国(今子洲县怀宁河流域)避难,介子推作为随行属臣同重耳在此生活了十二年。重耳复国后,赏“从亡者”,遗漏了介子推,他遂携母隐居绵山,文公求人心切,下令放火烧山,后在枯柳树下发现介子推母子的尸体。民众听闻后悲痛不已,为缅怀介子推母子,便于清明前后捏制装饰花鸟等物的“馒头”(又名“子推馍”)。关于这一习俗,清道光本《清涧县志·风俗篇》这样记载:“三月清明,士女插栢叶于鬓,祭墓,戏鞦韆,作馒头相馈,上缀各虫鸟形,名为子推。谓晋文焚山,禽鸟争救子推也。”[3]86文献中所说点缀虫鸟形的“馒头”即今之面花,彼时当地便以此互赠亲友。同书《地理志·山川》、《古迹》记载“县北九十里有怀宁河”[3]58,有城一座,“宋庆历时修,赐名怀宁,接横山一带”[3]71。这足以证明如今盛行于淮宁湾的面花至少在清代已相沿成俗。这是陕北地区面花源于介子推的最早记载和清明节前后民俗主要活动。
当然关于面花的真正起源,以及面花如何由早期单一的清明节祭品发展为其他节日礼仪用物,再发展到人生礼仪的象征物,因文献缺载,已无从考究,但是可以通过它在社会事实中与何种习俗活动结合在一起,也可揣摩出一些端倪来。功能学派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在《文化论》一书中认为人类有许多物质技术、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都起源于“人类有机的需要”[4]26,他把这种文化不断发展、社会持续进步的“需要”或推动力称之为“文化手段迫力”[4]47,所以在他看来:“风俗——一种传统力量而使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的行为方式——是能作用的或能发生功能的。”[4]33功能学派核心观点认为人类诸多文化创造是出于其有机需要,只要我们按照文化要素分析方法,一一析出这些文化要素或文化事项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何种功能,与何种社会事实结合在一起,就能知道文化产生的根源,也能探究出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我们知道,民间习俗的形成都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历史传统,它传承发展的动力恰恰源于其在民众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由于面花具有沟通人际关系、构建礼仪秩序等特性,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培养了人们内在的文化认同感、邻里守望和互助合作的族群凝聚力,最后自觉形成乡村道德伦理规范。
二、子洲面花与民俗文化生活互动
从现有资料和民俗活动来看,子洲面花不只作为祭品存在于民俗活动中,而且在一些人生重大礼仪、节日庆典中,均是不可或缺的道具或媒介物,甚至在一些庙会活动中也必不可少。接下来我们从人生礼仪和节日文化两方面考察面花如何在乡村社会构建起一个文化场域。
(一)人生仪礼
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说:“人生仪礼是指人在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5]156具体包括诞生礼、婚礼和丧礼等,面花可以引导我们探讨探寻民众对生命过程和生命意义的认知和理解。
1.诞生礼
生命的孕育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讴歌的事情,新生命的诞生意味着新希望的到来,事关整个宗族(家族或社区)的发展。围绕新生命的诞生,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着相同的习俗,即整个家族或社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尤其是在非常重视血脉相续的中国,当一个婴儿(特指男孩)呱呱坠地会被视为整个家族的头等大事,必须举行一系列的仪式活动以示庆贺,有些地方相应的祝福一直持续到孩子满十二周岁为止。陕北地区,过去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婴儿死亡率较高,所以当一个新生命诞生以后,他周围便充满了来自于亲朋好友的各种祝福和保佑,直至其长大成人。若所生为女孩,庆贺仪式则相对简化。
在子洲,生肖是伴随孩子一生的吉祥物,并通过谐音或生肖本身的寓意而形成大量吉祥用语,如“猴寓侯”、“兔平安”、“马成功”、“鸡同吉”等。因此,在婴儿诞生前,外祖母就要捏制具有祈福意义的生肖面花。满月这天,外祖母和舅家等亲戚都要送满月面花前来庆贺,类别主要有鱼馍、虎馍和兔馍,数量一般是十至十二个。面花个个形体饱满,色彩亮丽。当地巧手婆姨薛冬梅①说:“孩子出生后送的面花越大越好,这是希望娃娃们长得大大的、壮壮的。”表达了人们对婴儿生命力顽强、旺盛的祝福。
核心仪式如下:首先孩子母亲将其抱放在炕中间,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孩子胸前系一把五色锁线(象征阴阳五行),然后请家族中最为年长且最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辈,将亲戚们带来的鱼馍绕孩子放一圈。若是男孩,要在孩子旁边放象征阳刚之气的虎馍,寓虎头虎脑、虎虎生气;若是女儿,则放一圈代表阴柔机敏的兔馍,寓意将来像兔子一样灵动可爱。孩子一周岁时,须过周晬。满月时来过的亲友们仍带鱼馍、兔馍前来祝贺,这种庆贺方式一直持续到孩子满十二周岁为止。民间认为,孩子十二岁以后才“魂全”,此前父母十分注重保护孩子的元魂。十二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龄,类似于其他民族的成丁礼或成年礼,陕北地区孩子满十二后便可解除一些禁忌。
2.婚礼
婚礼是诞生礼之后的又一大事。《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6]1416结婚不仅仅意味着成年,也意味着一个年轻人从此正式进入社会人际圈,成为社会正式成员,从此开始承担抚育子女、奉养父母、养家糊口的各项责任,也要参与宗族或社区重大公共事务的商讨和决策,履行修路、筑桥等义务劳动,必要时要有义务出资资助村社和宗族的发展。儒家强调一个人应具备的“修齐治平”的德行修养和治理家国的能力在这一刻起进入实践层面。因此,婚礼就成为诞生礼后又一项重大礼仪,它既是身份转变的象征,也是开启人生新阶段的转折性标志,自然需要盛大的礼仪庆祝。这个过程离不开长辈们的主导,且一定会利用面花传情达意,将男女青年一步一步顺利导入角色。
按照子洲风俗,订婚后首个清明节男女双方需互赠面花作为定情信物。男方赠送女方一对莲花鱼儿,其造型为灵巧的鱼儿上方驮着盛开的莲花,寓意女子像莲花般高洁,如鱼儿般聪颖,这应该是阴阳相交、阳往而阴来的古老文化的物化表达②。有些村落送一对大抓髻馍馍③,当地有一句俗语:“抓髻扎起来,婆家不引来?”透露出女方待字闺中、男方急切希望尽快迎娶的心情;女方回赠男方一对大面老虎,象征男子阳刚、威猛、雄壮。
迎亲当天有三个展示面花功能的仪节,颇耐人寻味。首先迎亲队伍给女方家带来10 个长度约为20CM的喜馍,俗名“催妆馍馍”,意为感谢女方母亲十月怀胎之辛劳。关于“催妆”习俗,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北朝时已有此俗:“北朝婚礼……夫家领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娘催出来!’齐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7]4直到现在,陕北人均把迎亲当天夫家所带之物称为“催妆”,可见文化浸润之深之广。其次新娘迎娶回来与新郎进入洞房,之后男女双方盘腿端坐在炕(床)上,由家中女性长辈围绕二人放一圈俗称“围儿女馍馍”的面花,共由两个大的子推馍和十二个点彩小白馍组成,两个大的象征夫妻二人,分别装饰许多同样材质的小动物;十二个小白馍则寓儿女成群,绕膝承欢。然后夜晚就寝前,新郎母亲扮演“送子娘娘”,用擀面杖戳开新房窗户纸,往里扔2个白馍馍,此即“撂儿女馍馍”,新娘和新郎在屋里各接一个,祈愿新婚夫妻早生贵子。
喜事一过,这些面花及各式馍馍就可馈赠亲朋好友。交感巫术理论认为,人只要接触到某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吉祥物,便可拥有同样的能力。亲朋好友吃了这些“馍馍”不仅会沾染喜气,而且也会具有相应的繁殖力,儿女成群。纵观诞生礼和婚礼,正如已故历史学家常金仓所言:“文化因子的聚合分散不仅可以造出错综复杂的文化,而且某些能量较大的因子很可能削弱和改变文化某方面的趋向……如果我们看看新几内亚蒙杜古马人——这也是一个父权制的部落,就会知道,仅仅因为那里盛行换亲制度,就使他们特别重视多生女子,文化因子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是不能忽略的。”[8]61-62如今子洲当地的婚礼仪式已删繁就简,但面花的媒介作用并没有削弱,陕北其他各县亦有相同仪式,只是数量、造型上略有差异。
3.丧礼
与人生礼仪相关的另一项重大礼仪就是丧礼。各民族和地区,针对丧礼有不同的仪节和民俗,祭奠用物也有所不同,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在陕北广大地区,比较普遍的供奉给亡灵的最后献物也是面花,子洲叫老献,有的地方如米脂则叫大献。活着的人通过最后的用物表达对死者的敬意,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生者与死者的正式“分隔”媒介物,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价值。当然相较于前两者,丧礼中的面花造型和颜色搭配更庄重素朴,数量也较少。而且丧礼所需面花亦须请当地面花艺人蒸制,主要有老献和猴拜相两种类型。
老献,也称老馍、大馍,通身为一个未经装扮、施彩的圆形大馍。当地老人苗得库④解释:“这个大圆形象征混沌宇宙,意味着人从混沌出生,逝去后又回到混沌中去。”这种对宇宙奥秘和生命轮回的直观体悟通过一个大馍来代替,寓示了生命从无到有、复归于无的本原状态,他们对生命过程的理解充满了哲理,完全是中国传统道家对生命直觉体悟的哲学观念,不得不让人赞叹大道至简的民间智慧。老献使用数量因葬仪不同而不同。如果单埋,蒸半桌老献,即六个;如果夫妻合葬,则蒸一桌老献,即十二个。至于猴拜相面花,其造型为猴子坐于大象身上,双手举起向前叩拜,取谐音“封侯拜相”,寓意死者到了阴间以后也能封侯拜相,成就另一番功名。
由以上可知,围绕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人生礼仪,反映了传统农耕文明状态下老百姓的生活生产习俗,其中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核心价值,如孝悌友爱、尊老爱幼、慎终追远、团结互助等。此外,上述仪式巧妙地将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起来,面花的捏制不仅融合了现代手工艺品的手法和技艺,还充分借鉴国内外乡村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了乡村文明的与时俱进和创造性转化。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要保留乡村风貌,坚持传承文化。”[9]总之,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很大一部分是靠日常礼仪活动来巩固和维持,而现代乡村文明的建设除了依靠法治,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还须借助乡村固有的文化传统来凝聚人心,进一步整合和提升传统文化的功能与价值。
(二)节日庆典
节日是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透过节日,不仅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的变迁,也可以看到人们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的变迁轨迹。下文主要通过元宵节、清明节和中元节三个节日考察子洲面花习俗的发展和演变。
1.元宵节
元宵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年中第一个满月之夜,古称“上元节”、“灯火节”,子洲人在这一天的庆祝活动有转九曲、闹秧歌、赏灯逛街等。同时为了祈求神灵福佑,家家户户都赶蒸十五面花,其中既有祭献给天地神灵的大“枣山”,也有赠予亲友的小枣山和面鸡。
所谓“枣山”,主要是由面和红枣两类食材做成“山”状面花。因是献神之物,当地巧手婆姨周彩英⑤说:“枣山捏得越大越好,这代表着自己对天地神灵的敬意多,家里的发展也就越红火。”面必须提前一晚发酵好,艺师先取一部分面团擀成圆形薄饼作底盘,然后取小块面团搓成多个长条,捏制成回云纹,并在云纹间放大红枣,这样一层一层由大到小堆成小山一样的形状,通常为五层。 捏制好后的枣山放入一口大锅中蒸熟,出锅后由一家之主恭敬摆放在窑洞内或房间的天地神位,全家人都要祭拜,祈求平安顺遂。此外,元宵节期间还捏制许多小枣山和面鸡以赠亲友,由于“鸡”和“吉”谐音,寄托捏制者祈望新的一年中亲友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所以面花在这一场合不仅成为沟通人与神的媒介,也成为人际关系的黏合剂,培养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感。
2.清明节
清明节作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之一,在子洲县南川形成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这一天也被确定为“面花节”,尤其2013年面花被列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活动进行庆祝,届时媒体记者、地方政府官员都要出席,其影响力和传播力都远超附近县乡(如米脂和绥德)。文化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经历文化的聚合分散以后,有些文化因素得到发展并逐渐成为特色鲜明的文化特质,有些文化因素因此而消失,民俗文化尤其如此。
子洲县南川清明习俗捏面花活动与纪念介子推“割股奉君”传说有关,人们每逢清明节便捏制“子推馍”进行祭拜。面花节确定以后,面花遂成为子洲新农村文化与文明建设的主要表征。其造型、食材及制作步骤都与“枣山”类似,但颜色更加绚丽夺目,形状更大,装饰更加丰富多样,底盘面团超大,上面盘绕着具有层次感的三圈面条状装饰,每圈面条上歇息着众多活灵活现、形象逼真、施以各色的燕燕雀雀,再以红枣点缀其间。当心灵手巧的子洲人将面花这一艺术品展现在公众视野时,也展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心理。随着民俗文化的发展变迁,民间上坟祭祖,除了摆上象征荤食的猪头馍和子推馍,还要带时令新鲜果蔬酒菜。在子洲南川老君殿镇、何家集镇一带,为了攘除不吉、驱除邪气,清明时还为家人捏面花,为男孩捏制小老虎面花和燕燕雀雀面花;为女孩捏制“小抓髻馍馍”和小花篮面花;为从事耕作不辍的劳动人民捏“大燕背小燕”面花。
整体上北方地区清明节前捏燕燕的民俗活动可以上溯到宋代,《东京梦华录》说:“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旗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10]129宋代“子推燕”的大小形状现已无法考证,但我们看到当一种变动不居的文化现象一旦被社会民众普遍接受,节日文化标志物遂具象化,形成持久而稳定的民族风俗习惯。此外《榆林府志》还记载过西川一带民众佩戴柏树叶趋吉的习俗:“‘清明’,士女插柳毛(白柳芽),柏叶于鬓。”[11]96总之,清明节的各种祭扫文化将活着的和死去的人用共同的文化联系在了一个共同体中。
3.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道教称为“中元节”,佛教称为“盂兰盆节”,民间称为“鬼节”。虽难与元宵、清明等节日比肩,但陕北多地照样将之过得隆重红火。这一天人们会用新谷做成祭品酬谢先祖,以及各路风师、雨师和雷神等自然神,也包括孤魂野鬼,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子洲地处陕北腹地,常年干燥少雨,只适合旱作作物生长,产量极低。每逢七月十五日,诸多作物进入成熟期,风调雨顺才能保证最后的丰收,善良的子洲人便会通过虔诚仪式表达对天道自然和各路神鬼的敬畏之心,获其福佑。首先是祭祀谷神和风雨等自然神,届时农家巧手媳妇用新麦蒸制十二个大面卷,备好香火、黄纸、白纸和酒水,由家中老农带去田间祭祀。老农将所带黄、白色纸剪为长条在庄稼根部焚烧,再将酒水洒于田间,焚香插于地中,磕头祭拜。然后把大面卷掰成小块分成几部分,一部分撒向四方,恭请众神享用,民间谓之“泼散”。其余一部分用来献祭祖先,方式就是要在经过精心挑选、长势茁壮的庄稼周围撒一些,报答他们;一部分随意撒在外围,供孤魂野鬼取食,希冀他们毋行捣乱。光绪版《绥德州志》这样记载这一习俗的:“至‘中元节’,家家皆诣先茔烧纸钱,秋露既零,故祭祖焉。农家晨兴,向田间择禾之长茂者,以五色纸旗挂之,曰‘田幡’。”[11]79只不过现代人用黄白纸取代了明清时的五色纸旗。但当地老农加红高⑥说:“年轻人都不这么讲究了,过去老一辈的人种庄稼时,收成不好的时候才这么做。”
而陕北其他县域,如与子洲毗邻的米脂县高西沟村在这一天则举行庙会活动,或其他文艺形式如唱戏、说书、扭秧歌等进行庆贺,也有希望家中生意顺利或家人生病痊愈而给神许过愿的人家,他们会摆“花贡”酬谢神灵保佑。“花贡”就是各种式样的面花,数量多寡,造型大小不限,讲究的是虔诚。当地的面花传承人也会通过面花比赛向人们展示技法的娴熟和技艺的高超,造型别致与花样翻新的将会受到一定的表彰。所以这里的人们已经把传统节日变成了一场艺术盛宴,反映了新时代下民众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富足和乐的精神面貌。而中元节的源起,应该是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将传统“忠孝”观念由人道扩展到了天道,构建起人-鬼-神-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精神世界,将个人纳入到祖先与后代以及与神灵为一体的文化体系中,用费孝通先生话说,就是“他们用祖宗和子孙的世代相传、香火不断的那种独特的人生观为信仰,代替了宗教”。[12]233
综上可知,节日的最大功能除了娱乐,更重要的是在民俗活动中起到对乡民价值观和文化观的整合与认同,人民生活在一个具有共同祖先或神灵的庇护、拥有共同历史记忆的社区或村落中,而面花成为勾起人们共同记忆进而产生浓厚亲情的一个具象代表。
三、以面花为媒介的乡村文化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子洲面花起源及使用习俗的考察,我们发现该地面花文化已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精神与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信仰淬炼为一体,构建起一套以面花为媒介的文化符号体系,维系着人际秩序。它既包括人与神之间的交往,也包括人与鬼魂之间、人与祖先之间,以及晚辈与长辈老人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背后有着鲜明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所崇尚的“施报”特色,即《礼记》所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6]11费孝通先生说:“人的语言、人的行为模式、人的身份等,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积在社会里的个人创造,成为社会共同的‘遗产’,是文化的积累。”[13]82-83所以,乡村文化建设和加强不能单纯依靠经济,重点还得要有一套文化体系和理念。总结起来,有如下方面:
首先是沟通人际关系。凡生命个体都有生老病死,围绕这个过程,人类社会绝大多数民族都被纳入到一个由礼仪生活编织起来的人际网络之中。在子洲县这个人际网络之中,有一条核心主线不容忽视,人们会普遍遵循一种互惠互利原则进行来往。于是在一个世世代代生活共同体中形成赠予-收受-回赠无限循环的人际圈子,老人赠予婴孩,大人赠予儿童,希望孩子们一生平安顺遂,晚辈希望长辈健康长寿,颐养天年;生者送走死者,希望得到死者护佑。然后再将小范围的家族、宗族、社区的互惠扩大到某个集团、某个群体,某个地区,甚至将这种关系延伸到人与神、祖先和鬼魂之间,这种互惠原则在人类学家利奇看来,“献祭是人们给神敬献礼物、贡金或罚金,借以禳除不祥事端,获得神的福佑的过程。献祭仪式是互报原则的表现,人给神以礼物,神就得回赠人以好处。通过献祭仪式,献祭者在神界与人界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神的能力通过桥梁能够通达到献祭者本人。”[14]83此外,研究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专家褚建芳关于清明节上坟仪式(傣语谓“恨隆”)有这样一段论述:“在这个仪式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的祖先之间以及人与野鬼之间,分别发生了不同性质的交换行为。在人与人之间,亲属关系的纽带把不同家庭的个人联系在一起,参加仪式和聚餐的各个家户都带来一些大米,作为自己的饭费。在人与自己的祖先之间,人们燃放鞭炮,向祖先供献物品,并跪拜行礼,祈求祖先给予福佑和庇护。在人与野鬼之间,人们施舍给他们一些用生竹叶包好的米饭团,并口头安抚他们,以免他们因没有吃的而来抢自己祖先的饭菜。”[15]308对比发现,傣族与子洲县在文化观念上很相似,二者具有的共同文化观念充分说明,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正是相似的文化把各族人民联结为一个休戚相关的民族共同体。
其次构建起礼仪主导的秩序世界。考察人类社会秩序的构建,至今已有多种类型,有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构建起法律至上的早期法治国家,有通过宗教信仰原则构建起神学至上的政教合一国家,中国社会则恰恰构建起礼仪文化特别发达的礼治国家。常金仓先生在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类型的时候这样说:“某个文化类型……对于每一代人来说,他们考虑的仅仅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对付眼前面临的生活问题,而毫不计及采取某种措施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他们应付生活问题的种种措施中,有些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或者干脆因为时代相传的习惯,于是在该文化系统中,这些因素得到了优先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文化要素发展的不平衡,哪些优先发展起来的因素形成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并常常改变了其他因素的品质,文化类型便渐渐显示了出来。”[16]中国自古以来,很多生活场景都是通过礼仪活动主导,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类型形成的关键性因子,中国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因而我们看到,中国虽由众多不同民族构成,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同质的仪式性生活之中,无论是人生礼仪,还是日常性的节日生活。这些礼仪生活,具有超强的约束力。所以褚建芳说:“这种结构和秩序是以神圣性为特征的,不同神圣等级之间取送往还的施报原则构成了这种结构与秩序的基本特征和动力机制。”[15]314这当中“取送往还”的东西在子洲日常生活中就是面花。我们看到,面花除了食用功能,还有观赏价值,最关键它还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体现。所以常金仓在《中国古代的礼品交换与商品交换》一文中总结:“礼品交换……它使我们领悟到一个民族商品经济是否发达不仅仅是个生产力高低、剩余产品是否丰富的问题,它还与该民族的生活方式或文化类型具有密切的关系。”[16]356所以人们更看重的是附着于面花之上的情感沟通价值,而非面花本身,所以常金仓先生又说:“循环往复的礼物馈赠是靠良好的道德维持的,如果某人不守社会公德,那么就会遭到舆论的谴责而陷于孤立,甚至受到严厉惩罚。所以道德既是礼物馈赠的保障又是它的产物。”[16]364当代民俗学家萧放说:“礼仪实践与民间信仰、地方传统糅合在一起,共同构建了基层社会的礼俗秩序,有着高度的社会治理价值”,“是践之于身的行为规范,也是约之于心的道德规范”。[17]83-92
再次具有文化认同功能。所谓认同,其实就是一种心灵的归属感。在一些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看来,类似于面花这些地域特征突出的文化现象具有很强的文化认同价值,“民俗是文化共同体建立的基础,具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其中民俗记忆资源的多样性、多层次性构成认同的不同形态和不同层次。”[18]90-97文化认同,本质是价值认同,对于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们来说,由于拥有共同文化传统而产生某种归属感,人们遵循集体认可的习惯势力,不遵守者会被视作离经叛道,进而受到某种来自于习惯与习俗的谴责,获得了日常生活的意义。人生活在这个集体中,就必须接受一套先于他存在的文化体系。也有民俗学者将之称为“民俗认同”,即“以民俗为核心来构建和与维系多重认同并由此传承传统的精神意识与日常行为。因此,关注民俗认同就是在研究认同的构建和民俗的传承进程中,以民俗传统本身为主线,记录和分析一个传统事项的传承与演变机制,以及该传统如何与其他传统互动而创造新传统。”其核心是“共享的民俗”,本质上是一个群体所共享的“实践的民俗”。[19]9-17所以面花所具有的文化认同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围绕它所构建起来的乡村文化文明体系,就是当下子洲淮宁河一带人们的日常,这也是乡风文明的一部分,即在继承和弘扬乡村原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以文化为主导的山美水美人更美的生态文明社会。
总之,由于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某种意义上,乡村社会也是维系和传承历史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本,而民俗文化则是乡村社会的核心文化,这就决定了乡风文明建设中以民俗文化铸魂的重要性。被列入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子洲面花以及与此相关的民俗,不仅折射了乡村文化和文明中蕴含的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也反映了自然经济生产状态下人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观念,更彰显了以子洲为代表的陕北人民在世世代代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乐观豁达的奋斗精神。当然,我们必须强调并指出,民俗固然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经验累积和文化传承,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民俗中仍然包含一些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糟粕性的内容,对此要持批判性态度,优良习俗要继承,陈规陋俗要扬弃,这既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要求,也理应属于乡村振兴战略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薛冬梅:女,43岁,子洲县老君殿镇人,高中文化,非遗代表,2020年10月10日访谈。
②阴阳相交思想观念来源:郑玄在解释《礼记·昏义》时云:“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阳往阴来之义。”(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6页)莲花鱼是艺术表达形式,其中“莲花”象征女子,属阴,“鱼儿”象征男子,属阳。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阴阳交感的哲学思想完全吻合。按照靳之林先生研究,他认为民间有许多这样的艺术作品都指向这一哲学基础,如“鱼戏莲”“老虎吃南瓜”“狮子滚绣球”“猴吃桃”“老鼠吃白菜”“金鸡探莲花”等。(靳之林《中国民间艺术的哲学基础》,《美术研究》,1988年第4期。)
③抓髻娃娃是陕北剪纸中最经典的艺术素材之一,造型多种多样。据靳之林先生考察,抓髻娃娃典型形象是头梳双髻(鸡),双手举鸡,肩上双鸡,襟上双鸡,膝上双鸡,脚上双鸡,浑身上下左右都是鸡。鸡属阳,抓髻娃娃象征阴阳相合的生命守护神和繁衍之神,寓意多子多孙、子孙绵延。他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学术界所谓生殖崇拜、巫术崇拜等说法,是对靳之林先生理论的进一步阐发。面花中抓髻娃娃的艺术塑造并不多见,子洲县在男女订婚时送抓髻娃娃,其文化内涵我们从剪纸艺术可以推断出二者具有相同的生育文化的哲学思想。而遍布全国各地的抓髻娃娃文化现象,诠释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已存在的重视生命、繁衍之神的哲学思想。(靳之林《中国民间艺术的哲学基础》,《美术研究》,1988年第4期。)
④苗得库:男,73岁,子洲县老君殿镇人,小学文化,非遗代表,2020年10月13日访谈。
⑤周彩英:女,50岁,子洲县周家俭人,初中文化,非遗代表,2020年10月12日访谈。
⑥加红高:男,81 岁,子洲县老君殿镇人,文盲,非遗代表,2020年10月13日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