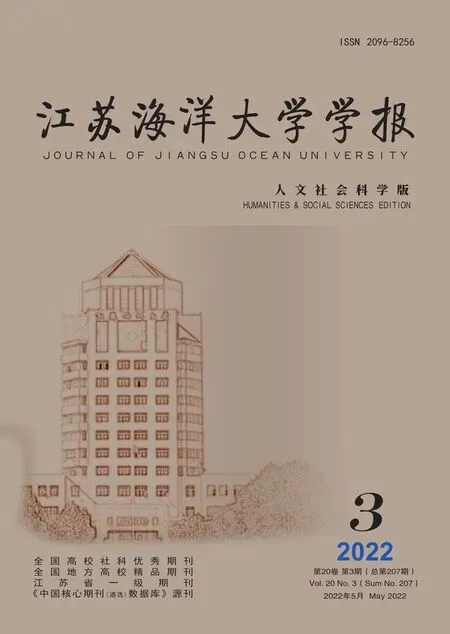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体理论研究*
2022-03-17马小茹马春茹
马小茹,马春茹
(1.宝鸡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2.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当前,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浪潮方兴未艾,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主体性强势嵌入,地球生命物种面临第六次大灭绝,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后人类时代。本文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立足西方哲学前沿“后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展开对后女性主义哲学家、后批判人文主义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1)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1954—),拥有意大利和奥地利双重国籍,索邦大学哲学博士,当代后人类批判学派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当代哲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欧洲女性研究的先驱。其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女性主义,著有《游牧主体》《后人类》《后人类知识》《游牧理论》《冲突的后人类》等多部后人类专著。从1988年开始任荷兰乌得勒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筹建乌得勒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后筹建荷兰妇女研究院,并担任首任主任(1995—2005),为推动欧洲妇女问题研究,先后建立两个欧洲大学校际网络机构,并担任主任(1994—2005,1997—2005)。的后人类主体思想的初步探究。
一、后人类理论研究的相关概述
“后人类”作为人文学科或者说跨学科的前沿性理论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学术关注焦点问题之一。而其作为哲学话题的提出,是以尼采发起“上帝已死”(2)关于“上帝已死”这一哲学命题,最初是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提出,而后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得到进一步的具体阐释。第一次是出现于该书第一部《查拉斯图拉之序篇》中:"上帝死了!上帝死了!我们杀了他!”该书第二部《慈善者》一节也出现了“上帝死了”。第三次出现“上帝死了”是在该书的第四部《退职者》一节中。具体参见: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m)宣言,到福柯“人已死”(主体的消失)(3)福柯在《词与物》文尾的最后一段阐释了“人将死去”的论断:“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人并不是已向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和最恒常的问题。让我们援引一个相对短暂的年代学和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我们就能确信:人是其中的一个近代构思。并不是在人和人的秘密周围,知识才在黑暗中游荡了好长时间。实际上,在影响物之知识及其秩序、影响有关同一性、差异性、特性、等值、词之知识的所有突变中——简言之,在相同(lemème)之深远的历史的所有插曲中——只有一个于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始而也许正趋于结束的突变,才让人这个形象显露出来。并且,这个显露并非一个古老的焦虑的释放,并不是向千年关切之明晰意识的过渡,并不是进入长期来停留在信念和哲学内的某物之客观性之中:它是知识之基本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诚如我们的思想之考古学所轻易地表明的,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假如,那些排列会像出现时那样消失,假如通过某个我们只能预感其可能性却不知其形式和希望的事件,那些排列翻倒了,就像18世纪末古典思想的基础所经历的那样——那么,人们就能恰当地打赌: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参见米歇尔·福柯.词与物[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以及福山宣布“人类历史的终结”为主要标志的,伴随后人文主义和后人类中心主义思潮而兴起的。
(一) 布拉伊多蒂后人类思想谱系简介
从国外学界对“后人类”问题研究态度来看,目前大致可以分为消极的、中性分析的、积极的三大态度类型:以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普遍道德层面的人文性后人文主义为代表的消极类型;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科学技术实证层面的科技后人文主义为代表的中性分析类型;以罗西· 布拉伊多蒂的批判后人文主义为代表的积极类型。其中,第一种“人文性后人类主义”,旨在重新思考人的本质, 这是自由主义者对后人类的回应性研究,是后人类主义发展的一种消极形式;第二种“主体性后人类主义”,试图解构传统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体,解除人文主义强加于主体的价值观束缚,这是后人类主义的分析形式;第三种“批判性后人类主义”,旨在构建一种新的伦理主体,履行后人类主义的批判形式。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体思想,正是在批判性吸收前两种后人类主义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
布拉伊多蒂作为批判后人类主义的主要代表,主要吸收批判后人类主义学派内部的最新思想研究成果:以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为代表的殖民主义理论;以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为代表的星际世界主义理论;以米斯(Maria Mies)和希瓦(Vandana Shiva)为代表的生态后人类主义理论。布拉伊多蒂后人类主体思想的谱系渊源包括:斯宾诺莎的欲望生成本体论;拉康对统一主体的精神分析解构;福柯的反人文主义、解构主体理论;德勒兹的生成性游牧思想;伊利格瑞的后女性主义反普遍主义论。
(二) 后人类理论研究现状
从广义来讲,“后人类”境况已经逐渐成为我们人类的共同现实,从学术研究来讲,“后人类”已经成为国际学术前沿主流话题。国内关于“后人类”主题研究不断升温,从知网大数据查阅来看,其中检索“后人类”主题词关涉篇目达到约3 000条,可以说“后人类”研究已经是显学。其中,卡里·伍尔夫(Cary Wolfe)的《什么是后人类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首次提出了“后人类主义”(4)参见WOLFE C. What Is Posthumanism?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这个术语;目前,后人类主义的理论研究主要以弗朗西斯·福山的《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5)参见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凯瑟琳·海勒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6)参见N.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以及罗西·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等为代表,它们分别代表了一种后人类主义文化理论。另外,还有唐娜·哈拉维的《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7)参见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是关于女性主义的赛博格(Cyborg)文化研究等。
可以说,在国际人文科学哲学领域,批判后人类主义的研究已经从多角度深入展开,布拉伊多蒂作为新生代批判后人类哲学、女性主义哲学领军性人物,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占据学界重要地位。其专著20多部,重要学术文章近上百篇,主要著作有《游牧主体》《后人类》《后人类知识》《游牧理论》《冲突的后人类》等,目前,她的主要著作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出版。总的来讲,国际上对批判后人类主义思想持多样性立场,既有肯定的观点也有否定的观点,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详细展开。根据相关文献数据库查阅调研,近期国内对后人类问题的关注不断深入,主要是围绕后人类主义文化理论探索,代表学者有王宁、蒋怡、李俐兴等;文学艺术领域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等后人类解读,代表学者有吴冠军和姜于辉等;还有就是对后人类主义的批评性回应,主要有刘悦笛、吴冠军、单小膳等学者。
对后人类哲学家布拉伊多蒂著作的引进及翻译,首先是由汪民安、张云鹏等组织主编人文科学译丛系列开始的,目前,国内唯一译者是宋根成博士,其中译本《后人类》一书已出版,另一本重要专著《游牧主体》尚未翻译出版。近期国内对布拉伊多蒂思想批评性解读文章主要有《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与技术后人类:两种后人类未来的文化讨论》,文章对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思想持批判性态度[1];《从“代理”到“替代”的技术与正在“过时”的人类?》[2],该篇文章对后人类的人的“过时性”做了深度关注和解释,涉及了包括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思想,尚未触及布拉伊多蒂的核心概念“后人类主体”的理论设计;还有两篇文章是对布拉伊多蒂的中国学生访谈录[3-4]。另外,从博硕学位论文研究选题看,国内对布拉伊多蒂批判后人文主义的研究,主要从文艺理论、科技哲学等交叉学科展开探讨。
综上所述,从相关国内研究动态分析来看,后人类这一话题的学术关注度在持续升温,但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需要学界投入更多的力量,值得持续深入研究。从哲学角度对布拉伊多蒂思想的研究分析看,目前,国内尚处在初级阶段,这正是本文选择“后人类主体”思想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布拉伊多蒂后人类问题的提出
随着后人类(Post-human)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生存际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选择,人类身份需要重新定位。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强势替代性介入生活世界,人沦为“过时的人”[2],所形成的人机关系需要理性应对;另一方面,现代主体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全面内嵌性介入,导致人类—非人类生命共同体系统生态失衡,面临物种灭绝的宿命。后人类主体理论的提出正是应对这一困境的积极方案。
布拉伊多蒂作为当代后人类哲学研究主将,着眼于后人类批判视野,立足现实问题,展开对人类当下处境的唯物主义思考。布拉伊多蒂继承德勒兹(Deleuze)的时间顺序重复视角[5]487-489,将当下一分为二:一方面,相对过去的已经发生的一切事实来讲,是即将终止的已经消失的“不在场”的存在和即将过去的不再发生的事物存在状态;另一方面,从趋向未来的当下来看,则是我们将要成为什么、生成什么、我们能够有什么作为。布拉伊多蒂选择了新的哲学行动:我们既不能悄无声息地随着时间洪流被任意裹挟,也不能一味消极意义上地批判诅咒已经发生的一切,从而趋向虚无主义,让事情更糟糕;我们必须面向当下的未来性,选择新的可能性行动入口,以一种积极的伦理态度发挥哲学批判性治疗功能。
“后人类”概念,是在批判人文主义,承接后结构主义反人文主义传统基础上提出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操控系统中,人文主义已经走向反动,其多层级的中心主义霸权范式历历在目,“历史上的人文主义发展成一个文明化模式,该模式将欧洲的概念塑造成自我反思理性的普遍化力量。人文主义理念演变成为一个霸权主义文化模式,并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推崇。这个自我强化的愿景认为,欧洲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定位,还是一个可将自己的品质给予任何一个合适对象的人类”[6]19。而反人文主义正是为了克服这种抽象的普遍性霸权,提出将人的主体性同这个普遍论的姿态相脱离,要求主体履行职责,即开展主体自己正在制定的具体行动。
布拉伊多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明确提出了她的后人类概念。布拉伊多蒂指出:“所谓后人类,我指的是我们人类现实处境的一个历史性标志和一种理论轮廓(theoretical figuration)。‘后人类’,与其说是对未来的一种反乌托邦视角(dystopian vision),不如说是我们历史背景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在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它是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和后人类中心主义(post-anthropocentrism)的集合。”[7]29也就是说,“后人类”作为一个既成事实的历史标志,就是一个“事件”——它宣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终结,而“事件”的终结,同时就意味着新的“事件”的可能性开端及理论的前瞻性设计。而且,“后人类”概念作为一种理论视角,也是一种伦理分析方法,即打破“原子式的人类”思维模式,采用极具包纳性的整体性“集合”思维方式。后人类集合(convergence),也是一种分析工具,用于理解我们目前参与的情动(affective)、社会和认知过程的基础、视角和责任性质,以及非人类代理(non-human agents)在共同生产它们中的作用[7]66-67。
“后人类”概念的提出,开启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视野,具有一种切换了“人类中心”的后人文关怀情结,尝试一种积极的“换位”式主体重建。正如布拉伊多蒂所言,“我们需要换一种方式看待自己。我把后人类困境视为一个机遇,借以推动对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自我表现的新形式的探寻,开拓一种新的可能性。后人类境况会敦促我们在生成的过程中批判地、创造性地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具体能做什么”[6]17。后人类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新的观念变革的到来,在这里布拉伊多蒂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引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三、布拉伊多蒂后人类主体理论的设计框架
当前,在后人类研究中,主体性在后人类困境中的定位很不恰当,我们需要一个与时代相称的主体性地位。学术界一方面对主体性理论的必要性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将主体性重新纳入人文主义传统,尽管有一些修改和修正。因此,后人类主体概念的提出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布拉伊多蒂抓住了自现代伊始构建的理性主体话语的消解命理,从积极肯定的后人类伦理方向,形构新的行动主体范式构想[1]。后人类转向,同时也是一个让人性重新以肯定方式更新自我的机会,我们需要为主体设计出社会的、伦理的和话语的新方案,以适应当下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布拉伊多蒂在哲学层面的后人类主体理论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超越人文主义的后人类中心主义视野下的问题范式
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体理论设计,首先从“后人类”的问题范式出发,提出必须超越人文主义倡导下的人类主体范式,走向后人类时代,后人类时代的人类文明不应该被人类——更不要说“男人”(Man)——作为其适当的研究对象所限制。相反,该领域将受益于摆脱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人”的帝国,从而能够以一种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来处理外部乃至全球的重要问题。后人类中心主义所要面对的问题主要指:“包括与有机和无机非人类他者的关系,科学和技术逻辑的进步,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和多元全球化的挑战,包括贫穷和结构性不公正。”[8]23
(二) 后人类主体理论是一种概念创造的多面相敞开活动
布拉伊多蒂提出,我们需要的是构建后人类理论,应该少一些抱怨,多一些概念性创造行动(conceptual creativity)。如果完全放弃主体性的实践,我们甚至不可能为这些翻转的情状(shifting conditions)绘制出足够的地图,更不用说开始为它们勾画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为后人类时代重新塑造(re-cast)伦理和政治主体性”[7]102-103。而且,这是一个有待完善的多面相敞开过程,它们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和创造性的工程(project)出现在后人类集合中,沿着后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拷问轴心(axes of interrogation)展开。后人类主体质问“我们”从过去继承来的、关于自我再现和人类传统理解获得的一切,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后人类主体理论探索了作为集体的“我们”的多面性和差异性本质。
(三) 后人类主体理论宗旨是再创造人的存在新可能
后人类主体理论在后人类处境中,对人类的处理不是一种泛人类(pan-human)倾向,而是对人的重建,或者说是对人在后人类时代的重新定位和安置,属于唯物主义式的扎根。布拉伊多蒂强调,为了这一新的主体概念与对后人类主体性的肯定工程(affirmative project)保持一致,主张一种不同的内在政治(politics of immanence)。我们不能逃到某种脆弱的泛人性(vulnerable pan-humanity)中去,而应当在当前混乱的矛盾中重新扎根(re-grounding),这是一种内在的、又是流动的重新扎根。这一立场是“唯物主义的内在性(materialist immanence)。而且,人类的后人类境况(the posthuman condition)远非标志着对人类的排斥、灭绝或贫困,而是一种重建人类的方式(reconstituting the human)”[7]111-112。
(四) 后人类主体理论构建的复调路径
后人类主体理论范式下对人及其主体性的重建,不是遵循“铁板一块”普遍必然性的线性方式,而是开拓复调路径,其中充满张力,呈现多种可能性。人类的这种再生(regeneration)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处于特定位置上的(situated)、透视主义的(perspectivis),因此具有内在断裂性和潜在的对抗性(antagonistic)。对一些人来说,它成为一种超人类提升(trans-human enhancement)的形式,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以盖亚(Gaia-oriented)为导向的收敛(down-sizing)人类傲慢的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需要某种对与其他人类团结一致必要性意义的认知,同时,也需要对非人类的拥抱。这一范围的选择表明,在这种后人类集合体中,存在着对人的重新定义和后人类主体形式形成的诸多动力因素[7]112。
(五) 后人类主体理论的批判维度
一方面,应对后人类困境需要后人类主体性知识,同时,对这种后人类主体性认知的获得,并不是主体的主观预设、形而上的真理性理念,它既面临着后人类理论谱系的质疑,也有因自身的不稳定性而内生的内在异质性抗力,也必然是一种批判性建设过程,这也就决定了理论发展的冒险性探索性维度[1]。“后人类时代召唤并且以后人类时代的知识主体为支撑,而后人类时代的知识主体是由一系列令人精疲力竭的矛盾和悖论构成的。它们产生了新的社会想象和社会关系最好的例子,就是跨学科后人类知识的动态领域,我称之为批判后人类。它们给了我对未来的希望。”[7]113-114而且,后人类主体的的批判立场,不是传统那种否定的后结构主义人文的解构性批判思路,而是以一种肯定的实践方式展开。后人类主体性的当代实践,致力于以更加肯定的方式来研究批评理论。超越了自我的统一视阈和主体形构过程的技术条件,后人类思维可以帮助当代主体努力去适应正在改变的世界,并对其作出积极的改变[6]284。
四、布拉伊多蒂后人类主体概念的解读
从对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后人类知识》《后人类状况》等文本的梳理来看,后人类主体作为一种新的多维关系生成性集合体概念,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和非生命的多重组合,没有固定的中心,呈现出去中心化的开放态势,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经验事实的理论概括和哲学描述,以及新的理性判断方法视角。它不是反人文主义的,也不是非人文关怀,而是在旧的传统人文主义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拓展和延伸。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体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后人类主体动态生成我们的“一”的集合体
布拉伊多蒂反复强调,“我们此时此地全部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不是一体的也不是相同的”。这里的“一”,必须是超越并突破人文主义的以人为本的传统框架,走向依据并包纳多样性非人类事物,以及作为生存载体的地球生命系统整体。并且,“通过‘后人类化(posthumanizing)’的主体性,它可以重新定位为一种跨后人类主义(trans-posthumanism)和后人类中心主义(post-anthropocentrism)矛盾的动力集合现象”[7]117-119。重建“我们”的聚合性情动集合体,旨在强调基础的、定位的和透视的维度,由伦理愿望来提升组成一个假定(missing)的人,一种横向主体组合的组成——我们的“一”,这是对我们的集合体潜力的实现(actualize)。
(二) 后人类主体是整合实体事物能量基础上的结构关系动力模式
构成主体性的是一种结构关系能力(a structural relational capacity),同时结合了任何一个实体被赋予的特定程度的力量或权力[7]120。它们向他者延伸和接近甚至成为他者的能力,它们构成了一个无中心化主体和无它自身的知识树根的主体。没有树状的主体(No arborescent subjects),只是根茎状的游牧主体。肉体(Bodies)是具身性和内在性的(embedded and embodied),具有关联性情动能力(relational and affective powers)。由此,它们能够以不同的速度生成不同的事物。这种游牧形式就是一种政治上抵制霸权、抵制排他性的主体性视野[9]23-24。
(三) 后人类主体是以“普遍生命力”为核心原则的多维关联体
后人类主体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建立关系:与自己(to one’s self)、与他者(to others)及与世界(to the world)建立关系。在所有这些因素的累积效应的培育下,它变成了一个被扩展的关系型自我。“后人类主体的关系能力并不局限我们人类,而是包括所有非拟人化的元素。生命物质——包括肉体——是智慧和自组织的,但又非常精确,原因是它无法割断同其他有机生命的联系。”[6]86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原则,是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的核心,它是对作为发达资本主义逻辑,即生命的机会主义跨物种商品化的一个唯物主义的、世俗的、负责的和非感性的回应[6]285。
(四) 后人类主体是外在呈现性和内嵌入式的横截贯通体
后人类主体,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自治的,是由关系伦理激活的内嵌具身性、关联性情动协作的实体。它“是一种横向联盟(transversal alliance),涉及非人类代理者(non-human agents)。这意味着后人类主体同时与地球有关——陆地、水、植物、动物、细菌——以及技术媒介代理(technological agents)——塑料(plastic)、电线(wires)、电池(cells)、代码(codes)、算法(algorithms)”[7]130。经常呈现为网络状的关联形态,而不再是二分对立的存在。
(五) 后人类主体是唯物主义一元体
后人类主体内在性与差异唯物主义(Immanence and Differential Materialism)是一致的,是一个内在的、后人类理论规划前提,即假设所有的物质或实体都是一体的,并且是内在于它自身。“人们总是迷失和虚幻的(missing and virtual),因此,它需要被现实化和组装(actualized and assembled)。它是实践的产物,是生产不同组合的集体参与的结果。我们不是铁板一块(We are not one and the same),但我们可以一起相互影响。”[7]143
(六) 后人类主体是去人的个体性的个体化过程
所谓的个体性,只是后人类主体的内嵌式的关联性影响的结果,不存在具有人的个性的个体性人。当后人类主体个体化时,他们将被具身化并嵌入到实现的过程中。这样的过程只能通过自然、社会、政治和生理关系的网络发生。“我们可以谈论在主体之上、之下和旁边的力量,以一种持续的相互叠加的流动(in a constant flow of mutual imbrication)。在主体‘上面’指向了制度和社会权力的超主体面孔(supra-subjective)。在‘下面’,主体操纵着次主体性的和情动的因素,包括奇异的精神景观(singular psychic landscapes),与之‘伴随’的那些主体是后人类关系的辅助生物技术组合(Protevi 2009)。”[7]147
五、布拉伊多蒂后人类主体的基本特征
(一) 实践层面:内在创造性生成唯物性
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体作为一个行动者,首先是以新的唯物主义过程本体论为基础(a materialist process ontology)。从实践层面来讲,后人类主体第一个特征就概括为一种虚拟现实化的创造性实践(a creative praxis of actualization of the virtual),而活力唯物主义即为后人类主体理论的出发点,“我认为后人类境况的公分母就是承认生命物质本身是有活力的,自创性的而又非实体的结构。自然—文化的这种连续统一性是我研究后人类理论的出发点”[6]3。这种连续观与一元论哲学观密切相关,反对二元论,强调生命物质系统的自组织、自创生力量,以及生命物质的本体性能量。同时,反对“特殊生命力”原则,尤其是人类或人种至上的等级性秩序。布拉伊多蒂最具有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遵循“普遍生命力平等原则”,与佛教的“众生平等”、儒家的“民胞物与”、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普遍生命力是延伸到生命之外的非人性力量,将死亡当作一种非个人事件进行研究的活力论方法。以生命为中心的过程本体论引领着后人类主体以清晰的方式面对这个定位,不用在道德恐慌或忧郁面前退缩。”[6]285当今世界是更加系统化、生态智性化的令人骄傲的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世界。
(二) 结构层面:外表现与内嵌性的关系本体论关联性
从结构分析,后人类主体性是由本体论关系构成的,这种关系是影响和被影响(the power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的力量。“后人类主体是生成的连续性浪潮的表现,由作为本体论的普遍生命力来驱动。该连续统一体既非属人,又非属神,而是无情的属物,致力于多个方向的,跨物种的关系性。”[6]202活力论唯物主义是生成过程论,而且这种生成并不是主体的一种理性设定,而是不确定的可能性。生命一定要继续,因为非情感的非人类的生命活动激活了它。生成的不可感知性标志着被缚的自我的疏散点或幻灭点,它们融入背景,融入中间地带,进入地球自身的激进内在性和它的宇宙共振中。“生成不可感知是个无法表征的事件,因为它依赖于个体,依赖于个体化自我的消失。”[6]202
(三) 批判层面:解域化非统一的游牧主体
后人类主体概念在批判层面呈现的特征为,指向解域化的非人类主体的游牧性存在。是批判地扬弃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更加尊重非人类因素的力量。“后人类批评理论释放普遍生命力的多元动力,这些多元动力与人类之间不存在巧合之处,更不必说和意识之间存在巧合。这些非本质主义的活力论的烙印塑造了后人类主体。”[6]204后人类主体的批判功能指向非统一的游牧性。后人类主体是建立在生成伦理学基础上的,支持复杂性、推动激进游牧特质,这种后人类主体最基本的表征形式就是“游牧主体”(8)所谓“游牧主体”,在布拉伊多蒂这里并不是一种无家可归、居无定所的流浪者、难民,而是指那种精神思想层面放弃所有固定“执念”(观念、欲望、怀旧)的人。这种游牧主体形象关键在于凸显主体精神能量的充盈流动越界状态,否定本质性实体主体的传统观点,重心相应地从统一主体性转换到游牧主体性,因而与高度人文主义和其当代变体格格不入。参见BRAIDOTT R. Nomadic Subject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作为后人类主体的游牧性呈现出哲学意义上的非统一性。“非统一性主体的后人类伦理学通过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障碍,提出一个更大意义上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包括非人类或‘地球’他者。”[6]72这种游牧的非统一性主体的意义功能,在于将生命概念朝着非人类或者普遍生命力的方向扩展。
然而,游牧主体并不是完全没有统一性,他/她的游牧模式是一种明确的、季节性的运动模式,通过相当固定的路线。它是一种由重复( repetitions)、周期性的运动(cyclical moves)、有节奏的位移(rhythmical displacement)而产生的聚合性主体样式。布拉伊多蒂将游牧主体看作是“男人/女人观念”的原型,这一后人类主体的政治本体论依据就是德勒兹的“块茎理论(rhizome)”,这种游牧形式就是一种政治上抵制霸权、抵制排他性的主体性视野[9]23-24。
(四) 生态层面:非人类横断贯通生成性
后人类主体在生态层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非人类贯通性生成,其横向主体性(transversal subjectivities)主要是以包括非人类行为者在内的生态—哲学组合模式(eco-sophical assemblages),从而构成横向连接的主体性深层生态组合。生成后人类最终是个重新界定的过程,界定自己同人人共有的世界以及一个领域空间之间的依恋感和联系感。这个空间可能包括都市、社会、心理、生态以及星球。生成后人类体现了多重的归属生态模型,同时,为了认识我们仍然可以称为“自我”的集体本质和向外求索的方向,它制定了我们的感知坐标。这实际是个位于一个共同生命空间内的可移动的聚焦点,这个空间没有人可以掌控、占有,仅仅只能居住、暂留,永远处于一个社区,一个群体,一个团队,或一撮人之中[6]284。对于后人类理论,主体是个横断的实体,始终潜藏于并存活于一个非人类(动物植物和病毒)的网络关系中。“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具身化主体掺杂着大气污染/病毒性的关系链接,这些链接彼此同各种各样的他者联系起来,从环境或者生态他者开始,并将技术设施包括在内。”[6]285
(五) 伦理层面:重建“我们”的聚合性情动集合体
后人类主体理论的提出,就是源于一种深度的伦理关怀使命,因此,要担当起重建我们的“一”的集合体的责任,必须同时强调后人类主体构建的伦理维度。在伦理层面,假设一个类似虚拟实体的人,即作为横向主体组合的组成“我们”的“后人类主体”,从而能够实现了(actualize)“我们”能够成为的未实现的或虚拟的潜力(that actualize the unrealized or virtual potential of what ‘we’ are capable of becoming)。它是集体管理社会变革进程的秘方,通过减缓加速(de-acceleration)和共同构建社会希望的视野发挥作用。
在此,普遍生命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边缘化的无权无势的弱者,我们必须与那些被剥夺权利和被剥夺权力的人在一起(除了他们中的许多既不是人类也不是拟人化人类,neither human nor anthropomorphic),这使得批判性思考者有必要开发新的系谱,发展出替补理论和新的合法性,表征我们正在努力思考探寻的新道路的新关联体系[8]33。
六、结语
总而言之,后人类主体概念并不属于后现代的,其构设依据不依赖于反基础主义的前提;它也不是后结构主义式的,不是依靠语言转向或者其他解构形式来发挥功能,因为它不是由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构建而成的。所以说,后人类主体并不一定要在一个本质上无力得到应有重视的体系中寻找自我存在的充分表征,它呈现为动态的可能性样式,是在动态场域诸多元素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中呈现的主体。后人类主体是在生成的连续性浪潮中呈现,由作为本体论的普遍生命力来驱动。
后人类主体理论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既是在后人类批判理论框架下走出后人类困境的新的理论设计,也是对现代伊始主体性问题的理论超越和重建。同时,后人类主体理论对我们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全球生命共同体三位一体的时代课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参照价值。不过后人类主体理论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就理论层面来说,有待修补后人类学派之间的裂缝,尤其是与技术后人类的差异分歧,以及协调和解是未来理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1],而且,就布拉伊多蒂对后人类主体理论的构建本身而言,也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创造性过程;就现实层面来说,面临超越“资本”系统的掌控从而难以实现,有可能沦为乌托邦式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