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灯
2022-03-15>>>大明
>>>大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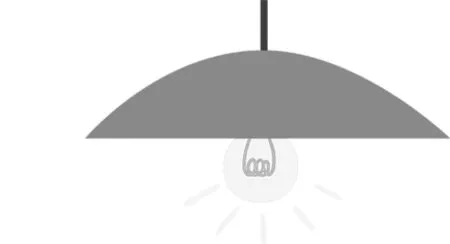
那年,我住在粮食局家属楼。因为在一所寄宿制中学担任班主任,每天晚上十点才能回到家。因是旧楼,院落极其狭窄且没有路灯,进院时免不了磕磕碰碰或碰倒那些摆放并不齐整的自行车、摩托车。
某一夜,我小心地推车进了院子,却发现院子里一楼一户的窗户里挂着一盏瓦数不高的灯泡。灯泡委屈地夹在玻璃和窗帘之间,透明的玻璃和遮光的花色窗帘一样清晰。很明显,窗里面的人已经睡了,灯泡照的是深夜才回家的人。
点灯的这一户住着老两口,八十多岁了,我们叫他们爷爷奶奶。爷爷行动不便,住在阳面的客厅里,而挂灯的这间则是奶奶的卧室。
老两口十分热情。我有时带女儿在楼下玩,会让孩子站在他们家前面的露台上,我与爷爷奶奶闲聊。爷爷腿脚不好,脾气也不好,但双手却是灵活的、柔顺的,甚至会拿着很粗的竹针编织看起来文艺范儿十足的毛衣。这时,奶奶会讲很久以前的趣事和刚刚发生的琐事。
我曾问奶奶,灯开着怎么睡得着?
奶奶说,睡着了,就不怕开着灯了。
我说,开灯是要花电费的。奶奶却不在乎地说,一度电的电费还买不了一根萝卜呢。
那盏灯一到晚上就亮了,直到天亮。几年后,我调动到公安机关工作,也搬了家。一个夏季的夜晚,我和女儿去广场散步,路上经过一个派出所。派出所独门独院,两层楼,像卧虎般守在那儿,几乎所有的房间都开着灯。灯光极其明亮,倒像是整栋楼会发光。
从楼外我能看到有的房间忙碌的身影影影绰绰,有的房间却只有光,没有人,像是多事的人用光糊住了窗。
我能感受到灯光是热的,即使在这个尤为炎热的时节。灯光煮沸了我对同事们的一切想象。灯亮,警察就在。灯是警察与群众对视的眼睛。
我忽然想起了住在旧楼的那位奶奶,都是点灯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人和一群人。
派出所的灯是使人心安的灯,所有路过的人应该都是这样想的吧。夜里的躁动只能匍匐在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
奶奶的灯,我懂。派出所的灯,担心遇到伤害的人也懂。
五年后,我到离家一百公里的森林公安分局任职。每次出警时我都会把警灯打开,即使是白天,穿过辖区内零星的村庄和空旷的山路,也闪烁着红蓝警灯。刚入职的辅警小李曾问过我,这给谁看呀?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谁会看到。
一日,一村民来分局报警。是一起林权纠纷:两家人因为一棵核桃树已经闹腾了数年,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
对这次调解结果,我没有多少信心。因为以前调解过,但谁也不让谁,我们更说服不了谁。这次却有些意外,报警人主动做出了让步,两家很快就签了调解协议。
谁知签了调解协议的第二天,报警人又来了。我大感头疼,以为他反悔了。报警人却跟我说,为求心安,要说清楚。
他说:就在调解前几天,他拿着一把锯子去了地里,准备锯倒那棵核桃树,并计划从摩托车里抽出一瓶汽油,点了对方的玉米仓。他已经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事发之后会拿着斧头,等着对方来报复。不过,那天恰好看见我们开着警车闪着警灯路过,他就有些出神,甚至联想到出事后警车开进家里,前来抓捕自己的场面。他坐在核桃树下想了好久,决定让步。
报警人说,警灯能刺得人眼睛疼,但脑袋会清醒。
原来,我无意之中也点了一盏灯。我突然想去看奶奶,把这件事讲给她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