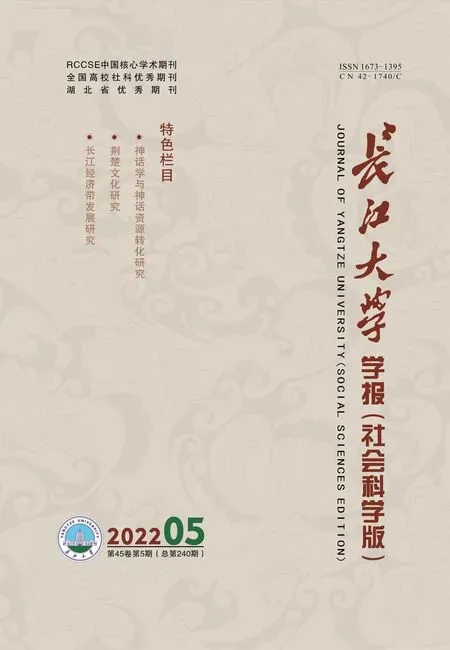巫风·楚雨·离忧
——屈原《九歌·山鬼》多主题导读
2022-03-15夏菁
夏菁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两千多年前,屈原创制了一种充盈着楚地山川风物与方言民俗的新诗体,成为中国古典诗歌“风骚”并举的重要一脉,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骚体诗”,自汉代始称之为“楚辞”。西汉人刘向编辑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以屈原作品为主,屈原的组诗《九歌》延续并发展了其在《离骚》中的瑰丽想象和魔幻表达,成为浪漫主义风格的另一典范。《九歌》在成为经典的同时,因创作年代久远,作者生平记载稀少,所叙之事为神鬼祭祀,历代以来,遭受了很多争议和质疑,阅读难度较大。东汉王逸说《九歌》“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1](P55)。这里的“不同”“异义”又以其中第九篇《山鬼》为最。
《九歌》这组诗是作者的原创还是改编,主题是自我寄托还是祈雨迎神抑或是人神之恋?《山鬼》的山是何处的山,山鬼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是神还是人,是鬼还是兽,是屈原自喻还是描写的野人?历代学者各持其据,论述纷呈,笔者从主题入手,对此展开分析。
—、《九歌·山鬼》形象主旨研究回顾
(一)重在自我感情的寄托
最早编辑研究楚辞的专家是东汉时期的王逸。他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对屈原创作包括《山鬼》在内的《九歌》组诗,有如下表述: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1](P55)
王逸的这段话是作者创作论。理由有二:一是作者在放逐途中,经常目睹沅、湘流域信鬼好祠、歌舞乐神的民风民俗,新奇之余,感觉其歌舞文辞浅陋粗俗,有必要为之匹配更雅正的文辞;二是作者两次放逐,内心极度幽怨苦结,那些无处言说、也不能自由言说的忠君爱国之情、兴邦美政之志,恰好可借参与宗教祭祀活动来表达。寄托或讽喻说法得以立足并传世,关键在于王逸对作者创作动机的揣摩与思考,此说以屈原的身世经历,特别是两次放逐、去国远君、有理想而不得实现的离忧之苦为依据,论证充分。
(二)对神鬼祭祀的记录与改编
宋代的洪兴祖、朱熹,清代的王夫之、林云铭等,都认为《九歌》是屈原对神鬼祭祀的记录与改编。洪兴祖说“杳冥冥兮羌昼晦”一句是“此喻小人之蔽贤也”,诗中的“灵修,谓怀王也”,还说“屈原陈己之志于山鬼也”。[2](P78,79)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在认可寄托主题说的同时,偏重考据,似乎又花了不少气力在求证这组诗歌是在写神鬼,而非君臣。
张元勋作“山鬼辨”时引用王夫之《楚辞通释》注 “旧说以为夔、枭阳之类,是也。……今楚人有所谓魈者,抑谓之五显神,巫者缘饰多端,盖其沿久矣。”[3](P182)从王夫之对山鬼概念的诠释看,山鬼或为独脚怪兽“夔”,或为食人野物“枭阳”,都属魑魅魍魉之类,而屈原描绘的山鬼形态状貌绚丽多姿,心性举止温柔缠绵,具有典型的屈氏浪漫主义风格,极大的认知差异可证明是作者屈原加工改造的结果,南宋朱熹也有屈原“更定其词”[4](P24)的说法。中国古代的神话都是口口相传,集体创作,其文字记载常常散见于其他典籍之中,所以其形象主旨在传播中往往多有改变。如今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祭祖时,还有跳“毛古斯舞”,唱“傩戏”的习俗。它们演绎神话故事,模仿生活场景,美化祭祀活动。此中的同一角色同一事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或许都有自己不同的样式。
时至现当代,苏雪林在《屈原与九歌》中转述胡适《读楚辞》中的观点,即“《九歌》当是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传统的屈原毫无干涉”[5](P150)。国光红在《九歌考释》中认为:《山鬼》描述的角色是两个,一个是祈雨的女巫,一个是雨师。《山鬼》为“楚国舞雩巫歌,所降神为雨神,山鬼即为祈雨女巫”[6](P225~232)。国光红提出这种观点的重要证据是:赤豹和文狸身上的花纹恰似云、雷形状,所以是雨师。但仅凭此一点,显然缺乏说服力。同样持有“祈雨”说法的还有陈咏,他在《屈原的九歌与祷雨的关系》一文中阐述了《山鬼》篇中的“神灵雨”就是“神降雨也”的说法。[7](P67~68)曹胜高则结合西周至秦时期南方地域先民们“祈雨于山川”的习俗,认为《山鬼》祭义是描写楚怀王祈雨于山川的过程,先是迎神祈雨,再是娱神降雨,最后是送神谢雨。[8](P50~56)
(三)写山神的追逐或人神之恋
清人顾成天在《楚辞九歌解》中提出“山鬼”即“巫山神女”的说法,今人郭沫若从原诗句“采三秀兮於山间”考证出“於山”即“巫山”的观点,孙作云在他的《九歌山鬼考》里对“山鬼之山,即巫山,山鬼之鬼即巫山神女”的论证更为详细。[9]他们认为《山鬼》写的就是巫山女神,表现美丽痴情的少女为爱恋而忧伤的故事,或为不遇,或为背弃,或为得而复失。后世赞同并跟进此类说法者很多,影响力也较大。苏雪林在《屈赋论丛》中将山鬼形象解读为“至于山鬼大约是一种山神。楚国多山,祀祭山神,原情理中事。这种山神的祭典流传至后汉还未断绝”[10](P95),甚至依据《山鬼》中女主的穿戴装扮有“薜荔”“女萝”,犹如酒神身上缠绕的葡萄藤和常春藤,便得出山鬼与古希腊神话里的酒神关联密切,“《山鬼》歌主是个美少年,即是酒神”[5](P495)。此说法在人物的时空交集上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所以接受的人极少。
至于现在不少研究者乐于接受《山鬼》是为神鬼或神人的恋情主题,或许就在于它能最大可能地满足现代各层次读者对古籍经典阅读的期待与接受,也更接近现实生活的自然状态。源于西方的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研究可“以读者为研究中心,通过考察文学的接受和产生效果的过程来揭示文学的本质和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山鬼》是作者的,也是读者的和文本的。“作品的潜能和价值只有在读者的接受活动中才逐步得到实现。”[11](P309~310)
站在多元的立场,《山鬼》的主题是表现了作者的自我遭遇,还是宗教祭祀,抑或再现了想象中的上古社会呢?在笔者看来,《山鬼》似一面多棱镜,它透射出上古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化纵深层次的心理情感。那些高山深壑之惊险神秘,巫风楚雨之气韵萦绕,伴随着青春女巫的祭祀祈祷,更寄托着一段曲折哀婉的恋情,叙说着楚民对美好生活企盼的愿景。以下从文本阅读入手,来进行探讨。
二、《山鬼》是一部多主题杰作
(一)视角与人称的转换,生发出多主题思考
这里说的视角指的是讲述者与其所披露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山鬼》的叙事视角有时是观者的,有时是巫师的,有时又是作者的。有时观者就是作者,有时作者又化成巫师。它们始终处在变换中,甚至相互叠加渗透。时而我、你、他,时而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他。在《山鬼》诗中,视角与人称时而一致,时而又各有不同。视角或人称何以如此变换,不同人称叙事代表着什么身份,表达着怎样的情感?厘清它们的过程就是生发多重主题思考的过程。
譬如《山鬼》首句“若有人兮山之阿”,就是全知视角,以第三人称开始整场祭祀活动的记录。第三人称视角又叫全知视角,以他者身份冷静客观地介绍故事的发生。它的优点是自由灵活,不受时空限制,反映生活面广,能够增强文章的全方位感。“若”是“好像”之意,是他者进入了观察。“有人”是他者观察的结果,此处指巫师。接下来的两句“被薜荔兮带女罗”“乘赤豹兮从文狸”,主语是承前省略的“若有人”,还是第三人称视角,他者继续进行着对巫师装扮、坐驾、随从的介绍。这种全知视角有利于读者对人物和事件进行全面具体的了解。在他者眼里,这是祭祀仪式的写实,时间、空间不受限制,如现代科技的航拍加跟拍,强调的是全方位感,360度无死角。开篇8句主要运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介绍山鬼的住处、行迹、漂亮的配饰妆扮以及娇好的仪容情态,描写所乘车辆的装备豪华、随从威仪,举止神情淡定自信,这是祭祀主持者巫师对神的模拟与想象,读者仿佛被逐渐引领进祭祀现场,身临其境,逐渐生发出巫师准备迎神的祭祀主题思考。
其中第四句“子慕予兮善窈窕”句,是一个叙事切换,将全知视角转换为有限视角,即以第一人称“我”或第二人称“你”来讲述故事。第一人称视角又叫有限视角,第一人称叙述有真实、亲切、自然的优点,这种叙事在表达情感,特别是人物的内心情感时,细腻真切,容易让读者接受。“子慕予”的大白话就是“你爱我”,是第二人称叙述,是山鬼的自言自语,此话语隐含的信息量就是山鬼的自信与自豪。这里的写喜,为后面的述悲做了铺垫。随后四句又转到全知视角,让观者回到现场,客观展示祭祀主持场景。自第九句始至最后八句止,则再转为有限视角,以第一人称叙事,其中有许多地方用到了“予”或“余”或“我”,有些句子还有强烈的“对话”味道,戏剧性强,矛盾冲突激烈。譬如:“留灵修兮憺忘归”“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君思我兮然疑作”等等。
当有限视角即第一人称“我”转换到祭祀主角巫师身份时,“灵修”“公子”“君”都可以理解为第二人称“你”,即巫师心中的“所思”——本次祭祀的神灵。这种转换主要还是为了增强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它具有透视的特点,以呼告手法展示一种面对面诉说的效果。人称的变化带来叙事视角的变化,阅读情绪的变化也更丰富,故事情节的变化更曲折,人物形象也更生动、更圆满。于是,这里的“我”(主持祭祀的巫师),在演绎对所迎之神的追逐中,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快乐与忧伤。于是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便成了楚地民间歌舞演出的盛事。百姓在表达对神灵先祖崇敬膜拜的同时,也在表现自己生活的哀乐愁喜,这与如今仍在沅湘大地流传的古老的傩戏有些相似。
倘若叙事人被代入角色,巫师的身份就会幻化成作者的身份。譬如“山中人兮杜芳若”句,洪兴祖认可王逸的说法:“山中人,屈原自谓也。”[1](P81)这是有依据的。屈原在《涉江》中说自己“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山林”[12](P145),是“幽独处乎山中”[12](P147)。《山鬼》中巫师的妆扮、神情和表演,引发了屈原20多年行走于楚地山野林间的千头万绪。巫师对心中所属的执念,变换成作者屈原对心中美好的渴求。这美好当是庙堂中的君王信任,是政治理想“美政”的得以实施。
是故,叙事视角的转换,增加了人物的代入感,强化了叙事的抒情性,揭示了角色的心理活动。在阅读时注意人称的变化,可以生发出多主题思考。
(二)场景与情节推进中的多主题状态
《山鬼》全诗27句,每4句一节,共为7节(第6节只有3句,疑有脱落)。将前4节一分为二,加上最后3节,诗歌分三部分展示出一场完整的祭祀活动,或是一个曲折动人的“不遇”故事。它们分别处于三个主要生活场景:山凹,山巅,山中,对应情节发展的三个阶段与叙事的三层题旨:兴高采烈地从山凹出发(故事的发生)——执着痴迷地登上山巅寻找(故事的发展)——在山中踟躇,久候不得的哀伤(故事的高潮、结局)。
《山鬼》的故事从巫师精心装扮、兴高采烈、隆重出行开始:“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巫师从蜿蜒低矮的山凹飘飘忽忽、若隐若现地走来,极尽山中之美妆扮着自己,极尽山中之威加持着自己,还揣上了一大捧“芳馨”,准备迎接心中的“所思”。钱钟书说巫者“一身二任”[13](P156),在祭祀仪式中,巫是以有形之身事无形之神者。巫师将自己妆扮得越接近神的模样,越容易与神合为一体。巫师的职责就是时而扮演巫的角色主持着祭祀的仪式,期盼着神的到来,时而扮演神已依附于身,与神合体,代神立言。读者明白了这一点,《山鬼》诗在第一部分,即清晰地呈现出了“迎神”的主题。
到了约定的地点,不见“所思”,巫居高临下地察看,“表独立兮山之上”,结果是“云容容兮而在下”,什么也看不见。此时场景已从出发时的山凹推进至高高的山顶,场景出现了变化,情节出现波澜,人物心理情绪也出现了变化。与“所思”约而不见,候而不得,是因“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还是“路险难兮独后来”?一边焦虑,一边体谅,一边解释,是迎神难?还是成事难?容易入戏的读者往往会跳脱出来思考,随着情节场景的推进,增添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情绪感受。“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洪兴祖认可王逸的说辞:“以言东风飘然而起,则神灵应之而雨。以言阴阳通感,风雨相和。屈原自伤独无和也。”[1](P80)
当情节继续发展,人物活动场景由山巅转至山中,“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此时山中之路已十分难行,乱石塞道,藤葛羁绊。这样的场景是现实生活中楚地自然山形地貌的真实状态。“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君思我兮然疑作”,这些幽怨、推测、猜想是现实生活中失意之人的正常情绪。情节推进至此,与其说它呈现的主题是巫师在迎神,还不如说它写的就是生活中普通老百姓的坎坷、艰难和不如意。若再与作者屈原的生平遭遇联系起来,人物深陷于执着寻找与内心反复纠结,这种执着与纠结,将故事情节推向高潮。
倘若说《山鬼》的第一部分很魔幻,第二部分很神奇,那第三部分就很写实了。屈原在《涉江》中这样描写自己流落到湘西溆浦一带的场景:“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12](P146)此文辞句法与《山鬼》的第三部分何其相似!而《山鬼》是祭祀乐歌,《涉江》是自叙行程,那它们是否都呈现了身处山野,浪迹江湖之“离忧”呢?
是故,《山鬼》场景情节的不断推演,从表象到内质,再至深层,可以读到关于宗教仪式的、关于世人生活的、关于作者内心情感的多重主题。
(三)象征与细节描写蕴涵了多层次题旨
骚体诗将《诗经》中最常用的“比兴”手法发展成了象征。象征的结果是一种精神产物,象征的过程是用具体的事物表示某种特殊意义,阅读象征意味浓郁的文学作品,有点像猜谜。比兴的谜底多明摆于谜面,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但象征的谜底全藏在谜里,要仔细琢磨才能想明白。《山鬼》诗中的象征不是存在于某处某事之中,而是存在于整体全部之中。从标题选用到细节刻画,从环境气氛营造到角色内心告白,都是象征,它就是一首象征体的诗歌。
传说中的《九歌》是夏启从天上盗来的,“《九歌》韶舞夏人的盛乐,或许只郊祭上帝时方能使用。启曾奏此乐以娱享上帝,即所谓钧台之享”[14](P193)。楚地祭祀活动频繁,屈原在辗转放逐中耳濡目染,借此曲名,创作了《九歌》,古今学者多无异议,但人们对其中《山鬼》篇所祀为谁却争论颇多。洪兴祖在《山鬼》篇名后列有“《庄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枭阳。楚人所祠,岂此类乎?”[1](P82)读者若将山鬼理解为“夔”和“枭阳”,则形貌太丑,性情太烈,与诗中描写严重不符。今人比较接受“巫山神女”之说,但仍有质疑:既然已经称“神”了,屈原为何还要取名为“鬼”?
笔者理解“山鬼”就是“山之精灵”。现在湖南人常常说的“鬼妹子”,就是指那些面目娇好、行动敏捷、天资聪慧的女孩子。对“精灵古怪”的少年郎,则笑嗔:“各咋鬼。”篇名“山鬼”何必坐实何山、何地、何出处?许是“博闻强志”“娴于辞令”[15](P1042)的作者,深得楚地民俗俚语的滋养,调制出的一款魅力独具之造型。他选取了神话传说中巫山神女的乖巧妩媚,现实生活里湘妹子的执拗多情,再加上作者自己内心所有的美好。此造型既是神鬼的,也是人巫的,更是作者自己的。他是巫妆扮的神,也是去迎接神的巫,还是作者的自我象征,同时也是作者心中崇高的理想和追寻。如此说来《山鬼》自标题始便开始运用象征了。
南楚大地,沅湘流域,多丘陵山地,山高林深,幽冥潮湿,降水量丰富,适合各种树木花草生长,较之屈原生长的江汉平原,这些起伏蜿蜒的山麓,犬牙交错的沟壑,开满鲜花的坡谷,折磨着屈原行走的腿脚,也激发着他创作的灵感。
山中四季可见各色奇异的花、各种芬芳的草,它们是大自然对南方山民的馈赠,是祭祀仪式上不可或缺的道具和巫师们妆扮自己的精美饰品。在祭祀活动之前,人们采集香草嘉木,搭建装饰祭坛,主持祭祀的巫师用香汤沐浴,希望以纯洁之身更易为神所接受,完成祭祀之职。所以香草嘉木最先有洁身去秽的实用价值和取悦神灵的特殊功能,被巫风盛行的楚民广为喜爱和使用,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芳洁之物行芳洁之事、代芳洁之德的比德现象。现在端午节人们还在大门上挂艾草,西南少数民族女孩子赠给情人定情之物多是香囊。香草嘉木代表着优秀品德和崇高理想,对香草嘉木的采集或与之同处是对优秀品德和崇高理想的追求。
《山鬼》中的“采三秀兮於山间”“饮石泉兮荫松柏”,字面意思为“山中人”在山中采摘灵芝,喝着从石头上流过的清泉,在松柏树下遮荫歇息,实质上要表达的是希望自己能如“三秀(灵芝)”一样永葆青春之美,能如石泉那般清澈纯净,如松柏那样崇高刚毅。屈原在作品中大批量引入香草美人意象,形成屈氏浪漫主义之象征集群。譬如《离骚》中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12](P4~12)等等。苏雪林说:“屈原的离骚全部是象征性质的文字,前半篇用各种香草象征他自己的学业,德行、志趣,政治上的作为(例如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比喻自己培植英才,提携新进),政界所树之仇敌(以荆棘莠草相比),甚至代名词也用‘荃’、‘荪’字样。”[5](P27)
在《山鬼》诗中,象征手法运用与细节描写紧密联系,象征意蕴更加丰富。譬如描写巫师的妆扮:“被薜荔”“带女罗”“被石兰”“带杜衡”。描写巫师的动作行为:“结桂旗”“折芳馨”“采三秀”“处幽篁”“饮石泉”“荫松柏”。描写巫师的心理活动:“留灵修”“怨公子”“思公子”“憺忘归”“怅忘归”“徒离忧”。其中动词或形容词的选用非常精准,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在祭祀活动层面,主持祭祀的巫师穿戴漂亮,体态优美,表情得当,“被(披)”“带”“乘”“从”“结”“折”“处”“采”等系列动词,展示着巫师曼妙的一系列舞姿,以娱神、迎神,希望神的降临。这些动词使人物形象更生动,文句表达更清晰,题旨更丰富,更容易引导读者进入情景,产生共鸣,从祭祀活动中体会到真实的生活。而对作者而言,则是一个早已失去了政治言说自由、被剥夺了公共话语权的逐臣,他的表达只能是文学的、个人的。他要借山鬼之作为,表现他自己的作为。巫师的内外兼美,隐喻着作者的身心高洁。巫师的各种行为动作都是他艰难跋涉、等待渺茫的见证。系列动词表现的种种细节,代表了作者屈原生命不止、修为不断的责任和自律。
其实屈原无意分辨是象征,还是比兴,他只是日日行吟,将心之所属、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写下来;将楚地巫师绚烂的服饰,一件一款地写下来;将女巫妖娆的舞蹈一招一式也写下来;将或野性或哀伤的歌词一字一句和着唱起来。审美是可以感召的,它会震撼到人的心灵。南方特有的芬芳植被,林中偶尔出没的赤豹文狸,各色藤蔓芳草,幽深的竹林,高大的松柏,石上潺潺流淌的清泉,它们就在屈原的身边,唾手可得。他不必刻意选择,他只需自然展示。或许屈原情不自禁幻化成巫祝去问过神灵:是不是自己独来太迟,错过佳期?你是不是太忙忘了约定?或已然厌弃,今生再不相聚?每至绝决痛极,梦就醒来,徒留离忧。
是故,读《山鬼》文字,乍一看是鬼神的,细品却是生活的,再深究其里,作者的那点心思就全露出来了。反观作者,未必不是将自己的“所思”浸泡在楚民生活的艰难与对美好的执着中,用祭祀的托盘请巫师端了上来,成就了一部多主题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