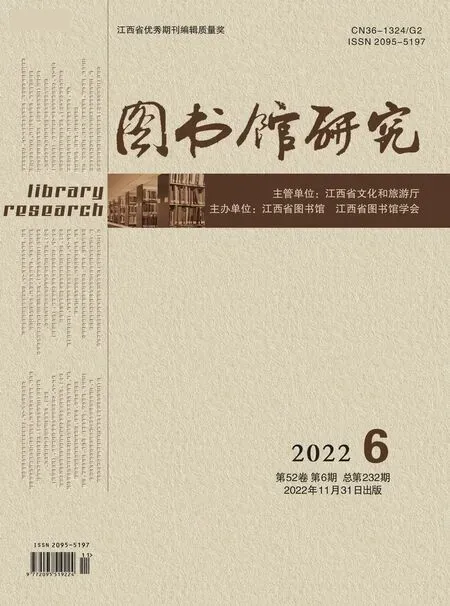古典图书目录小学类两种范式的成立、共存与转换*
2022-03-14毛伟林
毛伟林,耶 健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陕西 西安 710049)
1 引言
晚清至民国时期,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转型之际,诸多学者纷纷对传统学术进行总结。章太炎先生认为构成中国古代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三者合起来应该称作语言文字学[1-2]。章氏还在《国故论衡》中指出,秦汉以来“小学专任八体久矣”,八体即指文字[3]。章氏弟子黄侃明确主张:“小学者,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也。”[4]与此迥异,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小学类序》中则认为,古代的小学在周、秦以至宋代内容都一样,即如朱熹《题小学》所说,是“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5]余嘉锡还激烈反对将小学界定为文字、训诂、音韵,主张古代儿童讽诵的小学书主要是字书、蒙求和格言三种[6]。
章、黄与余氏的观点分别以清代汉学和程朱理学为宗,并沿袭了清代汉、宋学术门户相争的余绪,针锋相对,但是各自又都使用大量的文献证据作为支撑,所以无法简单地评判孰是孰非。本文认为他们的观点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小学的不同面相,构成了小学的两种不同范式。章、黄认为小学即中国语言文字学,核心是文字的形、音、义分别派生出来的文字、音韵和训诂,主要是一种专家之学,与传统的经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称其为小学的语言文字学范式。余嘉锡的观点秉承朱熹编《小学》的思想,适用对象为少年儿童,以“洒扫、应对、进退、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为特色,主要功能是进行道德教育和初级知识教育,浸透着浓厚的理学色彩,本文称之为小学的理学范式。它们分别有其产生的学术思想背景、流行的时代和语境,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融合共存、或相互竞争、或一家独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其具体情况,则有待于在仔细梳理文献证据的基础上展开论述。
图书目录作为一定时空条件下学术成果的整理和集中展现,“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重要功能[7],其灵魂图书分类反映了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对学术分类的认识,“能辨别源流,详究义例,本学术条贯之旨,启后世著录之规”[8]。因此,图书分类包括类目设置、位置以及著录范围,成为透视学术发展变化脉络的重要视角。中国古典图书目录从《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到《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总目》),包括官方馆阁书目、史志目录和私家书目,大多都设置小学类或相关类目,其著录内容的类别范围则几经因革损益,折射出背后学术思想和学术分类理念复杂的迭变迁转。以往的研究,包括张舜徽[9]、胡奇光[10]、赵丽明[11-12]、蔡雁彬[13]、李甦[14]、李成燕[15]等的著述和论文,受视野和资料范围的限制,都未能认识到元明清时期图书目录小学类的理学范式长期与语言文字学范式共存、竞争,甚至还两度发生范式转换互相取代的事实。因此,本文通过梳理历代图书目录小学类的设置及其著录范围的变化,从图书分类的视角,来探究中国古代小学上述两种范式的存续及其关系的演变。
2 汉至宋代图书目录的小学类:语言文字学范式的成立和成熟
图书目录中的小学类,创始于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志》。《七略》和《汉志》根据名为小学的文字学在汉代成为专门学术门类,以及经学的研习需要以文字的识读和训诂为基础的学术现实和理念,在“六艺略”中创立了小学类,著录《史籀》《仓颉》《急就》等字书及其包含音读的训诂。
《汉志》设立小学类著录文字书,并将其与六艺群经置于同一大类,在古典图书目录的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连续和稳定的传统,并且也创立了中国古代小学的语言文字学范式。
魏末晋初及南朝宋齐之际,荀勖《中经新簿》四部之甲部与王俭《七志》的“经典志”,分别著录“六艺及小学等书”。南朝梁时,阮孝绪《七录》于“经典录”设小学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图书目录,因文献无征难以考见其分类体系,但是根据《中经新簿》《七志》及此后唐宋时期诸家书目的分类传统来看,其不论采用七分法还是四分法,小学类的设置都应该与《汉志》基本相同。
唐初确立了四部分类体系的《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其经部小学类著录文字、音韵、书法、民族及外国语文、石经等类图书,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文化发展和学术变迁对小学的扩展。汉魏之际产生反切法用来给汉字注音,开始形成音韵学并出现专门著作。北朝时少数民族入驻中原,加强了民族语言的交流,产生了很多鲜卑语言著作。此时期书法文化极为兴盛,产生了许多专业的书法论著。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外文明交流,外国语文著作也诞生了。由于汉代熹平石经及曹魏正始石经的刊刻,诞生了石经文献,它们被著录在小学类也体现了小学与经学固有的联系。
唐代开元年间的《唐六典》记载秘书省“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其经部设小学类“纪字体声韵”。《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经部设小学类“纪字体声韵”,并将《尔雅》及派生文献从经解类中分离出来独立创设训诂类,但训诂类与小学类却是合并统计作“右小学一百五部”,其中小学类又被分为偏旁、音韵、杂字三种,实际著录文字、音韵、书法、石经等文献。《旧唐志》不仅初步将《尔雅》为代表的训诂文献合并进了小学类,还首次对小学类进行了明确的细分,对宋代小学类的内部界定和学科自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宋初的官方藏书目录《龙图阁书目》,分经典、史传、子书、文集、天文、图画六阁作为一级分类,其经典阁分正经、经解、训诂、小学等六类[16],训诂与小学分别为二级分类,并且与经解一起作为正经的附庸,与《旧唐志》颇为相似。其后的《三朝国史·艺文志》,其经部将《旧唐志》的训诂类和小学类整合为小学类一类,著录训诂、文字、音韵、书法等文献[17]388。《尔雅》等训诂文献正式与文字、音韵文献一起构成了小学类的主体,小学的语言文字范式最终成形,《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经部都予以沿用。稍后的馆阁藏书目录《崇文总目》,是中晚唐以来最为完备的综合性图书目录。《崇文总目》经部小学类著录训诂、文字、声韵、书法文献,其“叙”将小学视作儒学次第的基础和开端,并区分为以《尔雅》为代表的训诂之学、以《三苍》《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偏旁之学、以“孙炎作字音”为代表的音韵之学和以篆隶古文为代表的字书之学[18]。小学的语言文字学范式产生了相应的内部界分和理论说明,反映了其成熟后的理论自觉。
《崇文总目》的作者之一欧阳修撰的《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及南宋初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经部小学类著录训诂、文字、音韵、金石、书法文献。
南宋初晁公武的家藏图书目录《郡斋读书志》小学类著录训诂、文字、音韵、书法与金石著作。《郡斋读书志》小学类开篇《尔雅》提要中主张,文字学包括字体、训诂、音韵三个方面,分别以《说文解字》《尔雅》《方言》、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为代表,“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19]小学类的内部分科由训诂、偏旁、音韵、字书四分,演化为分别代表文字形、义、音三个面相或三种形态的字体、训诂、音韵,体现了小学作为学术门类的持续改进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也反映了其语言文字学范式更进一步的成熟。稍后尤袤的家藏书目《遂初堂书目》,其小学类著录训诂、文字、音韵类图书。
南宋后期陈振孙撰家藏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以下简称《书录解题》),认为小学当以《说文解字》等书“论偏旁”为宗旨,其经部小学类序主张历来图书目录将小学类配隶在经部,是“文字、训诂有关于经艺”的缘故,《两唐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将《书品》《书断》等书法著作著录在小学类实属庞杂,因而将之著录在子部杂艺类,并将金石目录改隶于史部目录类[20]85。所以,《书录解题》小学类只著录训诂、文字、音韵图书。《书录解题》的小学主张和小学类著录实践,再次反映了小学的语言文字学范式成熟以后的理论自觉和学科自觉。
南宋末王应麟编纂类书《玉海》,其“艺文门”于群经之后设小学类,分别著录上古至宋代的文字、算术、训诂、音韵、书法类图书信息,“唐六十九家小学”条后按语引用《郡斋读书志》小学类关于文字学分字体、训诂、音韵三个部分的论述。
3 南宋后期至元代图书目录的小学类:理学范式的成立
承袭唐代韩愈、李翱和北宋周敦颐、二程的思想脉络,南宋中期出现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朱熹在构建和宣扬理学学术体系的过程中,颇为重视对少年儿童的思想品德和知识教育。他认为先秦存在与《大学》相对应的《小学》,只是后来亡佚了,因而与弟子刘清之合作,广泛摘引《周礼》《仪礼》《礼记》《论语》等古文献编辑成《小学》一书。《小学》在朱熹的理学思想教育体系中具有基础地位,他宣称“修身之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这个是做人底样子。学之小大虽不同,而其道则一。《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17]436后人概括道:“《五经》以《四书》为阶梯,《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近思录》以《小学》为阶梯,此《小学》一书所以为万世养正之全书,培大学之基本也。”[21]伴随着理学的传播和普及,朱熹《小学》对后世的少儿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元、明及清前期,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对朱熹《小学》进行注解和诠释的著作,仅《千倾堂书目》收录就有四五十种,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文献群。
传世的古典图书目录中,最早收录朱熹《小学》的是《书录解题》,其将《小学》列入子部儒家类。为了区别作为图书的《小学》与作为学术分类的小学,陈氏借用朱熹的用语,将其书称为《小学书》,解题道:“朱熹所集古圣格言、至论以教学者,皆成童幼志进学之序也。《内篇》曰《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20]282
由于朱熹《大学章句序》主张“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因此,南宋后期的赵希弁为《郡斋读书志》撰《读书附志》,在小学类中著录了朱熹做过章句的《弟子职》和胡宏所著《叙古蒙求》,图书目录中开始出现与文字形、音、义、记诵无关的儿童道德教育图书,反映了朱熹的小学思想开始对图书目录的小学类产生影响,小学的理学范式开始形成。
元初马端临编撰《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下简称《经籍考》),其经部小学类著录训诂、文字、音韵、书法、金石著作。此外,《经籍考》经部小学类还著录了被《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著录在子部类书类的蒙求图书,被《书录解题》著录在子部儒家类的吕本中《童蒙训》、吕祖谦《少仪外传》、朱熹《小学》等书,以及被《书录解题》著录在子部杂家类的张时举编《弟子职等五书》(《管子·弟子职》篇、班昭《女诫》、吕氏《乡约》《乡礼》、司马光《居家杂仪》),体现了理学范式影响的扩大和小学类著录范围的扩展,也反映了图书目录小学类两种范式的共存。元朝官方编修的《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经部小学类沿用《经籍考》的做法,著录训诂、文字、音韵、书法、金石、蒙求及朱熹《小学》等类图书。
4 明代至清初图书目录的小学类:两种范式的共存与竞争转换
明代前、中期的官方藏书目录《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其分类“闯出四部牢笼”,集部之后又分类著录传统上多著录在子部的各种应用技术和艺术类书籍,其中韵书类著录文字及音韵图书,《尔雅》及其派生文献受《尔雅》位列“十三经”的影响被著录在经部诸经总类,朱熹《小学》被著录在经部性理类,蒙求图书则被著录在集部之后的类书类。《文渊阁书目》开创了有明一代及清初图书目录经部不设小学类,而在经部外设韵书类或字书类、字学类著录文字、音韵书籍的先例,今传本《菉竹堂书目》《宝文堂书目》《玩易楼藏书目录》《博雅堂藏书目录》《内阁藏书目录》《世善堂藏书目录》《脉望馆书目》《徐氏家藏书目》,都沿用了这种模式。
正德、嘉靖年间的学者陆深撰家藏书目《江东藏书目录》,分设经、理性、史、古书、诸子、文集、类书、韵书、小学医药等十四个一级类目,其中韵书类著录音韵文献,而小学医药类之小学部分则著录“幼教”图书[22]。由于该书目已亡佚,其具体的著录情况笔者无从详细考察,但是结合《文渊阁书目》开创的设韵书类著录文字、音韵书籍在明代颇为流行的事实,《江东藏书目录》的韵书类很可能也承袭了《文渊阁书目》的传统,而其小学医药类之小学部分著录的“幼教”图书,则很可能全部是朱熹《小学》及蒙求类书籍。因此可以推论,在《江东藏书目录》中小学类第一次从语言文字学范式转换成了理学范式。
稍后,高儒撰成家藏书目《百川书志》,其经部设小学类,著录训诂、音韵、文字、民族语文方面的著作,同时另设蒙求类。《百川书志》不仅小学类继承了宋代小学类的语言文字学范式,还创设了二级分类蒙求类,著录理学兴起以来大量增加并且地位上升的对少儿进行道德和知识教育的书籍,既响应了当时学术思想和图书生产对于图书分类革新的需求,又创造性地解决了小学类内部两种范式之间竞争和冲突的张力。遗憾的是,《百川书志》的这种方案在明代并未得到广泛地认同和效仿,从而成为特例。
明隆庆、万历年间,朱睦㮮的家藏书目《万卷堂书目》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其著录范围与《经籍考》《宋志》基本一致。万历中期,奉命编修国史的焦竑撰成《国史经籍志》,其经部小学类分设尔雅、书、数、近世蒙书四属,尔雅属著录训诂文献,书属著录文字、音韵、书法、金石文献,数属著录算术文献,近世蒙书属著录蒙求及朱熹《小学》类图书。随后的著名目录学家祁承㸁撰《澹生堂藏书目》,其经部小学类分尔雅、蒙书、家训、纂训、韵学、字学六属,尔雅属著录训诂类文献,蒙书属著录朱熹《小学》及蒙求类等用于教育幼童少年的图书,家训属著录家规家训家教类包括女性道德教育的文本,纂训属著录各种道德规范教育的汇编性文本,韵学属和字学属分别著录声韵类及文字类图书,书法类文献则被设专属著录在子部艺术家类。《国史经籍志》《澹生堂书目》小学类的设置,不仅体现了语言文字学范式与理学范式的共存,也反映了小学类的著录范围在理学范式下达到最大限度的扩展。尽管通过三级分类进行了内部的条理化,但还是难掩其芜杂和臃肿,变革势在必行。
清初钱曾的家藏书目《也是园书目》,其经部字书、韵书、碑刻、书、数、小学六类并列,字书、韵书、碑刻、书、数类分别著录文字、音韵、石刻、书法、算术文献,小学类分别著录《尔雅》、朱熹《小学》及蒙求等用于教育幼童少年的图书。同时,曹寅的家藏书目《楝亭书目》经部分别设有小学类、韵学类和字学类,小学类指称和著录幼教蒙求及朱熹《小学》类著作,并且位于著录宋代以来理学大家著述的理学类之前,韵学类著录音韵书籍,字学类则著录文字和书法图书。
同时期徐乾学的家藏书目《传是楼书目》经部小学类分设小学、书、数、近世蒙书四属,小学属著录《尔雅》类及朱熹《小学》类图书,书属著录文字、音韵、金石、书法文献,数属和近世蒙书属则分别著录算数及蒙求图书。黄虞稷主撰的《明史·艺文志》(以下简称《明志》)经部小学类分小学、女学、书数三属,小学属著录《尔雅》、朱熹《小学》、蒙求幼教类及家规家训类图书,女学属著录女性道德教育类图书,书数属著录音韵、文字、数学图书。
在《也是园书目》《楝亭书目》的小学类和《传是楼书目》《明志》小学类的小学属中,小学的理学范式明确取代了语言文字学范式,彻底完成了范式转换。《传是楼书目》《明志》的小学类在二级分类上体现了两种范式的融合,也显示出对宋、元学术传统的传承,但是在三级分类上,作为属名的小学则完全又是理学范式的,体现出小学范式转换的深层影响。两级类目或两个层次的小学同时存在,造成含义的混乱、分歧和不统一,也说明小学类语言文字学范式向理学范式的转换,加剧和激化了两种范式融合共存局面下固有的内在张力。
清康、雍年间王闻远的《孝慈堂书目》,其经部设有字书、韵书、碑刻、书、小学等类,字书、韵书、碑刻、书类分别著录文字、音韵、石刻和书法文献,小学类则著录朱熹《小学》及蒙求等幼教图书,这些类别的排列顺序,则应该是以各类所著录图书产生的时间先后为依据的。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命令各省访求图书,后曾出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的沈初编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其四部之经部尔雅、小学、六书分别设类,其中小学类著录朱熹《小学》的衍生著作和蒙求类等幼教图书,六书类著录文字及音韵书籍。值得注意的是,《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小学类和六书类的设置,皆异于其宣称分类所参考的“列代正史艺文志及马氏《通考》、晁氏《读书志》、陈氏《书录解题》”,说明这是撰者依据自身学术理念的有意创新。《孝慈堂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小学类的设置,反映了理学范式独尊的延续。
5 清代图书目录的小学类:向语言文字学范式的回归
清初学者钱谦益撰家藏书目《绛云楼书目》,其四部之经部分别设立小学类和尔雅类,小学类著录文字、音韵著作,朱熹《小学》及相关书籍被著录在子部道学类,书法图书被著录在子部杂艺类,蒙求书被著录在子部类书类,金石著述则在集部专门设类著录。《绛云楼书目》在经部分别设立小学类和尔雅类,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这两个类别在《汉志》和《旧唐志》中的传统,而朱熹《小学》、书法、蒙求图书的著录,则是恢复了《书录解题》等南宋图书目录的传统,不仅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对古典目录学术源流的熟识,还体现了图书目录小学类向语言文字学范式的全面回归。
著名学者毛奇龄还为小学的语言文字学范式回归摇旗呐喊,他结合《周礼》《尚书大传》《汉志》《白虎通》等文献,主张“小学本天子诸侯世子之学,而所学又止书数”,即小学的教学内容以写字、计算为主,并不包括朱熹所倡导的“民间小子洒扫应对”,而北魏兖州刺史高佑令州内村立小学,是民间小学的开始,但所教仍旧是“写字之学”,而非空谈道德性命之学[23]。
清顺治、康熙年间,黄虞稷撰成家藏书目《千顷堂书目》,其经部小学类在著录训诂、文字、音韵著作后,“补”法帖、碑帖二目分别著录金石、书法著作,又“附”算学、小学二目分别著录数学和蒙求及朱熹《小学》类幼教图书,反映了《千顷堂书目》在考据学兴起、古学复兴的学术思潮变革下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在学术理念上回归汉唐及宋代的传统,小学类恢复语言文字学范式只正式著录训诂、文字、音韵类文献,但另一方面在著录方法上却又不得不沿用元、明以来的普遍做法,将金石、书法、数学和蒙求及朱熹《小学》类书籍分别附录在小学类下,尤其是“附小学”专门著录蒙求及朱熹《小学》类幼教著作,体现了小学语言文字学范式回归的格局下,理学范式以附录方式的延续。
清康熙末年,学者姚际恒的家藏书目《好古堂书目》经部设有尔雅类和小学类,尔雅单独设类应该是受《尔雅》位列“十三经”的影响,而小学类著录文字、书法、金石、音韵书籍,显然是回归到了《新唐志》(《好古堂书目》不著录《旧唐书》和唐宋书目)小学类所代表的语言文字学范式,而朱熹《小学》及衍生著作则被著录在子部儒家类。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黄烈撰《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其经部小学类著录文字、音韵、训诂、金石、书法著作,契合小学在北宋时期的语言文字学范式,同样应该是受到《新唐书·艺文志》的影响。
清乾隆末年由纪昀等学者纂成的《四库总目》是中国古典图书目录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古代图书目录编撰的最高峰。《四库总目》小学类序称其遵循《汉志》的先例于小学类中惟录六书等文献,同时主张以《尔雅》为代表的训诂也是小学的一种,不认可《隋志》于小学类中增入“金石刻文”,反对《旧唐志》将训诂和小学分成两类,批评《旧唐志》《新唐志》小学类中“增以书法、书品”有违“初旨”,反对《读书附志》在小学类中并入《弟子职》及蒙求类书使其“益多岐矣”,不遵从《明志》将算术附录入小学类,而是将小学类中的书法、金石、蒙学、数学、家训等类著作全部移除,将朱熹《小学》及相关文献仍旧收录在子部儒家,分训诂、字书、韵书三属著录与诠释儒家经典密切相关的训诂、文字、音韵文献[24],恢复小学类严格的语言文字学范式独尊的局面,并彻底廓清理学范式的影响。《四库总目》对小学类的内部分科和严格的学科界定,与《郡斋读书志》和《书录解题》的论述极为相近,具有很大的继承性[25]。此后,谢启坤主编《小学考》,遵循与《四库总目》经部小学类相同的学术思想并略做改进,将全书分为训诂、文字、声韵、音义四大类。
清嘉庆年间,经崇奉汉学的阮元“手订体例”后由范邦甸等编纂成书的《天一阁书目》,曾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的汉学大师钱大昕编撰的《元史艺文志》,学出阮元门下的周中孚编撰的《郑堂读书记》,以及同治年间四川学政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光绪年间山西学者耿文光编撰的《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虞山瞿氏祖孙三代纂修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其经部小学类的设置也都遵从了《四库总目》的主张,沿用了语言文字学范式。小学类的语言文字学范式在清代中后期全面和彻底的回归,与其时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乃至金石学的蓬勃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6 结论
中国古代作为学术分类的小学存在语言文字学和理学两种范式。语言文字学范式创立于汉代,在北宋时期的《三朝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新唐志》中正式成形,到南宋时期的《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中最终成熟。理学范式则缘起于朱熹及弟子编撰的《小学》,从《读书附志》起开始对图书分类产生影响,在元代的《经籍考》《宋志》中出现与语言文字学范式融合共存的局面。二者的融合共存在明代的《万卷堂书目》《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中依旧得以延续,并在《国史经籍志》《澹生堂书目》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条理化。
受到明代《文渊阁书目》等将文字、音韵视为专门之学并不再冠以小学之名的影响,小学的语言文字学范式日渐式微,在清初的《也是园书目》《楝亭书目》及其后的《孝慈堂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中,理学范式完全取代语言文字学范式,发生了彻底的范式转换。《传是楼书目》和《明志》的小学类,在二级分类层面是两种范式的融合共存,但在三级分类层面理学范式也完全替代了语言文字学范式,体现出范式转换的深层次影响和两种范式固有的张力。
清初考据学兴起和古学复兴,小学类的语言文字学范式在《绛云楼书目》《千顷堂书目》《好古堂书目》中得到回归,再次发生范式转换。在经过《四库总目》的权威确认后,语言文字学范式成为清代中后期图书目录小学类的唯一范式,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从小学类两种不同范式的成立、融合共存和竞争转换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图书目录的分类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和内在稳定性,以至于“因”成为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的首要原则[26]。小学类从汉代创立以至宋代,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只是在著录范围上日益扩展,内容日益丰富,并且经历了内部的条理化和学科自觉,最终定形成熟。南宋末年以降,受到理学兴起的影响,产生了小学类的理学范式,但是其在很长的时间内只能与语言文字学范式融合共存。明初的《文渊阁书目》等将文字、音韵视为专门之学,取消其小学之名,成为小学类的理学范式取代语言文字学范式发生范式转换的重要影响因素和契机。此外,一些经典图书目录的类目设置,也会成为后世参照模仿的范例,如《汉志》《新唐志》《四库总目》小学类的设置,以及《文渊阁书目》取消小学类改设韵书类,皆对后世诸家书目相关类目的设置产生了借鉴意义和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小学类语言文字学范式向理学范式的转换,与中国传统学术从经学范式向理学范式的转换[27],尤其是朱子学的下移及朱熹《小学》的进一步普及和传播[28],基本是亦步亦趋的,充分地反映了学术思想变迁和经典著作的传播,对图书目录分类及其范式转变的重大影响。清初考据学的兴起和古学的复兴,推动了小学类的语言文字学范式的回归。当然,小学类的语言文字学范式在清代中后期彻底回归后成为唯一范式,既受《四库总目》的权威确认的影响,也受到清代中后期文字、音韵、训诂诸学问蓬勃发展的影响,再次印证了学术思潮对于图书分类的重要影响作用。